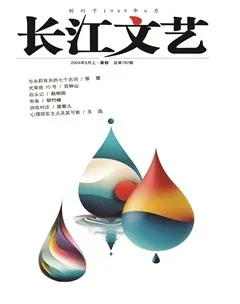老姊妹
尹子仪
茹曼蕊近些天来心中很不爽利,照理说她跟她家公家婆平日里就处得不好,闹出了许多从使眼色开始,却止于正面吵架的龃龉,这让平素里在娘家就直来直去,一不高兴就把姆妈骂得哭哭啼啼的火爆性子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娘家可以作威作福,在婆家就只能做矮子人。她婆家那些所谓的亲戚一向是表面一团和气,实则经常在暗地里戳脊梁骨的,她很是不屑。老公不喝酒,不抽烟,也从不和狐朋狗友三更半夜还在外头鬼混,还会说幾句滑头滑脑的话惹得她咯咯地笑,但一旦涉及到她和他们家之间的利益纠纷,从面上看,他一直在当和事佬,妄图打打太极,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聪明如曼蕊,早就洞穿了他面上两边不得罪的心思,其实就是要她受着,吃哑巴亏,看别人眼色,即使闹得再凶,哭得梨花带雨,气得心脏怦怦地跳,以至于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吃四分之一片保护心脏的药片,他还是以婚姻作为筹码,不让她有任何逾矩的行动。
不消说,老公是失败的,不懂得做和事佬,其实他在他家也是做矮子人,他家的风气就是这样的,哪个儿子赚的钱多,买东西给父母买得多,也不管行动上怎么样,地位就是高。比如曼蕊的小叔小婶,一贯是耀武扬威的,明明比自己老公小,自从她入门,话语权却完全偏向他们那边,吃饭也不自觉坐在主位,说话声音也总是如雷霆震天,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做生意赚了大钱,盆满钵满的,其他的人,包括父母,总是要靠他家施舍的。
但父母总归是父母,他们两个总还是要在血缘与辈分上压小叔小婶一头,有他们在,那两个总不敢这样张狂,而她老公却也只能在夹缝里说话,连带着曼蕊,更是插不进一句话,即使说了,也没人听,不过又是挣得一肚子气。在这样的境况下,因为自己一再忍让情势愈演愈烈,曼蕊又是个心气高的,家里成日里鸡飞狗跳是在所难免的。想着自己自从嫁进来,又是喉咙痛,又是胃不舒服,又是心率过快,全身上下都是病,还不是被他家的人气出来的,老公不给力,自己难免也到了骑虎难下的局面,她感到很熬煎。
家婆弥留那几天,家公全身上下都变得焦黄,小城市医院查不出个所以然,只是模糊地说可能是胰腺有问题。他打算守着家婆,看看还会不会好,不行,办完丧仪再去上海检查,若是她命不该绝,家婆情况稳定了,自己再去。可哪有这么好的事?菩萨再怎样神通,也是管不了人间生死的。一行人将婆婆的骨灰送到湖南老家的坟山上,埋葬好,便又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上海家里。即使婆婆生前对曼蕊再不好,但她毕竟是自己的婆婆,死者为大,生前种种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曼蕊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离开婆婆死亡带来的阴影,公公住院,检查,每日需要自家和小叔两家人家轮流送饭,忙得团团转,完全体味不到平静的生活。
一系列庞杂的检查做完,才确诊公公是胰腺癌。医生将老公和小叔两兄弟叫出来交底,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需要尽快做手术。不过,即使手术成功,他也很难挺得过两年。
丧母,父亲又这个样子,老公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主要矛盾一变,小叔子小婶子也就无暇再对曼蕊有什么神态上或是行动上的无视或侮辱,曼蕊的火气也就没那么频繁爆发了。不过,即使依旧有无视和侮辱,贤妻之于曼蕊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若是火上浇油无异于将处在低谷中的家庭弄得摇摇欲坠。火气被疲累替换,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得安生罢了。曼蕊看着锅里的荞麦面条发呆,汤汁变得浓稠,连带着面也煮成了面饼。公公的手术很成功,不过就像是前面说的,再成功,也就是捱日子罢了。小叔请了护工全天候陪侍着,钱也是他出,曼蕊撇撇嘴,更不愿意见他,看他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老公白日里要工作,中午和晚上还要见缝插针地到医院去看看公公,庖厨之事很多时候确实顾不过来,只得落在她身上。曼蕊从怔然中恍过神来,赶紧放下一团新面饼下锅煮。公公对吃食方面虽不挑剔,但刚做完手术,胃口差些,总得做得好吃些,更何况自己是作为媳妇煮这碗面,不好吃,又会落他的话柄。她现在比以前看得更开,不惧老公家的人在背后讲她闲话,自己也没法儿控制他们的嘴,耳不听为净,但在自己这边,总要做好来。曼蕊本就嫌她公公,但作为儿媳妇,总是要去探望一下,即使是在面上嘘寒问暖几句,也是要的。
曼蕊问老公,爸爸还要插鼻管吗?都这么多天了,什么时候能够出院呢?老公回答说,大医院都是这样的,其实早就可以出院了,爸爸偏要在医院多住些日子,他不放心。曼蕊点点头,公公不傻,一旦如实告知他的病情,即使再如何轻描淡写,透露出了“胰腺癌”三个字,他肯定就会在小叔给他新买的智能手机上搜索,利害性就完全出来了,对他病情的康复很不利,因而大家都不约而同瞒着他,只说是个小手术,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公公对此深信不疑,就像当时即将离世的婆婆一样,告知她真实病情,她不相信,坚持说是医生误诊,可再坚强的意志力也抵不过死神的召唤,她就在浑身紧绷,与病魔做斗争之时永远离开了人世。老公和小叔不愿自己的父亲重蹈覆辙,他们希望他能在安逸中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日子。公公出院后,依旧是请了一个男保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两个儿子也时不时去探望。公公的伤口处依旧时不时痛,究竟是隐隐作痛还是胀痛,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问医生,医生只说正常,每次都开一塑料袋的药,吃了,有好转,但还是痛,每日就这样过。老公觉得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提高公公生活质量的法子,小叔子却想尽尽孝,不仅从物质,连带着在精神上也得满足自己的父亲,以后也可死而无憾。他跟老公说打算给公公找个湖南阿姨陪伴他,都是老家人,说话也容易投机。曼蕊听到这话后一激灵,连忙问找阿姨是怎样的性质,是女保姆还是老伴,打不打结婚证。这些因素都是要考虑的,她在新闻上看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女保姆在老头子死后在地上撒泼耍赖,要不到钱就坚决不走的,曼蕊感到后怕。她是自私的,她坚信,无论谁都是自私的,让外人分走家产,她断断不肯依从。
小叔子也是这个意思,结婚证是不能打的,打了结婚证以后,到分家产之时打官司都打不赢,他就是打算给公公找个不要钱的保姆罢了;不过公公死后,补偿还是要补偿人家一些钱,但终归还是要比请保姆强,少出钱,培养感情,又可死心塌地。
曼蕊只觉得好笑,现在的阿姨个个都精得很,占了人家便宜还想诛心,不现实。小叔子自私,想浪费人家阿姨的年华,外加上自己也可以落得清闲,他和小婶又是两个懒鬼,懒得出油,懒得抽筋了的,可以时时过去蹭饭吃;曼蕊也是自私的,她百般撺掇着老公阻止小叔的粉红蘑菇泡泡梦,只因为自家条件差,到时补偿湖南阿姨,免不了要在遗产里平均分,有钱如小叔,自然是九牛一毛,不在乎的,可对于自家,却是一笔大数目,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外人占了一些去。由此,曼蕊只想着保持现状,让小叔请男保姆服侍着公公,让小叔当冤大头,自己受委屈冷眼便受委屈冷眼,冤大头总是小叔,赖不到自己头上,是威胁不到自家这份家产的。老公听了在理,却也不好说,更不论说自己说了也等于白说,于是又这样打哈哈过去,说自己没办法阻止小叔的意思。于是,自婆婆病危以来,曼蕊又一次在家里砸东西,又一次气急攻心,但依旧是毫无办法。
湖南阿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公公家,曼蕊即使再怎样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得不接纳她进入自己的生活。
中间是委托了媒人的,一个年轻时候不学好的同乡人,交游甚广,认得许多人,老了收敛了些,但对做这样的烂媒却也十分热衷,只要能得钱抽烟喝酒打牌就行,便瞒着那位湖南阿姨,说老头子的小儿子赚大钱,过去了,保管吃香的喝辣的。公公听闻这件事,欢喜得不得了,似乎是迎接了人生中的第二春,精神来了,梳头,抹发胶,穿得一身咔叽西装,戴上一副金边眼镜,装老知识分子去和湖南阿姨视频。不就是个农民嘛,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的,写文章错漏百出,字都认不全,能多有文化?曼蕊只觉得滑稽,跟跳梁小丑似的,她看见这个阿姨的相片,小叔小婶都说她是苦命相,都说好,太娇贵的阿姨是做不来这事的,倒是成为一个累赘,一个烫手山芋,来了就丢不掉的,十分满意。曼蕊端详着照片,皱皱眉头,只觉得这女人穿着朴实,看起来像是有个性的人,其他的,单从一张静态二维照片,也看不出来。
直到小叔叫老公和她到外边吃饭,出乎意料,那个湖南阿姨竟来得这样快,过于水到渠成,很让她怀疑背后的动机。曼蕊是一个传统女性,在她看来,经媒人介绍,虽说是老乡,但老乡中出坏人,出骗子之类的事情看得还少吗?双方简单视频,就敢千里迢迢从湖南跑到上海来和一个陌生病老头子同床共枕的女人确实是不可思议,她怀疑她是不是专挣这样的钱。老公辩白,说公公睡床头,那女人睡床尾,也还好。曼蕊听罢,哼了一声,觉得自己和老公话不投机,当初嫁这样一个愚钝的男人也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要是重来一次,她绝对不会嫁给他。
惊讶归惊讶,但面上工夫总得做足。曼蕊一貫就是个八面玲珑的女人,人前热情、善良、大方、知性,人后猜忌、敏感、歇斯底里,完全是两副面孔。再说,她总要探听到什么东西。她渴望了解这个女人的过去,以及现在藏在她内心深处的东西,既满足好奇心,长见识,更是为了知己知彼,防患于未然。于是,她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坐在湖南阿姨座位旁边,用家乡话和她攀谈。自己是公公家这边唯一一个和她同乡的女性,她猜她会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很容易卸下内心的防线,和她打成一片。但曼蕊只猜准了一半,她知道那女人叫黄铁蓉,家住得离她老家的房子不远,也是个爱说话的。她们谈开在菜市场里的张记炒货店,说那里的瓜子花生价廉味美,是城里一绝,于是又谈到小时候各自的姆妈在家里做炒货,当时没什么吃,却觉得满足,现在却再也回不去了。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地谈,却一直没有说到曼蕊想听的重点上。一场饭局下来,她觉得这女人不简单,三言两语之间就可感受到,心思很深,深不见底,口风很紧,严丝合缝。这也在曼蕊的意料之中,她觉得棋逢对手,不过日子还有这么长,见面的次数还有很多,她总能在黄铁蓉放松之际,不小心露出狐狸尾巴的时候猛地一揪,让她原形毕露。谁也不可能时时保持警惕,曼蕊觉得,自己只需要循循善诱,不怕她不与自己知心。
于是,每一次小叔请客,茹曼蕊都和黄铁蓉坐在一起,到后来,越说越投机,脸凑着脸,用手挡着,对着耳朵讲话,像是一对无话不说的老姊妹。曼蕊能体察到,自己和黄铁蓉都是用了真心在讲,不过理智总是牵引着她们规避彼此的敏感话题。曼蕊回到家,洗完澡,头上盘着玫瑰红的擦头毛巾,总是要坐在沙发上和老公一起分享她的新发现,不过基本上都是在原地打转转,例如说听话听音,肯定黄铁蓉是个厉害角色,且动机不纯,告诫老公要防着她,却又不让老公将她的话学舌给小叔小婶听,怕他们传话,到时候黄铁蓉就不再跟自己聊了,好不容易搭建的关系也会断了。老公打趣曼蕊,说她是个演技派,不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都可惜了,简直是浪费人才。曼蕊看不得老公的乐天派作风,明明是危机四伏的,却搞成没事一样,到时候栽大跟头,吃大亏,不过好在有自己。这样一来,曼蕊心中有事,听着床畔老公香甜的打呼声更是心烦意乱,一直拖到后半夜才睡着。
公公一开始本就很喜欢黄铁蓉,老夫配少妻,能不喜欢?黄铁蓉似乎有些小妾的味道,公公和她住了不到一年,就给她买了一整套的黄金首饰,这是婆婆生前都没有的。那个年代结婚,寻常人家哪买得起这些,再说也是稀罕东西,是作为工农阶级的公公婆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到后来,同甘共苦,老夫老妻,更是疏忽了这些。黄铁蓉很聪明,不会大张旗鼓地戴出来,在小叔小婶还有老公面前招摇,但还是有意无意在与茹曼蕊吃饭谈闲天的时候说了出来,自然又是曼蕊循循善诱的。曼蕊一直在她面前扮演好姊妹,似乎一直都是把她当好姐姐看,经常出谋划策,明面上为她争取利益,实则在暗地里捣鬼,即使再嫌公公和小叔,毕竟是大家庭的媳妇,没理由帮衬她一个外人。曼蕊说,黄阿姨,老头子心里有你,你看看,他对你多好,出去,不管去哪里,都带着你。黄铁蓉便连连点头,说,我知道老头子对我好,他给我买金器,还买了一个大榴莲给我吃,就在门口的惠民超市买的,二十多块钱一斤,买一个要一两百。我是看都不敢看的,叫他不要买,但他偏要买给我吃,自己还不吃,就看着我吃。曼蕊连忙附和道,是呀,黄阿姨,你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头子,没什么好操心的,你们可以相伴到老的。
饭后,茹曼蕊挽着黄铁蓉的手在小区散步,送她到公公所住那栋楼的防盗门前,轻松恣意的神态,向她挥了挥手,说些早点休息之类的惯常体己话,而后往家那边走,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见昏暗的路灯把黑黢黢的路照得斑斑驳驳,依旧是不真切。她再三确认没有熟人跟在后边,毕竟老公那边的人都和自己住在一个小区,才将脸猛地拉垮了下来,心里很不好受,但也想不到合适的词语,不能说怒焰燃烧,更谈不上含酸拈醋,是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家的钱一点点被外人掏空,却无可奈何的感觉。曼蕊进屋,老公正在刷抖音,看儿媳妇智斗恶婆婆的小短剧看得很入神,整个屋子里都是铿锵的配乐声和演员掷地有声的嘶吼,乌烟瘴气,弄得她头痛。她一把将老公的手机抢过来,把抖音关掉,随意将它扔在了茶几上,翻白眼,阴阳怪气道,我早说你爸爸是花花老头子,你还不信,他真将那个姓黄的老太婆当续弦了,我看哪,你也别叫她阿姨阿姨了,叫她妈算了,她可是你的继母啊!于是,曼蕊将黄铁蓉今晚跟她说的私房话转述给他听,当然不是客观的一五一十,而是夹杂着强烈感情倾向的揣测,以及像四大金刚一样怒目圆睁的神态与肢体动作;她知道什么地方该用重音,什么地方应该轻飘飘一语带过,什么地方又应该压低声音,营造神秘而莫测的氛围。老公显然是被她感染了,原本在这种情况下习惯默不作声的他接过话头说,爸爸每个月还格外给她一千块钱零用,平日里生活开支也是爸爸出钱。曼蕊听毕,愣了一会儿,顿时暴跳如雷,说,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姓黄的老妖婆压根就没有和我讲起过这些事情。她还不知道有多少事情隐瞒着我们,她还不知道明里暗里抠了老头子多少钱!
想到这,曼蕊再次悲从中来。她跟随老公到上海,投靠他们家的人,娘家姊妹都在湖南老家。自己在异乡,只能依靠老公,况且老公很多时候不向着自己。即使在上海买了房子,她还是像无根的浮萍,觉得自己与这座繁华大都市的快节奏,甚至可以说冷漠格格不入。看着鳞次栉比的楼房,她经常发呆,觉得自己被困在其中,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挣脱出去。她做姑娘的时候,一直不明白天底下怎么会有人把婚姻比做牢笼,结婚明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可跟随老公到上海之后,她才渐渐明白了。蜗居在几十平米的小家,不愿出去,出门,是陌生的乡音。而且,她每次出门买菜,十有五六会碰见在她看来面目可憎的公公、婆婆、小叔、小婶。有些时候,她眼尖,距离较远,便会立即回转身子,避免正面遇见;但更多时候,未曾注意前方,或是在转角,或是眼见他们的目光灼灼地落在自己身上,只得硬着头皮迎上去,不痛不痒打一声招呼。很多时候,对方只是“嗯哼”一声了事,连“买菜啊曼蕊”之类的寒暄也不会有;碰上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是会淡淡地瞟她两眼,而后与她擦肩而过,只留下曼蕊脸上那朵凝固着的,似笑非笑的笑容。
不是婚姻把她困住了,是老公那边的裙带关系把她困住了!她时时想,心中也时时锥心般疼痛,但除了按部就班,她别无他法。要说离婚,对于她这样大年纪的女人来说,毫无优势,加上她爱老公,既然无法割舍,那就只能按部就班,只能够牺牲。从这一点看,黄铁蓉的到来,让她愉悦,和她在一起,欢声笑语,不说其中的真心假意各有几分,但至少,她曾开怀过。
因而,面上和老公家里人同仇敌忾,将黄铁蓉视作仇敌,却又不得不当间谍,虚与委蛇的曼蕊,自己也没意识到喜欢和她待在一起,不仅仅是什么盯梢或是刺探情报。
黄铁蓉和茹曼蕊说,曼蕊呀,老头子的身体很虚弱呀。我前两天换被子,翻开床单铺盖,看见他睡的那侧床板上一团人形的水印子,把我吓坏了。我不好跟他们两兄弟说,你帮我传个话,要他们带老头子去医院看看,看看到底是哪里不好。
曼蕊听到这话,想起自己幼年在湖南老家那边听姆妈闲谈起的迷信说法,具体内容记得不真切了,只记得说是阎王爷在招魂了,人一身的精气被吸走了,就会在床板上出现人形印记,已然命不久矣。她自然不会将这番话讲给黄铁蓉听,她想到前段时间翻老公手机,看见公公微信中“看一看”栏目的新动态,不看还好,看了简直是让她又羞又臊:公公在看老年人同房应该注意什么。她第一反应就是跟老公讲,把证据摆给他看,省得他说自己无中生有,又免不了一场争执。老公接过手机,又是沉默。曼蕊便骂公公是个老色鬼,他自己病得成日肚子不舒服,一片片的药往肚里下,还不忘老男老女之间桃色那点事,如何能够给后辈儿孙树立榜样,他作为父亲,作为爷爷又还有什么脸面,什么尊严和威信?曼蕊一找着机会就要在老公面前踩几脚他那边的人,此言确实也有泄私愤的因素在里头,但公公为老不尊,却也不假。言毕,她又骂黄铁蓉是个老狐狸精,一个巴掌拍不响,曼蕊愈加怀疑她年轻时候不是个好货,绝不是她向众人宣称的年轻时候遇人不淑,嫁了个混混老公,而后离婚,从此凭借双手挣钱,未曾再嫁那样简单。这不过是官方套话,是黄老妖婆欲盖弥彰的障眼法!曼蕊对着老公慷慨陈词,老公便有氣无力地说,至少,我看见爸爸更开心了,即使病痛成日折磨他的肉体。他反正是活不长了,能够延长他的生命也是我这个做儿子的尽孝了。曼蕊听毕,骂道,你们一家都是自私鬼!随后,进入卧室,将门“嘭”地关上,反锁,任由老公夜晚睡在沙发上。
但茹曼蕊依旧是一五一十将黄铁蓉对她说的公公身体虚弱的话转给老公听了。曼蕊说她只能顺着她的意思来应和着,但听她这意思,是不知道公公得病而命不久矣。曼蕊觉得疑惑,她与黄铁蓉见了这么多次面,说了这样多的话,从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她聪明,后来,更是这样觉得,她难道连公公生大病这一肉眼可见的事实都看不出来?她怎会既聪明又愚钝!这个谜团,她思索了很久很久,觉得只有两个可能,一是黄铁蓉将计就计,从她敢从湖南坐车到上海来和当时还是陌生人的公公同睡一张床开始,她就已经明白了,至少猜得八九不离十,她就是专跟男人,跟了不知道多少个,从年轻时候开始,分一个结一单的钱,所以她举止才会如此老练,演技才会如此炉火纯青;还有就是,曼蕊不敢往这方面想,也许是她一直以来的偏见在作怪,黄铁蓉不至于此,是真心想和公公过日子的,只是她认为人心不会这样险恶,将她当作棋子一样利用,才没往病老头子这方面想。
当然这一切都是需要代价的,公公是小叔的父亲,小叔付出,无怨无悔,但黄铁蓉可不能白白地享受这一切,可不能真的把她当作姨太太来养,连带着公公还要拖着病体做事,拿个香案把她供起来,更何况公公一死,早晚都是要给她钱的。小叔小婶这下可算是钻到了空子,以前男保姆在的时候,只出这么多雇佣金,便也只会炒供公公一个人吃的饭菜;可现在不同了,黄铁蓉在,身份又是不清不楚的,抠搜的时候,不给钱,把她当继母,占小便宜的时候,一个星期要去公公那儿吃两三次饭,便把她当保姆,钱、滋补品、带她出去吃饭,不过是以小换大罢了,她还只能是带搭着的,唱不了主角。平日去公公家吃饭,总得是黄铁蓉在厨房里忙碌,炒出一大桌菜,小叔小婶狼吞虎咽地吃,她还在里头抹抽油烟机、清洗灶台之类,好不容易忙完,再随意扒点残羹剩饭,也不坐在椅子上,多是搬个小板凳在底下吃,陪着说两句话。他们的话不知为什么,似乎每次都说不完,总要讲到快十点钟,才懒洋洋地回家洗澡。走后,黄铁蓉洗碗、抹桌子、拖地,自己收拾完自己一身,总要快十二点才能够睡觉。这样的次数一多,她便偷偷地和曼蕊讲,说这样的时候太多,自己在湖南老家,从来没有这样累过,也从来没有这么晚睡过觉,她有点吃不消,也烦,又叫曼蕊传话给小叔小婶听。曼蕊这次可没有选择和她打太极,许是这样做总会露出马脚,黄铁蓉还指不定认为自己两面三刀,更多的还是有些情不自禁,加上面上也讲了这么多家常话,揣度归揣度,猜忌归猜忌,总是熟了,便有意无意说自己也和小叔小婶有意见,他们本就是狗眼看人低的,说不得。曼蕊这样精明,断不会一股脑从开天辟地讲到现在,事无巨细讲给黄铁蓉听,她熟练运用自己的语言艺术,使得自己和她拉近距离。其实,此情此景,曼蕊也有点迷糊,似乎同仇敌忾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两人之间更是有了说不完的新谈资。
黄铁蓉自信也逐渐得到了公公的几分信任,便自己和他说了这件事,合情合理。公公也不好为自己的小儿子说话,便转述给了小叔听,这才没来这么频繁。但黄铁蓉和小叔小婶之间的意见确实是显而易见了,互相嫌。
大概过了两年的潇洒日子,公公那几日觉得自己的肚子胀得厉害,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似乎有水在里头晃动,便执意要小叔送他去医院看看。老公和小叔担心是病发了,公公不明所以,觉得只是一个简单的腹腔积液,将水放掉就好了,结果确实是病发。老公和小叔恳求医生,无论如何都要延长公公的生命,医生便用了一个来自日本的技术,在公公的胰腺处装了一个支架,阻止癌细胞扩散至全身,并把他的积液排干净了。
那谁来照顾公公?重担自然落在了黄铁蓉身上。曼蕊早就想到了这一层,在公公身体还撑得下去的时候,黄铁蓉是保姆;在他缠绵病榻的时候,她是免费的护工。这一看护,就是几个月,黄铁蓉经常被逼得扫公公拉在病床上的排泄物,晚上觉也睡不好,经常被公公哎哎哟哟的呻吟声吵醒,又得强撑着倦意起来,安抚撑坐在病床上的他躺下;白日,即使是单人病房,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也无暇小憩。曼蕊怕过了公公的病气,加上平日的积怨,这次他病也只去了一次。时日一久,曼蕊更加觉得如果黄铁蓉单纯,明摆知道他时日无多,这时分早就应该溜走了,本就是陌生人搭伙过日子,还有什么留恋?正是因为她复杂,有心机,更因为她家不知道苦成什么样,才会愿意留下来照顾,不敢前功尽弃,一定要拿公公百年之后,老公和小叔对她的补偿的。就像黄铁蓉那日过生日,公公执意要给她操办生日宴,出钱请她到店里吃饭,买了一个大蛋糕,点上生日蜡烛,放起生日歌;她许愿,落下了晶莹的泪珠,她说她非常感动,感动得不得了,她已经几十年没有过过生日了。在那时,这话便成为曼蕊推断她的一个直接证据,黄铁蓉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老公说,他相信黄铁蓉对公公是有真心的,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得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这病是早就起了,有意瞒她的,她只知道他得了很重很重的病,可能再也不会好转了,满脸通红,急得掉眼泪,打电话给他哭诉。她是真的害怕,真的担心。
茹曼蕊听老公这么说,也点点头,说,我早说了,她是来图钱的,当然,日子久了,她也记得公公对她的好,她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顿了顿,她说,公公也对她有真心,不纯粹是利诱,他当然不会跟你们讲,他也不敢讲。
公公害怕,即使他觉得自己没什么,但病痛的折磨不得不让他疑心,他在清醒的时候对老公和小叔说,假如有一日,他离开了,要善待黄铁蓉。
曼蕊听言,冷笑道,他间接承认了,无声告白。
但没想到现实那样骨感,不到两个月,公公又人很不舒服,又被送进医院,已然“三进宫”了。曼蕊想,要是能三进三出就好了,这次,她有预感,他出不来了。
做检查,医生说,支架已经全被癌细胞堵塞,癌细胞已经在全身扩散,不论送到哪里,不论请医术多么高明的医生,也回天乏术。但他撑了这样久,在医学上,已是奇迹。
即使再不甘,即使再怎么留恋人间,公公依旧在苦苦挣扎后,在重症监护室的心率监测仪器屏幕上一会儿有些微心率波动,一会儿又归于沉寂后离开了人世,糊里糊涂,不知自己究竟身患何种病症,就去与婆婆作伴了。
曼蕊心想,按照唯心主义的说法,婆婆在那边也不会理会公公了。
曼蕊自然也有点伤心,但平日的怨气总是促使她无时不刻不挖苦两句。追悼会过后,又是一行人陪着,将公公的骨灰盒送回湖南老家,将它埋在婆婆旁边那个预留的墓穴中。
忙完,就该分钱给黄铁蓉了。曼蕊此时为了家产能少分就少分考量,对黄铁蓉说,老公和小叔记得你的好。黄铁蓉点点头,手却立马比了个钱的手势,眉飞色舞道,关键是要有这个。曼蕊心里想,反正我说的也不算什么,你去跟小叔小婶说吧。不过,曼蕊又有了些看热闹的心理,她想,小气刻薄如小叔,要是不能给黄铁蓉称心的钱款,她会不会原形毕露,在地上撒泼打滚,赖着不走呢?她倒要看看小叔该怎样应对。
小叔自然是嘴巴上抹了蜜糖似的,懂得一般人的心理,说给她5万,黄铁蓉说太少了,说老头子在世的时候,说怎么样都会给她10万的。于是,就开始像扯牛皮糖一样的拉扯,你一言我一语,话语间还算客气,到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小叔出到了7万块,黄铁蓉便应允了,转账,飞一般的速度。而说什么拿现金是不可能的,要是黄铁蓉日后反咬一口,也算是有一个转账凭证,不怕她诬赖。曼蕊两只手拍拍黄铁蓉的右手,说以后还做亲戚交往,不要断了联系。黄铁蓉便说,和曼蕊投缘,是同乡,话又能讲到一块儿去,一直想和她结姊妹。老头子在的时候,还不方便,怕乱了辈分,现在他已然不在了,也就不打紧了。曼蕊点头说好,心中想着,不过是口头上应承,又不弄什么仪式,是作不得数的,她一厢情愿罢了,真要付出什么,也是不可能的。黄铁蓉便打包好被子铺盖,打算第二天坐车回湖南老家,却在当天夜里觉得嘴角漏风,连带着走路也有些别扭,第二天便连忙去医院看病,检查出轻微的脑溢血,需要住院,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只好退票。曼蕊跟老公说,黄铁蓉的病是没日没夜陪护公公劳累出来的,医药费怎么样也得给人家出一点。老公反问,你不是最怕她分多家产的吗?现在怎么还为她考虑?曼蕊便不吱声了,一个人搭车到医院,在门口的水果店买了些苹果、香蕉、橙子,到住院部看她,看到她因为床位已满而不得不睡在走廊上,吊着吊瓶,身边只有一个干巴脱水的梨。黃铁蓉见她,惨然一笑,随意说起一些话,转而说她快一个星期没洗澡了,过几天出院,回去洗个澡。曼蕊听言,不好受,也有些讪讪的,心想她确实是个苦命人,没福气的。黄铁蓉腿一蹬,说无论如何,她的病因老头子而起,她本是健健康康地来上海,一点毛病也没有的,曼蕊也只是听着,想着确实是对她不住,钱倒是在一边,良心上终究是过不去,小叔要给她付医药费,也是理所当然,自己也没什么可说的。
黄铁蓉离开上海后,她快递了不少东西到自己家,茹曼蕊心中自是有想法的,想着她只会将些不值钱的东西,像晒米粉肉的筛子给自己,还说什么看不惯小叔小婶,知道他们想要,就不给他们,可却连带着公公生前的金戒指也不见了。曼蕊更是翻白眼,心想不搜刮干净也对不起她的这几年,林林总总,也弄了十万块钱回家。曼蕊和她说,你还年轻,碰见什么合适的老头子,还可以再找一个,黄铁蓉却连连摆手说不找了。曼蕊觉得她的话也信不得这么多。
公公的第一个冥寿,大家都回去祭拜,黄铁蓉也来了,曼蕊觉得她情谊是有,不想和这边断联系的想法也有,也许是为了自己以后有病痛来上海看病,投靠自家做铺垫。午间吃饭,席间,小叔委婉问她关于公公金戒指的事情,黄铁蓉便抽抽搭搭地哭,神情激动,说自己真的没看到。回到上海,却又在公公家的床缝里找到了,才知错怪了她。曼蕊却觉得,她要是看到了,据为己有,坚决抵赖也是常理。只是,和黄铁蓉住在一个小区也三年了,说了数不清的家常话,自己却一直看不清她,只能从轮廓上隐隐猜测一些东西,她的口风实在太紧,亲密无间却又有所保留,也太像自己。反正,什么老姊妹,也只是说说而已,当然,她也不像起初那样讨厌她了,在老家,有机会在大街上碰见,说几句话,聊聊近况,各自回家,也挺好。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