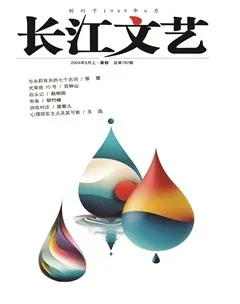一己之见
张楚
短篇小说
我们一直主动或被动地沉溺在生活之中。当我们被动性地不断叠加身外之物时,内心有一个先天准则,那就是:生活赋予我们的不能丢弃,不能废弃,它关乎记忆,也关乎对人性的注解,我们只能按照上帝的旨意保管,如此,我们的身外之物随着时光愈发沉滞,最后不光我们的肉身陷入泥潭,没准连灵魂也难以飞扬。
短篇小说写作也是这样,多个事件发生,你如何选择那些对文本自身具有构建性和决定性的情节?你必须学会扬弃和保留,学会甄别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否符合小说本身的内在逻辑,而途径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天分,一种是经验(或曰技术)。当我们按照天然的感觉在叙述中发现了问题时,我们要根据阅读经验沉淀下来的第六感开始控制小说的节奏和发展方向,我们至少要在某种主观猜度中知晓哪些是装饰性细节,哪些连装饰性细节都不是,而哪些又该是我们该去全力张扬的。这种舍弃和张扬本身,又有着自身的规律和个性,就像一个人如何费尽心思把书房里的书去除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去和留之间的犹疑和度量,考验着小说家的眼力、经验与天赋。
我觉得短篇小说里如果没有了诗意,犹如风干了的苹果,尽管吃起来味道不会太差,但总还是少了些舌尖被果汁里的维生素刺激时的微妙快感。短篇小说之所以不会被中长篇小说取代,不会被影像完全解构,或许就是因为它里面朦胧的、含混的、流星般一闪即逝却念念不忘的诗意,诚然,这诗意或是黑色的,淌着腥味的血。
当代作家的小说里,尤其是短篇小说里,很少有风物描写。大家都认为这是在浪费笔墨,而且是种很古旧的写作手法,似乎只有在19世纪的经典作品里出现,风物才算是风物。风物真的属于奢侈品或者展览品吗?其实对风物的描摹,看似一种闲笔,但正是这样的闲笔,让小说有点游离和走神,反倒可能誕生出意外的诗性,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性。对我而言,这种诗性天生有着阳光和植物的味道,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哀而不伤。
如果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是盆景,那么爱丽丝·门罗的小说是园林,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则是葳蕤茂密、辽阔神秘的森林。
细节描写
短篇小说是深夜里的一声叹息,是抹香鲸在月光下跃出海面的一瞬,是骆驼穿过针眼安全抵达沙漠的过程,是上帝的一个响指。
什么是细节描写呢?就是那声叹息是悠长的还是短促的,是男人的叹息还是女人的叹息,在声音从咽喉和嘴巴里传递出来时,这个人有没有哽咽或其他肢体动作;就是抹香鲸以锐角还是钝角跃出海面,在腾空的刹那月光只是印在它的尾部还是覆盖了它的整个身躯;就是骆驼穿过针眼的时候,它的两条前腿和两条后腿是蜷缩在一起还是像往常一样分开;就是上帝是用左手打的响指还是用右手打的响指,在打响指的时候,那两根手指是大拇指和中指、还是大拇指和食指,在响指发出声音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像普通的人类那样咽了下吐沫……小说家在对人物进行塑造、在戏剧性地推进小说叙事、在自己的逻辑范畴内讲述这个世界的卑微或伟大、光明或黑暗时,正是他有意或无意写出的饱满、闪亮的细节,带给我们有限的感官承受和无限思维发散,同时传递给我们只属于文字和小说的细小幸福。
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肖像描写的消失,反映了小说家关注点、兴趣点的转移,也反映了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的焦虑感和忧患意识。其实,貌似简单的肖像描写最能体现一名小说家眼界的犀利、通感能力的强弱程度和对人物的速写技能。尤其是对次要人物的肖像描写,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人物刻画出来,次要人物本身就没有太多的行动和戏份,精准狠毒的肖像描写既省事又干练,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词语
与小说里的动词相比较,我更喜欢小说里饱满的名词,名词不仅是装饰品,而且打通了细节与细节的疆域,它们是情节暧昧的推动器,是世界之所以如是的结论性标识符,尤其在长篇小说里,名词与名词之间通常会创造出揭示人物内心真实世界的细密纹络,以及涌动的气味。
动词是有限的,名词是无限的。
一个小说家的青春期在哪里,他的词语就在哪里,他小说的根就在哪里。
场景
譬如,小说中十人以上的在场场景,对话不是问题,只需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即可,难的是如何进行场景切换腾挪,既需洽合的人物动作特写,微妙的个体心理愿景和选择性的人物互动,还需特定的场景描写、微物描写和氛围建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必须在这转换中毫不怯场,有股混不吝的自信。从这方面讲,我由衷地佩服曹雪芹和托尔斯泰。
遗憾
在我的想象中,一个有勇气有气力在小说中开天辟地的天才作家,他的人生故事犹如上帝最得意的响指。可为何至今还没有哪位导演去关注这位生活在小镇上的酗酒者?这委实是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没错,关于作家的电影不计其数,比如 《成为简·奥斯汀》《莎翁情史》《最后一站》《明亮的星》《时时刻刻》《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连托马斯·沃尔夫也有关于自己的电影《天才捕手》,而那个喜欢电影并且在小说里信手拈来使用蒙太奇手法的大师威廉·福克纳,却只能在天堂里安静地欣赏着银幕上他人的虚假人生。
风格
大多数的写作者在多年的写作后,会有一种意识:哦!我的语言是这个样子,我的写作主题有这样的特点,这就是我的风格。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有两种选择:一是由于长期自我重复写作主题和写作技法,他确实有一种改变的决心,他抛弃了他熟悉的小说世界,开始有意识地用矫正后的语言去讲述矫正后的主题,这种主观的变化可能会催生一个更优秀的小说家,也可能让他在自我革新的过程中丧失主体性,变成虚构中的那个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知道自己的写作风格,却没有去进行自我革命的勇气。也许他会认为,一个小说家在某一时段内的作品,均围绕这一时期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格局展开,这个时候,他不会去刻意改变风格,风格的局限性对他而言,是一个伪命题。如此,他听从内心的声音,遵循着写作的内在规律,在时光的抚慰中,缓慢地变化、调整着自己。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会在同一种写作风格中老去,写作风格与年龄没有过于明显的关系,例如在我们阅读马尔克斯、阿特伍德或者帕慕克时,我们很难从他们的著作中感受到写作风格的变化——那些天才型作家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风格的局限性,对他们而言,青春期不会消亡,写作主题和写作技巧的更迭,更多地是被时代所主导所牵引,至于如何重新定义写作条规和写作戒律,对他们而言,可能并不是重要的事。
一个小说家不敏感,就不会感同身受地体验这个世界;一个小说家不柔弱,就不会窥探到最底层的污浊、暴戾与美;如果一个小说家既敏感又柔弱,而不歹毒,那么他就不会去主观地防御、对抗这个世界,如此,他就不能完整地、主动地开始这一场有关自我创造和自我追寻的没有终点的伤感旅程。
性别观
我个人觉得,大多数作家应该都渴望自己的写作是中性写作或无性写作。脱离了性别意识才能摆脱性别的桎梏和约束,才能更客观地去描写和探索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人性的复杂性,时代的曲线发展和文化的多样并存。虽然如此,即便如此,我们在写作过程中难免会下意识地流露出些许性别意识,这不是出于我们的意愿,而是出于我们的本能。我们阅读那些伟大的文学经典,会发觉我们不会格外留意其中的性别意识,我们更关心的是作家讲了什么样的故事,用什么样的方式讲了这样的故事,以及这样的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作为阅读者的作家和作为写作者的作家在不同的身份中呈现出的关注点的迥异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小说中的性别意识的无意义或意义的有限性、局限性。成年后的性别意识类似我们的血型、星座甚至性别本身,它已然固化,但仍会在细胞核内发生裂变或衍生,我们本来应该能看到,可是我们看不到。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对于作家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迟钝的思考者,后知后觉之后发生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
读者
我写作时很少考虑到读者,比如他们的口味,他们的喜爱。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老是考虑读者,他可能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优秀的小说家应该培养读者的口味,让读者翻越固有的审美藩篱,接受并享受新的审美范式。
其实,和某些读者的交流常常让我感觉惊讶,他们的灵魂和我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契合的。那种从未相识却又如此心心相印的感觉,可能也是小说家創作时潜意识里的一种动力。
《与永莉有关的七个名词》
这篇小说缘起于我的一名高中女同学。高三那年她被她的男朋友强行辍学之后,我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这么多年来,我时常想起她。按照惯常的揣测,她要么在城里打工,要么成了一名出色的农村主妇。无论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对她报以最诚挚的祝福。小说中的永莉比我的那位同学更勇敢,“被出走”后,时间没有将永莉滞留在过去,而是加速了对她命运的书写。小说中的七个名词,前六个都在高处,只有到了“地下室”,永莉的世界才真正安稳牢固起来。她的坚韧、执拗和勇气,让她无论站在哪里,身居何处,都不会再战战兢兢,心底只有坦然与自由。她知道往哪个方向行走。
与其说这是篇关于女性如何寻找自我、塑造自我的小说,不如说在这篇小说中,我在试图探讨人与混沌世界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被动的,更有可能是相互渗透的。
责任编辑 喻向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