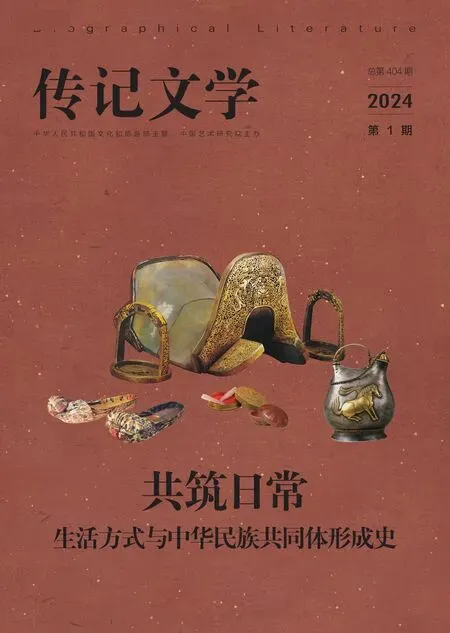竖牛之乱与鲁国兴衰
王予立
“好善而不能择人”的叔孙穆子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在鲁襄公及太子卒后,作为当时鲁国三桓之一的叔孙穆子,并不愿意立年仅19 岁、“犹有童心”的齐归之子裯为国君,说出“年钧择贤,义钧则卜之。今裯非嫡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1](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539 页,第1539 页。的话。他认为,继承人在年龄相仿的情况下应该择贤而立,资质不相上下时则应通过占卜的方式选定,而昭公裯在襄公卒后居丧期间,不仅没有表现出悲戚之态,甚至还面有喜色,按照服虔的说法,是“言无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539 页,第1539 页。,显然在是否贤能的问题上不符合成为国君的条件。
但就是这样一个强调“择贤”的叔孙穆子,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吴国季札出使的内容中,却被季札说成是“好善而不能择人”[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观乐一事,并有季札言于叔孙穆子:“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参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355 页。者。特别是叔孙穆子作为鲁国国卿,在国家治理中担当大任,一旦他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不够谨慎,就容易招致祸患,这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批评了。季札这个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他通过观乐便可知政治风俗之兴衰,《文心雕龙》即称其为“鉴微于兴废”[2](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101 页。;他在观人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例如他到了晋国,欣赏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就预言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第四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4361页,第4355页,第4421页。,不久之后果然就有了三家分晋之事。那么,他对于叔孙穆子如此严厉的评价自然不应随意对待,或者说,这个评价至少在预示着叔孙穆子的某一“不能择人”的行径。
杜预注认为季札此言是在“为昭四年竖牛作乱起本”[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第四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4361页,第4355页,第4421页。。通观《左传》的记述,最能表现叔孙穆子“不能择人”的,确实是他因为一个梦境而任用竖牛为家臣之事,甚至最后他更是直接死于竖牛之手,这样的结局同样符合季札“祸必及子”的感慨。那么,季札对叔孙穆子“不能择人”的评价,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昭公四年发生的竖牛之乱。我们先来看竖牛被任用的完整过程: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齐,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第四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4361页,第4355页,第4421页。
按照上引《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538)的记述,竖牛被任用并且有宠于叔孙穆子是凭借一个神秘的梦的预兆:叔孙穆子在齐国的时候,有一天做了个怪梦,梦见了天穹整个向自己压了下来,想要抵抗却实在无法脱身。就在这个时候,他一回头,竟然看见了一个长相怪异的人,此人肤黑而驼背,眼窝深陷,唇状如猪嘴。他赶紧高声呼喊:“牛!助我!”于是,就在这个人的帮助下,穆子终于得以脱险。醒来之后,叔孙穆子便想要找到这位在梦中帮助自己的能人,可惜召来了所有的随从都没能找到,只能先记下这件事。就在他回到鲁国后,曾经在庚宗留宿过的那家妇人带着孩子前来拜见,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和梦中那位能人长得一模一样。叔孙穆子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过问,便直接用梦中呼喊的“牛”来称呼他,并任命他为“竖”,即让他作为自己的家臣管理家务。
叔孙穆子之所以不假思索地任用竖牛,是否果真是出于这样的梦的预兆,还是有其他原因?有学者认为,叔孙穆子任用竖牛实际上是因为竖牛是他和庚宗妇人的私生子。《左传》提到穆子“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这样的表述似乎对穆子和庚宗妇人之间的关系有所暗示。所以杜预就认为,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叔孙穆子在哥哥叔孙侨如作乱之后,为躲避此事对自己的牵连,就趁着鲁国参与讨伐郑国的机会前往齐国,因而在庚宗处留宿。等到襄公二年(公元前571),穆子已经以鲁臣的身份出使宋国了,所以可以判断,这个时候穆子已经归鲁。从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到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历经五年而庚宗妇人之子“能奉雉”,如果竖牛确实是叔孙穆子和庚宗妇人所生之子,穆子在成为鲁卿之后所见到的竖牛大概是五六岁的年纪。但是五六岁的童子是否真的能进行“奉雉”这一行为?要知道,“奉雉”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向主上效忠的表示,所以不少学者对此都有所怀疑。不过,即使竖牛真的是叔孙穆子的私生子,在《左传》的叙述中,竖牛受到叔孙穆子的任用并没有牵扯到他可能的私生子身份。所以,在理解竖牛之后在叔孙氏内部展开的夺权行为时,与其强调两人之间的隐秘联系,认为竖牛因为具有叔孙家私生子的特殊身份从而可以与同为穆子之子的孟丙、仲壬争夺叔孙氏的继承权,倒不如从家臣与家主之间斗争的角度来考虑。
竖牛之乱:家臣与家主的斗争
《左传·昭公四年》在追叙完竖牛的任用过程后,对竖牛作乱的经过进行了详细描述:
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叔孙为孟钟,曰:“尔未际,飨大夫以落之。”使竖牛请日。入弗谒,出命之日。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杜洩见,告之饥渴,授之戈。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彻。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421—4422 页。
这段文字叙述了竖牛为夺取叔孙氏家权所做的三件事:其一是竖牛在叔孙穆子想要孟丙宴飨大夫、举行钟的落成仪式时,并没有像孟丙所说的那样让穆子确定日期,反而假称穆子的命令定了日子。等到宾客都到了,穆子以为孟丙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举办了这个活动,还邀请了母家的客人,十分生气,就将孟丙杀了;其二是竖牛在仲壬想要将鲁昭公给予的玉环送去给穆子看时,隐瞒了这件事,出来后又假称穆子的命令让仲壬佩戴上玉环。竖牛之后还假意询问,让穆子以为仲壬私下面见了国君,穆子于是就将仲壬驱逐。经过了这样两件事,竖牛成功地将不愿与自己合作的两位继承人孟丙、仲壬,从叔孙氏的权力构架中排除。紧接着,他需要解决叔孙氏原本的家主叔孙穆子。当时穆子已经病重,为了不让逃往齐国的仲壬回到鲁国继承叔孙氏,竖牛没有按照穆子的命令召他回来,之后甚至囚禁了穆子,连食物都不提供。穆子又饥又渴,无法联系到自己的臣下,最终死在了十二月乙卯日。
由于此前叔孙穆子为家主时,担任叔孙氏家宰的只有杜洩一人,竖牛仅为“竖”,主要职责是管理家务,想要彻底掌握叔孙家,竖牛便选择贿赂叔孙昭子和季氏家臣南遗,让他们挑起季氏对于杜洩的不满,“使恶杜洩于季孙而去之”[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422 页,第4431 页。,利用季氏的力量除掉杜洩。这样一来,杜洩就不再对竖牛的掌权之路构成威胁。就在竖牛充分掌控叔孙氏家政之后,他更是在南遗的帮助之下攻仲壬,并取叔孙氏“东鄙三十邑”来回报南遗[2]参见谢乃和,陶兴华:《春秋家臣屡叛与“陪臣执国命”成因析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6 期。。竖牛为了争权而在叔孙氏内部为乱的这一系列行动,客观上使得叔孙氏的整体实力下降,无法与鲁国当时日益强盛的季氏相抗衡。可以看到,竖牛在杀了叔孙穆子及其嫡子孟丙之后,叔孙氏很快便陷入混乱局面,竖牛随即便执掌叔孙家政,诬陷叔孙而讨好季氏。等到仲壬从齐国闻丧而来,季武子本来想要立仲壬为叔孙氏家主,南遗就对季氏说:“如果叔孙氏实力强盛了,季氏就会被压制,现在叔孙氏正处于混乱的状态,您不要干涉,不也是可以的吗?”意思就是不要帮助叔孙氏稳定下来。南遗甚至还“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3](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第 四 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431 页。另外,孔颖达《正义》即以为“季孙因叔孙之弱,欲四分公室,己取其二,故谋去中军”。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423 页。,相助竖牛以对抗仲壬,这同样也是出于薄弱叔孙氏的目的。
叔孙穆子死后,“牛立昭子而相之”,竖牛显然是以家臣的身份另立昭子为新主;而且从“强与孟盟”、“强与仲盟”来看,他在最初应该也是希望通过扶立孟丙或仲壬的方式实际掌握叔孙氏的权柄,并没有利用自己与叔孙穆子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趁机上位的意图。不过,就在竖牛扶立昭子为叔孙氏家主后,昭子并没有宠信竖牛,反而指责他“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嫡立庶,又披其邑”[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422 页,第4431 页。,直接点明了竖牛所为对叔孙氏的祸害。他的罪行一个是混乱嫡庶,杀害孟丙、驱逐仲壬;另一个则是将叔孙氏的封邑送给了季氏,这些都让叔孙氏在与季氏的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可以说,原本仅发生在叔孙氏内部家臣与家主之间的竖牛之乱,由于季氏的有意介入而直接改变了鲁国三桓的实力对比,而这一点实际上也影响到鲁国三桓与公室的权力争夺结果。
三桓“卑公室”:季氏专鲁政的实现
鲁国季氏的崛起是暗藏在三桓“卑公室”的整个过程中进行的:
襄公十一年《传》: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1](清)阮 元 校 刻 :《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232—4233 页,第4430 页。
昭公五年《传》: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2](清)阮 元 校 刻 :《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232—4233 页,第4430 页。
季武子在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作三军”的真实意图在于对鲁军力役、赋税的重新分配,本来全属于鲁公的二军之赋,在增加为三军之后被平分给了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不过叔孙氏和孟孙氏都将自己的份额部分归还给了鲁公室,所以最后就演变成了鲁公掌握三军的十二分之五,季孙得十二分之四、叔孙得二、孟孙得一。等到昭公五年“舍中军”,鲁公的权力就被彻底剥夺了,季孙掌有了其中的二分之一,叔孙、孟孙二家各得四分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三桓,特别是季氏,其势力愈加强盛,而鲁公愈加卑弱。刘逢禄《箴膏肓评》就指出:“何氏所见左氏说,以舍中军为卑公室,出于季氏一人之私。”[3](清)陈立撰,刘尚慈点校:《公羊义疏》第五册,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2168 页。可以看到,“作三军”和“舍中军”两事,最终不仅达成了三桓“卑公室”的结果,使得鲁公室在与卿大夫的对抗中处于下游,同时还实现了季氏在鲁国一家独大、专有鲁政的意图。
对于鲁三桓分公室的这一情况,《国语·鲁语》记载了叔孙穆子在季氏“作三军”时所进行的劝阻:他首先是指出大国三卿虽然可以统帅三军之众,但是需要听从王师的号令以征讨不义之邦,那么季武子如果想要作三军,同样也应该有天子之命;他接着指出,此时鲁国仅是小侯,实力不济,同时在地理位置上又处在齐、楚这两个大国之间,从保全自身的角度来看本应服从于大国诸侯,但如今季武子却想要作三军,容易引来齐、楚的猜忌,齐、楚或将“代讨于鲁”[1]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181—182 页。。当然,这些都是明面上的理由,如果从《左传》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的记载来看,在季武子告知叔孙穆子将要作三军时,穆子先是对季氏说:“政将及子,子必不能。”[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232 页,第4422—4423 页,第4430 页。意思是鲁政将要到您手中,您会难以执掌;穆子的劝阻并未有效制止季武子作三军的举动,所以他之后就要求与季氏“盟诸僖闳”,这一盟诅的内容“是要季武子保证既作中军即不能再舍之(实即不毁三军之制),履行三家各掌一军的诺言”,是希望可以借助盟誓的力量,使得三军之制所划定的利益分配不要再有过多的变化,保证鲁国内部公室和三桓力量的某种平衡,从而对季氏专鲁政的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3]朱凤瀚提出,叔孙穆子在此情况下对季武子“作三军”的劝阻是从尊国的角度出发。参见朱凤瀚:《关于春秋鲁三桓分公室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84年第1 期。。
不过,这个盟诅很快就被摧毁了,这实在是有赖于叔孙氏家臣竖牛的帮助。事实上,在季氏协助竖牛谋取叔孙氏家权之后,竖牛的回报并不仅仅是以叔孙氏之邑作为贿赂,更在于他以叔孙氏的名义帮助季氏解决了此前有关不毁中军的盟诅,推动了季氏筹谋“舍中军”的进程。这在《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前后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昭公四年《传》: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季孙谋去中军,竖牛曰:“夫子固欲去之。”[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232 页,第4422—4423 页,第4430 页。
……
昭公五年《传》: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书使杜洩告于殡,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232 页,第4422—4423 页,第4430 页。
在竖牛使计饿死叔孙穆子后,季氏图谋“去中军”。竖牛于是就凭借叔孙氏家臣的身份,表示叔孙穆子在世的时候也想要这么做,为季氏的这一谋划提供了来自叔孙氏的支持。杜预认为,竖牛在这里所说的“夫子固欲去之”,是为了将毁中军的谋划强加到叔孙穆子的头上,从而实现讨好季氏的目的。原本作为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盟诅的主要推动者、坚持反对毁中军的叔孙氏现在反而变成了支持者,这就使得不毁三军之制的盟诅变得不堪一击。第二年,季武子就用策书的形式让杜洩在叔孙穆子的棺椁前告慰,说“穆子您本来就想要废除中军,现在已经废除了,所以就来向您报告这件事”。杜洩明知叔孙穆子的心意,知道他为了不让季氏专有鲁政,一定要与季氏盟诅,坚持不废三军之制;但在季氏和竖牛达成合作的情况之下,穆子成为了季氏不敬鲁公室的替罪羊,他也无力改变什么,所能做的只有率领手下的人哭泣起来,悲痛于穆子竟然被小人诬陷[1]杜注以其“痛叔孙之见诬”。参见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423 页、第4430 页。。可以看到,竖牛在叔孙穆子死后,诬陷叔孙氏本来就意图毁中军,而季氏之后告叔孙之柩的行为更是坐实了叔孙穆子在“舍中军”这一过程中的主导身份。这从而使得季氏在名义上摆脱了作为“舍中军”进而“卑公室”的主导者所应具有的对于鲁公的不敬之罪。
在《左传》的记述中,季武子筹谋废除中军正是在竖牛为乱以致叔孙穆子卒之后开始的。这样说来,无论是在名义上为季氏“舍中军”进行了遮掩,还是使得叔孙氏整体实力下降、没有底气阻拦季氏专鲁政的筹谋,并进而为季氏于昭公五年(公元前537)的“舍中军”提供了契机,竖牛之乱所导致的最为关键的后果,就在于它深刻推动了季氏专鲁政的进程。《左传》在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四分公室之前追言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作中军”之事,一方面说明了季氏从始至终都在为专有鲁政而谋划,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三桓在这两次事件之后的势力对比变化: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叔孙氏的份额本来较孟孙氏而言更多,但等到昭公五年在季氏主导下的四分公室,原来积极参与国家军政的鲁公室的力量被拆解之后,叔孙与孟孙的份额等同,季氏则从之前的十二分之四转变为如今的四分之二。三桓“卑公室”,而季氏在经过了两轮的军制改动后,在这三家中实力一跃而成为最强,《左传》对这一过程的叙述,特别突出了季氏的伪善与专权。而昭公四年(公元前538)所发生的竖牛之乱,与《史记》略过不提的叙述方式相比,《左传》对此的细致记载着重体现了这一事件中竖牛与季氏的互动关系,加速了季氏专有鲁政的进程,鲁国由此真正完成了国政倒向大夫的局面。
结语
竖牛之乱的发生应该放在春秋时期家臣作乱频繁的背景下考虑,这一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与当时公卿政治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在诸侯实力增强、不断对周王权威发起挑战的同时,大夫们也借助对外战争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本。特别是鲁国自成公以后,世执鲁政的“三桓”皆出自公室贵族,宗族势力十分强大,“卿族不绝后嗣……这与晋、郑、卫等国时常出现的数世之卿族,一朝而灭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1]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213—214 页。。有学者提出,此种“卿族不绝后嗣”的原则较为鲜明地体现出鲁国直承周代的宗法、礼乐制度:宗法继承制使得三桓能有“百世不迁之宗”,而鲁国承继周人“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坚持为宗族立后,这也使得鲁国卿权世代承继[2]林宝华:《试论三桓世卿的性质及其对鲁国的影响》,《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2 期。。例如在叔孙侨如被逐出鲁国后,就对叔孙穆子说:“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421 页。认为鲁国为了保存叔孙氏,一定会召回当时还在齐国的叔孙穆子,作为叔孙氏新任家主。可以看到,鲁国的这一态度对于三桓势力的稳固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由于卿大夫执掌国政,本应管理家族事务的家臣,在自身政治经济实力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妄图进一步插手国家事务。有趣的是,隶属于某一公卿的家臣,他们所需要效忠的仅仅是自己的家主,而非家主所效忠的公室。简单来说,正如周王不具备直接管理那些隶属于诸侯的大夫的能力,对于诸侯而言,同样也存在“大夫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情况。所以,为了脱离家主的掌控,部分实力强劲的家臣甚至可以利用国内国外、君权与卿权的复杂争斗状态,借助公室的力量来与家主对抗[4]谢乃和,陶兴华著:《春秋家臣屡叛与“陪臣执国命”成因析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6 期。。在阳虎之乱之前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作为季孙氏家臣的南蒯,因为不满于时任家主的季平子的轻待,就对昭公的儿子公子慭说:“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4479 页,第4507 页。南蒯这里是在与鲁公室进行一个交易,我帮你得到季氏的家产,那么你就要让我成为公室的臣子,相当于是试图摆脱局限在公卿家族内部的家臣身份。不过,这件事情最后由于公子慭出使晋国而未能成功,南蒯也带着费地叛逃到了齐国。齐景公一次饮酒时便戏称南蒯为“叛夫”,南蒯解释说自己其实是想要壮大公室,齐大夫韩皙就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4479 页,第4507 页。身为家臣竟然想要越过家主而使公室强大,实在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春秋时期家臣想要从与家主的从属关系中脱身而出,其难度可见一斑。
季平子之后,季桓子成为季氏新主,“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的局面形成,礼崩乐坏的状态已经到了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政”的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局面的产生实际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作为季氏家臣的阳虎具备了掌握季氏的实力,一是季氏也在此前与公室以及叔孙、孟孙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后一点的达成,在《左传》的叙述中,正是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竖牛之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孔子对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曾有这样的感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五册,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5477 页。对应到鲁国的情况,虽然竖牛并没有直接为最后阳虎所谓“陪臣执国命”的结果提供引导,但阳虎得势的前提是季氏的专权,季氏的专权又不得不追溯到竖牛之乱带来的便利条件。鲁国伴随着政治权力的不断下移而走向衰落,叔孙穆子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因为一个神异之梦而宠信了一个家臣,竟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以称谓为教学切入口解读《季氏将伐颛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