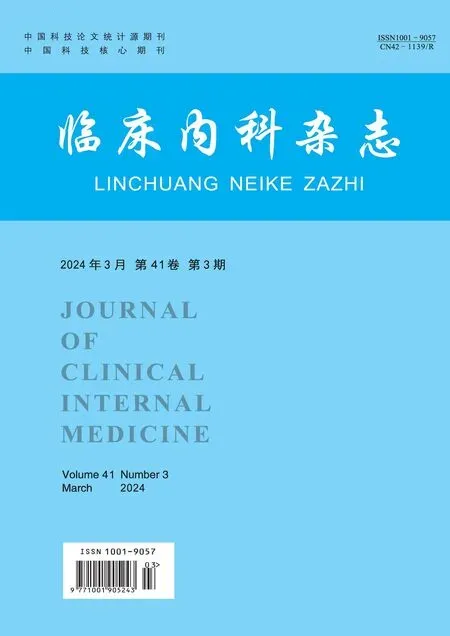生物制剂对溃疡性结肠炎合并肠道巨细胞病毒感染影响的研究进展
郭文娟 杜时雨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由遗传、环境、免疫等因素引起的非特异性慢性复发性肠道疾病[1],病变主要累及结直肠,表现为黏液脓血便、腹泻、腹痛等症状,也可伴随肠道外症状,如关节炎、坏疽性脓皮病等。中重度UC的治疗经常需要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及生物制剂[2],同时疾病本身的消耗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常会并发肠道巨细胞病毒(CMV)感染。CMV属于β疱疹病毒科,为双链线性DNA病毒,人类是唯一的自然宿主,可引起一系列疾病,从无症状感染到严重靶器官损伤[3]。CMV病毒感染人体后可潜伏在宿主体内,当机体免疫力降低时引起脏器损伤,如结肠炎、肺炎、肝炎、脑膜脑炎等。
目前炎症性肠病(IBD)的治疗进入生物制剂时代,但解决随之出现的合并感染问题也已迫在眉睫[4-5]。2007年我国引进首个生物制剂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IFX),2020年我国批准阿达木单克隆抗体(ADA)、乌司奴单克隆抗体(UST)、维得利珠单克隆抗体(VDZ)用于IBD的治疗[6]。本文就生物制剂对UC合并肠道CMV感染的影响进行综述。
一、UC合并CMV感染的流行病学
CMV在人群中的感染率高,但多为潜伏性感染,终生伴随。当机体由于基础疾病或医源性因素引起免疫力降低时,病毒可再次激活,引起特定器官疾病。以血清CMV IgG阳性为依据,人群中感染率为45%~100%,且南美洲、亚洲、非洲的感染率高于欧美地区[7],我国武汉的数据显示,人群中CMV感染率为50.69%,与国外的数据一致[8]。一项Meta分析研究结果显示,IBD患者CMV感染率和对照人群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69.6%比51.8%,P=0.59),但当以血清CMV DNA(42.5%比26.4%,OR=4.99)或血清CMV抗原血症(40.4%比6.6%,OR=7.4)阳性为依据时,UC组CMV再激活率高于对照人群[9]。在急性重度UC患者中,肠道CMV感染率高达21%~34%,在糖皮质激素抵抗的UC患者中,肠道CMV感染率为33%~36%[10]。
二、UC合并肠道CMV感染的诊断
临床医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鉴别UC复发和UC合并肠道CMV感染。由于两者有着相似的临床症状,如发热、腹泻、便血、腹痛、体重减轻等,从临床表现方面难以鉴别两者;而内镜方面,尽管深凿样溃疡、不规则溃疡、鹅卵石样改变等征象均有助于预测肠道CMV感染,但却不能以此来确诊肠道CMV感染[11]。
此外,区分CMV活动性感染和肠道CMV感染也很重要。CMV活动性感染指血液CMV-DNA、CMV-IgM抗体及CMV-pp65三者中有1项以上检测结果为阳性,但CMV活动性感染并不意味着有肠道受累,实际上,只有部分CMV活动性感染者会累及肠道。当前,肠道CMV感染诊断的金标准仍为结肠黏膜组织HE染色阳性伴免疫组织化学法(IHC)和(或)结肠黏膜组织CMV-DNA PCR阳性[12]。问题在于,虽然HE和IHC染色法特异性高达92%~100%,但敏感性不稳定,据一项Meta研究显示,HE染色敏感性最低甚至只有组织PCR的4.7%,其结果高度依赖于病理医生的阅片水平;IHC的敏感性略好,但也只有组织PCR的23.0%[13]。也有研究报道IHC的敏感性可达到90%以上,但此结果显然不具备普遍性[10]。
组织CMV-DNA PCR检测也有局限性,其结果中可能包含的潜伏CMV会造成假阳性。针对这一情况,有研究者建议应用组织CMV-DNA定量检测代替定性检测[14]。目前结肠黏膜组织CMV-DNA定量检测的临界值尚未确定,有研究提出以250 copies/mg为病毒载量临界值,同时对于病理取材部位加以限定,由于溃疡的基底部和边缘病毒载量高,建议在上述部位取材[15]。
三、生物制剂对UC合并肠道CMV感染的影响
目前国内批准用于治疗IBD的抗肿瘤坏死因子(TNF)-α单克隆抗体药物包括IFX和ADA,通过结合可溶性及跨膜性TNF-α,从而发挥阻断炎症、改善IBD病情的作用。2019年美国胃肠病学院(ACG)建议中重度活动性UC患者将生物制剂(含抗TNF-α单克隆抗体、抗整合素单克隆抗体)和糖皮质激素作为平行选择。因此,IFX在急性活动期UC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已有关于抗TNF-α单克隆抗体与肠道CMV感染的研究报道[16]。
一项回顾性对照研究显示应用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甲氨蝶呤)、年龄>30岁是IBD合并CMV感染的危险因素,应用抗TNF-α单克隆抗体并不增加CMV结肠炎的风险[17]。纳入了含16项研究的Meta分析也显示相似结果,暴露于糖皮质激素和硫唑嘌呤可增加肠道CMV感染风险,但TNF-α拮抗剂的应用并不增加肠道CMV感染的风险[18-19]。Pillet等[20]的前瞻性观察研究显示,抗TNF-α单克隆抗体并不增加肠道CMV感染风险;并且该研究对20例肠道CMV-DNA阳性患者予抗TNF-α单克隆抗体治疗8周后,其中11例肠道CMV-DNA载量稳定、2例降低、4例转为阴性,因此认为在肠道CMV-DNA阳性患者中,予抗TNF-α单克隆抗体治疗并不加重肠道CMV的载量。这可能是由于CMV病毒的复制需要促炎因子TNF-α,而抗TNF-α单克隆抗体降低了促炎因子TNF-α含量。因此,从机制上讲,TNF-α拮抗剂对抑制CMV病毒的复制有一定作用[21]。
VDZ是重组人源化IgG1单克隆抗体,可特异性地拮抗α4β7整合素,阻断T淋巴细胞表面活化的α4β7整合素与其配体肠道血管内皮细胞表达的黏膜地址素细胞黏附分子1(MAdCAM-1)的结合,阻止T淋巴细胞迁徙到肠道炎症区域,减轻肠道局部炎症反应[22]。VDZ为肠道高选择性的新型生物制剂,靶向肠道并具有组织特异性,因此理论上其诱发全身机会性感染风险较其他生物制剂低。目前对于VDZ与肠道CMV感染的相关研究少,仅有少量个案报道。Bonfanti1等[23]报道了1例UC合并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既往应用IFX、ADA、戈利木单克隆抗体治疗无效,在联合应用VDZ及硫唑嘌呤4个月后出现了原发性CMV感染,予更昔洛韦治疗后患者病情缓解,由于该患者联合应用了硫唑嘌呤,猜测CMV感染与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的联用有关。Rawa-Goębiewska等[24]报道了一例糖皮质激素依赖性全结肠型的UC患者,肠道组织CMV免疫组化检测为阳性,仅予VDZ诱导治疗后,肠道组织CMV免疫组化检测为阴性。Hommel等[25]报道1例UC合并CMV肠炎患者,在抗病毒治疗1周后,予VDZ诱导及维持治疗,肠道组织CMV-DNA值维持在稳定的低水平状态(11~18 IU/100 000个细胞)且CMV免疫组化检测结果为阴性。因此该文章认为,对于活动期UC合并肠道CMV感染,在抗病毒治疗前提下,应用VDZ可能是安全的。但仍需大样本研究以证实VDZ在UC合并肠道CMV感染中的安全性。关于VDZ是如何影响肠道CMV感染的机制,目前尚无明确定论。有研究显示,VDZ对肠道T淋巴细胞丰度仅有轻微影响,但可显著影响先天免疫,特别是肠道巨噬细胞数量。有学者推测通过阻止已感染CMV的单核细胞招募到肠道黏膜,从而减轻肠道CMV感染[26]。
UST是一种人源化IgG1κ单克隆抗体,可与人IL-12、IL-23的p40蛋白亚单位特异性结合,从而阻断Th1和Th17细胞增殖而发挥抑制炎症作用。UNIFI研究是一项全球Ⅲ期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在既往接受生物制剂或传统治疗失败的中重度UC患者中评价UST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该研究纳入了961例中重度UC患者,其中348例患者予乌司奴单克隆抗体维持治疗,仅有2例患者在维持治疗中出现了肠道CMV感染[27]。
托法替布是一种全新的小分子口服制剂,对JAK激酶具有靶向性,主要通过与JAK1和JAK3的ATP结合位点作用,抑制激酶的磷酸化,阻断细胞内炎症通路而发挥抗炎作用。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该药物用于治疗UC。托法替布Ⅲ期临床试验OCTAVE induction2 纳入了541例活动性UC患者,其中429例接受托法替布治疗,仅有1例患者出现肠道CMV感染[27]。
四、UC合并CMV感染的治疗进展
2021年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提出,对于肠道CMV再激活的IBD患者,不应停止免疫抑制剂的治疗,但糖皮质激素应逐渐减停。对于糖皮质激素难治性IBD合并肠道CMV感染患者,应予抗病毒治疗。对于有症状的全身CMV感染,建议停止免疫抑制剂治疗。治疗方面,建议予静脉注射更昔洛韦5 mg/kg、每日2次治疗5~10天后,随后予缬更昔洛韦每日900 mg口服,直至2~3周的疗程终止。如患者对静脉注射更昔洛韦反应佳,可考虑早期更换为缬更昔洛韦。对于更昔洛韦不耐受或耐药的患者,可予膦甲酸钠治疗,但需警惕肾功能损伤[28]。
对于生物制剂是否停用,目前指南没有给出明确结论。但部分研究显示,与免疫抑制剂相比,如抗TNF-α单克隆抗体引起肠道CMV再激活的风险低;VDZ在抗CMV病毒治疗的前提下,有成功治疗糖皮质激素抵抗UC合并肠道CMV感染的报道[24-25]。UST、托法替布对肠道CMV感染的报道仅为临床试验中的个例报道,数据有限。因此,不同生物制剂在UC合并肠道CMV感染治疗中的安全性仍需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证实。
五、总结
UC合并肠道CMV感染使患者病情复杂,免疫抑制剂在机制上有加重肠道CMV感染的风险,随着生物制剂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IBD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对于UC患者,如存在肠道低载量/水平CMV感染、CMV潜伏感染或CMV再激活的高危因素(如高龄、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史),生物制剂(如TNF-α拮抗剂、VDZ)较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似乎更有优势。但由于生物制剂在UC合并肠道CMV感染中应用的报道较少,且多为回顾性、小样本的研究。因此,需要前瞻性大样本的研究为临床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