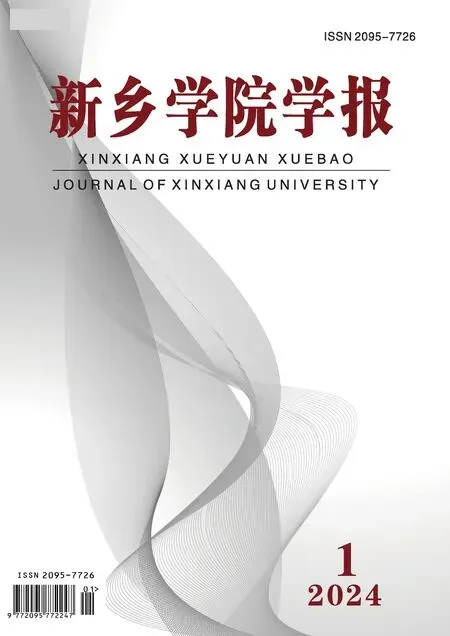《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田园书写
赵晓晓
(新乡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是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巅峰之作,该小说既是对传统维多利亚爱情故事的模仿与颠覆,又是对传统田园书写的继承与创新。订婚恋人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去莱姆度假,偶遇有着“法国中尉的女人”绰号的萨拉,受其影响,查尔斯无可救药地走上存在主义自由之路。该小说中有大量的自然景致描写,使得福尔斯的田园书写特点展露无遗。
一、田园中的动物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对田园中的动物进行了多次描写。小说中间部分,叙述查尔斯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他很忧郁:他已经和错误的女孩订了婚,而且刚刚被剥夺了祖传财产的继承权。当查尔斯进入莱姆·雷吉斯周围的树林时,道路上有一只狐狸穿过,还有一只公鹿在安静地散步。这一景致堪比15世纪意大利艺术家皮萨内罗的画作《尤斯塔斯的幻象》。卢克·赛森和迪利安·戈登指出,“这幅画是为展示皮萨内罗描绘不同动物的技巧,并让赞助人惊叹于它们的诗意多样性和林中居民的神秘性”[1]。皮萨内罗画的不是罗马士兵,而是意大利王子,这使得这幅画更适合于贵族查尔斯的隐喻。就像皮萨内罗作品中的尤斯塔斯一样,查尔斯与自然的相遇使他感到震惊。
自然界并非只是上面讲的那两只动物才重要。树林中还有数不清的鸟儿在歌唱。黄莺、白喉雀、鸫鸟、画眉、白鹭、班尾鸽的歌声在晨曦中荡漾着,使清晨有着黄昏的静谧,却没有黄昏的哀伤色彩。查尔斯觉得自己像是走在动物的世界里。他感到,每一片树叶,每一只小鸟,小鸟唱的每一支歌,都是那样美,但彼此间又有细微的差别,这就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大千世界。[2]277
在《尤斯塔斯的幻象》中,有精心渲染的雄鹿、母鹿、熊、天鹅、鹳、鹈鹕和苍鹭等动物群,而查尔斯所看到的各种鸟类都以“细微的区别”出现,这些动物似乎来自一个完美的世界。就像乔叟在《鸟的议会》中对自然的描述一样,结合了自然学家描述的现实细节[3]。主人公的注意力被附近大嗓门的鹪鹩吸引了,这只鸟的高声鸣叫充斥着他的头脑。他在所有这些非人类生命的背景下思考自己的处境。而他在这一场景中的最后情绪是“我不知道”。叙述者解释说:“他被关在外面,失去了伊甸园,像萨拉一样——他可以站在伊甸园里,但不能享受它,只能羡慕鹪鹩的狂喜。”[2]278在这个场景中,查尔斯看到了“普遍存在的对等性”,看到了周围的动物所处的和平环境,尽管它们的环境很卑微。然而,查尔斯沉浸在他个人的、存在的担忧中,感到被拒之于这种平等的存在之外。
根据奥布里的说法,“平等存在”的概念最好的解释是达尔文式的动物平等观,它“掩盖了垂直组织的、按等级排列的存在之大链的各个环节”[4]。奥布里将中世纪的“存在之链”概念与查尔斯在这一场景中的看法进行了对比。然而也应该看到,由于人类意识的性质,“存在的对等性”是复杂的。查尔斯在散步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并注意到这些动物就像他一样,也有情感。因此,存在具有对等性。查尔斯也注意到它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然而,查尔斯本人复杂的人类意识以及对过去和未来情景的把握,似乎让他感到焦虑。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可能是人类的亲戚,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某种平等的存在,或普遍共享的共同身份,但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并不同人类一样有巨大的忧虑后世的潜力。
查尔斯凌晨四点后走到莱姆·雷吉斯的乡下,一夜未眠,陷入沉思。遇到大自然“宁静而满足的脸”后,虚构的查尔斯感到“被驱逐出”黑帽和白头翁所共享的和平境地。福尔斯不能被指责为一个虚无缥缈的自然作家,他将自然世界设定为一个良性的宁静的地方,同时又默默地忽略了自然界使人类成为人类的特殊品质。这种“自然角”的陈词滥调在福尔斯的小说中得以避免。在对福尔斯的一次采访中,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提出了以下问题:“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你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抒情表达所打动……然而,这种抒情难道不是一种错误的标准吗?自然界是美丽、平静和恢复性的,恰恰是因为它缺乏痛苦的自我怀疑……的人类世界。”[5]73这样一个问题引来了反驳,福尔斯的小说并没有假定一个非人类的世界。自然界的平静和姿态,可以与人类生活相提并论。
《智者》是基于福尔斯在大学期间的哲学笔记的自画像。这本书被编排成一个“笔录集”,大概是受到了18世纪法国作家如帕斯卡尔和拉罗什作品的启发。福尔斯认为,在正常条件下,自然界中所有有生命和有感情的生物都可以分享幸福,除了人类。
二、田园中的人物
对牧羊人、铁匠、木工、农民的描写是《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田园书写的又一特点。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查尔斯的男仆萨姆来到他主人在莱姆·雷吉斯的卧室。
萨姆拉开窗帘,清晨的阳光洒满了查尔斯的全身[2]44。
楼下传来小蹄子啪嗒啪嗒的落地声,接连不断的咩咩叫声。查尔斯站起来,向窗外望去。街上有两个穿褶皱外套的老人,正面对面地站着讲话。其中一人是牧羊人,用牧羊人的弯柄杖斜撑着身子。十二只母羊和一群大羊羔慌慌张张地呆在街上。古代英国流传下来的这种衣着样式到一八六七年虽并非罕见,但已不多,看起来很别致。每个村庄里都还有十来个老人穿这种外套。查尔斯想,要是自己会画画就好了。的确,乡下真叫人陶醉。他转身对仆人说:“说真的,萨姆,在这儿过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回伦敦去 了。”[2]45
正如迈克尔·贝拉米所说,“查尔斯缺乏艺术天赋,预示着现代游客忘记了他们的相机”[7]。这个典型的田园组合——靠在羊角上的牧羊人、穿着罩衫的长者、咩咩叫的羊群,被查尔斯唯美化了。他希望画出这两个人和动物,暗示这种对场景的审美理解可能会取消这些人物所体现的独特的思想和个性,把他们仅仅当作画布上的装饰品。
查尔斯的感叹具有讽刺意味。“我再也不想回伦敦去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个舒适的卧室里。仆人正忙着准备给他做早饭,帮他刮胡子,然后,为他收集“双份松饼”。眼神呆滞的查尔斯俯视着一个显然没有从舒适的环境中站起来的牧羊人,说出了这番话。牧羊人可能从黎明开始就已经出来了,当时抚摸着胸口的温暖晨风可能并不那么具有诗意般的温柔。
在这部小说中,这位可以轻易考虑“不想回伦敦去了”的绅士代表了整个英国社会的一个阶层。在去他叔叔的乡村庄园温斯亚特的旅行中,查尔斯认为自己正在重新进入“万古不变的平静乡间”[2]226。他的车子驶上了车道,“几英里内都是春意融融的草地,威尔郡的广阔平原尽收眼底。远方的房屋已清晰可见。屋子灰白相间,两侧耸立着高大的雪松和著名的铜色山羊榉树,后面是隐约可见的成排马厩”[2]226。查尔斯对庄园的观察是连续的。
他们碰到了他伯父的几个雇工,其中有铁匠埃比尼泽,他正在一个小火盆旁将一根弄弯了的铁栏杆打直。在铁匠身后,有两个木工向查尔斯问安。第四个是名叫本恩的老人,他身上穿着年轻时穿的外套,头上戴着毡帽。他是铁匠的父亲,是十几个获准住在庄园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之一。这些老人可以象庄园主一样随意在庄园里走动。这是温斯亚特庄园八十多年来相沿成习的规矩,至今如此。[2]225
查尔斯看到一个铁匠、两个木工正在打发一天的时间。第四个人是一个长者,他仍然穿着年轻时的罩衫,戴着古老的小帽子。叙述者以特有的方式进行表达:英国大房子的主人喜欢勤奋劳作的农民,就像喜欢被精心照料的田地和牲畜一样。
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农村不公正和贫困并没有影响到温斯亚特这样的地方,但这些庄园主对员工的相对善意“可能只是他们追求家业兴旺过程中的副产品”[2]226。对温斯亚特的工人的介绍范围很广,他们顺利地融入到视觉风格化的全景中。将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作为一种田园风光的消费者置于社会之中,一个侵入性的、讽刺性的叙述者的出现加强了这种表述。
三、田园中的景观
田园中的景观表述是《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又一特色。景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这个时期的地主们在外出时看到克劳德的画作时,学会了新的观察方式,并回到英国在自己的庄园中创造这样的前景。如威廉·肯特或兰斯洛特·布朗,他们受雇于富有的庄园主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美学效果,在克劳德或普桑的艺术传统中是“自然的”和阿卡迪亚的。在那之前,正式的花园都是在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影响下建成的,所以在景观园林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品位转变。乌维代尔爵士(1747—1829)在19世纪初影响了许多景观设计师,他希望景观要像著名艺术家的画作那样美丽。他写道,场景应该是“如诗如画”的,这个词用来指的是“已经或可能在绘画中得到良好效果的每一个物体和每一种风景”[8]。场景中的物体应该具有基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些物体的纹理应该具有粗糙度和不规则性。
在《乡村与城市》中,雷蒙德·威廉姆斯强调,18世纪的地主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业主。该世纪的景观设计革命推动了“令人愉快的前景”这一概念的提出,这种景色从大窗户、露台和草坪等高处可以看到,并且隐含着一种控制和命令的表达。这种强调从一个远处的、可控制的有利位置进行占有的做法,就是威廉姆斯所说的“占有的分离”[9]126。景观园艺中创造令人愉悦的前景,意味着景观园艺师、诗人、画家和地主获得了支持,并被赋予了抽象的审美。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重点都在视觉感知上,而视觉感知必须符合一种文化理想(风景被组织成美丽的图片)。然而,人类与自然本身有一种距离。显然,18世纪的庄园主和风景园林师并不厌恶绿色,但这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自然只能从远处看到,而且只有在它呈现出令人满意的面貌时才能看到。
到了1867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场景,英国景观园艺的伟大革命已经成为乡村的固定资产。当查尔斯沿着车道向他叔叔的房子走去时,他观察到了田园风光“宜人的前景”和迷人的农民。然而,《法国中尉的女人》并不是一部19世纪的小说,这部1969年作品的作者被给予了更多的理论勇气,因而不是简单而不自觉地向读者展示另一种牧歌式的田园诗。正如威廉姆斯所争辩的那样,这种对自然和那些从事自然工作的人的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视觉上的魅力,是一种在控制土地及其前景方面的一种微妙的剥削[9]126。大房子的奶油色和灰色被其周围的雪松所包围,并以威尔特郡的山地为背景;各种各样的农民心满意足地在车道边上磨蹭着;所有这一切都优美如画。然而,这种自觉的观察模式,必须从根本上将福尔斯本人以及他代表的整个阶级分离出来。查尔斯看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但他是作为一个牧民的消费者,而不是作为一个对农村生活有洞察力的观察者。叙述者在他的旅程中插话说:“今天那种‘明智’的现代管理的目的可能也不会是为了对他人有利。不同之处在于,过去那些善良的剥削者追求的是‘家业兴旺’,而今天这些善良的剥削者追求的是‘高生产率’。”[2]226与读者可能期待简·奥斯汀所展开的田园风光不同,福尔斯的后马克思主义智慧在文本中体现在辨别阿卡迪亚全景下的经济关系上。
根据马里内利的说法,田园诗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个理想的或至少是比较纯洁的世界被感到失落时写的,但又不至于完全摧毁对它的记忆,让人对它产生怀疑,使得现在的现实和过去的完美之间产生想象性的交际[10]。
四、田园中的树林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查尔斯在一个清晨走过莱姆·雷吉斯旁边的一丛树林。树冠被描述为藏有“无限”的阴影,枝繁叶茂,半遮半掩,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暗示性、不可预测性。“我一直厌恶平坦和缺少树木的乡村。那里的时间似乎是主宰,它像时钟一样无情地跳动。但树木扭曲了时间,或者说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时间:这里密集而突兀,那里平静而蜿蜒……”11]7。
福尔斯说,不是时间被树所改变,而是人的经验被树所改变。作为“流动”的时间确实是人的经验,而梭罗说时间被他周围的森林赋予了摇曳和阴影的复杂性。这位伟大的美国自然作家预示了福尔斯的信念,即神秘对人类生活的生命力,以及它在野生自然中的体现。在接受采访时,福尔斯说:“我对小说研究的唯一持续兴趣是我自己的自然史(和行为主义)。作为一个作家,我自己是一只小白鼠。”[5]72他在《树》中又说:“我从来没有尝到在孤立的发现的经验之外的任何滋味——就真正的地理探索而言,为了适当利用的发现。我对自然(和人类)史的许多分支都有所涉猎,但对任何一个分支都不了解。除此之外,无数的其他事物也是如此。我喜欢的是一种游荡在森林中的熟人,仅此而已。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不是一个演奏家;总是在绿色的混乱中,而不是在印刷的地图上。”[11]57
伴随着对神秘的欣赏,对发现的欣赏,福尔斯重视自然界的神秘性,也重视对这种神秘性的体验性发掘。
五、结语
福尔斯的一生总是寻找机会远离城市,作为一个业余田野自然主义者或作为一个华兹华斯般的自然爱好者,他曾到希腊、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美国、英格兰的乡村生活。“福尔斯的自然书写既是其本人热爱自然的情感表达,也是对英国田园文学传统的传承”[12]。福尔斯常年与自然为伴,常年经受自然的浸润,这激发了福尔斯对自然的无限热爱,成就了他小说中的田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