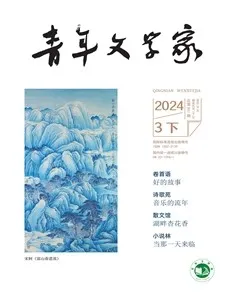叙事学视域下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的解读
谭利民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细数这位文学大家的作品可以发现,蒲宁在其一生的艺术探索中关注的就是关于美与爱、生与死、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关系的主题。在蒲宁的小说创作中,以中篇或短篇居多。其中,“爱情”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他的所有作品,爱情是作家把脉丰饶世情的道具,更是浸透作家生命的沉甸甸的爱的符号。在短篇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中,蒲宁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饱满丰盈的情感道出动人的爱情故事。笔者将以此作品为例,从文章的叙事结构入手,深入分析蒲宁的爱情小说叙事特点,挖掘这位伟大作家内心深处的爱情观。
一、短篇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的叙事手法
(一)叙事结构
在蒲宁的爱情小说中,“爱”与“死亡”总是牵连在一起。笔者认为作家的大部分爱情小说叙事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生离死别”,如《娜塔莉》《在巴黎》《寒秋》等;第二类为“一见钟情—无法相爱—生离死别”,如《安提戈涅》《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佐伊卡和瓦列里娅》《米佳的爱情》等。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多样,却都逃不过爱的吸引,无论是生理上的荷尔蒙还是精神上的依恋,都驱使着他们陷入爱的旋涡。命运的安排和爱而不得的痛苦让死亡降临,生命陨落,爱在回忆里永生。
短篇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中,“我”在车站与一位女郎邂逅,“我们”之间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一见钟情),然而女人已有婚约(无法相爱),“我们”被迫分离,女人给“我”写信道出自己的思念与爱意,正当“我”为此感动想要给予回应时,收到了女人去世的消息(生离死别)。故事以女人的讣告结尾。这样的叙事结构搭建出“爱与痛苦交织,生与死并行”的爱情故事。
(二)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即“叙述故事时的观察和讲述角度”。如何对叙述视角进行分类也有着众多讨论与争议。本章节将以学者申丹的叙事学理论作为参考,对该小说进行分析。
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中整体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由“我”讲述与“她”的故事。开篇便是:“这天傍晚,我俩在火车站上相逢了。”用第一人称叙述,仿佛真实的、身边的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让读者能轻而易举地带入,体会故事内容。故事中的“我”一直在对“她”进行观察、打量和揣摩,当“我”跟在“她”身后,步入幽径,注意力也总是放在“她”的身上:“她走在前面,而我呢,两眼一直望着她的裙子,望着她怎样听任裙摆缠在她脚上,望着她的方格短上衣和她用辫子盘成的沉甸甸的发髻。她灵巧地选择着比较干的地方落脚,不时弯下腰去闪开树枝。”“她”的美丽、天真、任性鬼使神差地吸引着“我”,让“我”不由自主地任“她”安排,向“她”靠近。由于第一人称体验叙述视角是有限的,我们通过人物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因此可以更自然地直接接触到人物细腻、复杂的内心活动。在这篇小说中,读者从“我”的视角出发,观察“她”的神态、动作、语言,与故事中的“我”产生共振,从而更清晰地了解“我”的心理状态和坠入爱河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故事主线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但作家巧妙地通过书信对叙述视角进行了变换。小说的第二部分由女主人公的信件内容构成。“我”与“她”分别四个月之后,收到了“她”的信件。“她”在信中坦白真心、流露真情,表达自己汹涌的爱意和思念,一字一句写下作为伯爵妻子的无奈,以及无法与心上人相爱的痛苦。在小说的这一部分,叙事从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转换到了另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书信带来的视角转换也使得原本单一的叙述模式变得丰富。由于建立起了男女主人公的双重视角,这使得叙述线索并不紧紧围绕“我”这一位人物展开,而是从多角度、在多个层面上对故事进行探讨,从而多层次地刻画人物。对“我”而言,客体的“她”掌握了话语权,心理活动一并展开,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女主人公细腻、复杂的内心活动,使得这一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立体,普通的爱而不得的故事也因此显得扑朔迷离、扣人心弦。
(三)叙事时间
叙事学家关于叙事与时间的研究主要从“故事”与“话语”关系入手。“故事时间”指所述事件发生需要的实际时间,“话语时间”指叙述事件所用的时间。
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在整体上依照“自然时序”进行叙述。“我”在某一天(按后文可推测出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与“她”邂逅,短暂地尝到爱情滋味,继而分别;在四个月之后(三月初)收到“她”的来信;“我”心生向往,决定踏上寻爱之路,在三月末回到北方的村子,收到了“她”的讣告。时间线看似非常明确,小说也在话语上呈现出线性叙事的特点。然而由于小说中穿插了女主人公的信件,使得时间线发生了交错和偏离。从信件和电报内容以及“我”的经历可以得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写信向“我”表白心意,在“我”满怀感动,决定追逐幸福的时候,“她”已驾鹤西去。从男女双方的不同视角来看,故事层面的时间具有交错、偏离的特征。
观察时间轴可以发现,在小说叙事中,由于整体上采用了男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体验视角,话语时序依照故事中“我”的经历,导致故事时序與话语时序并不完全一致。
分别后,女主人公在爱与痛苦中写下并寄出长信,也不知心爱之人能否给出回应,而同时期的“我”也因离家在外未及时收到信件而错失良机—在这段时间里,女主人公的心理挣扎不得而知。“我”收到信件后深受感动,决定为爱放手一搏,然而因为通信不便,在“我”的心意传达之前,女主人公便遗憾辞世。
“我”在第一个时间点和第三个时间点之间经历了什么?“她”在第二个时间点和第四个时间点之间又遭受了怎样的痛苦与精神折磨才让生命走向尽头?
在作家的叙事安排下,错开的时间线更体现了大背景下命运的捉弄与爱人错过的无奈,让读者为故事唏嘘的同时,人物的心理活动层面也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供读者想象。
(四)叙事空间
经典叙事学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对“空间”进行了探索。叙事学家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提出“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语空间”则是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中依次展现出多个故事空间:
在第一部分中,故事空间从人潮涌动的车站转移到隐秘暧昧的树林,空间的变换也暗含着故事人物的感情走向。从山岗到洼地再到干草堆,快速的空间移动也展现了女主人公性格中活泼的一面,以及人物的情绪潜流:“我”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因此空间移动并不如“她”跳脱;而“她”紧张又激动,因此空间多样且切换迅速。
第二部分的内容里,“我”正在克里米亚,收到了来自“她”的信件。由于叙述视角的转换,叙述空间和故事空间也有了变化。叙事空间转移到女主人公写信时所在的阿尔卑斯山的小旅馆,女主人公在信中写下自己在幽谷、山路、树林、洞穴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表达自己无尽的爱意、思念和哀愁。从“她”视角中,小旅馆是“冷彻骨髓的、空荡荡的”,进山后的景象全是“满目凄凉”,寂静极端深邃,连湿淋淋的灌木在她眼里都是在“饮泣—轻轻地,轻轻地饮泣”。她在黑暗的冬夜里想到自己“置身在真正的死亡的王国中”。所有描述都带有人物的主观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物的情感如游丝般在环境中交错,衬托出人物近乎绝望的哀愁,以及对爱情痛苦的渴求。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叙述视角又转变为第一人称体验视角。“我”在南方收到信,在酒馆又读了一遍,随之“在酒店里再也坐不住了,我走到户外……”在原野之上思绪飘飞。叙述者对无边无际的山峦和广袤无垠的云层进行了详细的描写,突出了“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心境的转变,为之后启程返乡进行了铺垫。在回家路途中,“我”同样看到峭壁与幽谷,但在“我”眼中,幽谷“绿荫森森、风景如画”,与第二部分里“她”笔下的阴森寒冷的幽谷和悬崖形成对比,突出了人物心情的差异,突出了“我”满怀对春天和幸福的向往的情绪状态;同时,从白雪到绿荫的变化也暗示了时间跨度之大。在文章末尾,叙述者对返乡事宜进行了概述,回到北方的村子后,“我”收到“她”故世的电报。
以人物视角展现的空间,既是人物所处的真实空间,同时又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投射,环境与心境相互映照。因此,在小说中空间的转换和场景的描写,无一不在反映人物处在不同阶段时的心理状态。
二、蒲宁“爱与死”的爱情观
西方学者认为:“爱”与“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正如本篇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以及蒲宁其他的爱情小说作品中都能见到死亡的结局。或是自杀,如《米佳的爱情》中,米佳因心里的挣扎和痛苦选择开枪自杀;又或是意外,如《娜塔莉》的结尾,怀孕的娜塔莉由于早产与世长辞……
而在《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中,女主人公死亡的原因尚未说明,但因讣告是由遗愿寄出,可以推测出女主人公的死亡不会是意外。她或是因为思念成疾,患病去世,笔者更倾向于是因无法与爱的人相见,又因爱意未能得到回应而痛苦至极,最终选择了结生命。西方学者曾对爱而不得作出自己的评价:什么是地狱?我一直认为是不能去爱而遭受的折磨。女主人公无法控制汹涌的爱,就算在群山之间也能因为猫头鹰想到与男主人公在一起的日子,回忆不断刺痛她的神经,让她控制不住写下那封满怀爱意与绝望的信。她在信中表达自己迫切想要见面的欲望,渴望得到回应。然而因为男主人公差旅导致的时间差异,女主人公误以为石沉大海,爱情终结。命运的捉弄和心灵的纠缠构建起了这样一部悲剧。
从上文的叙事手法分析中可以看出,作者故意打乱了时间线,让人物都成了命运的棋子,真爱被暗中掌控的命运之手掐断。蒲宁在文中借女主人公之口道出对爱的理解:“人们曾千百次地歌颂过爱情,然而爱情又是什么呢?也许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有无爱情。不久前,我在一位已故作家的书信中读到这样一句话:‘爱情—这是渴望得到那种子虚乌有的东西。”对作者而言,爱是一种感受,是一种对“子虚乌有的东西”的渴望,如果渴望无法满足,那么痛苦就会来临。一旦痛苦达到无法承受的顶点,当渴望的东西化作泡影,就只有死亡这一条路可以让人从爱的旋涡中解脱。有学者指出,蒲宁的作品暗含了他的宗教觀念,其中就包括了道教中“甚爱必大费”(《道德经》)的思想。是故“甚爱必大费”,即“过分地爱惜必然会产生过大的代价”,从这一方面分析,“爱伴随着死亡”这一模式成为蒲宁爱情小说的主线并不奇怪,反而更加体现了作者对于爱和浪漫的理解—一种理想主义者对于浪漫的渴求。
在蒲宁的爱情观中,爱是对人生一切缺陷不足、虚妄、苦痛的补偿,纯精神的恋爱却不能得到圆满的结局,小说结局往往以一方的死亡而告终,这是源于崇高的浪漫精神—一种幻想、空幻境界和解脱,人在浮生中容易被无知与欲望所拘禁,挣脱了拘禁,就意味着觉悟,或者是除去了欲望的涅槃,达到回归,回归到最初的纯洁,实现了人的重生,生命借此实现了永恒。因此,蒲宁作品中“爱与死”的标签还带有作者对短暂与永恒的思考。“插曲”是意外的、短暂的,爱的火花在短暂中迸发,而思念却绵长久远。
在短篇小说《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中,蒲宁用穿插书信的方式促进叙述视角的转换,并由此丰富了原本的线性叙事模式,增加了叙述层次;书信情节的安排也让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出现了偏离,体现了命运安排的无序,为作品蒙上一层朦胧的悲剧色彩,让故事更耐人寻味,是体现主旨的关键一环;蒲宁从人物视角对场景进行描写,切换故事空间,运用人物对环境的感知映衬人物心境,对比男女主人公眼中的世界,在突出人物性格的同时又让混乱的时间线变得清晰,推动情节发展。
蒲宁通过自己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展现其对爱情的理解,诠释爱情与生命、死亡的关系,但并不能简单用“爱加死亡”的程式给其作品贴上俗气的标签。作家用深思熟虑的叙事手法讲述的不仅是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在宏大的宇宙里,作为渺小星尘的男男女女在生与死、短暂与永恒中追寻的理想的泡沫和爱的圣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