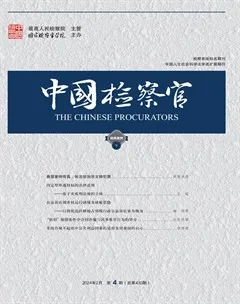违规处置重金属超标废水法律责任 认定分析*
韩广强 鲍伟群
一、基本案情
酸洗废液经过处理可以销售给印染企业,用于处理碱性废水、调节PH值,从而使其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在行业内称为“以废治废”。A公司是一家水处理剂生产销售公司,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为处置、利用不含镉、锰、镍、铜等重金属的酸洗废液。2014年8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沈某、杨某在经营管理A公司期间,明知该公司缺乏从钢铁酸洗废液中去除重金属的技术和能力,仍违反国家规定,逃避环保部门监管,向28家钢铁企业回收3万余吨含镉、锰、镍、铜等重金属的酸洗废液,并向上游企业收取处置费用人民币1240余万元。[1]对于收购的2.4万余吨酸洗废液只进行简单处理、0.6万余吨酸洗废液未作任何处理,在均未去除重金属的情况下,打着“净水剂”的幌子非法销售给20多家印染企业,致使无重金属去除及监测能力的印染企业在误以为符合污水排放标准的情况下,将酸洗废液中的重金属附随废水、污泥排放至外环境。经检测,上述“净水剂”和钢铁酸洗废液中重金属镉、锰、镍、铜均有项目超过国家排放标准三至十倍以上。
二、分歧意见
在本案办理中,沈某、杨某对将回收的酸洗废液未经处理作为“净水剂”销售给下游印染企业的基本事实并无异议,但在该行为的定性及含重金属污染物浓度认定方面存在较大争议。
(一)未直接与外环境关联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污染环境
有意见认为,下游印染企业系排放含重金属污染物的直接责任方,A公司销售未经处理酸洗废液的行为并未与外环境产生直接关联,A公司没有违规排放行为,将酸洗废液销售给下游企业用于印染废水处理亦不属于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不应认定与造成的环境污染相关,因此,沈某、杨某不构成污染环境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A公司是将未经处置的酸洗废液作为产品销售给印染企业,在这个过程中A公司虽未直接将含重金属的酸洗废液排放入自然环境,但由于印染企业不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处理重金属的工艺和能力,在此情形下致使含重金属污染物附随废水、污泥进入水、土壤中,造成环境污染,其实质是A公司利用下游印染企业不需要对重金属进行检测的漏洞,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沈某、杨某构成污染环境罪。
(二)重金属污染物浓度能否适用刑事推定原则
有意见认为,由于本案中含重金属污染物混合在其他物质中,经充分稀释后最终与外环境物质融合,难以科学、准确检测污染物含量,根据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应采用较低的重金属污染物浓度作为定罪标准,即采用案发后下游印染企业排污口取样检测的污水中含重金属浓度作为入罪标准。
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下游印染企业无针对重金属进行特定处理的工艺,故酸洗废液中重金属成分不会减少或去除,所以提取的钢铁企业酸洗废液重金属浓度应视为进入环境的污染物浓度。
三、评析意见
上述分歧意见中,笔者认为沈某、杨某利用A公司销售含重金属的酸洗废液给下游印染企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构成污染环境罪,该行为与直接排放危险废物至外环境具有相当性。根据含重金属废液由钢铁企业到A公司再到下游印染企业的传导关系,可以将钢铁企业提取的样本中重金属含量视为进入环境的污染物浓度。以下围绕认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和污染后果的认定两方面展开分析。
(一)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的认定
1.超过国家标准含重金属废水系有毒物质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含重金属的污染物”系刑法第338条明确的“有毒物质”之一。但由于法律允许在规定标准范围内排放污染物,基于此,对于“有毒物质”须从实质上加以把握。[2]其原因在于重金属不能被生物降解或自行净化,故含有重金属的废水排入水体或土壤,不仅会直接污染水体及土壤本身,造成环境质量的严重恶化,还会在生态系统中存留、积累和迁移,最终通过食物链在末端的人体中富集,危害人类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在本案中,上游钢铁企业产生的废酸经检测均具有重金属成分且浓度超过国家标准,并附随下游印染企业废水排放。重金属污染物所具有的毒害性及不可降解性,决定了该类危险废物在自然环境中具有高危性和持久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亦将金属表面处理加工后留存有重金属的废水规定为危险废物,并对此类危险废物的处理提出了差异化处置要求。因此,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有毒物质”具有严重危害性。
2.非法处置行为的内涵外延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31条第(四)项对“处置”作了明确解释,是指“将危险废物焚烧、煅烧、熔融、烧结、裂解、中和、消毒、蒸馏、萃取、沉淀、过滤、拆解以及用其他改变危险废物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危险废物数量、缩小危险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所或者设施并不再回取的活动”。
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是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构罪行为方式之一,其与非法排放、倾倒处于并列地位,但其相对于排放、倾倒而言具有兜底性质。在“两高三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中关于非法处置行为的认定明确提到,对名为利用实为处置的行为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因此,非法处置行为并非依其外在表现形式不同而区分,而是根据非法处置行为对环境法益造成的实害程度进行認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0条、《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15条均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处置的经营活动。该规定是基于危险废物具有的腐蚀性、毒性等特点,经营危险废物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工艺、技术、场所、设备和应急措施,以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故而,合法处置危险废物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具有经营许可证;第二,在经营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第三,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制度开展经营活动;第四,无论是出于以利用为名义的处置还是贮存等目的,均不得向未持有经营许可的单位提供危险废物。
A公司的具体行为表现为:其一,明知不得回收含重金属的废酸而回收,在未去除重金属的情况下作为原料加工成“净水剂”销售给多个印染企业;其二,明知不应向未获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提供危险废物,而把回收的含重金属废酸假冒“净水剂”,非法提供给多个印染企业,致使下游企业将购买的假冒“净水剂”与印染废水混合,稀释重金属浓度后排放,导致重金属随废水排入环境。
3.外环境的认定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对不同种类污染物的取样点及排放标准作了明确规定:如含第一类污染物的污水,不分行业和污染排放方式,也不分受纳水体的功能类别,一律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含第二类污染物的污水,在排污单位排放口采样。《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 37条规定,外环境是指污染物排入的自然环境。在办理污染环境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照排入外环境的直接取样结果来认定是否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
本案中,A公司虽未将含重金属的酸洗废液直接排放入自然环境,而是作为产品销售给印染企业,但A公司的行为目的在于借助不需对印染企业污水中重金属进行监测的漏洞,逃避环境监管,违法排放污染物。因此,A公司的重金属污染物销售行为危害性与直接排放到外环境具有相当性。
综上所述,以是否与外环境直接关联作为判断能否构成污染环境罪有失偏颇,在司法实务中应当根据行为目的、行为方式、主观明知等方面作出实质化判断,第一种意见中仅根据印染企业与外环境直接相关性否定A公司对环境造成污染属于形式判断。需求净水剂的下游印染企业系基于A公司提供的是合格净水剂而使用,其主要需求成份为酸性化合物,对购买的净水剂中含有重金属成分并不知情,故其废水处理工艺无针对重金属的特殊措施,即使在处理过程中能吸附部分重金属,亦无法避免重金属排入外环境。因此,下游印染企业虽为导致污染物排放至外环境的直接方,但对于排放含重金属污染物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沈某、杨某的行为实质是借印染企业这一渠道排放危险废物,其将去除“有毒物质”重金属的责任寄希望于不知情且无处置工艺的下游企业,主观上有转嫁风险、放任发生环境污染后果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借通道排放有毒的危险废物的行为,虽为间接方,但正是因为A公司非法提供的废酸内未能减少或消除废酸中的重金属,最终造成环境污染,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
其次,第一种意见中关于非法处置的认定存在一定错误。销售净水剂行为本属于正常市场经营行为,但在此过程中以未经处理的酸洗废液直接作为净水剂进行销售属于明知故犯。A公司在此过程中充当了“中转仓”的作用,应根据其行为对环境的实害性认定为非法处置。
(二)污染后果认定适用刑事推定原则
1.刑事推定原则在实务中的作用
刑法中推定是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然后根据客观事物之间联系的规律推导出另一事实的存在。[4]其基本逻辑为由基础事实至待证事实,即推定成立的前提为控方通过证据充分证明基础事实,再根据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间的密切联系来认定二者之间的演绎推定过程。刑事推定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其一,基础事实部分有充足证据予以证实,此为推定成立的必要条件;其二,待证事实部分难以通过证据直接证明,而是存在诸多间接具有盖然效力证据;其三,基础事实部分与待证事实部分之间具有常态联系,二者之间具有正向推导关系。[5]
在适用刑事推定的情况下,并非是对涉案人员权利的剥夺,辩方仅负担对污染物来源反驳的举证责任。刑事推定并非是一种“类推解释”,其推定目的是减少诉讼成本,增强诉讼效率,并确保社会法律秩序的稳固性。故刑事推定原则在司法实务中具有积极意义。
2.重金属浓度推定具有合理性
2016年颁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条明确规定了镉、铬、镍等重金属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但在本案中,由于相关污染物系经充分稀释后最终与外环境融合,难以科学、准确地检测出污染物的含量。遂需要利用污染物传导过程中的同向相关关系,根据基础事实并通过正常生活经验及表现形式进行推定事实的证明。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中规定印染企业排放标准中重金属仅涉及到锑,并非强调没有相关规定的重金属指标可以排放,而是正常印染工艺中不可能出现其他重金属。印染行业工艺中需要长期使用强碱腐蚀织物表面的化学物质,因此其废水无法直接排放,需要用酸性化学物质进行中和处理。钢铁企业使用酸性化学物质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皮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业惯例,但酸洗废液中重金属离子极易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因而,钢铁企业产出的酸洗废液必须经过特殊工艺进行处理。A公司制作水处理剂的的工艺流程中仅对酸洗废液添加催化剂,该工艺并不能去除酸洗废中的重金属,即由于缺少重金属分离过程,造成酸洗废液中的重金属转入A公司出厂的水处理剂产品中。故此,重金属污染物的传导具有明确链条,印染企业排放污水中重金属来源可以溯源至钢铁企业酸洗废液。第一种意见中以印染企业的排放口作为检测依据的基础即来源于此。
但是,一方面,由于印染企业生产过程中并不产生重金属,环保监管机构缺少在长达四年时间内印染企业排放污水中镉、铬、镍等重金属污染排放监测记录,事后对印染企业污水进行取样分析丧失时效性,所作出的检测报告是否具有证明力亦存疑;另一方面,印染属于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其排放污水中绝大部分为正常生产用水,仅使用少部分“净水剂”用于酸碱中和,酸碱中和反应过程中也会产生水等物质,进而致使在印染企业排放口污水取样中重金属含量明显偏低。因此,印染企业排污检测结果不宜用于认定重金属污染损害后果,第一种意见中就轻认定存在明显事实认定错误。
在本案中,将构成环境污染犯罪的起始时间提前至酸洗废液脱离上游企业管控之时,将缺乏处理技术的工业流程中一类污染物在车间或排放口的采样浓度视同为进入环境的污染物浓度,这一做法成为了适用刑事推定原则的必选项。其一,本案基础事实明确。经调查,上游钢铁企业用于处理去除金属氧化皮的制造工艺无技术更新,原料未发生改变,其产生的酸洗废液虽受不同批次钢材的影响,但废液中重金属种类基本保持稳定,重金属物质浓度亦在合理区间内。其二,推定以钢铁企业酸洗废液重金屬浓度作为认定标准是基于整个链条中稳定的或者必然的传导关系。A公司从上游钢铁企业收购的酸洗废液中含有重金属,在生产水处理剂的流程中无去除重金属的工艺,下游印染企业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添加重金属。因此,从整个重金属污染物传导链条中不难看出,下游印染企业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完全来自于上游钢铁企业出厂酸洗废液,无异常介入因素。其三,涉案人员的主观明知实际产生于收购酸洗废液过程中,换言之,在长期的买入卖出酸洗废液市场行为中,涉案人员对酸液废液的传导流程及重金属污染物浓度心知肚明,相关人员在明知企业不具备重金属去除工艺情况下,仍收购酸洗废液并对相关重金属污染物去向有了明确的规划,其目的就是为了出售给下游印染企业谋取不当利益,即使早已知道出售的酸洗废液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基于此,本案重金属污染物浓度应以产废酸单位处提取的样本中重金属含量进行认定。
最终,该推定方式得到一审判决、终审裁定的支持。本案经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沈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0万元;判处杨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800余万元。
*本文为2023年度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基层检察机关重复信访案件实质性化解研究”(SJ202324)的阶段性成果。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二级检察官[215600]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215600]
[1] 案涉钢铁企业在选择危险废物处理企业时已核实 A公司具有环境保护局(2018年4月起变更为生态环境局)发放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括处置废酸(许可处置类别HW34,代码涵盖313-001-34等)。
[2] 参见喻海松:《污染环境罪若干争议问题之厘清》,《法律适用》2017年第23期。
[3] 参见《两高三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1902/t20190220_40857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2月5日。
[4] 参见何家弘:《论司法证明中的推定》,《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5] 参见窦璐:《刑事推定辨正》,《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