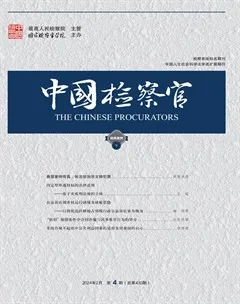行为人购销走私货物行为辨析
沈娟 季军 金兰
一、基本案情
陈某甲在国外经营冻品生意,陈某乙在国内辅助负责接货、卖货等。2022年2月,陈某乙在走私货物入境后,联系了长期从事冻品生意的被告人张某,询问其是否需要冻品鸭爪,并告知张某冻品正在山东某公司更换国产包装。被告人张某赶至换包公司现场,看到工人将走私货物换成国产包装。换包完成后,被告人张某以每吨43000元的价格,购得走私冻鸭爪14.35吨,支付货款人民币617000元,并联系物流车辆将货物发往湖南分销给他人。本案中,在货物运至湖南后,张某在得知冷库有检查的情况下,曾将走私的冻品鸭爪暂缓入库。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张某的犯罪事实较为明确,但办案机关在罪名认定方面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应认定构成走私罪。在案证据显示,张某在明知陈某乙所称的冻品系走私的情况下,购买了已换成国产包装的冻品,并实施了分销行为,应当按照走私罪定罪处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应认定构成洗钱罪。虽然张某明知是走私货物、物品且明知实施了换包行为,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主观上明知陈某乙是直接走私人,因其购销行为实质上已经为陈某乙的走私犯罪所得和收益起到了掩饰、隐瞒的作用,因此以洗钱罪论处更为适宜。
三、评析意见
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对张某购销走私冻品的行为认定为洗钱罪更为合理。本案中,张某明知冻品是走私物品仍予以收购并分销,但对陈某乙作为走私人的身份,其主观上是否需要“明知”;如何界定走私犯罪所得及收益,走私物本身能否作为洗钱罪的犯罪对象;“掩饰、隐瞒”是否需要推定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等问题的厘清,是对张某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
(一)对“走私物”和“走私人”主观上均应明知,否则不能认定为“间接走私”
刑法第155条规定了“以走私罪论处”的几种情形,其中对于“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行为,明确依照走私犯罪定罪处罚。“以走私罪论处”,即该行为本不是走私犯罪,法律将该行为拟制为走私犯罪,理论上一般称为“间接走私”或者“准走私”,对此类行为的处理方式,当前司法解释规定的比较明确[1],旨在通过较重的刑罚来增加违法犯罪活動成本,打击走私犯罪。[2]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间接走私行为所判处的刑罚高于直接走私人判处刑罚的情况。如上述案例中,上游犯罪嫌疑人陈某乙在与他人共同犯罪活动中,主要实施了境内接货付款的行为,综合考虑其违法犯罪情形,法院认定其为从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但若将张某认定为间接走私,其不仅仅实施了购买行为,还有分销行为,依照规定,可能需要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一案件中,对间接走私犯罪判处的刑罚却高于上游犯罪的刑罚,并不合理。本文认为,对于“间接走私”行为,要精准审慎认定,才能符合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的刑法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归罪的原则,法律不强人所难,人只能对主观上认识到、预见到且意志选择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如认定行为人构成刑法第155条第(一)项规定的犯罪行为,重点需要证明行为人主观具有“明知”,既要明知其接触的对象是直接走私人,也要明知其收购的货物、物品是走私物。否则,如果只需要行为人明知收购的是走私物,不需要明知是向直接走私人购私,有可能出现具有相同收购走私物品故意的行为人,在实施了同样的购私行为的情况下,仅因上游犯罪嫌疑人是否系直接走私人的不同而导致部分行为人涉嫌洗钱罪、部分行为人涉嫌走私犯罪这一根据上线身份不同客观归罪的情况。同时,在“明知”的加持下,行为人又从对方的手中收购了相应的货物、物品等行为,即可认定行为人在意志因素方面,存在积极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心态。具体到上述案例中,张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主观上明知其收购的换了国产包装的冻品系走私物,客观上也实施了相应的购销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张某明知陈某乙为直接走私人,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不全面不充分,因此不宜认定其行为构成间接走私。
(二)走私犯罪中的走私物本身可作为犯罪所得,亦可认定为洗钱罪的犯罪对象
我国刑法多个条款明确提及违法所得,如总则第64条,分则第175条高利转贷罪、第214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及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等等。[3]在上述罪名中,违法所得数额或作为入罪门槛,或是量刑的重要依据,是区分罪与非罪以及认定罪行轻重的关键。在走私类犯罪中,刑法虽未将违法所得作为本罪定罪量刑的要件,但其作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之一,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是洗钱罪的犯罪对象,是洗钱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具体的物,精准认定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范围和金额,有助于更好地打击洗钱犯罪,更加客观公正地定罪量刑。
司法实践中,走私犯罪获得的收益当然是作为洗钱罪的犯罪对象,但走私的货物、物品本身能否作为走私犯罪所得,实践中有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走私物本身以及因走私犯罪取得一切收益均可认定为走私犯罪所得,走私物当然可以认定为洗钱罪的犯罪对象,因此收购走私物的行为有可能构成洗钱犯罪。另有观点认为,走私犯罪中,犯罪所得仅指在实施走私犯罪过程中的获益部分,走私的涉案货物应认定为走私对象,并不能作为洗钱罪的犯罪对象。[4]折中观点认为,应该根据走私犯罪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即分为涉税类走私和禁限类走私。对涉税类走私货物、物品,国家并不否认行为人对走私对象的实质权属关系,犯罪所得仅为偷逃的应缴税款。对禁止类走私的货物、物品,包括走私物本身和一切收益均为犯罪所得。对限制类进口的货物,则应根据有无许可证、是否超配额数量予以认定。[5]
本文认为,在界定走私犯罪所得及收益范围时,首要考虑的应当是洗钱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从立法进程来看,我国首次规定洗钱罪,是在1990年出台的《关于禁毒的规定》中,主要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击毒品犯罪。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洗钱罪单列,并根据司法实践,将上游犯罪扩充到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三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又进一步扩充至七类罪名,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及时切断上游犯罪的资金链,剥夺其产生的利益,减少再犯可能性,进一步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犯罪所得资金跨境转移更为便捷,我们在打击犯罪时有可能需要开展境外追逃追赃,而跨境追赃存在的最大阻力是各国对上游犯罪的规定各不相同,无法协同打击犯罪。各国将洗钱入罪,则可以直接回避各国上游犯罪的差异,更好地加强赃款追缴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管理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我国刑法将七类罪名设定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不仅能够更加公正高效地惩治贪腐、毒品、走私等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金融市场管理秩序安全稳定、妨害司法机关打击犯罪活动的上游犯罪,确保法益得到更好地保护,受损的法益得到及时修复,也可以更好地承担国际义务,履行大国担当。
再者,将走私货物物品本身作为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具有现实的法律基础。如最高法、最高检、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中,将走私货物、物品的“进出口完税价格”及“实际销售价格”认定为违法所得,而上述两种价格中,均包含走私货物、物品本身价格。再如,2019年最高法、最高检、海关总署《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在定罪处罚部分,对于向非直接走私人购买走私的成品油的,根据其主观故意,以洗钱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这也可以说将走私货物、物品即成品油认定为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系与上述第24条的观点一脉相承。从上述立法目的来看,在走私犯罪中,无论是涉税货物、物品还是禁限类货物、物品都是通过违法手段入境,都属于非法的贸易活动,货物的取得本身就不合法,应被视为广义犯罪所得的一部分。
因此,本文认为,从有利于切断上游犯罪的角度来讲,对走私犯罪违法所得及收益进行必要的扩充解释是有必要的,这也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明确将违法犯罪活动中获得的任何财产规定为犯罪所得[6],这与“不让任何人从违法犯罪活动中获益”的现代法治精神和理念也是相契合的。因此,将走私的货物本身认定为犯罪所得,完全符合近年来我国以及国际反洗钱国际追逃追赃的实践。综上,如果行为人实施了向非直接走私人收购走私物的行为,依照刑法第191条之规定,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合理。
(三)对洗钱罪中的“掩饰、隐瞒”应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考量判断
较修正前,刑法第191条的主要变化在于,不再要求行为人在实施本条列举的五类行为时,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掩饰、隐瞒的对象是七类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及收益。有观点认为此种修正是否会过于扩大刑法的打击面。本文认为不需有此种担忧,因为删除“明知”,并不意味着洗钱罪的主观要件发生变化,僅仅是降低了行为人对犯罪对象的认识标准,因为“掩饰、隐瞒”本身即带有故意实施相关行为的意味。
在实践和理论界,当前对“掩饰、隐瞒”的性质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洗钱罪是目的犯,行为人为了达到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和收益来源及性质的非法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刑法第191条列举的五类“洗钱”行为。在目的犯中,犯罪目的并不属于犯罪故意和过失的组成部分,其和罪过是并列关系,均属于犯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另有观点认为,洗钱罪是行为犯,“掩饰、隐瞒”并不属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范畴,而是客观方面的关键要素,即客观行为,洗钱犯罪中的五类洗钱行为,实则是“掩饰、隐瞒”的具体行为方式,即客观行为要素。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具有可取之处,实际操作中,应当注重吸收不同观点中的合理之处,做到有机融合,灵活运用。具体而言,在罪过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对洗钱罪上游犯罪所得和收益进行掩饰、隐瞒的故意。一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其实施的掩饰、隐瞒行为会侵害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等法益。同时,还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掩饰、隐瞒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使得上游犯罪中获取的非法财产的来源及性质发生了变化,造成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混乱,导致司法机关无法追踪赃款去向,无法对其进行追缴。须确保主客观相一致,否则不能认定构成洗钱犯罪。
同时,在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洗钱罪时,还要综合考量行为人的生活、工作、违法犯罪等经历,结合案件实际,对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方式,即对掩饰、隐瞒的行为属性进行客观公正地判断。在办案实践中,行为人往往会辩解,其在交易时,并没有关心和过问交易货品、物品的来源,其并不知道其购销物品是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属于掩饰、隐瞒行为,而是正常贸易。面对此种辩解,则需要办案人员借助客观事实予以综合判断,即利用刑事推定予以认定。具体到张某洗钱案中,经审查发现,张某自2013年学习冻品批发生意,2017年左右独立从事冷冻鸭爪批发生意至案发,从事冻品生意达十年之久,应当知道从事冻品供应需要相关检验检疫手续等。且张某在从陈某乙处购进冻品之前,就已经听陈某乙说,并在现场看到了走私冻品“变身”的过程。此外,张某还因担心走私冻品被查处,存在暂缓将冻品入库的行为。因此,上述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张某对于其从陈某乙处购进的货物系走私货物是明确知晓的,其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走私犯罪所得的故意。
(四)走私犯罪与关联犯罪发生法条竞合时应结合案件实际客观公正处断
广义的反洗钱包括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规定的三类罪名。从刑法条文来看,上述罪名存有一定差异。一是罪名上的差异。刑法第191条掩饰隐瞒的对象仅包括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和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而第312条掩饰、隐瞒的对象更为广泛,可以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洗钱罪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刑法第349条掩饰、隐瞒的对象仅为毒品、毒赃,范围更窄。二是内容上的差异。刑法第191条和第312条既包括为自己实施的犯罪所得和收益进行掩饰、隐瞒,又可以是协助他人掩饰、隐瞒赃款赃物。而第349条,从文义理解,多指为他人实施涉毒犯罪提供窝藏、转移、隐瞒等行为。
因此,针对法条之间的差异,在办理刑法第191条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案件中,需要准确处理上述法条之间的竞合问题,以此更加精准高效地打击犯罪。实践中,建议按照如下原则进行:一是特别条款先于普通条款。行为人实施了七种上游犯罪后,为了逃避司法机关打击,又自行实施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按照“自洗钱”行为定罪处罚。同时,对他人实施的上游犯罪,实施了掩饰和隐瞒行为的,一般情况也是按照刑法第191条定罪处罚。二是重法优于轻法。如果按照刑法第191条定罪处罚的结果畸轻,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未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则应当适用刑法第312条或者第349条处罚较重的条款,确保量刑的衡平。
此外,从刑法相关条文中可以看出,洗钱罪强调的是要发生“化学反应”,通过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和来源,将不法合法化。而刑法第312条和第349条规定中,窝藏、转移、隐瞒等行为,更多是针对赃款、赃物本身的一种“物理反应”。因此,在法条适用过程中,对掩饰、隐瞒的目的也要予以重点关注。上述案例中,张某主观上明知是走私的犯罪所得,也明知陈某乙通过換包装方式将走私货物合法化,仍然通过购买和分销的方式,协助陈某乙将走私货物销售转换为现金,将上游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披上合法外衣,以逃避法律追究和制裁。对张某的行为,应认定构成洗钱犯罪。
本案经一审法院审理,以张某犯洗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并处相应罚金;责令张某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级检察官[224000]
**江苏省盐城市大中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级检察官[224005]
***江苏省盐城市大中地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224005]
[1] 《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货物、物品,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或者没有合法证明,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走私货物、物品的种类,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 参见曹芬芳、宋典:《间接走私法律适用的困境与出路》,《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24卷。
[3] 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此条文旨在明确没收、追缴财产的范围。分则中涉及“违法所得”的罪名除了正文中列举的罪名,还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经营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对单位行贿罪等。
[4] 参见王键波、宋思佳、徐邦国:《涉走私案件洗钱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探析》,《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22期。
[5] 参见周国良、须璐、田娟、王林生:《“走私洗钱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研讨观点综述》,《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22期。
[6]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一章第2条第(五)项规定,“犯罪所得”系指通过实施犯罪而直接或间接产生或者获得的任何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