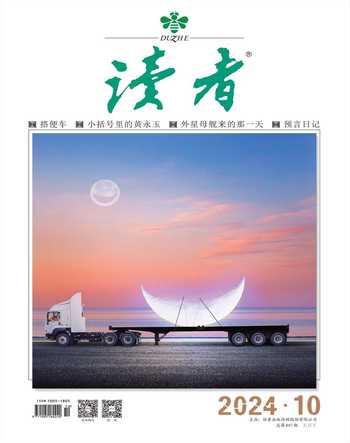小括号里的黄永玉
李斐然

黄永玉去世前立了规矩,不办纪念活动。按他生前经常提到的方法,想他的时候就“看看云,看看天”。后来我发现,即便不看云和天,我依然会在一些瞬间想起他。北京有条街上的字画店他经常去,晚年他到这里看画,围了一圈的相机和话筒,主持人请他说两句寒暄的客套话,他诚恳地解释自己的为难:“你不如让我现场给你打个滚儿,这事我还好办些。”
他的身上有一种不受限制、自由生长的力量:文章还可以这样写,画还可以这样画,日子还可以这样过。他有一部写了很多年的作品,《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面最让我难忘的地方是小括号。你很难见到一位作家写文章,小括号里的内容有时候比正文还长。
黄永玉的小括号里装着五花八门的事,有时候是注释,有时候是感慨。写到汪曾祺,他在小括号里反问自己,去台湾采风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上汪曾祺同行呢?写跟父亲一起上车放行李,小括号里是惆怅,多年后才知道,那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朋友去世了,他伤心,这件事虽跟他写的正文搭不上边,但他不管,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放在小括号里,还搁在正文前面。还有一次,正文写到了小时候养的狗,小括号里是87岁的黄永玉跟它道歉,自己竟然花了80年才回想起儿时场景,醒悟过来那时候生了崽儿的哈巴狗为什么不理睬他,他跟哈巴狗约定,在天上找个地方再详谈吧。
好多时候,小括号里的内容跟上下文完全挂不上逻辑联系。他有一个说法叫作“猴子捡到姜”,吃下去辣嘴,扔了又舍不得,天天搁手里难受。好几次的小括号一上来就跟读者告白,请原谅他接下来要写一段往事,有点儿意思,却又说不上什么意义,没有正经到要跟谁汇报,但不说出来,总觉得这世上又少了点趣儿,这不知道往哪里搁的一块姜,姑且放在读者诸君这儿啦。
读他的文章久了,我开始习惯了这些冷不丁冒出来的小括号,有时候还很期待它们跳出来,从讲历史的正文里出来打个岔,就好像遇到一个突然敲门拜访的老朋友,来做做客,聊聊天。大概全世界的中文系都没人这么教写作,以前没人这样写,以后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我想起第一次跟黄永玉吃饭,他突然停下筷子问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面一个“因为……所以……”“虽然……但是……”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得意,像是在坚持某种纪录。他说,这些是白话文运动后的规矩,他不信这个。这是一个只有活过百年的人才能注意到的差别。后来我读他喜欢的《世说新语》,读《诗经》时,也会常常想起他的这句话。汉字曾经是以自己的法则存在的,它有过更精练的模样,起承转合也不是非得用助词才能实现的,字与字、句与句之间的分界,曾经有过不同的重量。原来即便是文字本身,也能活出另一种面貌,选择不一样的生存方式。
所以,我不只是在看到云和天的时候想到黄永玉,路边肆意开放的花,硬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绿芽,颜料盒里最亮的颜色,开水煮到沸腾时自由跃起的气泡,所有不设边界的活法,都会让我想起这个老头儿。可能就是因为他这种蓬勃的生命力,让我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常常忘记他的高龄。谁能相信,这么鲜活的人居然出生于100年前。现在他不在了,这个年纪倒成了一种提醒,人生百年,这样活也没问题。活在规规矩矩的正文里是一条路,活在小括号里的黄永玉,也得了将近100年的自在。
(如 是摘自《人物》2024年第2期,黄永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