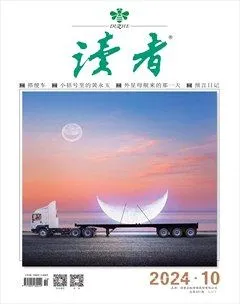看电影
王祥夫

我常想,看电影其实是可以写一篇大文章的。
我知道,几乎所有人都不讨厌看电影,而且还喜欢看。鲁迅在他的日记里就记过不少看电影的事,并且记下都和谁一道去看,看的又是什么片子。我小时候看电影,是毫无挑选,什么片子都看,只要是手里有了电影票就必去看。我记得一次我和姐姐两个人去看一场夜场电影,回来晚了,天那么黑,路也那么黑,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我和姐姐从西门外过来,往我们的院子里走的时候,扑面便是那古老的城墙,城墙下护城河边的树影也都黑洞洞的,因为我们的院子就在护城河边。那样的晚上,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周围就是城墙、树影,以及夜晚浮动着的似烟非烟的雾气。那时候,我们的院子外还有庄稼地,这就是当时中国城乡接合部的特色,绝无田园的风情,更没有蛙鸣虫吟。那晚上的庄稼地,着实有点吓人。
电影的魅力真是很大。小时候,总是和几个小伙伴想着怎么翻过电影院东边的那堵墙,溜进去偷偷看一场电影,从东墙翻进去就是电影院的厕所,从厕所再进到电影院里是没人会怀疑的。但想归想,那么高的墙却让人不敢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电影院的外面等,等着有什么人看到一半不想看了出来的时候,跟他要他手里的票,有了那张票,是可以进到里边接着看下半场的。印象中,总有人看到一半就不再看了。这时候便会有人一拥而上去讨他的票。
这时候,电影院外边卖香烟和瓜子的小贩还在,还有卖汽水的小贩。有汽水瓶被打开的声音,“气”的一声,又“气”的一声——是一男一女,在那里喝汽水,他们互相看着,忽然笑了起来。喇叭裤其实顶难看,但那男的就穿着一条喇叭裤。喝完汽水,他们又相拥着一起进去了。电影院外边的灯光下,有人蹲在那里看小人书,两分钱看一本,随便挑。华三川的《白毛女》和贺友直的《山乡巨变》被翻得乱糟糟的,但还是有人看。有一只猫,蹲在小人书摊子旁边,身子一转,两眼顿时如两盏小灯。
小时候总期待大院里放电影,那是大公司给员工的福利。放电影的消息是早早就传开的,人们早早去占位,老头老太太搬着小板凳,他们会把最好的位置都占了,并且会一下子搬好几个板凳,给家人也把位置占好了。电影快开始的时候天已黄昏,老头老太太们虽老眼昏花,也还是看得清自己的家人,但他们唯恐家人看不到他们的所在,不免站起来急切地大呼小叫,挥胳膊招手。这场景是时代性的,现在想想都让人欲流泪。那时候,我们住的大杂院是工程公司的大院,很大的院子,东边四排房,西边六排房,中间便空出来一个很大的院子,电影幕布就挂在院子中央的两根杆子上。那时候,我们看电影的一大乐趣是到幕布的背面去看。这么一来呢,一切看在眼里的场景都是反的——而在这个人间,你看到的东西何曾都是正的?
直到现在,我都喜欢看电影。有时候去电影院买张票,一个人进去,嗡然的电影院气息便马上在周遭响起——其实亦不是响起,只是自己感觉到了。电影里人物的道白毕竟和电视剧里的不一样,在我,亦是一种享受。有时候亦不是为看那电影,只是想体会一下那种多少有点惆怅夹杂在里边的快乐。灯黑了,电影即刻开始,儿时的那种感觉纷至沓来。有时候,我会看着看着就睡了过去,但亦不是睡,而是在心里还醒着,蒙眬之中只觉是一种享受。
人不知为什么偏偏要长大?长大又有什么好?电影院的好,就是好在你一进去,那氛围,那声音——那空阔而又实在的声音,会把你马上再次孵回到童年里去,如果你是一只卵的话。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只卵,一只卵……
(崎 峰摘自《文化艺术报》2024年3月6日,亚 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