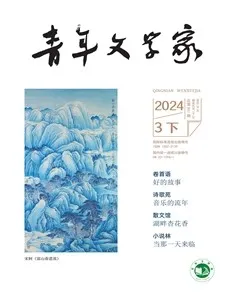论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范贺贺
郑敏自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开始写诗,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找到诗歌的写作源泉,她创作出了许多别有意味的诗歌,可谓诗坛的一棵“世纪之树”。她以奇妙的联想、辩证的思维使意象超越具体时空,凝结出永恒的意义,为20世纪40年代的诗坛增添了一股新鲜之气,而郑敏独特的女性意识,也为其诗思合一提供了鲜活的力量。分析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观照郑敏诗歌魅力的线索。
一、女性个体的审视
女性意识涉及女性的性别意识、自我意识以及对社会实践的主体意识。从不同角度来看,诗人作为女性个体,因性别差异而产生的爱情观念,对自我生存状态的认知,对时代社会的责任承担,都隐含着女性的心声。通过分析郑敏的诗歌,可以审视她的个体女性意识。
(一)对爱情观念的思索叩问
从某种意义上讲,郑敏的诗歌始于对爱情的追问,她在早期爱情诗里直率地追求相爱双方之间的心灵默契。20世纪20年代,以冰心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关于爱情的书写还尚显朦胧,“爱”是女性诗歌的禁果;20世纪30年代的林徽因则写满了内心对“爱”的矛盾与渴求;而在郑敏这里,“爱”上升为对心灵共鸣的追寻,强调精神、灵魂的沟通,而非表面的爱欲。
郑敏在《晚会》中写道:“我不愿举手敲门……如若你坐在灯下/听见门外宁静的呼吸……无声推开大门/你找见我。等在你的门边。”“我”希望对方能在自己不敲门的情况下,在两人无声的心灵交际中达到情感的交流,除了“宁静的呼吸”之外,再没有媒介能沟通双方的心灵,完全是两颗充满着企盼与思念的心灵的共鸣。《怅怅》里“为什么你只招着手儿微笑呢/原来一个岸上,一个船里/那船慢慢朝着/那边有阳光的水上开去了”,通过对“你”的疑问,写出两性之爱的经验差异,岸是静止的,也意味着人的原地停滞,而船是流动的,是可以前进、追求的象征,岸与船的分离带有爱情的孤独感,隐含女性对爱情无法同步的怅惘,但船是向着光明而去的,这怅惘又减轻了几分。《永久的爱》中写道:“那清晰的头和美丽的肩/坚固开始溶解,退入/泛滥着的朦胧/……/那在一切苦痛中/滑过的片刻,它却孕有/那永远的默契。”在这里,美丽少女的身影从坚固变得朦胧,消解了爱情的永恒稳定性,但在这片刻的时间中,隐含永远的默契,消逝的时间获得了凝定的意义。郑敏质疑“永久的爱”,认为正是在“片刻”中爱才获得了永久性,爱情在现代时间里呈现出漂浮感和隔离感。由此,郑敏就从传统的在两性交往中寻找爱情转变为在时间构成中感受爱情,显示出女性经验下的独特时间尺度。
(二)对生存状态的独特体悟
20世纪40年代的动荡,前所未有地制造出历史的非秩序状态,在感时忧国的焦虑中,郑敏从生存空隙里获得了一个审视女性主体成长的际遇。她在其中发现时代带给女性的一种自由姿态,但也敏锐地感受到女性生存状态的寂寞、孤独与痛苦。
郑敏在《秘密》中这样写道:“天空好像一条解冻的冰河/……/在这扇窗前猛地卻献出一角蓝天/……/一切,从混沌的合声里终于伸长出一句乐句。”其描述了在沉默已久的时代里,女性突然得到时代所“献出”的一角“蓝天”,得到些许自由的生存空间,表现出异常惊喜的反应。《黎明的到来》中写道:“这被每一个闭着眼睛的女人意识着/她们在醒了的梦里意识到黎明的走近/风,雨,和正在长大的光明。”女性从闭着眼睛到意识到黎明,显示出女性主体对自我束缚的一种突破。诗歌无法掩饰地指出“自我”的出场。《寂寞》中的“我的眼睛/好像在淡夜里睁开/……/我的耳朵/好像突然醒来/听见黄昏时一切”,从时代献出蓝天,到闭着眼睛意识到现在的睁开眼睛,女性主体面对世界,开始听见外界,这是个体生命的世界位置的发现,呈现出女性自我的存在体验。从童年到青年,诗人的生存状态一直是寂寞的,但诗人终于认识到这痛苦体验有着最严肃的意义,“我也将在‘寂寞的咬啮里/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寂寞》)。这是女性对时代的理性认识和对自我的深刻把握。在这里,寂寞是一种自足状态,不同于个人的孤独感,而是社会集体活动中心灵独立的超脱,对寂寞的咀嚼可以找到存在的价值,也就找到了自我生命在心灵隔膜状态中的积极意义。
(三)对时代使命的自觉承担
由于时代的动荡,大部分女性诗人放弃了个体深层体验的开掘,而卷入了集体性主流话语之中,即诗人主体必须在时代主流话语中才能得以确立,而郑敏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她在感悟个体生存状态的过程中揭示了女性自我的历史上场与时代的关系,进一步言说女性作为社会人对时代的自觉投入,带着独特的女性思维感知世界,承受起时代这“严肃的负担”。
郑敏在《荷花》中写道:“这弯着的/一枝荷梗/……/却因为它从创造者的/手里承受了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如果将荷花看作女性的外化意象,那么在这里诗人歌颂了荷花对生的承担,实际上就是对女性承担苦痛的赞美,将女性被生活压弯的脊背视为女性对时代使命的认领,言说了女性在时代中的地位。《池塘》中写道:“女孩子蹲在杵石上要想/洗去旧衣上的垢污/理性的人们在会议的桌上/要洗净人性里的垢污。”两个事件排列放置,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女性的日常家务置于时代的更高地位审视,与上诗荷花弯着的荷梗有相似之处。《Renoir少女的画像》中写道:“追寻你的人,都从那半垂的眼睛走入你的深处/……/瞧,一个灵魂先怎样紧紧地把自己闭锁/而后才向世界展开。她苦苦地默思和聚炼自己/为了就将向一片充满了取予的爱的天地走去。”在对少女的思索中,诗人联想到自己,用独特的女性经验将笔下的少女由静态“复活”为动态的个体。可以说,这首诗就是诗人的自画像,她让少女走向爱的天地,也祝福自己投身时代的洪流,用个体灵魂的沉思锻炼提升自我对时代的承担能力。《小漆匠》里一方面小孩为别人的世界涂下色彩,但阳光却不曾温暖他的世界,这是一个悖论,“我”赞美小漆匠的奉献,却又为他们的无知天真而痛苦,通过对“永恒的手”创造者是否为小漆匠带来幸福的质疑,表达出“我”抒情女性对现实的批判。而“增加了我的痛楚”,这是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痛楚,通过对普通人的平视,显示出对自我与时代的反思。
二、母性思维的呈现
郑敏认为:“女性最伟大的特点是母性,女性诗歌要尽可能地展示女性的母性景观。”(《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当诗歌从单一个体的审视升华为群体观照时,就从局限的个人小天地跳出,视野投向整个世界,而女性意识就体现为更为广博的母性思维。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郑敏在诗歌中展示的母性景观以及其中蕴含的生活哲思,加深了女性诗歌诗情哲理化的思想深度。
(一)对母亲形象的价值肯定
郑敏在个体女性观察之外,关注到母亲这一女性群体。母爱有时是带有奴性、压迫性质的旧式妇女美德,而郑敏在诗歌中不断出现母亲意象,以及与之相对的“婴儿”这一暗含母亲的词语,将母爱升华为永恒的思想,肯定了母亲形象的价值,为以博爱的母性思维观察世界奠定了基础。
其代表作《金黄的稻束》提升了母亲的形象。诗人从近处稻束地站立,“想起”“看见”母亲,通过抒情个体“我”的联想认识到母亲的疲倦,割过的稻束,皱了的脸,其实是双方相似的付出,母亲的脸虽“皱”但“美丽”,这一矛盾的用语写出了母亲奉献的伟大。这里稻束用来比喻母亲,但远距离的观察后,母亲与稻束融为了一体,难分彼此,她们同样的伟大,肩荷着同样的疲倦。而稻束作为食物,对人类文明的意义是永恒的,女性的意义却在男性附庸、男女平等、“要女性不要母性”的过程中变换,对不变的稻束与变的女性进行统一,就展现出母亲这一女性形象永恒的母爱价值。因而,在她们身上凝固的伟大孕育能力和无私奉献精神,就有了沉思的雕塑式的意蕴。恒长的历史在对比下,也消解了线性时间的宏大意义,变得渺小,让位于人类生命的思想凝聚,这种辩证思考实现了诗人所追求的哲理与诗歌的融合。《时间》中的“对于东方和西方/时间是无私的母亲”,这里直接将时间等同于母亲,再一次显示出郑敏独特的时间经验,在彰显时间的平等之时也衬托出母亲的无私宽容,将东西方内化为两个婴儿,母亲的形象在此已经有了更广阔的母性意义。
(二)对生命之树的情感投射
树在自然中是生命力的一个象征,春去秋来万物复苏,树木孕育着新芽,犹如母亲孕育婴孩,将宽容的母爱投射到自然之中。由此,树成为郑敏思想知觉化的客观对应物,承载着诗人的丰富情感。从稻束到母亲,再到树,物性与人性的相互转换,是郑敏情感视野的不断变换,彰显着她以更开阔的母性思维对世间生命的平等思考。
起初,郑敏并未真正从“树”上发现生命的真谛。《秘密》里写道:“一棵不落叶的高树,在它的尖顶上/冗长的冬天的忧郁如一只正举起翅膀的鸟。”树是冬天里不落叶的存在,是一种忧郁的黑暗物。诗人希望的是Fantasia里“我是一个无阻的/伸开的树林拥抱了/整个向着我的美丽的天”,期待从“古怪的森林”里走出。当她从博爱的母性中得到启示后,她开始将这种情感投射于满含生命力的树木,使诗歌拥有天人合一的内在气质。《树》中写道:“当春天来到时/它的每一只强壮的手臂里/埋藏着千百个啼扰的婴儿。”树木孕育新生,但树又像“失去民族自由的人民”,在蛰伏中等待着希望的到来。“在它的胸怀里小鸟来去/而它永远那么祈祷,沉思/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正是民族沉稳坚定的象征,包含着一个伟大的慈悲胸怀。《求知》中写道:“你来,为了完成这个世界,用人的树增加它的美。”树是希望的旗帜,是人的代表物,是慈母般的奉献,为世界装点着生命的壮美。
(三)哲学目光下的母性悲悯
当以一个母亲的姿态观察世界时,会不自觉地带有母性思维,超越一般对子女的母爱呵护,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的博爱与悲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传统的性别对立视野,从超性别意识层面关注生命。郑敏从这种更为自由的母性思维出发,用独特的哲学目光,传达出对时事的悲悯情怀。
郑敏在《旱》中写道:“荒废了的土地上,人们/已经没有彼此要说的话/……/在人类心里有一种/母亲的痛苦和恐怖/当她听见大地无声的啼哭。”诗歌对旱灾做了描绘,在灾难面前,土地荒废,人们彼此失语,希望寄托于雨,人们心里母亲的恐怖实际上是大地母亲的痛哭,但用“她”来人格化,大地“无声”又照应人们的失语,旱灾可以喻指人们内心对某种观念的呼唤,用母性思维关注普遍的人民心理,已经有了一种人与自然共通的饥渴。《战争的希望》中写道:“回到同一个母性的慈怀/再一次变成纯洁幼稚的小孩。”此诗在经过三个听觉意象的转变对比后,从现实的战争上升到思考超验世界的战争,当生命死亡之后双方士兵才能摆脱生前各种意识形态叠加的身份定位,回到诞生之初纯洁无知的状态,从而在同一个自然母亲的怀抱中相亲相爱。“哲学的眼光,使诗人超越时代和现实,产生强烈的反战意识;而圣母的情怀,则把这种反战意识提升到人类之爱的高度。”(郑景华《哲人目光和母性慈怀—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的独特性》)由此,《金黄的稻束》中母亲形象在哲学层面上升为永恒的母爱价值,到这首诗就从母爱上升为更悲悯的全人类之爱,是哲學目光与母性思维的又一次结合,完全可以看出郑敏在诗歌中所展现的对人民和时代的理性思辨。《最后的晚祷》中的“同一块土地孕育了慈悲,又孕育了仇恨,孕育了圆寂/又孕育斗争”,郑敏将甘地之死与耶稣之死联系在一起,指出两者共同的为人类献身的精神,她敏锐地发现了人性的复杂本质,不仅看到悲悯,也看到循环往复的爱恨交织,在矛盾思辨中透露的是她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郑敏以其独特的哲思,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中写出女性自我的复杂体验,20世纪80年代后的诗歌也接续着她独特的母性思维,在诗歌实践中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鲜、繁盛的生命世界。其思想凝聚着一个知识分子对自身、时代以及人类的责任感,超越诗人所处的特定时代,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启示着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在浮躁的社会里,我们能够在郑敏的诗歌中获得一个自由、沉思的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