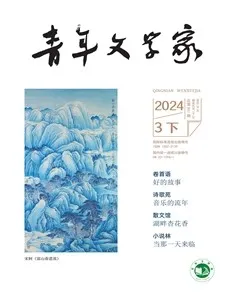南方的春天
熊佳林
惊觉春天的到来,是骑单车路过一树繁花的时候,闻到了那弥漫在空气中清新的花香。坐在车上,春天于我只是窗外的浮光掠影,但骑单车就不一样了,穿行在一树树花枝下,雨丝中飘落了一地细碎的花与叶,抬头一看,那密密的新叶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这城市里见缝插针的春天呀,它还是来了。
风铃木的春天是短暂的,它就像一场盛大的烟花,让人又惊喜又忧愁。在蓝天映衬下,一团团如火焰般肆意而浓烈的金黄的焰火,好像要把天幕点燃。没有风铃木肆意燃烧过的春天,好像一个人没有经过快意恩仇的青春,终是不完整的。它是天地间最调皮的那个精灵,不经意地来,匆匆又溜走。一不留神儿就错过了街口的黄色风铃木盛开,等我看到的时候,枝头只擎着零星几朵,那沉寂的背后,只有飘零的豆荚和新叶,好像烟花过后余下的灰烬,只能在空气里作甜蜜的回想。风铃木,多好的名字呀!曾经有多少串风铃在我们的春天里叮叮当当地摇过呢?它去了哪里呢?是不是变成街头骑着单车摇着铃铛擦肩而过的少年?曾经错过的一场又一场风铃木,会不会在以后加倍还回来呢?
木棉花的春天是孤傲的,它在高高的枝头,仰望天空吹响春天的号角。那一朵朵质地坚硬的五瓣花,像一只只对着蓝天鸣放的小喇叭。在乡下,春天是布谷鸟叫来的,那悠长婉转的布谷声,在寂静的村庄里回荡,然后才是田野一夜之间铺上了一层新绿。你能听见鸟儿的叫声,你却不曾听见城里这高架桥下、高楼大厦之间小喇叭嘟着小嘴的一声声号响。先是枝头的旧叶掉光,腾出了营地,然后光秃秃的粗枝上,绽放了第一朵,它陆续叫醒了其他的花苞,好像清晨营地里的哨兵。它们铆足了劲儿,把整个枝头都染红了,有一天你突然抬头看,才发现它远远地停在那里,轰轰烈烈的一片红云。木棉的谢幕也是刚烈的。一朵木棉花,从高高的枝头突然掉下,啪的一声,好像突然被暗地一道寒光冷剑刺中的侠客,带着几分坠入尘泥的决绝,跌倒在地,却依然保持着高傲且倔强的姿势。一朵接一朵,渐渐满地都是,长剑跌落在地,飘飘衣袂被渐渐渗透的血迹染红。分外醒目的木棉花,立在那旧日的街道,俯视着人群潮来潮往。布吉,那旧世界里的辉煌已归于沉寂,如今又旧又堵。人群也是灰蒙蒙的,与提着行李箱、塑料桶的人们擦肩而过,他们好似迁徙途中沉默的鸟。出了地铁站,路旁就停留着三三两两拉客的摩托车,他们低声地吆喝,对每一个走出地铁口的人满怀期待。摩托轻松地跨越一排排拥堵的汽车,像飞翔在水面的燕子,满满的优越感,虽有点儿冒险,但是又能在风里自由穿梭。付了款之后,听到身后载客的大叔在盛开的木棉树底下夸张地大声对我说:“妹子,你是个好人,祝你一生都平安!”这样的祝福已经意味着人海中的偶遇今生不会再相见,也不会再相识,因而显得特别真挚而有趣。
三角梅的春天是热烈的,霸道且铺张。它藏在寻常巷陌,在旧时的房子阳台上,在砖瓦缝隙之间,出其不意地闯入你的眼帘,让人暗暗心惊。最神奇的是园博园的那一株三角梅,好像一個人要从头到尾霸占整个春天。那是一整株的老桩三角梅,藤蔓交织,曲折迂回,一院子都是它。而马路两旁的三角梅像鲜红的地毯,一路铺向天边,铺向那花海的深处。深一脚浅一脚,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踏进了它为你铺好的夏天。
在黄昏的春天里静坐,也能感受到涌动的春的气息:暮色将远处的海湾卷起浪潮,将近处的层层楼宇淹没,等那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亮起,照亮那一树树的繁花。即使是灯影阑珊、人声鼎沸处,空气里也弥漫了荔枝树浓郁的花香。街头紫荆花瓣的飘落是无声的,随风而散,好像那不经意回眸的淡淡一瞥。而木棉凋谢后,不久就会在枝头挂起一团团的木棉絮,被风吹得满地拉拉扯扯,像丝丝缕缕的离愁。那个时候,夏天的风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