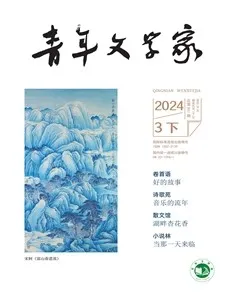北方求学记
廖明锦
躺在学校宿舍的床铺上,我思考着选择来北方求学是否慎重?经过反复的自问,我想这是必然的结果,也不曾后悔自己所作的决定。
床头的同学阿平和我对着睡,他和另外几名新同学辗转反侧,不时地传来床板的嘎吱声,恐怕他们都没有睡着。听着阳台外的对话声,我们似是忘却了两日舟车劳顿,还是很有精神的样子,但此刻大家都感染了乡愁。
室内吊扇拼命地吹,仿佛变成了直升机,它的螺旋桨想把整栋房屋拔地而起。一位同学伸手调高了风挡,可并没有多大的凉意,风扇旋转的声音反而更大了许多。我担心可怕的离心运动会导致意外发生,好在它的外面罩了一层铁丝网。
九月,大小暑刚过,炎热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加以阳台外的朋友带来了更为紧张的气氛,他哭泣着与家人的通话声就像催化剂,加剧了我们对千里之外的亲朋好友和故土的思念之情。
“睡着了没?你想家吗?”阿平悄声地问,怕被其他人听见一般,话里或多或少有些牵挂。
“哪儿有不想的啊,但我们是来读书的,放寒假就能回去了,早点儿睡,明天还得去报到呢。”听得出他有些想家,我安慰着回答。其实此时的我,内心比他们还难受。
那阳台上的朋友踱着步与家人对话,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也随着熬了半宿。为何不称呼他为校友或同学,因为他明天就要返回南方了,今天傍晚刚认识,或许在明早他就踏上归程,所以我们的缘分仅仅不到一天,算不得校友或同学这样的称呼。对面的新生偷偷地嘀咕他没出息,搞得大家此刻都十分思念家乡,其他几人表示同意。我默然,想着坚持几天,多认识些同学也就习惯了。
毫无悬念,这位仁兄还来不及向我们介绍他的名字,第二日天刚亮,在煎熬中度过一夜的他,反而神采奕奕,不见了昨日那般病恹恹。他早早收拾了行李,动作极为利索,很好地诠释了“归心似箭”的意义。他只简单向我们道别:“你们别送我,我要回去复读,明年再上离家近的学校。”他的话语透着爽朗、轻松。我们没有勇气送他出校门,生怕又补上一张返程车票。
半月前的一封邮件,让我与北方拉近了距离。我的第一志愿被录取了,也是我这个分数能选择的最好的学校,还是我心仪的建筑专业,我自然是开心的。从邮局回来的车上,遇到一个叔叔帮我付了搭车的费用,更是愉快。
童年时遇上下雨天,便会和伙伴躲在屋檐下,然后唱起那首不知誰编的儿歌:“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那时,我的心中就种下了对北京向往的种子,这次没有在北京,好在天津距离那里并不远。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这北方之行似乎早就定下了缘分。我从小喜好面食,尤为爱吃馒头和包子,这在母亲看来是极不符合常理的,她曾好几次念叨:“这孩子就爱吃麦面,也不知道买些其他的。”是的,母亲眼中的面食就算个早点或者零食,是不能替代大米成为主食的。
阿平原本就和我一个县城,还是高中同学,难得的是,共同选择了同一所学校的相近专业。我们很早就商定了前往天津的路线,在北京转车到天津站,再从天津站坐公交到大学城,这是最合理的安排。
第一次出远门,我们十分谨慎,走在哪儿都在一块儿,在现在看来是多么稚嫩和青涩。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心情澎湃也有着期盼。正值开学之际,在火车上遇到了许多去河北、北京,甚至还有去东北念书的学生,我们不知疲惫地和周围的人聊着天儿,因而结识了临县的学生小陈。想不到他竟然与我俩是前往同一所学校的,就这样三人结伴同行了。
我们买的是坐票,而且还是硬座。到了晚上,各种呼噜声传遍了车厢,偶尔还有脱了鞋的人,过于“上头”的环境属实让人难以入眠。我和两位同学熬到了凌晨两点,总算趴在餐桌上睡去了,直到推着餐车叫卖的路过,方才醒来。
到了北京西站,这里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得多。果然是首都,连火车站都如此宏伟气派,我心中暗自想。这时已过了下午五点,校车早早地等在天津站迎接新生。联系我的是一位学姐,她很是热情,普通话十分标准且动听,前后来过几次电话嘱咐我们注意安全,提醒到了天津及时联系她。后来到了学校,曾几次通话叨扰过她,我也想见见她的芳容,可惜终究是未曾谋面,想她定然是位楚楚动人的美人。
抵达车站出口处,我们三人已是在站内转了好几个圈,方才出了这“迷宫”。上了去北京南站赶动车的公交,看着北京城的繁花似锦,这算开了眼界,转而想到担心错了路这可不好,为此我跟他俩确定:“没错吧?这里太大可不能迷路,眼看要天黑了。”
“没错,放心吧!待会儿我们买了动车票,直接就可以到达天津站了。”阿平很确定地回答。我这才算放了心。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公交车上的到站播报,到了南站第一时间排队下了车。
望着眼前的南站,却没有寻见动车的影儿,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到一会儿,好几辆三轮车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奔来,司机们热情地招呼搭车。我们先是一怔,然后提高了警觉,果断地拒绝了他们。他们依旧慢悠悠地跟在后面,一直跟着,着实把我们吓得不轻。我们面面相觑后默契地加快了步伐。就在我们想办法如何甩掉后面的三轮车时,几名戴有红袖套的阿姨朝我们走来。于是,我跟他俩说:“这戴红袖套的,肯定比这几个拉车的靠谱。”我们心中有了希望,再一次加快了步子,朝她们迎上去。
“孩子们,是不是找不着方向了?”带头的阿姨关心地问我们,她做了小波浪发型,慈眉善目。我们绷紧的神经总算稍作松懈,回头看时,后面跟着的三轮车也放慢了速度,随即改变了方向往他处驶去。
我们尴尬地笑了下。小陈和阿平开口告诉了阿姨要去的地方,他俩的普通话比较糟糕,沟通陷入了障碍。我这蹩脚的普通话,这时竟然成了我们三人与外界的沟通渠道。在阿姨们的帮助下,我们这才再一次踏上赶去南站的公交车。此刻的我,回想刚才的一幕,仍心有余悸。
折腾一路,我们三人总算是坐着京津城际的动车朝天津出发。看着车厢上方的时速表越来越快,窗外的白杨树和玫红琉璃瓦房瞬间划过眼前,我深深地感觉到外出的不易,那句俗不可耐又蕴含着真理的“在家时时好,出门步步难”正是方才窘境的写照。
抵达天津站后,阿平买了一张地图。此时,夜幕开始降临,霓虹灯也早早地亮了起来。面对这座陌生的城市,我感觉空空荡荡的,甚至有些无依无靠。我第一时间准备联系学姐,这时发现手机里是她发来的未读信息,她告诉我:太晚了,接新生的校车已经提前走了。随后在她的指引和交代下,我们登上了大港区(旧称,现为滨海新区)大学城的公交车。
天津的房屋,应该是受到了早期欧洲的影响,一路看到了不少欧式建筑,让我们对这座城市更为陌生。公交车内的人十分多,捂在里面的我们有些昏昏沉沉,但都没有合上眼睛,生怕错过了站点。约莫过了一个半小时,一片耸立的罗马柱映入眼帘,听旁人对话得知,这是进入了大港区。又过了几个站,按学姐的提示下了车。
我们此时的劲头又上来了,毕竟即将和期待的学校相逢,我们将会在这里度过几年的求学生活。阿平拿出地图后,我们拉上行李箱铆足了劲儿,大步流星地按照上面的方向走去。就这样走了二十多分钟,夜幕下降到了一半,还是没有见到学校的踪影,我总感觉背道而驰,难道是又走错了路?
三人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小陈似乎也觉得迷路了。我们止住脚步,拿着地图研究起来。我觉得是南辕北辙,但是说不出哪里出了问题。他俩再次确定没有问题。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只好继续跟在他俩身后。过了好一会儿,我看到了在公交车上望见的那一片罗马柱。
“不要走了,肯定是走错了路,前面的罗马柱就是我们在公交车上见到的。”我叫停了他俩,有些心神疲惫。
“对啊!我们又绕回来了吗?”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了这句话。
“再走,真的是天黑了,拿地图过来我看看。”
“好!”阿平话落便将地图递来。这次或是急中生智,我一眼就看出来问题,原来竟将地图拿反了。纠正了错误后,我带着他俩往回赶。
过了半小时,我抬头远远地望去,看到了远处学校的模样,有些喜出望外。为了确认无误,我拿出通知书,看着上面的照片和远处的建筑物作了对比,这才结束了第二次迷途。我们三人相视而笑。
来到了学校门前,此时已有两名同学在保安室等待。保安叔叔向我们五个迟来的新生说道:“你们五人去找宿管老师要一间宿舍,临时住下来,明天报完名就能确定分配的房间了。”
保安叔叔热情地领着我们穿过了学校,路过校食堂不忘提醒我们:“这就是食堂,待会儿你们放下东西,赶紧来这里随便吃一点儿,免得太晚关了门,饿了肚子!”
“好的!谢谢叔叔。”我们几人回了话。
陌生的地方,還没来得及熟悉环境,所以我此刻是没有胃口的,甚至忘记了饥饿。跟我们三人一块儿的两名新生,其中一个我已忘记了他的名字,另一个就是那位“阳台朋友”。
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总觉得他面色不佳,有些苍白,甚至有一些苦瓜脸的模样,还以为是晕车惹的祸。没想到晚上就是他给了我们第一次到校难忘的夜晚,这么多年过去,那晚依然记忆犹新。
第二日,我们送走了“阳台朋友”,调整了心情,没吃早餐就去学校大楼报名了。坐电梯的时候,遇到了后来的同学大冰,也是相处几年的舍友,只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过于奇葩。
“你们也是外省的吗?我叫大冰,今天刚到,先过来报名缴费。”他主动与我们打招呼,憨厚、微笑的脸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阿平和小陈先后作了回应,大概的意思是告诉他我们来自哪里。
大冰努力且认真地听了,反复地又问了没听清楚的几句,实则是发音不标准他没听懂。
“我们都是来自贵州,同学你是哪里人啊?”我补充介绍。
他这才反应过来,“哦”了一声,然后说:“你们是贵州的呀,我是宁夏银川的,他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大冰有着西北男人的直爽,这话实则是对我音准的认可,可也把阿平他俩搁一旁而略显尴尬。
下了电梯,大冰冲我们一笑,说:“你们先去报名,我去这边缴费,待会儿咱俩住一起。”后面这句话是对我说的,此话看来简直就是莫名其妙。想着大家都是新生,但不一定是一个系,不一定是一个专业,不一定是一个班级,这么多不可能,让我断定是不可能跟他住一块儿的。后来“咱们”这个词如何使用,还是他教会我的,现在写文也落下了这习惯。
“好啊,那我们先去报名了。”出于礼貌我回答道。
报完名我们随即分到了自己的住处,小陈和我们不是一个系,所以他去了其他的宿舍楼;阿平和我一栋楼,他住进了三楼,我的房间则是在二楼,这下我们有了自己的固定住所。宿管阿姨告诉我们轻易是不会调整的。
刚进入宿舍,我找到了靠近门前的左边床铺,打量下这上床下桌,环境倒挺好,昨晚因为思乡情绪的泛滥和初来乍到的缘故,没来得及仔细观察。相邻的床有一位同学在整理着床铺,他是背朝我的,我也在自顾整理带来的衣物和旅行包。
“嗨,是你啊!你的床铺是这个吗?”大冰露出一排牙齿笑着说,他随手往我的床铺一指。
我先愣了下,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奇怪的新生,回答:“对啊,你还真的和我在一间宿舍了。”我很是诧异,这可不得了,出乎我的意料。直到后来,偶尔谈起刚进学校,就会提起他说和我一个宿舍的巧事,他表示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还真的挨一块儿。实习那年,我和大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家公司,还一块儿分到了一个工地实习。
我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大冰是一个爽朗大方的人。
在校期间,我会计较一些琐碎的事,他倒是无所谓,时至今日都还没向他表示一声歉意。
过了两日,我们随着大巴车去到了消防总队,接下来是持续十多天的军训。过往的饮食习惯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我较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记得早晨吃的是稀饭和水煮鸡蛋,中午是白面馒头、凉菜和榨菜,还有两个菜我已经记不得了,晚上和中午的用餐差不多。这可苦了南方来的同学们,因水土不服,他们的身体出现了各种不适,严重的则腹泻了好几天。
在校期间,我进一步吃了许多面食,刀削面、鸡蛋大饼、窝窝头、擀面、拉面……为此,阿平还告诉了他母亲,说我的胃口好,白面馒头都能吃上好几个,这还是后来在我母亲那里知晓的。同学时常调侃我,要吃惯了面食,今后才能在北方找对象,这话也是一语成谶。
白驹过隙,岁月如歌,大学时光那么惬意而短暂,一晃毕业十余载。
近年因工作的变化,诸多同学又来自天南地北,加上联系方式的更替等缘故,彼此联系得少了,多是断了联系。
去年通过山西的同学加上了大冰的联系方式,他却没有当年那般健谈,我也不再像当时那般啰唆,这就是所谓的成长吧。那年离开的“阳台朋友”,我想他现在也该前程似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