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不被定义的文学人生
高塬 许晓迪

4月22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环球人物》与3位写作者——胡安焉、周慧、黑桃一起,进行了一次直播,引来众多网友在线互动。
去年,《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最受关注的原创非虚构作品之一,“快递员作家”胡安焉为大众所知。周慧与黑桃,也于不久前推出了各自的新作——在《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中,“蜗居”深圳洞背村10年的周慧,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当下的中年;在《我在上海开出租》里,“的哥”黑桃把乘客们的故事一一呈现,记录下职业生涯中的难忘片段,也记录下这个时代奔忙的人群。
相对于长年置身文学圈中、经过严格写作规训的“职业”作家们,这些来自民间,职业背景、成长路径各不相同的写作者,用本色自然的文字,记录下个体和他者的生命经验,展现出大千世界的众生相。他们的写作,被冠以“素人写作”之名,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写下的是尊严
搅动起文学场域一池春水的“素人写作”,在多年前已悄然酝酿。
2010年,矿工陈年喜开通了博客,在上面写诗。11年前,他走进矿山,从秦岭、祁连山到天山、阿尔泰山,一次次地和导火索的燃烧速度较量,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赛跑。他的诗里,有曹操、刘备、李自成,有苏三起解、白蛇传、铡美案。他写秦腔:“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真情和真理,皆在民间。”写工作:“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陈年喜在河南秦岭金矿宿舍里写诗。
2019年,陈年喜的首部诗集《炸裂志》出版。16年的爆破生涯,在他身上留下各种创口,右耳失聪,颈椎错位。2020年3月,他被诊断为尘肺病。写作并没有中止,只是伴着金属质地的尖厉咳声。一年后,非虚构作品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出版,艰辛的劳作、无常的生死,每一个故事,都像陈年喜在矿山深处敲下的石头一般,坚硬、炫黑,悲怆又炽烈的生存力,震得人头皮发麻。
文学的回响可以来自矿洞深处,也可飘浮于厨房上空。2020年,80岁的退休老太杨本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秋园》。她的前半生,种过田,切过草药,在小县城的汽车运输公司做过夜班加油员。60岁那一年,母亲的去世激起她重述往事的欲望,写作由此开启于灶台边,伴随着女性不得不承受的琐碎日常:持家、做饭、带孙子、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两年多里,杨本芬写下10多万字,稿纸足有8公斤重,故事里,是母亲在时代洪流中浮沉的一生。
在《秋园》自序中,杨本芬写道:“人到晚年,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火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驶去。”之后,她以《浮木》追溯乡村故事,以《我本芬芳》回望婚姻生活;到了《豆子芝麻茶》,又将视线聚焦老年女性群体,讲述奶奶们的情爱与无奈、日常和无常。在素白坦率的叙述中,她写下的不仅是家庭、历史和生活,更是尊严,有尊严地生、有尊严地死。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早在17年前,《秋园》已被杨本芬的女儿发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在网上“挂”了10多年,直到2019年,出版人涂涂读到其中一篇,它们才有了被“印在纸上”的命运。
“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素人写作背后的新媒体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很多‘素人写作成果在传统报章杂志上很難找到合适的发表机会,因为题材和表达方式与现有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需求和标准很难匹配。最终即使顺利发表,影响也相对有限。但通过论坛、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加持和扩展,‘素人写作能迅速成为爆款,不断获得关注。这种量级的传播是传统文学期刊望尘莫及的。”
让“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能言者
新媒体上“一夜爆红”的情况在近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2019年11月25日,胡安焉就职的快递公司解散,被动结束工作后,疫情又严重起来。糟糕的境遇下,他在豆瓣上写下工作点滴。其中一个故事——“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成为爆款,收获30多万浏览量,多家媒体转载,出版社的编辑也纷纷找上门。随后,他将自己的故事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了《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冷静、客观又不乏自嘲的口吻,回顾了自己20年换19份工作的“打工史”。目前,这本书的发行量已达12万册,版权已出售至美、英、法、德等12个国家和地区。
快递员在写,外卖员也在写。因为顾客填错地址,王计兵跑了3趟才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上。那天晚上,他因此超时了3个订单。下班路上,他写下《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8个月后,这首诗被诗友发到微博,“外卖诗人”成为热搜,浏览量达2000万。网友评价说,这是真正的“劳动者之歌”。2023年2月,王计兵的第一部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豆瓣评分高达9.3,稳居当当网销量榜前三。
网络时代让“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能言者,更多的声音正从四面八方发出,于是从去年开始,“素人写作”迎来了蓬勃的春天,遍地开花。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中,“挂职副局长”杨素秋写下一座“临时图书馆”的建造史,告诉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喧嚣,但是还有书籍;《我的母亲做保洁》中,“白领”女儿张小满走进“蓝领”母亲春香的打工世界,书写出城市巨轮运转下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我在上海开出租》中,河南奶粉店老板黑桃在2019年来到上海,每天在楼山路海里巡游,将出租车这个谋生存的移动空间,变为与这座庞大都市紧密连接的窗口;《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中,月薪近2万元、每天有五六个小时“摸鱼”的人事经理周慧,窝进一个山村里清贫度日,花鸟虫鱼、云雾山海,枯涩琐碎的日常,在她笔下呈现出别样的美感……
“素人写作不是中国文学写作的局外人。”项静认为,“素人写作正以天然、真实、淳朴、拙力和新鲜感,去打破权威和过于世故的成熟所造成的障碍和帷幕,创造出全新的写作景象。”

杨本芬和她的作品《我本芬芳》。

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周慧的作品《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黑桃的作品《我在上海开出租》。
给当代文坛一点刺激
《环球人物》:在我们的读书日直播活动中,谈到“素人写作”时,胡安焉说他不认为自己是“素人”,周慧则调侃自己是“荤人写作”。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定义“素人写作”?
项静:我的研究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很早就开始关注非虚构写作这个方向,“素人写作”可以看做非虚构写作的一部分,这个词旨在强调写作主体的特殊性。
首先,“素人作家”不专门从事写作,他们有各自的职业,不像作家、学者、记者等与写作关系紧密,并基本以其为主业来谋生。其次,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素人作家”还特指未进入当代文学体制的写作者,他们的成名往往跳脱出传统的文学生产、传播和评价机制,也未进入成熟的文学市场机制,相对于在市场上获得较大收益的畅销书作家,他们起先都是未获得写作平台资源和市场化写作技术的普通人。
至于一些作者拒绝被贴标签,也很正常。文学领域的很多概念很难做到严丝合缝。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兴起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寻根作家”一词出来的时候,当时有些人也拒绝被归于其中。所以概念并不重要,当我们讨论一个现象时,它就是一个方便概括的说法。
在我看来,“素人写作”这一命名中还包含着期待与设想,对一种未被成规沾染、充满活力的写作的期待。从这个角度讲,“素人写作”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胡适对“白话文学”的观照到鲁迅把平民的文学看作是未来中国文学,从解放区文学的“真人真事”书写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工农兵作者的培养,及至21世纪的“打工作家”和“底层书写”,在这个漫长的文学脉络中,我们一直期待着“素人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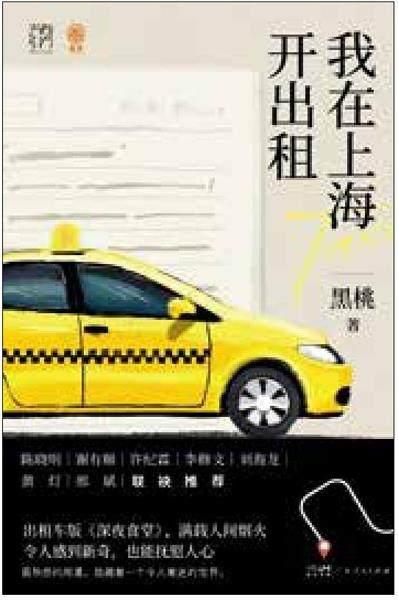
《环球人物》:从最初的一两个特例,到如今遍地开花,“素人写作”何以成风?
项静:今日媒体、文学界和社会大众对“素人写作”的喜爱和讨论,首先是对精英叙事的反拨和不满。实际上,网络文学出现后,文学就开始突破精英叙事,汇入人民的汪洋大海。我们发现,故事的讲述,对具体的人、生活场景、社会生态、某些有意味瞬间的描摹可以来自名流,来自职业写作者,也完全可以来自贩夫走卒、升斗小民。
当下,我们对真实的渴求,回归对“附近”的探索也极大促进了“素人写作”的兴起。保安、保洁、快递员、外卖员就在我们身边,一个真实的现代人不会对他们冷眼旁观,相反,我们时刻希望对周围的世界有具体而微的认识。纵观近几年的“素人写作”,基本是在自述“真人真事”,这些个人独特、复杂、丰富的真实生活经验,很容易唤起人们对他人经历的好奇、自我生活的记忆和公共话题的关注,可以说是自带流量。
另外,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能在新媒体上广泛传播,还得益于创作者自身的写作水平。“素人”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写出具有专业水平的作品,通过各类访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作者都热爱阅读和写作,其阅读书目的多元繁杂大大超出一般人,他们是真正的文学青年。这种经由阅读和自我训练形成的不亚于一些成名作家的表达能力,是这些作品最终能够出版的必要条件。
说到他们的表达,当下这些作品的语言风格整体上都有冷静、克制、娓娓道来的特点。这种不过度渲染苦难、失败、伤痛的文学手法,符合近20年来大众的阅读审美。就像余华的《活着》最近被年轻人重读,他们为福贵苦难的一生唏嘘,更被文本之下幽默、坚韧、乐观的底色所打动。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目前这股创作风潮是否能够持续?会有新的发展吗?
项静:这两天我也在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聊,大家发现“素人写作”现在似乎开始套路化了,从书名就能看出,总是“我在哪里做什么”。同时,对个体经验的陌生感、新奇感随着文本数量的增多的确会稀释、消失。因此,“素人写作”在惊艳开场之后,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持续性和具体作家写作的可持续性仍需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就像陈年喜所说,把他们放在这个时代所有作家当中,“用同等的尺度,去看看他到底写了什么,他的文本能不能成立”。
至于“素人写作”未来的发展,我更倾向于把它纳入当代文学这一整体中去考量。“素人写作”的出现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正面刺激——它让纯文学作家注意到另一种写作群体的存在,在文笔上,他们不故作高雅、过分雕琢,简单、直接、晓畅;在实践中,他们投入生活,更加深入地理解普罗大众,和读者共情。他们以个人的经历诠释了中国城乡二元化空间中文学青年的命运,执着于人文理想,与困蹇的现实进行搏斗,最终以“素人写作”的方式实现了梦想,拥有了不被定义的文学人生。他们就像一群“求道者”:表现自我、追求人类和社会的真实,在生活的自述和自我形象的塑造中,所抵达的是普通劳动者的“众声”。
而在影响力较大的“素人作者”之外,还有大量没有进入聚光灯下的写作者,他们不把出版发表、自我突破和成名成家作為第一位的问题,而是通过写作表达自我,与他人交流,创造生活内部的社会性和有机性,这可能是比文学性更加重要的社会价值。
(编审 张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