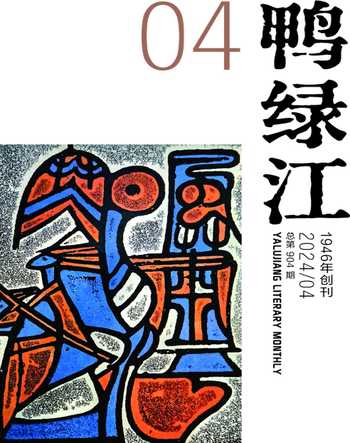边界(组诗)
孙担担
边界
新年第一天,我用新买的米做饭
经历水洗高温
白米粒暄腾腾地挤在一起
丝丝热雾,把米粒心里的寒暑交集
往外拖
我的手总有摸不到的地方,无论多么近
我父在咳嗽,用力咳
把米饭上的热雾都吹散了,我去扶他
我双手沾满了热雾的碎片,还是够不着他
他怔怔地看着我,瞳孔中的晶亮
原来是一个终点
我的手在热雾里跋涉
每一颗米粒上都粘着离散
光感,声响
扣在我中年的心脏上,成为
没有边界的沉闷
我咽下新年里的新米饭
米粒在我的体内修缮我的过错
维持我的体温。我父因此
随时找到我
暴雨
暴雨认定自己的到来是正确的
也是正义的
“云深不知处”
“别后不知君远近”
“梦中不知梦”
无论这世间这人心有多少法则
一场暴雨仍给出答案
云到泥的距离,可测
君远近,不可测
梦里梦外,隔着一个额头
暴雨倾泻后
也可以取消任何答案
如果一切重来
那是暴雨给予的正义
行者
白纸黑字,或者黑纸白字
都善待不了真相
月是最本分的行者,善待明暗
也善待不明不暗
蜡梅在雪中钻出枝条
只是偏离秩序,不为烈
一座城中如果没有废墟
就耗尽了历史
行者留下的叹息,是典籍里
黯然的篇目,修辞懒惰
行者不识疆
所以云朵轻
梦靥繁
虛构
我打着埋伏
时而绷紧如被俘之雀,时而跳脱
如候鸟跳出季节
南飞北回的路上,翅下的江山
疏密线条不随风动
随风动的线条只在人的心里
交错处,叫作际遇
我析出血液,为相逢
落日析出血色,为涂抹掉
我的所见
地震
那蓝光,是绝望的眼神
地表层的根深蒂固
有时是谎言
以经度和纬度可以确定震中
以震中可以确定所有的爆发都是非盲目
那些被吞咽的魂魄
承担永久湮灭
也将承担永久驱动
盲目或非盲目
洋甘菊之夜
花瓶内是花瓶外的别处
失而复得的温饱、欢颜、羞耻
在这透明的花瓶里
清晰毕现,相安无事
花瓶外,有更多的别处
春风带来的前程刚开始
洋甘菊隔着玻璃
在夜的中央
醒与不醒,皆奔天明
夜中央的黑暗,及黑暗中的永恒
只漫出一种形式
黑暗也不能被占有
孤儿
麻雀落在枯枝上
它回眸
成一个逗号
变成逗号的样子
就要等待填补
就有身世进入
左边没有鸟
右边没有鸟
它刚好把目光投向我
我对韶华的理解
开始驱逐时间
鞠大红
那天的桃花正拥挤地站满枝头
风吹过,没有桃花肯落
四月里的花和人,都倔强
大红妈满脸桃花色
飞奔过桃花树,飞奔向马路对面的县医院
她后悔了
邻居们还在裁判
这次吵架她是七成赢还是五分输
敌敌畏已经让她在医院的长椅上
置身事外。虽然,扔下鞠大红她多么后悔
鞠大红穿的布拉吉
在四十年前具有突兀之美
大红妈缝裙子的时候,掌握了美学密码
在不容突兀的年代
等满树的桃花都飘落
七岁的鞠大红,经常穿着布拉吉站在树下
多大的风她都不动
女邻居们更仔细地盯住布拉吉
琢磨用料尺寸和缝纫法
男邻居们盯着布拉吉
仿佛盯着大红妈
演唱会
——记一次理疗
她说——我开始啦!
“梨花开,春带雨——”
娇羞的声音,推开一筹莫展的爱
君王、布衣,皆折磨
她的手在我的头发里
有的穴位种花,有的穴位兵变
一个青花瓷瓶,站在我头颅上最高的穴位
我盼望,让瓷瓶快点跌下来
她的高音区闪出金属,兵器林立
那些遗传的痛楚,又一次停止挣扎
玉环刚刚离去
她说——后背刮痧会有些痛
我就唱“都有一颗洪亮的心”吧!
我为何有这么多疼呢?
这些疼被铁梅用大辫子抽出来
我后背上开始痧线密布
这是带着密码的修补术
她在高音处顿了一下,声音和手
同时打个转
音落于“心”,手止于我的后心
替我的疼痛,交出停战书
我问她——你怎么可以唱这么好?
她眼光暗下来
她的好嗓音来历不明
并不是来自她出生的那个小山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