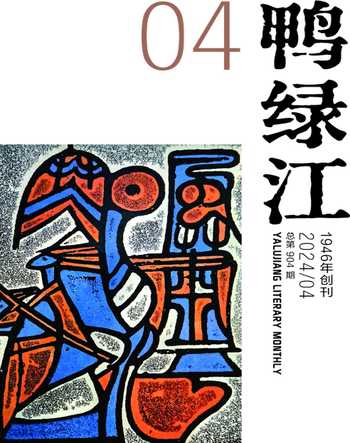穿越时空的旅行
苏兰朵
夜幕中的伦敦
抵达伦敦的时候是晚上,我和皮皮拖着沉重的行李,在希斯罗机场通往地铁的电梯前耽搁了很长时间。皮皮将箱子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了公交卡。望着快过20岁生日的他,我确信到伦敦来陪伴他是有意义的,但一个母亲内心从未消退的忧虑还是在心底起伏了一下。
地铁里的噪声还是那么大。出口很破旧,通往地面的扶梯高得吓人。我一手拽着箱子,一手紧紧握住扶手。当然还是有没有电梯的台阶,箱子很重,我试了一下,放弃了,等着皮皮一个一个拖上去。这个时刻,我有点庆幸,还好是个儿子。一个女孩子出来留学的话,怕是从这一刻起,兴奋就消失殆尽了。在这夜晚的异国街头,会有陌生人帮助她吗?
出了地铁还要倒公交车。但是皮皮在确定公交车站的过程中迷惑了,谷歌地图用得也不顺手。我们拖着三个大箱子在街上走了很久,包括一些重复路线。他有些歉意,我压制住心底的焦躁,劝他,没关系。温度很低,比国内低。冷风顺着牛仔裤肥大的裤管一次次袭上来。我的外套也很薄,就是件防晒服。我问皮皮冷不冷,他说不冷。精力还持续在寻找正确的公交站点上。这条街很僻静,街边店铺几乎都打烊了,灯光昏暗。地铁口有流浪汉围着毯子坐在地上,还有拎着酒瓶子的中年男人,瞪着眼睛没有表情,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从他面前经过数次。我终于对皮皮说,打辆出租车吧。
打车也不容易,不是随便招手就叫得到。皮皮用优步软件叫到一辆。等了很久,对方跟皮皮通电话,说是到了,但是我们站的地方不能停车,需要走一条街。我们拖起箱子快步去找车,但是奔波了五六分钟也没找到,后来车走了。冷风吹得我开始打哆嗦。皮皮的歉意更深了。我劝他,没事,再叫一辆。
终于坐上了宽敞的出租车。伦敦出租车的大小跟SUV差不多,一般会有六个座位,放行李的地方也很宽敞。司机是个黑人,态度非常好。我们下了车后,因为一时确定不了在网上租的房子是哪个单元门,看着门牌号找了半天,他还特意将车开到我们身边,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这是我们踏上英国的土地后,感受到的第一丝温暖。我禁不住又在想,如果是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在夜里降落到伦敦,经历了这一切,会不会悄悄落泪?或者莫不如说,我代入的是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留学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梦。那时候,看看外面世界的冲动是那么强烈。这份渴望似乎能化成无尽的勇气,战胜一切困难。而此时此刻,人到中年的我,站在伦敦的夜幕下,心中却替年轻的自己担忧起来。可能正是缘于此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在伦敦的街头,看到一张独自行走的东亚女孩儿的面孔,都忍不住多看她们几眼。我希望我眼神中的温暖可以被她们感受到。我希望心底微弱的祝福可以真的给她们带来一丝安慰。
哈克斯顿街
房东萨维莉亚告诉我,顺着我们公寓门前的马路一直向东走,有一条街叫哈克斯顿街,能买到我日常生活需要的所有东西。
之后,我成了那里的常客。
步行去哈克斯顿街需要十分钟左右,沿途会经过一个小教堂、一个小公园、一个小学,还有两个十字路口和几个居民区。运气好的话,会遇到横穿马路或者在树上蹿来蹿去的松鼠。萨维莉亚说,以前公园里有红狐狸出没,这几年见不到了。遇到鸽子不算稀奇。在伦敦鸽子到处都是,一点不怕人,身材肥胖,你走到近前也无法打乱它们从容行走的节奏。
我最常去的是一家食品超市。他家的店面很大,里面从面包、饮料、酒、熟食到生鲜、粮油一应俱全,店铺的外面还支了防雨棚,下面摆放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烟火气特浓。最难得的是,每到周日,整条街大部分店铺都关门休息,他家还是开门营业的。站在收银台后的女人三十多岁,棕色皮肤,头发卷曲,高鼻子、黑眼睛,按照我的审美,是很漂亮的。她喜欢微笑,也喜欢收现金。去了几次,我感觉她应该是老板娘。我买东西是很慢的,因为语言不是熟悉的母语,生怕买错了什么,拿起一件东西总要看半天。第一次去这家店回来,皮皮看着我买的牛奶,问我,这上面也不是英文啊,你是怎么知道它是牛奶的?我看到了。我拿过瓶子,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那两个我熟悉的英文单词——全脂牛奶。皮皮接着告诉我,除了那两个单词,这瓶子上写的都是土耳其语。我恍然,那个棕色皮肤的漂亮老板娘应该是土耳其裔。不久,我在哈克斯顿街发现了一家好吃的馅饼店。本来是试探着吃了一次,没想到大大超出我的预期。要知道,英国人没什么做饭的天赋。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才弄明白,这根本不是英国的本土美食,而是土耳其馅饼。老板娘比超市的那个年长一些,40多岁,不过她们的容貌确有相似之处。她也喜欢微笑,并且更热情,记忆力也好。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又点了同样的馅饼,她就笑着问我,咖啡也还是拿铁吗?不难猜到,这条街的周围,一定聚集了很多土耳其裔的居民。于是,我时不时地在街上遇到裹着头巾的女人,也就容易理解了。
挨着食品超市的店铺是一家杂货店。门口堆着撮子、拖布、刷子、塑料桶等生活用品。我的拖鞋、毛巾、牙缸都是在这买的。老板是个印度裔,看起来至少有60岁了,头发花白,皮肤黝黑。来过几次,买东西都很顺利,但最近一次却遇到了障碍。我想买一个金属蒸屉,在店里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折叠的,一看价钱,11镑,合人民币有100块。我不甘心,又找了半天,发现一个金屬的小筛子,铺上蒸布应该也可以用。这个只要4镑。虽然30多块人民币买这么个东西也觉得贵,但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了。我拿出信用卡去交款,没想到印度裔老板一直摇头,让我用现金。我说今天没带现金。他什么也不说,只对我重复一个单词:现金。这个倔老头儿,宁可不卖给我,也要现金。我只好放下东西离开了。不过回家后我重新寻找了一番,终于在一个置于橱柜顶端的高压锅里找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蒸屉。
哈克斯顿街上有很多小饭馆、小酒吧,在街的中间还有一个封闭的小花园。花园里有五六张长椅,总有人坐在里面休息,吃顿简单的午餐,或者喝杯咖啡。周日的时候,花园的小铁门会被锁上。我一直很奇怪是谁锁的。政府部门吗?或者这是一个私人花园?花园的门口有一辆餐车,卖汉堡、薯条、炸鱼。餐车的经营者是个黑人。周日他会休息。他休息的时候,整条街会特别安静。周日以外的时间,他的经营是非常热闹的。车里的音响会放说唱音乐,餐车周围总聚集着三五个人。我注意观察了几次,他们不全是食客,有两个好像是老板的朋友。他们不吃东西,就站那儿跟老板说话,边说边跟着音乐舞动身体。有时候,他们手里会拿着啤酒。我从餐车前经过无数次,看着那些食物,还是很有食欲的,但一次也没有停下来买过。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没有把菜单贴出来,让我看一眼就知道花多少钱可以吃到哪些东西。那么,如果我想吃,就要跟他说很多英语。我的听力不好,会很麻烦。
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是肖迪奇图书馆。它在这条街的南端。再往南走不远就离开了哈克斯顿街,进入哈尼克区的中心地带。我曾经漫无目的地步行去过那里。除了更宽阔的街道,那里有伦敦最具特色的街头涂鸦。肖迪奇图书馆全天开放。不需要任何证件,随时可以进去,待到闭馆也没有人打扰你,还有免费的Wi-Fi。图书馆有两层。一层是阅览室,地下一层是自习室。我一般直接去自习室。挑一个喜欢的位置,打开电脑,将带来的饮料摆在桌上,就可以安静地待上大半天。下午四点多,我收起电脑,准备回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高个子的白人。他通常穿着制服,胸前挂着工作卡。他的头发白了很多,脸倒是还年轻一些。我无法判断出他的年纪,总感觉他已经退休了,在这里工作是做义工。我总是会在门口遇到他,每次遇到,他都跟我微笑,然后说再见,仿佛我们很熟识。
我走在黄昏时刻的哈克斯顿街上。这时候,附近小学的孩子们通常放学了。他们穿着合身的套装校服,三五成群,占据了这条街。有的站在街边吃东西。男孩子嬉笑打闹,女孩子表情生动地讨论着什么。他们中有梳着满头小辫子的黑人,有一脸雀斑的白人,有裹着头巾的土耳其人,也可能是印度人,偶尔也会有几张华裔面孔。卖汉堡的餐车这时候正热闹得起劲儿,附近工地的建筑工人下班了,聚在这里吃汉堡喝啤酒,花园的门口都被堵上了。
如果我从图书馆出来得再晚一些,街的中央就会冒出很多新的摊贩来。他们一般在往支架上挂衣服,或者在地上摆放小商品。我知道,夜市快开始了。
我会拐进食品超市,买点新鲜的蔬菜,或者第二天早上吃的快餐食品,拎着回家。那样子,好像我刚刚下班。我一般不会买太重的东西。这样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可以走到公园里坐一会儿。在那里可以看到玩耍的孩子、遛弯儿的狗,还有大摇大摆的鸽子们。我隐藏起内心的孤独,对着脚边的鸽子微笑,貌似很开心。是的,我知道,如果此刻我20岁,想必已经把到伦敦第一夜的不快经历忘在了脑后,投入到对一个新世界的探索当中了。这时候,我经过一天的学习,离开坐满各种肤色同学的图书馆,漫步在绿草坪上,正在思考着晚上吃点什么,或者选择哪个同学做朋友。虽然还没想好,但是这一天我很充实,此刻很开心。是真的开心。毋庸置疑,这些秘密都写在皮皮的眼睛里。
查令十字路84号
在伦敦,你不必期待天气。那是一件最变幻莫测的事。
早晨拉开窗帘,大多数时候天是阴的。望望地面,也经常是潮湿的。你以为今天不是个好天,也许十多分钟后,太阳就出来了。走在路上,明明艳阳高照,下一秒就有雨落下来。你刚想找地方躲一下,雨就停了。一般的雨,伦敦人根本不躲,该干吗干吗,就当它是风。你若担心雨,那就天天带着伞。但据我观察,大多数伦敦人采取了另一个极端的策略——反正带着伞也用不了几分钟,索性什么天都不带。这或许可以解释风衣为什么会在英国流行。一方面是气候决定的,冬季不冷,夏季不热,风衣穿的时间长。另一个方面就是风衣防雨。总有小雨不期而至,穿风衣最保险。
被雨捉弄久了,人也就没什么脾气了。一个任性的孩子,你能拿他怎么办?到伦敦一个月后,我就不再看天气决定是否要出门了。如果因为阴天心情不好就更加不合算。
伦敦人因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真正晴朗的好天气。每到这种天,每一块我能见到的草地,都有人或卧或坐,或踢球,或玩飞盘,或野餐……连鸽子也停止了脚步,将头窝在身体里,肉嘟嘟地趴着,安静地享受阳光。
出门与天气脱离了关系,就变得简单了。
我住的公寓楼下有一个公交车站,是四条线路公交车的站点,其中三条线路经过市中心,有一条还是24小时运营的。伦敦的公交车大多是双层巴士,基本都是红色。我喜欢坐在上层,如果能坐在第一排就更好了。那里是女人和女孩儿最喜欢的位置。视野开阔,可以悠然看街景。
不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就会坐上红色巴士,在伦敦的街头游荡,寻找那些能触动我兴趣的缝隙。20岁的我在我的身体里,闪烁着新奇的眼神。甚至从我的身体里走出来,坐到我的身边,挽着我的手臂,向我指认在书里到达过的地点。我因而不再孤独。
我们喜欢76路。转过圣保罗教堂后,会到达美丽的弗利特街,再往前是河岸街。沿途有很多美丽的古建筑,无论在哪一站下车,都可以步行抵达泰晤士河。那边又是另一种风景。
这一次,我们在查令十字站下了车。没错,我们想去看看查令十字路84号。在大学工作的时候,我从图书馆里借到了这本书,却没有看完,因为不太喜欢。但是这个地点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想,如果20岁的时候遇到这本书,或许更相宜。相遇是时间的艺术。正如我在20岁的时候遇到了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才能深刻地走入我的灵魂,从此,所有的爱情小说都变得黯然失色。
从查令十字站到查令十字路还有段距离。我按照导航的指引,先抵達了特拉法加广场。不能不停下脚步。此刻阳光好得没法说,拍的照片里景物全都模糊不清,哪个角度都反光。喷泉池周围聚满了人,我也曾在这里坐过很久,看游人喂鸽子。那一次是去广场旁边的国家美术馆,出来的时候正赶上一支乐队在这里表演。我听了一首歌,然后走到广场对面的咖啡馆,喝了一杯拿铁。
绕过国家美术馆和它身后的国家人像画廊,又走了五六分钟,查令十字路终于出现了。率先看到的门牌是24号,看来还要再走一会儿。
下午三点多,街上的人非常多,分不清本地人和游客,耳畔有不同的语言飘过,包括熟悉的汉语。街边店铺的汉字突然多了起来。直到我一扭头看到旁边街巷里悬挂的成排红灯笼,才反应过来,我已置身中国城附近。
查令十字路84号离中国城非常近。它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是一座五层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在正面墙壁的左侧,贴着一个不起眼的金色圆牌,上面写着:“马克思科恩书店曾开在此处,它因海伦·汉芙的书籍而广为人知。”
居住于美国纽约的女作家海伦·汉芙因为无法在本土找到需要的古书籍,于1949年首次联系了伦敦马克思科恩书店的古书销售商法兰克·铎尔。此后,汉芙与法兰克以及他的所有员工,发展出了一段远隔重洋的友情。他们彼此通信,交换圣诞礼物、生日礼物。英国在二战后食品短缺,汉芙也常常随信附上一些食品包裹。当然,他们谈论最多的还是书籍。汉芙曾在信中多次表示将到英国旅行,并且造访该书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成行。时过境迁,书店最终关门停业,法兰克和其他一些员工也相继离世。为了纪念这段不曾谋面的温暖友情,海伦·汉芙将二十余年来的书信结集,于1970年出版,书名就叫《查令十字路84号》。
这本我没有读完的书,被视为爱书人的圣经。
然而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地点,现在是一家麦当劳餐厅。来到这里的人不是为了买书,只是想吃点儿快餐。这多少有点荒诞。在它的斜对面,是演出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的专门剧场。那里总是聚满了拍照的年轻人。因为哈利·波特,我记起来曾经坐着公交车从这个十字路口经过。就是说,我曾经完美地错过了查令十字路84号。
我没有看她。我无从得知,目睹眼前的一切,20岁的我是否会更加失望。我也无从得知,如果我20岁时遇到了这本书,此刻是否会为书中结尾的那句话而更加动容。“若你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路84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它良多!”
我望着她站在90年代,那一双水一样干净的眼睛打量着金色圆牌上的文字。有那么几秒钟,她的眼睛潮湿了。我怎能嘲笑她呢?我是羡慕她的。轻易地被爱打动,那是一种因为年轻才特别具有的能力。
我终于释然了。虽然相遇是时间的艺术,但迟到也并不都令人遗憾。因为,她站在90年代,永远无法想象我的感受。她无法带我前来。而我可以牵着她的手,去我们曾经想去的任何地方。就像我牵着皮皮的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