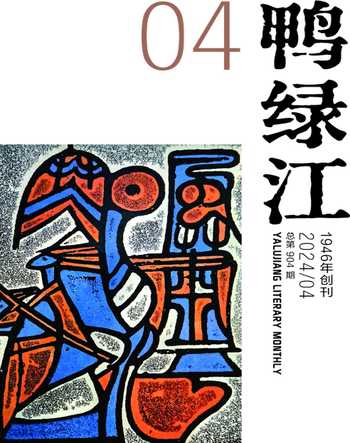鼓角梦
沈俊峰
像一锅岁月的馒头,终于等到揭盖的时候,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疑问,今朝真相大白。我坐在小小的会议室,见到吕海生、柏太子,没有丝毫陌生感,就像见到久违的战友。情感的水蒸气蒸腾开来,将我彻底笼罩。我开门见山:“说说搬迁进城前的那一段军工生活吧。”柏太子说:“那时候真是太苦了。”说完这句,70多岁的柏太子哽住,说不下去了。吕海生将脸扭向窗外,半晌不回头。
我的心猛然一震。柏太子的话一下子让我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恍然如梦。如今时过境迁,我早已习惯浮华对岁月的掩盖、淡忘和漠视。然而,此时此刻隐隐传来的鼓角争鸣,声声击打我心,有一种遥远的疼痛。
1
我忘不了小三线军工凤凰涅槃的新生。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从大山深处搬迁出来的军工厂,像迁徙的远古部落,职工们拖家带口,离开扎根二三十年的大山,带着历史的尘烟,带着生产设备和生活必需品,向着遥远的城市艰难进发。
这是一次长征,是时代与命运的转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当年,父辈那一代人以千军万马之势扑向大山戈壁,甘当一粒石子,默默无闻地燃烧生命的激情,苦筑国防长城。后来,他们完成使命,从大山撤离,向历史谢幕,军转民寻找新生的起点。跟随他们撤离的,还有我们这些自小在山里长大的军工二代。一切来得突然,令人猝不及防。
那时的合肥,远没有今天的规模和繁华,却成为皖西大别山多家军工厂渴望已久的归属地。柏太子、吕海生所在的皖东机械厂,职工和家属以朝圣般的信念,向合肥眺望,仿佛那里有一座明亮的灯塔,能照亮他们的灵魂和脚下的路。距离合肥不过一百公里,如今开车只需一个多小时,他们却整整走了十多年。
那是无法言说的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军工厂要搬迁至淮河岸边的蚌埠市。我在搬迁筹建处干过半年,天天跟着领导找市长,跑规划局、设计院、供电局。开车路过一片荒地,有人说,皖东厂也要搬到这里,瞧,那就是皖东厂的新址。可是,我一直没有见到皖东厂的人。后来听说他们改变目标,要搬往省会合肥。90年代初,我调到合肥,我父母所在的工厂也顺利搬迁合肥,仍然不见皖东厂搬迁。“皖东厂职工在给当地农民打工”,这些道听途说来的消息让我震撼,我半信半疑,却无法去了解真实。
如今,小三线军工企业成为历史,皖东厂也不复存在,对那段往事的真实回放、军工精神的承继,成为我无法释怀的责任。
2020年9月,安徽省国防工业工会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三线精神”军工文化霍山行活动,省国防科技工业文化协会副秘书长钟宁听了我的想法,立刻让于长胜帮我联系皖东厂的老职工。胖胖的于长胜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从皖东厂调出来的,对那段历史也非常熟悉。”
2
1965年7月,在大别山东麓的舒城县山七镇小河村,皖东厂开始筹建,翌年5月破土动工。1970年9月,产品通过国家鉴定,开始批量生产军工产品。
进入新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中心,中国向世界宣布裁军一百万。在时代大潮下,小三线军工的军品任务锐减。皖东厂的军品任务只有一点点,后来比一点点更少,只能生产一些训练用弹或拍影视剧用的无弹头空包弹。到1987年,军品任务为零。曾经的省国防工办大庆式企业,顿失昔日风光。
没有任务,就没有效益,全厂五千多人陷入生活困顿。人要吃饭,企业要搬迁,皖东厂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
搬迁进城,恰如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开拓进山,同样意义非凡。当年建厂,是以举国之力为保证,如今进城却要凭企业的自身实力。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像一个基本不会游泳的人被扔进奔腾的长江,全靠自己扑腾。
皖东厂开始生产童车和兰花牌自行车。兰花牌自行车一度行情看好,供不应求,得批条子才能买到。想一想也是,以軍工技术生产出来的钢圈,一次成型,质量过硬,上海自行车厂都慕名前去定制钢圈。
然而好景不长,兰花牌自行车不知怎么转让给了兄弟厂,皖东厂开始生产荷花牌自行车。兰花,荷花,一字之差,气运好像就变了,再也没有之前的红火。至于兰花牌转让的原因,被说成是兄弟单位的互助。对此,皖东厂人无语,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寻找新的拳头产品。
他们和上海大隆厂、天津大港合作,生产石油磙子链。他们生产的链条拉力大,很快赢得市场。干了两年,不知啥原因停产,改为生产双管、射钉枪。双管是给其他军品配套用的一种零部件,射钉枪是民用产品。好在天佑皖东,这两种产品销路都不错。遗憾的是,这不错的两种产品后来也被兄弟单位“互助”去了。
皖东厂变得两手空空,无米下锅。职工们困惑不解,议论纷纷。有人自嘲说,皖东厂就是一个民品研发基地,研发成功都给了别人,自己倒成了一个穷光蛋。
依靠不断研发民品,厂子支撑到1992年6月。7月,“口袋”终于空瘪,再也不能按时发工资。工资推迟一两个月是常事,后来干脆推迟一年多。“弹尽粮绝”之下,上级多方协调筹措过来的资金,只能给坚守岗位的职工每月发40元,不上班的职工每月发20元。这几十元勉强可以买点糊口的粮和蔬菜。
那时,于长胜在车队开车,日子要好过得多。
山里交通不便,职工出山非常困难,驾驶员吃香的喝辣的,成为热门职业。厂里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都是车队从省城转运站拉回来,驾驶员借机帮当地人拉沙子。合肥城正值建设,修路,盖楼,沙子正好卖进城里。拉一车沙,可挣35元至40元。于长胜每个月去合肥二十七八趟,每趟交给车队一点管理费,剩下的归己。除了拉沙,他们还帮人往外拉木材、门窗、毛竹、石头。大山是一座宝库,藏着多种宝贝。
厂里发不出工资那年,于长胜托关系调进了省城。能走的都走了,生活到了生存的地步,活下去便是朴素的意义。
然而,大部分职工的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
3
有技术的职工纷纷进城帮人打工,另谋生路。没有技术或家庭拖累走不了的,只能窝在厂里。厂区就巴掌大一块,一个穷山沟,能生长出什么金子来呢?皖东厂像一艘落了帆的孤船,困在茫茫大海,船上的人一边自救,一边等待救援。
有人从沙子里看见了更值钱的铁沙,开始沙中淘铁,将铁沙晒干,一斤能卖一毛钱。捞铁沙很简单,把吸铁石绑在棍子上,在沙堆里不停地搅动,铁沙像着了魔,黑芝麻粒似的层层聚集于吸铁石上。
吕海生的岳父母也捞铁沙。
吕海生6岁跟随父母进山,在军工厂长大,高中毕业去参军,退伍后在皖东厂保卫科当干事。厂里没有生产任务,保卫科却是一切正常,重点岗位保卫人员仍然全天候值班。空闲下来,吕海生就去帮岳父母捞铁沙。他发现岳父母弄来的吸铁石太小,吸力不大,就想法去弄一块大的。
搬迁去马鞍山的一家军工厂,职工被打散分到多家单位。吕海生的亲戚正好分在一家磁性材料厂。他请亲戚帮忙搞到一块大吸铁石,往沙堆里一放,果然威力巨大,战果明显。用这块大吸铁石,吕海生一天能捞五六十斤铁沙,颇有成就感。
与吕海生相比,柏太子吃了更多的苦,受了更多的累。
柏太子从部队退伍进厂。没有军品任务那年,他才三十多岁,两个孩子,大的上技校,小的读小学,老婆无工作,全家依靠他四十多元工资生活。军工的优越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不复存在。柏太子打枪、站岗是行家,却不会车、刨、钳的技术。他能做的,就是争取上夜班,好腾出白天去附近窑厂打工。进厂时,他没想过自己的手脚还会再沾泥巴,现在不仅要沾泥巴,甚至比当兵前的农家日子更苦。
他深知土地的好处,有土地就有生活,可是他在军工厂没有土地。这个被当地农民羡慕了许多年的工厂“老大哥”,此时非常羡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伯伯”。他不得不放下身段,穿着工作服给“农民伯伯”做砖坯。
做砖坯是半机械化操作,他只需要把砖坯从传输皮带上拿下来,垒在独轮车上,推到空地,层层码起,通风晾干。一块砖坯挣6厘钱,他一天多则能挣十七八元,少则几毛钱。
他打赤膊,穿大裤衩,大汗淋漓地搬砖坯。一辆独轮车能摆三板子砖坯,最少有180斤。刚开始他不会推,力量跟不上,技术也不行,走几步就会歪倒。后来熟练了,掌握了平衡,才走得顺畅。上坡下坡,掌控起来全凭力气,没有力气推不动,下坡也收不住脚。他出大力、流大汗,每天累得筋疲力尽,睡倒就爬不起来。
周围有好几家窑厂,柏太子挑一家近的,跨过门前的小河就能到。在窑厂干活儿,一个班最少12个人,分工协作才能运转。柏太子中午回家匆匆吃口饭,饭碗一撂,拔腿又走。周围窑厂干活儿的都是皖东厂职工,农民嫌窑厂的活儿太脏太累。柏太子说:“没办法,一家人要生存,必须要干。”
窑主知道三线厂已是落魄的凤凰,迟早要飞(搬迁),就故意拖欠工钱。他们拿窑主也没办法,毕竟还有国企职工的修养和风度。直到现在,窑厂还欠着柏太子的工钱,成了死账。
在窑厂打工累,挣得却多,只是不稳定,时常停产。窑厂没活儿时,柏太子就去帮农民插秧、割稻、砍柴、扛树,只要给钱,啥活儿都干。
往山下扛树,大树他能扛一棵,小树能扛两棵,走一段山路,便累得呼呼喘粗气。按重量给钱,100斤挣5元。路上要歇多次,用一根带丫的粗棍顶着树,腾出肩膀,扶树站着喘息。木棍与肩膀要差不多高,停下或再走,比较省力气。湿透的衣服被山风一吹,寒凉彻骨。肩膀磨起水疱,水疱烂过几回,成为硬茧,也就不再起疱。他感觉自己像一块火红的铁,在汗水中、在风中淬火,然后变成另外一个坚硬的柏太子,一个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陌生的顶天立地的汉子。
收获的季节,柏太子和工友一起去给农民割稻。七八个工友,和农户谈好价格,就动手下镰。割稻沙沙响,跳跃着,欢乐一片。收割、挑运、脱稻,然后颗粒归仓,一条龙下来,能挣二三十元,几个人平分。他们常常是挑灯夜战,一鼓作气干到天亮。
说实话,手上在干活儿,心里却不是滋味。想当年工厂风光,附近农民想尽办法进厂做小工,盖房、修路、搞卫生,挣个活络钱。如今,他们要给农民兄弟打工。想不通也没有办法,生活会让人想通。柏太子有了境由心转、转念成佛的体验,生活变得天高地阔。
柏太子的妻子也非常勤劳。春天帮农民摘茶,一天能摘七八斤茶草,挣七八元。春夏帮农民插秧。柏太子插秧比不过妻子,干一会儿就腰酸腿疼。妻子比他有韧劲儿,能坚持,手也灵巧。
一天深夜,妻子见柏太子没回家,就替他去厂里站岗值班。值班人员配有一把半自动步枪,防人盗窃。之前,就有人把仓库的厚墙挖了一个洞。
大山之夜,漆黑沉沉。岗亭的灯光像大海上的一盏孤独航灯,承受着风浪与黑暗。黑夜生出无数的恐惧,直往她心里钻。她攥着枪,像攥着一根烧火棍。坐在岗亭里,她看不见黑夜,只看见眼前稀薄的一豆灯火,身子不由自主地发抖。之后,她再也不敢去岗亭帮丈夫值班。
我见到柏太子时,他已经七十多岁。吕海生说话时,他默坐喝茶,听着,不发出任何声音,像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潜伏者。他瘦高个子,肤色微黑,身板坐得挺直。待吕海生说完,他沉默半晌,说了一句“那时候真是太苦了”,便忍不住抹泪,半晌不能语。
他从小没怎么干过体力活儿,没想到临近中年竟补上了这一课。他咬牙坚持,希望这一段艰难快快过去,早日柳暗花明。他期待有人领着他们奋勇向前,蹚出一条生路;他期待早日搬迁进城,让一切走向正常。“如果失去了希望,一天都难以坚持。”柏太子的目光闪着亮,像舞蹈的火苗。我感受到了那火苗的灼人温度。不绝望,不向命运屈服,这就是人生,也是生活。柏太子的经历让我感动,也给了我力量。这是人世间无声的抱团取暖。人与人,陌生或熟悉,都需要这样的鼓励,都需要一盏希望的灯。
他们被困在山里,紧张地关注着城里的搬迁建设情况。听说城里盖房没有钱,停工了,他们真是急了,绝望了,从山里跑到合肥,跑到省政府。省政府立刻派人接待,听他们的诉求,坚定他们的信心,然后派出几辆大客车连夜送他们回家。
这一番奔波,他们感到踏实,知道省政府一直在记挂着他们,并非孤军作战,身后还有党和政府。許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是感动,是委屈,还是难以言说的块垒,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4
1999年1月,新世纪前夕,皖东厂的人终于见到胜利的曙光,迎来命运的向好转折,全厂开始往合肥搬迁。柏太子听着鞭炮齐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厂里的汽车都已交给地方,职工只能自己找车搬家,费用由厂里报销。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谁不着急呢?大家找关系想办法,各显神通,只求有辆车能将他们的坛坛罐罐运进城里。
当地有人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希望厂里能多留下一些东西,帮助当地经济发展,或者说是对地方的反哺,毕竟工厂在这里待了三十多年。于是,山上倒下的大树将出山的路给拦住了。那天,工厂在灯光球场举行庄严的搬迁仪式,当地政府和公安都表态:为保证军工厂顺利搬迁,谁拦路就处理谁。
吕海生把家搬到合肥,又返回山里,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搬到合肥,仍然没有军品任务,暂时也找不到民品路径。好在职工的眼界变得开阔,活动范围宽广,谋生的门路也就多了。吕海生有驾照,去帮人开出租车,后来到一家单位值夜班,再后来帮江淮汽车制造厂送汽车。
皖东厂占地三百亩,在寸土寸金的都市,这是发展的看家本钱。经过协调,江淮汽车制造厂同意接收皖东厂。作为回报之一,江淮汽车制造厂免税三年。这样,皖东厂职工有了一个华丽转身,成为江淮汽车制造厂员工。
吕海生结束临时打工生涯,回厂上班。他被编入应急小分队,仍然是给客户送汽车。不过,他有了家的归宿感。
呂海生的岳父母都到了退休年龄。退休金先由厂里发,后转入社保,由社保部门统一发放。退休金不多,生活时常捉襟见肘,但是他们很满足,觉得自己身体好,还能出去找活儿干。老两口找到一家新单位,一个在食堂做饭,一个看大门。他们在军工厂多年,习惯于吃苦耐劳,连性子也变得像大山一样,坚韧而沉静。
2020年,吕海生把父亲获得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捐给渡江战役纪念馆,纪念馆给他们兄弟姐妹仨人每人发一个证书,奖励一千元。现在,吕海生、柏太子也早已退休。吕海生的女儿、柏太子的一双儿女都读完大学,各自成家立业。他们在家带着孙辈,享受天伦之乐。
山里的厂房、宿舍依旧矗立,成为见证共和国成长的一块小小的里程碑,也成为两代三线军工人听从召唤、无私奋斗的印证,更是吕海生、柏太子和工友们无法忘怀的思念之地。那里是他们奋斗半生的地方,他们曾经的骄傲自豪、困苦艰难、热泪汗水,他们的军功章,都默默矗立在那里。苍穹之下,青山绿水,向天而歌。
俄罗斯作家果戈里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还在说话。”那些静默的厂房宿舍,在诉说什么?向高山大地诉说什么?向后人和历史诉说什么?鼓角之音,渐行渐远,却依然清晰真切。天空中,我能清楚地看见小鸟飞过的痕迹。
5
夜色中的合肥,满城灯火,恍若银河闪烁。森林般的高楼大厦,撑开一个火树银花的世界。这座新兴的国际化、新一线大都市,如出水芙蓉,在夜色中妩媚动人、熠熠生辉。已是凌晨时分,我却浮想联翩,无法入睡。
我一直想看看皖东厂的厂志,想让那些历史的记载充实今天,与今天的现实相互印照。我询问多位相关人士,都说没有见过皖东厂志。我坚信一定有,因为我编写过所在单位的厂志。那是一个时期各军工单位的硬性任务。多方打听之后,有知情人士告诉我,因为经费拮据,皖东厂志只有一个手稿,没有印刷。前些年,这些军工方面的档案、志书等资料都被移交给了省档案馆。
我想,即使仅有手稿,那份手稿也会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我能理解厂志编撰者的心情,也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份遗憾和失望。
那天,我开车去位于滨湖的省档案馆。接待台后面坐着三四个年轻女子,我向她们说明来意。其中一个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原来在军工单位,现在写一篇文章想核实一些材料。她说,这牵涉到保密,不能给你看。我说,六十年前的往事,而且皖东厂已经不存在了。她说,那也不行。
我深感失望。在一些人看来,那些不过是冷冰冰的材料,他们不会知道那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后面,都带着两代军工人的体温和血汗凝成的情感。它们躺在冰冷的铁皮柜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太可惜了。
没有厂志作参考,这篇文章会少一些生动的颜色,却丝毫不会减少我心中的敬意,对历史、对两代军工人的深深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