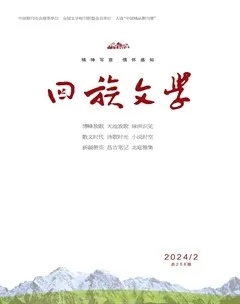九十岁到一百岁的距离
唐新运
许三爷终于死了,我以为他永远都不会死。
许三爷和我爷爷同岁,我爷爷已经去世多年。按照我的想法,他还没有活到他应该活到的岁数。他的身体向来没有大小毛病,饮食起居正如常人。他经常会有咧嘴会心不说话的一笑,有着好心情。他不乱吃东西,五十岁之后戒烟戒酒。儿女三人,孙子孙女绕膝随行。他只穿棉布衣服。他再没有重返故土安慰自己,是因为家里、手里没有余钱。七十岁之后,他还赶着毛驴车上田下地,爬到树上砍树枝搭凉棚。
我始终记得爷爷去世后的面部表情。我当时并不能够感受和理解失去一个亲人再不会相见的难受,还有疼,脑袋疼,心口疼,心里疼。当他是在睡觉,以为他还会醒来,打着一个接一个的哈欠醒来,舒展懒腰,左右晃动,东西摇摆。明天他一定醒来。他走了远路,看望亲戚。到底有多少亲戚,我没有数清楚,我父亲也没有完全清楚,但我知道,亲戚越多,说明我们这个家越来越好,除了人丁兴旺,还有六畜满院满圈,值得亲戚走动往来。他往南边去,他往北边走,不論离我们多远,他总会回来。哪怕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一个打雷闪电的黄昏,一段村里所有人都睡觉做梦磨牙放屁说胡话的凌晨时分,他沿着黄土小路从远处而来,鞋靴泥浆,胸前背后,挨家挨户寻找,找自己的家,找自己天天都睡在上面的土炕、木床。他走在路上,他的右臂和肩膀擦过我们从来都没有触碰的土墙,尘土半身,终于敲开院门。手里提灯,一盏马灯,风雨不侵,不惧霜雪寒冷。
爷爷不痛不痒,无喜无忧,静静躺着,和前些年在大炕上沉沉入睡没有什么区别,和前些年在树荫下毛驴车上偶尔翻身也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我的耳边,还有轻微鼾声。那时候,我却睁大了眼睛,月亮正圆,星星眨眼。爷爷最大的那两颗门板牙没有提前商量,照样一前一后,还挤左右邻居。挪一挪,让一让,邻居只能左右前后,所以,我们那个村子,再怎样刷牙,牙齿都不整齐,也不排行。再怎样刷洗,也只能前后,却不能左右。
我爷爷被风刮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却根本无能为力,他可能有安顿和交代。还有些事情,他可能背过我们说给了许三爷,细细地说,慢慢地讲。他一定说了,二十岁有二十岁的狂妄嚣张,三十岁有三十岁的乐趣,四十岁有四十岁的话题,等到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可能也有安排,可能也有约定。
许三爷的老婆是我的许三奶啊,一个大个子女人,面如满月银盆,可小脚三寸,永远都没有长大。我奶奶也是小脚,可她背过许三奶泡脚梳头剪趾甲。她能在中午到下午的那段时间,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慢慢耗费光阴,光阴陪她,她伴光阴。她泡脚,把脚泡得仿佛肿胀,发白,把趾甲泡软,用剪刀细细剪,慢慢磨,抠、挖,还有挑。当然,她要先一层一层一圈一圈拆开她的裹脚布;当然,洗完后她还要一层一层一圈一圈把布裹在脚上。她说自己忍不了自己的脚疼,趾甲剜进了肉里。她的洗脚泡脚剪趾甲,从来都没有告诉过许三奶,所以,许三奶走路会一瘸一拐,但我奶奶一直都没有大病小灾。她脸上有红晕,多年不变黑灰色的便宜衣服总是干净整齐。我们天黑时分回家,劳苦一个整天,有时候还要加上一个整夜,她就站在我家墙后门前,向左看,再往右看。她照看着我们的这个家,看有没有埋火,看有没有锁门,看有没有人把锅从灶上搬下来,急急快快走回去在锅里撒盐加醋。
人忙的时候,就会忘记好多紧要的事情,牛的水够不够,羊的草还多不多,猪前些天把圈墙拱倒还没有修补。一场大雨落下来,究竟是往南流呢,还是向北淌,最好不要流进我家院子。如果这雨水过大,三天三夜都不会停,还水汪汪亮晶晶泛起水泡,简直成河,出门的时候免不了滑倒和摔跤,就算是没有倒,也会弄脏鞋面裤脚。她也忘不了,小儿子要攒够力气新修房子,那房底子周围的树,种的是什么树,这些树在哪天,在什么时候才能长起来,洒下阴凉。她能不能等到那一天,等到树长起来,新房子盖起来,炉灶不冒倒烟,砖混墙壁干透,没有灯光借着月色星亮解手,如常回到床上的那一天。
我爷爷和许三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美男子,许三奶为什么没有选择我爷爷而选择了许三爷。他们来自一个原乡,一片故土,相邻而居,相距只有十里,有相似无二的一对父母,也有年龄相仿的姐妹兄弟。
我奶奶做了些什么啊,她是不是背过我爷爷做过些什么?我奶奶和许三奶高矮胖瘦差不多,长相也不相上下。我爷爷为什么选择了我奶奶,却没有选择许三奶。我有时候又在想,万一选择了许三奶,我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我,我的背后、脚掌、胳膊肘、左边屁股、脖子和肚皮上的痒,还有肉皮一样颜色的瘊子和黑色的痣,就不会和父亲一模一样,多多少少都有我奶奶的印迹和留痕。我们不是一个种,也不是一个人,我们没有长在同一根瓜蔓和藤条之上,那怎么我们就居然成了一家人。
没有了奶奶,怎么会有我父亲,怎么会有我啊!随着年龄渐长,我们说话的语气、声音,走路摇摆的姿势,穿着打扮的喜好,钟情在意的颜色,多加的醋和少放的盐,都和父母越来越像。
前几年,我回到这个村庄。只要我和我父母离房子越来越近,还没有打开院门,许三爷就会出现,因为他听到了狗叫。狗一叫,人就会出现,狗叫专门就是为人现而生。人,如果没有狗的陪伴会感觉到孤单。狗见到生人才会叫,见到熟人一声不吭,会摇尾巴。远远地看着你,将一泡热尿撒在树下。
我听父母说过,我也见过,许三爷已经活到了九十三岁。我不相信,可是我父母怎么可能骗我。许三爷拄着院子旁边榆树丫杈砍削的榆木拐棍一次次走到我跟前的时候,他顶多五十二,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三。他和我爷爷当年一模一样,除了黑灰色衣服,也有笔直的鼻梁,还有龇牙咧嘴的笑,还有白中泛黄的门牙。他们从来都没有刷过牙,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闹龋齿牙疼,也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智齿恼人。他们从来没有商量过,却不约而同地在人多处从不说话,人背后偷偷发笑。他们都知道了好多事情,他们也觉得可笑,可从来都不开口,更不可能会去说破。
我觉得许三爷会长命百岁,至少能活到一百零五岁。我没有奢望他活到八百岁,如果他活成了神仙妖怪,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我们的相见,那会是天上一片任意飘过的云彩,是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刮过的风,片刻不留,疾行赶路。我爷爷都已经活了这么多年,再活几年,十几年,又惹了谁。我爷爷提前上路,他没有活够的岁数,他就不能让给许三爷,让许三爷用吗?让许三爷多活几年,帮他和替他,看这个世界,见人,听声音,闻饭香屁臭,看天地之间的从未经历,还有新人落地,一直都喜欢吃的豆腐、油糕,一盘从来都没有吃饱过、吃厌倦的面,把爷爷从来都没有传过的闲话传一传,把他还没有来得及捣的是非捣一捣。可是,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人啊!他们说的事情,都是村里的大事情。
许三爷的这一死,村里好多年前去世的人,知道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村庄,就此掩埋了那些曾经穿梭其上行走其间的人,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名字,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发出的声音,他们的恩爱情仇,还有穿过的衣裤鞋袜,全部埋在了黄土之下。黄土之下,草头之上,再过去好多年,连许三爷都没有人会知道,更不会有人记起。许三爷的后人,也照旧如常一天比一天更老。他们无法抵抗和拒绝,父亲在前面的招手和回头。
一个人的真正死亡,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死亡。这一刻将是真正的死亡,从此不会有人知道你来过这个世界。
许三爷知道谁,记得谁。在离开之前,他肯定默默地数了一遍。
许三爷的这一死,这一离开,这一被风刮走,我们这个村庄,就此简直坍塌,没有哪个人,再没有哪个比他更年长的人,能够顶天立地般撑起这个村庄,像他一样小心谨慎地守护着这个村庄。村里人都在午睡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东北方向的墙根之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那个地方高,高出我们常走的路半米有余,他能看到每一张陌生的面孔。他熟悉经过的所有羊群,认识每一张羊脸,哪一群羊是常住久居,哪一群羊是来往过客,哪一群羊还在犹疑,该走过去还是留下来,这里看起来水草丰美,前面是不是还比这里水丰草美。夜深人静,许三爷不会睡死,更不会死睡,他半睁半闭着眼睛,天是黑的,窗户玻璃映了清亮月光,可他的耳朵却能听到老鼠打洞、蚂蚁赶路的声音,不会错过蚊子求偶的声音,准备随时起身。我爷爷在世时,也比不了他操的心。因为他操的心多,他不能和我爷爷同行,他还有自己没有做完和安顿好的事情。
这个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年纪大的更是越来越少,等他们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没有人再记得和知道这个村庄的前世今生,那这个村庄就真的从这块地上消失了,正如它当年的生发,也如它如今的死亡,从头到尾,都和唇边的饭粒一样,随手一擦,就再不可见。
他死了,我可怎么办呢?我回去之后,找谁说话?狗还会叫,那个人却再不见了。再过几年,那狗也会老去,衰老到叫不出声来。我站在房前屋后,再等不到那些熟悉的足音,干咳无痰,榆木拐棍,外凸门牙,和我爷爷一模一样铜腿的石头眼镜。
从九十数到一百,我的孩子顺口就可以滑过;从九十块钱数到一百块钱,我只要沾点口水动动手指;可从九十岁活到一百岁,怎么就那么难啊!难道是许三爷自己没有使劲吗?我觉得许三爷自己也根本无能为力,他使了劲,他使的劲是他每天长出的力气,吃的饭,喝的水,晒过的太阳,轻拂过的风,打湿裤脚鞋面的露水,还有,许三奶满月银盆脸的映衬,暗地里的出力鼓劲。他使的劲去了哪里,怎么就不能把自己从九十往一百推一把,搡一下,怎么就不能把一百按住只向后不往前。
有些人,再怎样攀爬,都不能到达山顶;有些人,手脚并用,还是够不到树梢。是什么原因啊?我想来想去,原因只有一个,天生就这个品种。瓜就是瓜,豆就是豆,洋芋和萝卜都长在地下,可圆洋芋永远都不会變成长萝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