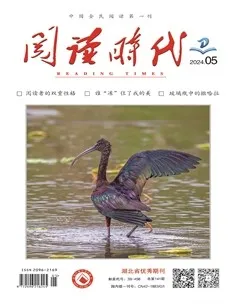紫鸿班
周吉敏
一
赣地的乡野,在我心里一直有陶潜的隐逸之气。癸卯仲夏,我走进赣东北的金鸡村,那里果然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山中夏日长。村里请来横峰镇牛桥村莞草池的紫鸿班来演木偶戏,戏词被风带着,在村里到处走:“恨苍天,害得我双眼失明……”演的是一个孝道伦常的故事,木偶戏把行孝的因果仔仔细细演绎出来让世人看。
戏中的不孝媳鲍氏被丈夫打了一顿,负气回娘家,途经关帝庙,神灵见这女子是如此一个恶人,就把她变成一条狗。丈夫向关帝百般求情后,鲍氏才变回了人形。此后,鲍氏再也不敢苛待公婆了。
世事沧桑,才有了戏。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成了戏。芸芸众生皆是戏中人。木偶戏与真人戏是戏曲古藤上的双生花。木偶戏被称为“戏曲之祖”,妙在模仿人,妙在各种机巧中闪烁着灵性。
那提线老旦的是一位男子,40岁开外,七尺身躯,面色黧黑,眉宇间却有一股戏文浸润出来的书生气。提线小旦的女子,粗朴中有细腻,似山野间的紫薇。他们右手操线盘,左手手指把八九根细长的线钩来引去,台上的木偶随之举手、投足、扑倒,再爬起、坐下、站立,仿佛真人表演。观者近在咫尺,却看不明白其中的机关所在,唯望而赞叹。
赣地的木偶戏唱的是赣剧。“老旦”一开口,那嗓子浑厚沧桑,仿佛被江流冲刷过。“小旦”演的是恶媳,音色中有一种霜凝寒枝的凛冽刺骨。这赣剧的声腔里流淌着一条大河,沿岸的村落、田园、红壤、丹山都可以被细细品味出来。
村人这边围着看戏,那边围着做灯盏粿。大人小孩忙活着把捣好的糕团捏成一个个灯盏的模样,然后在盏心里填入南瓜、肉丝、豆芽、辣椒做的馅,再上笼屉蒸过,撒上葱花,红红绿绿的,煞是好看。一口咬下去,美食落入腹中,田野的芬芳久久不散。戏声裹着米粿的香气,何尝不是信江两岸日出日落的滋味呢?
二
木偶戏灵活轻便,适宜在山区表演。横峰多山地,也就多木偶戏班,当地人叫“吊戏”。真是乡语生动见风情。
据说,横峰木偶戏从邻近的玉山传入。玉山在浙赣交界处,是江西与浙江的陆上交通要道。旧日,从玉山转陆路80里可至浙江常山,而后进入钱塘江水系。南宋城破之际,临安勾栏里的诸色伎艺人散入赣地,他们是花瓣也是种子,几度春秋,又会长成一棵花树。元代诗人贝琼曾见过它繁花似锦的气象。
大概是元末明初的一天,贝琼到玉山游玩。这位浙江桐乡人从常山走山路进入玉山。在玉山,贝琼看了一场窟儡戏,还写下一首《玉山窟儡歌》:“玉山窟儡天下绝,起伏进退皆天机。巧如惊猿木杪坠,轾如快鹃峰尖飞……”简直是对戏的现场直播。那场戏演的是汉高祖平城之围,是一部历史大剧。能担当如此大戏、能有这么高的演艺水平的,应是临安来的伎艺人或是他们的后裔子弟。
紫鸿班供奉着“杭州风火院铁板桥头二十四位老郎先师”的牌位,与赣剧的戏祖同一来处。这二十四位先师应是最早从浙江进入江西的伎艺人。他们担着戏箱跋山涉水,来到相对繁荣稳定的江西讨生活,带来赣地戏曲文化的繁荣。
三
莞草池自古就是个“戏窝子”。清时有七个木偶戏班,紫鸿班是其中一个,也叫“老七班”。莞草池这个地名不由让人想起《诗经》里那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地方。“莞”是水葱一样的植物,可以编草席。戏也恰有伊人在水一方的意境。
一路上青山连绵回环,仿佛试图阻挡外人进入,路边的狗尾巴草却像旧家的小狗迎着人来。莞草池所在的牛桥村的文化礼堂在一片开着紫薇花的山坡地上,正是紫鸿班的驻地。周就锋是紫鸿班的团长,周就云是那天在金鸡村表演老旦的男子。他们给我看祖传的木偶——十几个木偶落满时间的尘垢,斑斑驳驳的。“他们”在橱窗里笑着、皱眉头、怒目、调皮眨眼……表情的鲜活与外表的陈旧,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时空交错感。
这些清代的木偶,身形比现代的木偶高大,雕刻手法稚拙粗朴,勾描技巧如童子笔意,五官与神态更接近生活中的人。这些木偶没有现代木偶已经程式化了的艺术脸,想来是按着真人戏中某个角色的扮相来制作的,这也是当时艺人们唯一可以参照的对象。
我还意外地看到二十多张纸糊的戏剧面具,每张只有手掌般大小,白底,红、褐、黑三色勾描,有大花脸、小花脸、阴阳脸、狐狸脸、猴子脸等等,涂画随意粗陋,能想象它们是出自一双怎样的手。周就锋说,木偶不够才用面具来代替。
紫鸿班还保存着多部手抄剧本,有《龙凤阁》《龙凤配》《拾福天官》等,笔迹各异,字迹也不端正,文中可见许多错别字,一看就是出自民间艺人的手。这些密密麻麻的戏词里,藏着古老的戏音。
穿过一条花草鲜美的乡道,看到绿树浓荫中的莞草池。溪流穿村而过。风里满是稻花的香气。再过几个月,谷子就可以收割了。从前,秋收后稻茬干净了、落了霜,戏班子就会进村来,戏文在村子里传播開来。咿咿呀呀的唱腔,无论高亢还是绵长,都让人的血气涌动不似平常日子。
据《横峰县志》载:紫鸿班于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由莞草池人周添兴创办,后来传到周就云的曾祖父周德标、祖父周春芳以及外公严邦茂那里,他们带着那些木偶、面具和剧本,一次次从莞草池走出去,走过千山万水,历经世事沧桑,人与戏最终都藏进了莞草池的时光深处。
传统如干燥的种子,遇上适宜的雨水总会发芽。2015年,周就锋打开了周家封存了半个世纪的戏箱。第二年暮春,他找了村里8个志同道合者重新组建紫鸿班,是为第六代传人。那时,他93岁的外公、曾经的优秀鼓手在一旁看着他们排练。第二年,老人就走了。
周就锋和周就云给我们表演了《西游记》中《猪八戒背媳妇》的一段,安静的村子顿时锣鼓喧天。回去的路上,想起周就锋说的话:“现在木偶戏已不是一个行业,赚不来饭吃了,更多的是传承,是情怀。”他眼中的无奈一闪而过。但也正是民间艺人在困境中的坚守,让传统文化的根脉源远流长。
(源自《解放日报》)
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