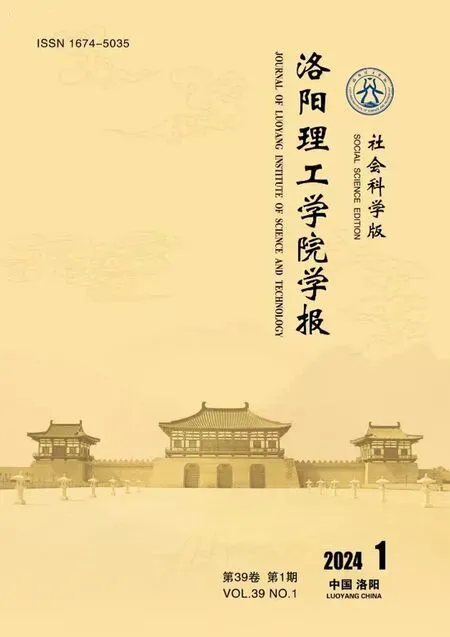河洛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及时代意义
陈 智 宇
(洛阳市司法局,河南 洛阳 471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不断取得理论创新的成功密码。在法治中国建设伟大进程中,更加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紧密结合,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注入更多源头活水,是新时代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洛阳是蜚声中外、名重天下的世界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称为“华夏之源”“最早中国”。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诞生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作为河洛制度文化的基本内核——河洛法治文化也同样孕育、形成和发展于此。河洛法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产生的法治思想、法治理论、法律制度、法治实践等法治文明的总和,是河洛制度文化的基本内核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法治文化的源头和主干。推动河洛法治文化研究,对加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法治文化最早孕育、形成和发展于河洛地区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河洛地区是我国最早进入文明形态的区域之一,孕育了我国最早的法治元素,诞生了河洛法治文化。河洛法治文化滥觞于史前,奠基于三代,完备于周秦,成熟于汉唐,余绪于宋元明清,传承有序,脉络分明。
(一)我国最早的法治形态萌芽于河洛地区
在距今大约7 000~4 700年,河洛地区进入仰韶文化新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与三皇五帝传说相对应,而三皇五帝活动的区域基本都在河洛地区。三皇时期,河洛地区已率先出现法的基本要素——习惯和规则。传说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司马贞《三皇本纪》记载,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君书·画策》言:“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所谓义礼就是基本的社会规则,刀锯就是指最初的刑法。五帝时期,河洛地区已经出现了原始法律形态即五刑和专门管理机构,以及“士”官职。帝尧晚期,舜乃“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1]29帝舜命皋陶作士,开启了我国历史上以法为政的时代。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1]46“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1]50。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法治神兽传说也最早诞生并流传于河洛地区。王充《论衡·是应》记载:“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今洛阳栾川县仍有以獬豸为面具的独角兽歌舞表演,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我国最早的法律制度奠基于河洛地区
夏、商、周时期,河洛地区率先进入国家形态,法律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产生。《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说明已有专门的成文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周礼·秋官司寇第五》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郑玄为之作注:“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诸侯同。”[2]1873这说明国家均已设立刑官。特别到了周代,中央政府在大司寇、小司寇下边还设了士师、乡士、遂士、县士、司刑、司刺、司圜、掌囚等官职,说明周代已经形成了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互相制约的司法管理体系。
我国最早的监狱出现于河洛地区。早在虞舜时,刑官皋陶就曾建造监狱,战国典籍《尸子》言“听狱折衷者皋陶也”,皋陶是我国古代的狱神。《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第七代王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夏桀还曾将商族首领汤囚禁在夏台。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狱名,夏曰钧台”,即在今天的河南禹州境内。商末,“帝纣乃囚西伯羑里”[1]151。羑里在河南汤阴县。到了周代,监狱分为拘押徒刑的圜土和拘押重犯的囹圄。郑玄在《周礼·秋官司寇第五》“遂士”后注:“其职云掌四郊,四郊有六遂之狱故也。”196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发掘东汉刑徒墓地500多座,位于汉魏洛阳故城的西大郊村[3]。
(三)我国早期的重大法治事件大多发生于河洛地区
兵刑之法起源于河洛地区。法既起源习惯和规则,也起源于最初的部落战争和诸侯征讨。有了战争,军令和军法也随之诞生。《国语·晋语六》记载,“君人者,刑其内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和而外威。夫战,刑也”。《国语·鲁语上》也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这说明在夏商周时期对内用刑和对外用战本质是一样的。《尚书·甘誓》记载,夏启继位后,诸侯有扈氏发生叛乱,启率兵征讨,大战于甘地。关于甘之战的发生地,有学者指出在洛阳丰李镇甘泉河流域的古甘国[4]。此外,《汤誓》的发生地陑,《泰誓》的发生地孟津、河朔,《牧誓》的发生地牧野等,也都在河洛地区。
周公制礼作乐作刑于洛阳。武王灭商之后,周公奉命营建洛邑。《尚书·洛诰》说:“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在制礼作乐的同时,周公借鉴上古及夏商治政经验,在五刑的基础上又作九刑:墨、劓、刖、宫、大辟、流、赎、鞭、扑。《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了鲁国大夫臧文仲的一段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赃,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2]4041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作刑真正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基础,为我国三代时期的礼乐文明向秦汉之后的礼法文明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郑国、晋国铸刑鼎也发生在河洛地区。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为适应封建社会新型生产关系,先后制定本国法律,成为我国古代法制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鲁昭公六年(前536)三月,郑国大夫子产铸刑鼎,成为诸侯国立法的首次记录。公元前513年,晋国大夫赵鞅、荀寅也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冬,晋赵鞅、荀寅率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西晋学者杜预注:“汝滨,晋所取陆浑地。”[2]4614陆浑在今洛阳嵩县。
(四)我国法家代表人物和法治理论大多诞生和形成于河洛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河洛地区进入百家争鸣时代,以推动社会改革为主的法家代表人物和以刑名法术为代表的法家理论,逐步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郑国大夫子产铸刑鼎、作丘赋,开郑国法治改革之先河,与其同时期的邓析作竹刑,成为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私人制定律法、帮人代理打官司的第一人。战国时代,法家理论逐步在河洛地区形成流派。韩国的申不害是法家重要创始人之一,著有《申子》一书。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用他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诸侯不来侵伐”[1]2263。主持魏国变法的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是魏国安邑人,曾著《法经》,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主持秦国变法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卫国人,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商君书》中。还有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丞相李斯,为楚国上蔡人。《史记·李斯列传》言:“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斯皆有力焉。”他在上秦二世的《行督责书》中建议秦二世要“明申韩之术,行商君之法”。由此可见,李斯也是继商鞅之后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
(五)河洛地区的古代法治文化遗存
目前,河洛地区仍有不少古代法治文化遗存。一是洛阳周公庙。该庙是纪念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周代洛阳城的缔造者、中国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姬旦的祠庙,又称元圣庙,始建于隋末唐初,现为全国四大周公庙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是宜阳县甘棠村的召伯听政处。召伯姓姬名奭,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弟弟。《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唐张守节为之作注:“召伯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1]1877今宜阳香鹿山镇甘棠村有“召伯听政处”碑,为清雍正二年(1724)河南府尹张汉题写、宜阳县知县郭朝鼎立。三是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该馆现有文物藏品6万余件,主要包括房田契约、诉状、合同、分单、遗嘱等司法文书数十种,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宗法制度、法律法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情的重要实物。四是法治类墓志碑刻。河洛地区长期作为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上地下保留了大量的墓志碑刻,其中具有法治、司法、刑狱、契约性质的数量可观,年代从秦汉至明清。例如,1990年在河南偃师城关北窑村出土东汉永平十六年(73)姚孝经砖铭,是截至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买地券。据《东汉时期墓券的内容与类别》一文介绍,目前国内已经公开发表的东汉墓券108件,其中洛阳出土30件,占总数的27%。东汉洛阳刑徒墓地共出土刑徒砖832块,对徒刑犯的姓名、籍贯、罪名、刑期和死亡时间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内容涵盖永初元年(107)四月至永宁元年(120)共13年时间。还有,2008年在洛宁县发现的清道光十六年(1836)的“村规民约”碑,在孟津区发现的清道光十一年(1831)的“狱空三载”碑。这些都为研究河洛法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河洛法治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
文化既有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也有制度层面,而制度则是文化的基础和内核,在文化的发展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河洛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始终引领中华文化发展潮流,与其先进的制度文化是分不开的。《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如果说礼乐制度是河洛制度文化的“阳”,那么法律制度则是河洛制度文化的“阴”,二者相辅相成、相生相依。河洛文化的发展一直影响和规定了河洛法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河洛法治文化又为河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法制基础。可以说,河洛法治文化是河洛制度文化的基本内核和重要组成部分。
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易经文化是河洛法治文化的思想源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是易经文化起源、发展的摇篮。易经既是河洛文化的思想源头,同样也是河洛法治文化的源头。在易经六十四卦中,就有一些卦象、卦辞和最早的刑、法有关。《蒙卦》曰:“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这说明刑罚对于国家治理的必要性。《讼卦》有“讼,有孚。窒惕。中吉。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息讼无讼思想。《师卦》曰,“初六:师出以律”,强调了法律对军队出师作战、严肃军纪的重要作用。此外,《噬嗑》《丰》《贲》《旅》《中孚》《解》《豫》等卦中都蕴含了许多法治思想[5]。特别是易经所包含的阴阳互补的辩证思维、阴阳五行的运行法则、阴阳和合的价值理念等,对河洛法治文化中德法相依、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出礼入刑等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司法制度方面,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秋刑制度,也与四时五行有很大关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礼记·月令·孟秋之月》记载:“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2]2972在案件审理方面,西周时期实行“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等五声听狱制度,要求刑官从言辞、神情、呼吸、听觉、目光等五方面去了解当事人的心理活动,这也是阴阳五行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2]1887。
礼乐文化是河洛法治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河洛法治文化又为礼乐制度、礼法制度、宗法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6]1028。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作刑,创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礼乐制度、礼法制度和宗法制度,目的是“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既有“礼经三百”,又有“威仪三千”,充分体现了周公敬天以保民、制礼以序民、作乐以和民、宽政以惠民、省刑以恤民的政治思想。礼中有乐、礼即乐,礼中有法、礼即法,宗中有法、宗即法,礼乐一体、礼法一体、宗法一体,这是河洛法治文化也是中华法治文化的独特现象。到了汉唐时期,不仅“引礼入法”,说经以解律,而且还创造了“《春秋》决狱”的司法模式,礼乐成为最高的立法依据和司法标准,长期影响我国的司法实践。与此同时,在礼乐制度影响下的法治理论、法治体系又为封建社会礼乐制度、礼法制度和宗法制度的长期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儒家思想在相当长时期内规定了传统法治的走向,法治的完备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西周初立,周公被封于鲁地。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作刑,其后人即以礼乐政刑制度治理鲁国。春秋时期,孔子习得礼乐,并来洛问礼求教,是为儒学之初兴。两汉时期,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价值观,这一转变影响中国古代法制的走向。西晋时期,杜预、张斐在为《晋律》作注疏时,强调要重“理”任法、以礼率律,使引经入律的理念得到强化。近代学者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7]115
天人合一思想对河洛法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河洛法治文化又对统治阶级君权神授、君权天授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强化。“天垂象,圣人象之;河出图,圣人则之。”以天应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价值判断,同时也沦为统治阶级维护皇权的工具。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天命”“天理”,以“天命”“天理”为制定法律的最终依据,树立了“则天立法”的最高原则。因此,《尚书·皋陶谟》中有“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的记述。《汉书·刑法志》说:“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制五刑。”这说明统治阶级在制定刑罚时,往往以天理、天象为准则。而在这一准则指导下的法律,又进一步维护了天意不可违、皇权不可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地位。《孔子家语·五刑解》记载:“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
三、河洛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河洛地区诞生的河洛法治文化,不但是河洛制度文化的内核,更是中华法治文化的源头和主干,古圣先王为其开纲立目,周公姬旦为其奠基集成,刑名法家为其黻黼堂奥,儒家文化为其导引前行,法制理念先进独特,法学理论自成体系,历代法典系统完备,长期成为古代社会的制度之基,始终居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地位。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核心价值
法产生于阶级社会,必然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主导和影响。夏商周三代,敬天保民成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史记·夏本纪》记载:“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通过皋陶与大禹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虽然认为刑法的作用在于“天讨有罪,五刑五用”,但其目的还在于惠民、安民。此外,《尚书·大禹谟》中“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及《尚书·康诰》中的“用保乂民”“用康保民”等民本思想一脉相承。民本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正因如此,我国在古代立法、司法实践中才有了重民、宽民、恤民的原则。
(二)礼乐政刑、四位一体的治理结构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既重视礼乐的教化之体,又重视政刑的管理之用,四者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形成我国历史上独特的社会治理模式。《史记·乐书》言:“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于治道也。”《汉书·礼乐志》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誖,则王道备矣。”帝尧之时,“流共工于幽陵,放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1]34。“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1]1382。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在治国理政中既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又重视政刑的规范作用。
(三)以德为先、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
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就认为,治国之术有二,一是德,一是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手段,便是刑赏结合:“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国君有意识采用赏罚督责官吏、管理百姓,是为“刑德二柄”:“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刘向《说苑》言:“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西汉洛阳人贾谊在《新书》中也说:“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在德与刑的关系上,始终坚持以德为先、德主刑辅,将刑罚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手段。
(四)明刑弼教、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
《尚书》是我国最早记录帝王之政的经典,其中蕴含许多重民生、慎刑罚的法治思想。《舜典》记载了虞舜“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的恤刑思想,《大禹谟》记载了虞舜“明于五刑,以刑五教”的明刑弼教的思想以及皋陶“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宽刑思想。这些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沿袭和继承。《尚书·康诰》记载,周文王“明德慎罚”“显用俊德,慎去刑罚,以为教首”,最终能够顺应天意、民心归附、一统天下。在这一司法原则的指导下,历代都实行宽刑慎罚的法律制度。《周礼·秋官·司刺》就制定了“三刺三宥三赦”的定罪量刑制度,“以赞司寇听狱讼。壹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2]1902。也就是说,国君在审理大案要案时,必须和群臣、群吏甚至是百姓反复计议,然后定罪判决,以示审慎。《隋书·刑法志》评价“周王立三刺以不滥,弘三宥以开物”,出现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1]171的政治局面。
(五)条律完备、传承有序的法典制度
法典制度是我国古代法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唐律疏议·名例律》记载,战国时期魏国人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国已有成文系统的法典,后来的秦律、汉律等无不承袭其制。曹魏末年,晋王司马昭修订律令,史称《晋律》或《泰始律》。唐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组织人员编写《永徽律》12篇、502条,亦即《唐律疏议》,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法律的集大成者。宋建隆四年(963)编修《宋建隆详定刑统》,经宋太祖下诏刊行天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此后的《大元通制》《大明律》《大清律》也都因循传承了这一重要制度[7]171。
(六)法平如水、唯明能信的法德思想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法”做了最为贴切的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造字之初,便赋予了“法”字法平如水、唯明能信的道德价值。《史记·五帝本纪》《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命皋陶作士,要求他做到“惟明能信”“惟明克允”。《尚书·益稷》也记载“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形成了比较完善、丰富的法德思想,概括起来是:清正廉洁,公平公正,法不阿贵,公私分明等。在《慎子·君臣》中,战国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认为,君主治理国家要做到“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在《韩非子·有度》中,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春秋时期,晋国的大理狱官李离因过失错判人死罪,晋文公有意赦免他的死罪,但他却说,“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1]3771,遂以自杀谢罪。在《后汉书·董宣传》中,东汉洛阳令董宣因执法不避皇亲国戚,被汉光武帝称为“强项令”。今洛阳老城区仍有董公祠、董公槐等遗存。宋代司马光在上书皇帝《论正家上殿札子》中说:“仍敕公主,若屡违诏命,虽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
四、河洛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河洛文化与黄河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讲,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历史定位上讲,河洛文化则是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长期处于主导和正统的地位。河洛法治文化作为中华法治文化的源头和主干,也同样具有根源性、系统性、独特性、创新性、先进性等文化特征。
根源性。所谓根源性,一是指在诸种文化中发端时间最早,对文明发展方向有引领作用;二是指作为文化核心的思想富于原创性。河洛地区孕育了我国上古时期最早的法治形态,产生了我国最早的法律制度,发生了我国古代重大的法治历史事件,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法家学说,河洛法治文化无论是在制度、思想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引领性。
系统性。河洛法治文化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河洛大地上诞生了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法家理论,建立了连续不断的制度传承,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司法实践,而且这些思想、理论、制度、实践一脉相承,延绵不断,自成一体,具有系统、完整的东方法学话语体系。
独特性。河洛法治文化诞生于河洛地区,根植于中华大地,深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浸染和滋养,经过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发展成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它既不同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也不同于印度法系和伊斯兰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形成于中国本土,但其影响力遍及东方相邻国家,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产生影响。特别是《唐律疏议》作为代表性的法典,成为东亚各国的“母法”[8]。
创新性。法律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必须因时因地而制、不断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司寇的职责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韩非子对这一思想做了更为全面地阐发:“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这就是说,制定法律只有随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才能实施有效治理。从这一角度讲,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既有传承,也有创新。虞舜夏商时期作五刑,周公因之而作九刑。魏国李悝“集诸国刑典”制《法经》,汉代萧何在此基础上增加户、兴、厩三律,编成《九章律》。这些都是中华法治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典型代表。
先进性。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在司法原则上,我国早在《尚书》中就提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罪疑唯轻的概念,这比西方的疑罪从无的原则早了2 000多年。在西方,欧洲到了18世纪才真正确立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观念和司法规则。再如,召伯甘棠听讼创立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司法审判和司法调解模式,真正实现了罢访息讼、定纷止争。还有,我国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五声听讼”的司法制度。这些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
五、河洛法治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
河洛法治文化有着弦歌不绝、体系完备的法治历史、法治思想、法治理论、法治人物、法治事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先进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推动河洛法治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中国特色、时代价值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契合性,对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深化河洛文化研究。河洛文化研究30多年来,学术成果丰硕。但在制度文化研究方面还有欠缺,特别在河洛法治文化方面仍是一个新领域。推动河洛法治文化研究,有利于河洛文化的多学科交叉交流,有利于丰富河洛制度文化的新内涵,有利于从时代价值出发找到更多河洛文化研究的契合点和切入点。
二是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新转化。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话语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深化河洛法治文化研究,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法律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多文化底色和中国特色。
三是有利于提升洛阳在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部署,提出建设黄河法治文化带的重大战略。洛阳作为河洛法治文化的主要起源地和核心区域,应加快建设一圈(河洛法治文化圈)、二区(黄河法治文化传承发展核心区和黄河法治文化价值弘扬地标区)、三带(生态法治文化带、水利法治文化带、景区法治文化带),努力打造黄河法治文化带主地标城市。要认真研究梳理河洛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和时代价值,搞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叫响河洛法治文化品牌,促进法治洛阳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