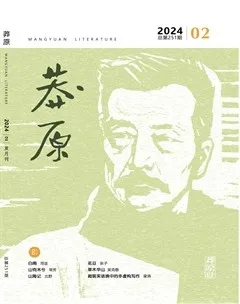乡村音乐
钟扬
说 书
评书,琴书,三弦,大鼓书,坠子书,在古城许昌以西统称为“说书”,流传最广的是河南坠子。它的说文唱词就是日常土话,插科打诨皆用乡野俚语,主打乐器是坠胡,比板胡大,比二胡圆,音色也融合了两者的优点强项,喜调高亢澎湃,悲声沉郁低回,恰恰托住了唱者的土音老嗓。
说书者多为主辅两人。辅者全场站姿,一手简板,一手鼓槌,司职节奏;主唱手把坠胡,足蹬脚梆,四五种乐器联动,说唱交互,好书场营造出的氛围,不输戏台。说唱组合多有盲人,老天忘给一双眼,却送他伶牙俐齿。口口相传,耳听心记,十几年苦学徒下来,脑袋里已装下几十部书。绕口令,颠倒话,滚口白,七字五字韵;开场书,歇场书,压场书,张嘴就来。那把日影夜随的老弦子,经过多年捋摸拿捏,油浸脂润,包浆幽光沉静,滑熟可喜,操持起来,熟同碗筷。
小户大喜,大戏不敢想,锅里多添碗水,请书匠说场《劈山救母》;大户小喜,非年非节,把说书的接到祠堂,唱半本《呼延庆打擂》;场光地净,下大啦,麦罢啦,谷子秫秫长大啦。当年风顺雨遂,几大姓主事人一碰头,从族资中匀出半斗玉米,听段《割肝救母》;冬日天短夜长,这时候已到生产队主事,遇有说书人来到村上,队长一咬牙把饭派了,点名要听《烈火金刚》,飞毛腿肖飞英雄孤胆,大白天单闯敌营。
说完一部书要六七天,三两晚的书,只能隔山跳界说精华,单场书往往是同一类型几个小故事。书好书歹,全凭说书人的本事能耐,称心了,沉入其中;不对耳,书场也是热闹场,漫漫长夜,困时已到深更。
再好的书,也不会一直说下去,开场、歇场、终场,两三个钟头。说慢了,干货稀释得不见踪影,众人昏昏欲睡,还不到半场,人就散了;说急了,早早结束,有敷衍了事之嫌,牌子砸了。高明的说书人都会聚拢气场,设伏笔,抖包袱,起承转合,成竹在胸;差错难免,肚里有的是垫场书,随用随上,依然行云流水,从不显短露怯。
乡下时光金贵,书大多在晚上听。
鸡上宿儿,牛羊进圈,灶房碗筷消停下来,一家老小提椅捉凳,汇向“书场”——碾盘旁,古槐下,麦场,牲口屋,今晚是三通间大仓房。现在,天已全黑,书桌上,碗灯豆黄,灯影摇曳飘忽,只能照见说书人眉眼脸面——这就足够了。辅书人缓缓举起枣木简板,一连串“哒哒”脆响,惊飞檐下夜雀;鼓槌飞花,皮鼓震响,荡起的烟灰、土雾喧腾;坠胡“嘶啦”声起,脚梆欢快插入,器乐先缓后急,刹那间,疾风暴雨冲向房顶,将达巅峰之时,戛然而止。满场气屏声息,说书人轻抻长臂,中三指夹起核桃大小惊堂木,“啪”的一声,听客不觉伸头仰脖,感觉有碎物落下,少顷,目光齐刷刷落在说书人黄灿灿的阔脸上。开书了。
今晚书说《小将杨宗英大战金兵》,说唱人是位硕壮盲人,肩宽臂展,声大气粗。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照例,盲汉开始暖场,句式合辙押韵,一路排比下去,三皇五帝,三山五岳,奇闻逸事,阵阵掌声中,说书人把口齿捯饬得利利落落,手中家伙什儿花活儿翻飞。又一阵鼓板嘈切,坠胡急奏,说书人稳稳引出了开场书:
太阳出来照正东,
种下萝卜长出葱,
八十老头儿正气娘,
刚出生的小孩儿闹牙疼。
东西大街南北走,
路上碰到人咬狗,
拿起狗来砸砖头,
反被砖头咬住手。
全场哄笑,盲书者看火候已到,猛然拍下惊堂木:“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宋金交战百余天,直杀得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宋军损兵折将,气息奄奄,那金军大举南下,要直捣宋营。说时迟,那时快,大宋援兵一路狼烟拍马赶到。仔细去看,统帅竟是一员小将,白盔白甲,头戴花翅金鸡翎,手持丈八钩镰银枪,胯下是一匹枣红赤兔马”。唱戏的腿,说书的嘴,那盲书人更是不同凡响,自始至终,现场都被他牢牢掌控。只见他,时快时慢,时说时唱,刀枪剑戟,马嘶人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上阵大员有名有姓,十八般兵器,细述神通。不知不觉间,书至中场,个把钟头过去,停在了杨宗英被暗器所伤,困在了庙中。乐住声止,高大的盲书人缓缓起身,在辅者扶持下润嗓理私。桌前书场一阵聒噪,如同锅开,大家眼巴巴盯着书桌,急切地等待主角归位。
两袋烟工夫,简板又起,坠胡再响,人未开口,听乐声就知道书事已经离开惊心动魄的战场。果然,一段歇场书,不紧不慢,娓娓道来。
弦子一拉颤音音,
我来劝劝众乡亲。
为人处世要行善,
善恶有报在近前。
由此,盲书人引出一段书生行善的故事。书生进京赶考,荒郊野地,口渴难忍,正恍惚间,道中突然现出一个手掌大小的马蹄印,印中卧着半口清水。书生急急切切趴卧下去,刚要就饮,却见几只蚂蚁漂浮水上,个个惊慌失措,似在呼救。书生强忍住口干舌苦,捡根枯草,将蚂蚁一只只拂出蹄眼,再看,马蹄内只剩半盏湿印,只得继续赶路。试罢,考官阅卷,有试卷文眼之处关键一字,点划不像墨着,手抚去,竟是撮儿蚂蚁!原来是书生疏忽,殿堂内蚂蚁即有感应,组团搭救恩公。
听客入神,嗟嗟喟叹,悄然之间,书已回位——金贼决意赶尽杀绝,宋军将士视死如归,多番杀进杀出,战事终于暂停。小庙紧锁大门,门槛之内,隐隐约约露出一双战靴,岿然站立。众金兵深知杨宗英的厉害,蠢蠢欲动,却无人上前。金军主将上来,犹疑半晌,拿枪捅去,靴倒了。
“大智大勇杨宗英,重伤之下,乱军之中,摆了一出空城计!那金将恼羞成怒,起兵猛追,发誓要杀掉杨宗英。看来,这一次,小将杨宗英在劫难逃,性命難保。小将军到底是死是活,明天接着往下说。”
这时候,灯油只剩碗底,火苗渐弱,月钩西沉,已近子时。书到关键处,听客兴意盎然,心瘾难解,都想知晓结局,胸中火急。“接着说”“说到底”,喊声此起彼伏,盲书人正欲合弓起身,被一莽汉一把按回桌前。几经商议,坠书复唱,正本放下,续段返场书,今晚到此完篇歇息。
弦子再拉嗡嗡响,
手摸良心想一想,
人人都是父母养,
孝敬爹娘可应当;
椹涧自古孝子出,
母慈子孝美名扬。
拾葚喂母咱不讲,
也不讲《割肉还娘》的迷途羊,
夜深人静鬼神在,
单表不孝罪人哑巴郎。
真是遇见了好书!仨钟头过去,盲书人说起小品小段,依然气沛神足,半条街洪声回荡。
百年前,一对母子相依为命,无地无房,只能在几里地外乱石岗开荒种粮。儿终日耕作,晌午不回。娘疼儿天天苦力,食难果腹,便每天上午外出行乞,把讨来的碎馍剩汤送到地头。儿看娘一双小脚挪几里路,粒米难咽,由怜到恼再怒。娘铁了心,日不错影,放下碗就走。莽撞之儿终失理智,屡屡举拳威吓,恶语相向。这天,他锄地刨出一窝田鼠,鼠仔胎毛尚白,还未开眼,母鼠满眼惊恐,却始终抱子不动。莽儿幡然悔悟。午时,再见娘来,飞奔前迎,想让老母少走几步。娘以为儿气急打人,丢碗回跑,撞树身亡。儿一口郁气从肺管喷出,卡在喉头,结出蛋大个疙瘩,哑了。哑巴砍倒老杨树葬了老母,把剩余的板板块块捆绑上身,见人就下跪磕头,额头整天黑血凝结,嘴里“呜呜啦啦”,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书说至此,全场哑然。两行清泪从盲书人枯干的双眼无声流下,在暗淡的灯光中,亮汪汪一片。局面开始失控,盲书人深陷书中,他由哑及瞎,想到自己的家世残身,似老牛堕坑,一声闷吼,扑倒在惊堂木上,号啕痛哭。
第二天,村中有老人谢世,大家都忙活丧事去了,本来三天的书,停在当晚。全村人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在盲书人的版本中,杨宗英命运如何。
响 器
大多数乡下人终生平平淡淡,像地里的庄稼、路边的草。芽发苗长,籽满穗黄,身枯形消,复归泥土。留在身后的是几间老屋,三五棵槐榆,一眼老井,还有像他一样籍籍无名的子子孙孙。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天青眼普惠,把他们的高光时刻放在了终点。
今天,老屋传出的哭声,再次打破了村中的平静。一帮人行色匆匆,开始从这家柴门小院进进出出。
出嫁的闺女们火急火燎地赶回来,没有往日回娘家的细致打扮,进门“扑通”扑倒,压抑的哽咽瞬间爆发,雨泣风号;妯娌们白衣重孝,手帕捂脸,一路哭啼,急奔娘家报丧;孝子们分头出门,朝不同方向,挨门串户,逢人便跪,叩首泣告——
是的,有人西去。村里没了往日的嘈杂,从那家门口路过,大家不约而同,小心翼翼:主家没有齐备,还不是登门造访、表情致意的时候。大家在等一个团队到来。
果然,没过多久,陌生人陆续进村。看他们肩挎手提的器物,就已心知肚明,不用开口,就把要落脚的人家述说周详。孩童早已按捺不住,牵衣扯袖导向带路。一个时辰后,锣鼓铙钹镲齐响,笙起,唢呐声喷薄而出,元气淋漓的《大开门》如期而至。
响器班到了!从现在开始,他们要护送一个非亲非故,甚至不知道姓名的陌生人走完世间最后的路程。在这几天,他是全村的中心,嫡亲宗亲,故知近邻,心热腿勤的男帮女助都放下手中的活计为他忙活。响器有条不紊,吹奏着流传多年的《念亲恩》《哭苍天》《十跪母》《大悲调》,嫡亲孝子一遍遍跪叩,向前来吊孝者,也向着刚刚离去的至亲哭诉衷肠;宾朋邻里一拨拨向他鞠躬,为他送行。天地之间,死者为大,纵使存有过节,依然前来唁别,毕恭毕敬,一揖泯恩仇。响器声托着悲悲切切的哀声哭音,传遍大街小巷、各家院落,时而风高浪急,汹涌澎湃;时而向隅泣诉,悲怆低回。听到响器,大家无论在干什么,都会驻足凝神,从流年碎影中,反反复复打捞梳理逝者的陈年旧事,说道他的苦难艰辛,念颂他的厚德善行。
响器,就是响器班,俗称“响儿”,在过去很多年,都是乡下白事治丧的标配“哀乐”,少了它,就像菜中无盐。“响儿”来了,事项开始按部就班,主家身后有了依靠,心里有了底。高门大户,老人去世,至少两班对吹,三四班也不鲜见。大门两边,十字路口,大槐树下,竞争谁的音准、调稳、动静大,谁的桌前看客多;家小底薄,至亲儿女,侄男阁女,姑亲姨亲,合力也要攒集一班“响儿”,亮亮堂堂,送亲人上路。
响器班都属兼职,平日里就是地里的庄稼汉,牲口屋的饲养员,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或是自幼拜师,或是半路学成,执着加悟性,上了阵,都能不看乐谱,多种曲牌,随手拈来。称之为“班儿”,就是团队,他们各司其职,从称呼便能看出位次。敲梆专属一人,自古就有“响器不停梆不停”的说法,它主导乐队的节奏;鼓锣镲铙钹,两人兼顾,视情况加减,不断变幻、丰富、放大打击乐的效果;笙分长短,两人分持,谓之“捧”笙,实则是伴奏和声;吹唢呐的叫“掌”大笛,掌者,执掌也,由他引领团队的主旋律。响器班水平高低,唢呐占十之六七。在他的带领下,什么阶段,何种曲牌,高低快慢,自成体系,即便远在村外,现场入殓盖棺,起殡转灵,只听乐声,就知道到了什么阶段,行的什么礼仪。
闲余时间,响器班开始“飚响儿”,主题之外,自由施展才艺,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看家本领、独门绝技。上桌敲,跑着“捧”,鼻子吹,脱去外衣,甩掉帽子,最后,把两颗又弯又长的獠牙插上嘴角——曲调一次次达到高潮,人们潮水似的围将过来,霎时间挤满了半条街,拍手激赏,手舞足蹈,口哨连连,尖叫声声,掀起的浪潮,顿时盖住了孝男孝女悲悲戚戚的哭声。
这与子孙们哀恸并不相悖。请来“响儿”,把白事办热闹,热热闹闹送完人世间最后一程,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世上,他们最亲近的人,走了。
戏 台
大戏大喜,大喜大戏。
多年以前,大戏是望族富裕户的专属。子嗣接续,寿登期颐,求雨祈丰,仕遂才达,许下的往往是一場大戏。大喜之事,动静要大,唯有大戏,方能彰显财气,光耀门楣。
吃酒亮家当。寻常百姓,天大之喜,也请不起一场大戏。“有钱买炮放,没钱也听响”。他们唱大戏,乡邻当宣传员,每张嘴都是肉喇叭,把人家的遂愿之事宣讲一番的同时,也把大戏的讯息扩散了出去。激起的动静,“响”遍十里八村。大家都在翘首掐算,等待好戏开场。
这样的日子,往往也是村村寨寨清闲下来,热热闹闹团聚的时候,春节、灯节、庙会,占了大成。有了大戏加持,这一年盼头陡增,像久不见荤腥的灶房,煮了一锅肉,加足了大茴、小茴,葱、姜、蒜。
这一天,哪个村子唱戏,它就是方圆中心。家家户户,洒扫庭除,开门迎客。老闺女们纷纷回娘家;妯娌媳妇们喜气洋洋把爹娘接来;姑表、姨表、舅表,祖辈、父辈、孙辈,嫡亲旁亲,新朋故友,大家或有约相赴,或不期而至。他们的轨迹,有的可能终生都不会重叠,今天,围绕着这台大戏,联结在了一起。营生、世情、经济的、精神的,将在今后的日子里交叉套合,谁也不知道就此会平添出多少故事。
戏台上的故事,也在一阵欢畅喧天的锣鼓闹台之后,开演了。
萝卜白菜,各有其爱。事主有嗜好,戏班就不同。古城许都周边无外乎豫剧、曲剧、越调,《穆桂英挂帅》《铡美案》,《李豁子离婚》《柜中缘》《白奶奶醉酒》《收姜维》,几十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生旦净丑,兵将丫鬟,帷幕三面合,再摆上一桌两椅,“角儿”们浓墨重彩,粉墨登场。这次本地,下次外地,你邀漯河,我请新郑,有的戏班唱腔正,有的剧团乐器精,多数人比来对去看热闹,真正懂戏的,是上了岁数的老戏迷。
戏台前,由近到远,三层分明。近前是核心观众,老年人。靠板椅、罗圈椅,腿脚不灵便的,索性由小辈拉来,裹著半床被子以车当座。老腔老调老故事,虽然滚瓜烂熟,老戏迷依然津津有味,沉浸其中。英烈悲壮,世态炎凉,才子佳人,苦寒悲伤。“话说三遍淡如水,戏听百遍无人厌”,任凭唱腔韵白被弦子帮衬着,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来来回回揉来抹去。椅子阵后面,站着壮年人,他们的心思一小半在戏台上,一小半在前面自家老人身上,还留有一些,招呼门庭里外,人来客往。外围,槐树下,山墙根儿,是一簇簇小伙儿、姑娘,嬉笑打闹,一个个望着戏台方向,看似认真,其实,目光都是虚的。
道道人墙隔开戏台,也阻断了四周街巷的声浪。油馍摊儿烈火烹油,“刺啦”声响,浓郁的醇香沿街流淌,孩童说是来看戏,心却被牢牢拴在这里;小媳妇围着女红铺,针头线脑,比来划去;边缘处,是牲口市,牵牛赶猪,听着戏,就完成了交易。
最过瘾的,是连台大戏。有的连台戏,能传诵几辈人。
多年前,村里戏台旁,走丢了一个孩子。这家人,上边三个闺女,最末遇到了这个男孩儿,圆脸,大眼,双眼皮,像花儿一样。生下他不久,他爹得了一场急病,死了。家里无力供学,他着草篮站在私塾窗外听,一年下来,识字诵文,竟超过塾童。他是家里的“宝贝蛋儿”,走丢后的几年,他娘哭瞎了双眼,每天都摸索着来到村口的碾盘旁,梦呓般呼喊:“孩儿,回来吧,娘给许了三天大戏。”最终,她趴在碾盘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二十年后,儿子再出现时,已是福建十几条船的船主。原来,当年油馍摊儿前,有个陌生男人已看他多时,抓着一把油馍,把他领到了村外。后来,不知被人贩子转了几手,把他卖到了海边。多年来,记忆模糊,财力有限,他始终找不到家,最终决定沉下心来,埋头挣钱,等待时机。终有一天,他做生意遇到了许都人。城西,二月二,龙抬头,庙会唱大戏,还是油馍摊儿,戏台边——
他把爹娘重新葬了,在娘的忌日,在碾盘旁,留下三天大戏。开戏前,他走到台子中间跪下,泪雨滂沱:娘,今后,你年年有戏看,天天有油馍吃。
后来,戏一度断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的一群子孙回来,把戏重新续上,日期改成了村里庙会的日子——这是他的遗言。现在,每年阴历二月二,龙抬头,恍惚间,他还在陪着老爹老娘,坐在罗圈椅上,看戏。
大体也是在戏断的那个时期,邻村有个小名叫“全儿”的,在戏台南边惹出了风波。“全儿”平日手脚利索,却不干净,那天,他在牲口市儿上顺手牵羊,让人抓了现行,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儿,被五花大绑,捉上了戏台。大家传来传去,槐王庄“全儿”偷羊,变成了“槐王庄全偷羊”,自己丢了名声,全村也受牵连。污点难抹,“全儿”扒火车去了山西,在一个没有熟人的煤矿,下井当苦力。
十几年后,“全儿”坐着崭新的桑塔纳回到村里。他很低调,默默捐款修了村学,翻盖了老宅,又在原址起了本族祠堂。最后,在祠堂前,钢架水泥结构,搭了一座宽敞的戏台,许诺今后每年过年,五天大戏。
这五天大戏,前所未有,连续几年,震动乡邻。后来,“全儿”的煤矿瓦斯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他是矿主,进了大狱。现在,他的老宅在,祠堂在,那个偌大的戏台也在。戏台坐北朝南,四角堆满杂物,中间晾着粮食。大家依稀记得,“全儿”红火的时候,前前后后只提了一个要求,戏台的功德碑上,不要留他的名字。
责任编辑 刘淑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