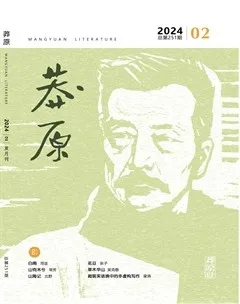老嫁妆
王俊义
祖母的父亲张伯园,是河南西部一个士绅,出版过诗集《晚霞》。张伯园良田千顷,富甲一方,当地人称之为张半县。
张伯园家族有个宿命,谁也逃不开这个宿命。不论哪一代,总有一个男人会流浪如风,漂荡如萍,路见不平,拔剑相向,至死不归。到了张伯园这一代,家族的宿命落到了他身上。
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在北京就职。这件事情,本与民间士绅张伯园毫无关系,但是张伯园认为,曹锟贿选,是对国民的侮辱,更是对他张伯园这样的读书人的侮辱。他在《申报》上读到曹锟贿选的消息,立即卖掉了一些土地,把银圆换成金条,背着沉重的行囊,准备到北京的总统府质问曹锟,并要国会弹劾。
张伯园到北京怒骂无果后,又到天津码头购买船票,要去“国联”起诉曹锟贿选。去没有去“国联”无人知晓,但是自从1923年离开老家,张伯园便一去不归,身在何方,杳然无息。自此张半县家道慢慢衰落,良田千顷的富庶和辉煌,一去不复返。
尽管张伯园的无影无踪,直接影响到了张半县家族的显赫,但是曾经富甲一方的张半县的女儿下嫁给我祖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地域性民间轰动。虽然祖父的父辈们很努力地经营,到了祖母嫁过来的时候,家中也只有几百亩地,和张半县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老虎死了虎皮在,大船烂了钉子在。祖母嫁给祖父的时候,带了一份厚实的嫁妆。经过岁月的涤荡,到了1945年春天,我们村作为中日军队厮杀的战场,损毁严重,那些嫁妆大都化作烟尘了。残留的几件老嫁妆,至今还在老家的老宅子里,拂去尘埃,依稀还能看出曾经的日子。
马 杌
祖母嫁给祖父时,是1929年。那时,一匹马是很值钱的。祖母的嫁妆里,就有一匹枣红马。
陪着这匹马来的,还有一个马杌。
枣红马高高大大,鬃毛油光发亮。祖母要骑上这匹马,先要站到马杌上,经由马杌骑到马背上。
祖母的父亲张伯园读的是四书五经,却是个豁达的人。祖母生于1910年,溥仪还在做皇帝。祖母出生后,按照习俗是要缠脚的。张伯园把女儿抱在怀里,说:“我张伯园的女儿,不缠脚,不做小脚女人。”
祖母的母亲说:“不缠脚,就是一个大脚片子,将来嫁不出去。”
张伯园说:“大手大脚,是天给的,是爹妈给的。缠脚就是缠天,就是缠爹缠妈。”
于是,出生在清朝尾巴上的祖母,有一双大脚片子,在那个年代很是与众不同。
祖母的一双大脚,显然有很多好处。陪嫁的马杌二尺高,上马的时候,祖母很轻松地就能踏到马杌上。假若是一双小脚,登上马杌简直无异于登一座山峰。
女人骑马,在1929年的偏远村庄,绝无仅有。祖母骑着马到镇上去,惊动了沿路很多个村庄。
那个时候,有人背着西洋镜到村庄里。把一个卡片丢进去,人们对着镜子能看见上海滩,也能看见上海赛马场赛马的图片。祖母骑马产生的震撼,远远超过了西洋镜。
枣红马后来与一匹黑马配做一对儿,拉着村里唯一的马车到镇上。两匹马和一辆马车成了村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载体,村子里的人都可以坐着马车到镇上。
那匹枣红马还参与过一件改变祖父命运的事。
祖父18岁时,去西峡口读新学堂。很快,他就和西峡口学堂里的六个学生结拜为兄弟,被同学们称为西峡口七君子。
七君子里有五人是地下党员,祖父和一个叫郑浮子的,是进步青年。七君子里的老大叫吴子兰,被地方民团活埋在老鹳河的河滩上,一起活埋的还有个叫陈少淳的。其中叫贾殿一的青年,被地方民团杀害后,头颅挂在了城墙上。
剩下的四个人,各自回家之后,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7年冬天,他们四人决定到延安去。他们没有告诉自己的老婆和父母,悄然地就走了。祖父的父亲是个读书人,清楚他们的去向。他套上了枣红马和黑马,连夜赶着马车追到了一个叫蒲塘的小镇上。在唯一的客栈里找到了他的儿子,胁迫他坐上马车回到了村庄。一起坐车回家的,还有郑浮子。
假若没有那匹枣红马,祖父的父亲也就追不到远去的祖父,祖父的命运将会是另一种样子。二十年后,那两个到延安的结拜兄弟,一个叫庞坦直,成了后勤学院的教研室主任;一个叫陈少景,成了旅大的书记。
祖父被他的父亲追回来,就只能蹲守在村子里,当一个乡村老头儿。
最让人觉得命运不可捉摸的是,七君子里的五个地下党员,直接领导人竟然是祖母的六爹张明河,他的年龄和祖母一样大。过往的岁月里,婆婆和儿媳妇比着生孩子,是屡见不鲜的。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后,张明河是平津纠察总队的司令。
祖母去北京时,张明河开车,拉着祖母在北京转了一圈儿,还见到了祖父的结拜弟兄庞坦直。张明河与庞坦直说到祖父去延安被追回的事情,祖母说:“这都是命。命里没有这个福分,就是去了延安,说不定早死在战场上了呢。”
枣红马很早就死了,它拉过的马车最后归于生产队,我年少时还坐过那辆车。不过那时变成了牛拉的,叫做牛车。
赶车的把式说:“这是你们家的马车。”
我说:“是生产队的牛车。”
马杌,作为祖母的嫁妆之一,最后变为了一张小桌子。来了客人,摆上四个搪瓷盘子,很是体面。马杌的四边,还雕有很精致的梅兰竹菊。祖父坐在马杌边吃饭时,说:“过去你奶奶的大脚片子踩踏的马杌,现在成了吃饭的桌子。”
1966年秋天,在北京大女儿家住了大半年的祖父回到村庄,立马说:“把祖先牌屋砸碎当柴烧吧。”
祖先牌屋是一座金丝楠木做的精致的小房子,摆在堂屋的条几上。里边放着家族老祖宗的塑像,还有一个老君爷的塑像。往常,逢年过节都要在堂屋祭祀祖宗,在牌屋前边摆上一碗饺子或是五个大馒头,还有一块四四方方的猪肉。见到了那个金丝楠木的牌屋,就像是见到了老祖先和老氏宗。
祖父去了一趟北京,就要砸碎祖先的牌屋,一家人愕然。祖父说:“我们砸了烧锅,還能落一堆柴火。我们不砸,也有人要砸。”
砸了牌屋,祖父又把马杌四边的梅兰竹菊的木雕也砸了。祖父说:“这样,马杌就是一个地道的小木桌。不砸梅兰竹菊,这个马杌也就保不住了。”
砸掉了梅兰竹菊的马杌,四边留下了四个空洞,跟村庄里很多人家的小木桌子一模一样。
过了几天,几十个中学生到村庄里砸房子上的脊兽,龙啊虎啊凤啊的,砸掉了一大堆。村庄除了我家有牌屋,老穆家也有一个。几个学生掂起斧头,就把穆家的牌屋砸碎,在院子里烧了。接着,他们挨家挨户,把雕着喜鹊登枝的太师椅砸碎烧了,把堂屋墙壁上的老四扇屏撤下来烧了。村庄的老物件毁坏殆尽,祖母带过来的老嫁妆,由于祖父的远见,残留了下来。
后来我读初中,回到家里就趴在马杌上做作业。有个二元一次方程应用题,列方程计算地主如何用高利贷剥削贫农。做题的时候,我踢踢马杌问祖父:“咱家是不是也放高利贷剥削贫农?”
祖父说:“咱家哪有钱放高利贷?”
我问:“钱弄哪儿了?”
祖父说:“银圆会跑的,我的钱都跑了。”
我又问:“跑哪儿了?”
祖父又说:“跑到别人口袋里去了。”
1948年,西峡口镇改为西峡县,祖母跟着二女儿进了县城并住了下来,祖父则留在老家做农民。祖母回到老家,坐在马杌边吃饭时,会说:“这个马杌是我的嫁妆啊,老了老了,嫁妆也会老的。”
祖父去世的时候,马杌摆在棺材前,上边放了几个贡飨馍,还搁了一个小盆子,倒了半盆香油,搓了一根棉花捻子丢在盆子里。点燃了棉花捻子,就是一盏长明灯。摇摇晃晃的灯火,会把祖父的魂灵照亮。他到了坟墓深处,也不会孤独。
夜深的时候,香油灯散发着油坊打芝麻油时的芬芳。
祖母去世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马杌,同样的摆设。祖母享受的祭奠待遇,和祖父的一样。假若祖母有灵,一定会看见某个很老的日子,自己踏上马杌,骑上枣红马,走在村庄的泥路上。
清明节回去,摆在堂屋界墙边的马杌,上面一层厚重的尘埃,覆盖了斑斑驳驳的土漆桌面。马杌上方,两个镜框挂在界墙上。一个是祖父的照片,一个是祖母的照片。两个人的目光似乎都落在了马杌上。他们曾经年轻的日子,都摆在马杌上,如同贡飨,祭祀着岁岁年年。
人啊,比马杌老得快,比马杌死得快。我用指头在马杌的尘埃上,写下了两个字:日子。
日子也会老的。
樟木箱子
祖母的老嫁妆,还有一个能装八斗小麦的樟木箱子。
跟着祖母来的时候,樟木箱子里装的是被子,苏州的缎子被面和绸子里面。
民国早期,西峡口人家很体面的嫁妆,也只是南阳产的绸子和缎子被面。谁家的女儿出嫁,有南阳的缎子被面和绸子里面做两床被子,整个村庄都会啧啧地惊叹不已。而祖母嫁过来那天,樟木箱子里装着六床苏州绸缎被子。送祖母的人打开箱子展示嫁妆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都震惊了。
除了苏州的绸缎被子,还有苏州绸缎做的褂子和裤子。村里的老私塾先生说:“褂子为衣,裤子为裳。苏州绸缎做的衣和裳,是绝配啊。”
樟木箱子隔潮,雨季就是再漫长,装在里边的绸缎都不会潮湿。在那些发黄的老日子里,樟木箱子是专门来装贵重家私的。祖母带过来的金银细软,也都装在樟木箱子里。
任何绸子和缎子都是有寿命的。祖母不知道那六床绸缎被子是什么时候没有的,也不知道那些苏州绸缎衣服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当樟木箱子空空荡荡的时候,祖母把小麦装了进去。小麦一斗六十斤,祖母装了八斗才把樟木箱子装满。
装过苏州绸缎和金银细软的樟木箱子,装上了八斗小麦,这是祖母生活转向的开始。她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张半县的女儿,而是一个仅仅能够有吃有穿的村庄女人了。祖母拍拍樟木箱子说:“有八斗小麦也是不错的。”
樟木箱子做工很细致,箱子盖子和箱子吻合得十分紧密。锁扣是黄铜打造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箱子前面有两个锁扣,红铜打的,又厚重又精致。每个锁扣上,常年锁着两把与箱子配套的红铜大锁。可以看出在很老的日子里,中国的工匠们,在每一件家具上都很用心。
祖父叫王天矶,和他岳父张伯园的性格很相似。祖父在西峡口,弹三弦排第一位。后来西峡口改设为县,祖父的三弦还是排第一位。
县剧团有个弹三弦的,曾和祖父私下比赛。之后他对祖父说:“王天矶啊,你那个颤音,我学不来。”
祖父常常背着一把三弦,到西峡口的茶馆里,要一碗很浓的普洱茶,一边弹着三弦一边唱着河南曲剧比较喜洋洋的调门《太平年》《银扭丝》,一边腾开手喝普洱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样的生活,让西峡口很多人都羡慕不已。
中午,祖父会去西峡口最著名的海承夫牛肉馆,切半斤卤牛肉,要一斤黄酒,吃饱了喝足了,下午继续到茶馆弹唱。
三弦是蛇皮张的。黄颔蛇的皮,音质最好。祖父花八块银圆,买了一整张黄颔蛇的皮,每年裁下来一节,给三弦换上,让三弦一直保持纯粹的音质。祖父曾对我说:“我的三弦流出来的声音,轻而易举就把其他的三弦比哑了。”
祖父是天生的民间音乐家,任何歌曲,只要听上一遍,就能在自己的三弦上很随意地弹拨出来。1966年秋天,几十个中学生经过我们村,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祖父听过之后,对一个学生说:“我会弹你们这个歌。”
祖父把三弦放在腿上,一只手弹拨三根丝弦,一只手在丝弦上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调门。那个中学生惊奇地说:“你是个音乐天才。”
祖父得意地又弹了一遍。
祖父还有一手好字。南阳宛西十三县抗敌自卫军司令部招收师爷,几十人当场挥毫比较优劣,祖父以第一名被选中。
司令叫别廷芳,据说清末读过西峡口最后一任巡检颜士璜创办的简师。他对祖父的字,很是欣赏。祖父假若中规中矩,在司令部里混个一官半职是很容易的,但是祖父喜欢弹三弦,有空就在司令部里弹。师爷的头目对祖父说:“这是司令部,不是你們家的院子,不要弹了。”
隔了一天,祖父又弹了起来。弹了几次后,别司令对师爷头头儿说:“让弹三弦的王天矶回去吧。”
没想到,离开了司令部,祖父倒像是离了鬼门关。那些师爷,留在司令部混个团长团副的,最后都是挨枪子的结局。祖父一介平民,倒是安然无恙。
祖父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到镇子上赌博。一天夜里银圆赌完了,祖父和他二弟就卖了三十亩地。夏天小麦收割之后,祖父的父亲没有等来地租,让管家去问,佃户说: “大少二少去年冬天就把这三十亩地卖了。”
祖父的父亲于是开始分家。祖父弟兄四个,每个人分了八十亩地。祖父有了自己的土地,赌起来就更来劲了,很快就输掉了七十亩。
这时,祖母说:“剩下十亩是保命的地,不能再赌了。”
祖父说:“好吧。”就不再拿土地做赌注。
接着,祖父把几亩梨园输掉了。祖母说:“不吃梨可以活。”
祖父又把三亩桃园输掉了。祖母说:“不吃桃也可以活。”
实在没有赌资的时候,祖父把象牙笔筒输掉了。还有一副象牙象棋,祖父很是珍惜。几个村庄象棋比赛的时候,祖父曾用它获得过冠军。在赌性面前,一切都是次要的,一夜之间祖父又把象牙象棋输掉了。
祖父实在没有可赌之物了,就蜷缩在家里。十亩地,九亩种庄稼,一亩种鸦片烟。别人家豌豆熟的时候,祖父的鸦片也熟了。别人家收割豌豆,祖父收割鸦片。别人家烙豌豆面锅盔时,祖父拿出一个红铜瓢熬鸦片。
一亩地的鸦片,不够祖父一年吸食。没有烟土的日子,祖父惶惶不可终日。
祖父去世后,那个熬大烟的红铜瓢,是他留给我们的唯一念想。过了很多年,我把红铜瓢归于己有,偶尔抚摸一下,有点儿沧桑,也有点儿滑稽。
祖母出身大户人家,行为准则却和她那个年代的任何一个女人一样,默默地忍受了祖父那些败家的做派。祖母总是说:“你爷的三弦、骰子、铜瓢,把他的一辈子搞得七零八落。后来想想,那三个物件,却是三个救命的金疙瘩。”
1948年,西峡口被陈赓的部队解放,只剩下十亩保命田的祖父祖母,不是地主不是富农,只是个小土地出租。十亩土地没有割掉一分,家具没有分走一件,祖母剩下的几件老嫁妆,也悉数留在自己的屋子里。那个时候,一亩地的麦子产量就是一百多斤,十亩地的麦子也只有一千多斤。麦子收割晒干之后,祖母先把那个樟木箱子装满。她说:
“不到万不得已,这八斗救命的小麦,谁也不能挖去一瓢。”
祖母把那两把铜锁锁好,紫红色红铜钥匙挂在她的裤带上。樟木箱子装满了小麦,祖母的心也踏实了。
1950年前后,祖母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儿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秋日的周末都要回来背大米,作为一个星期的口粮。星期天从早上开始,祖母坐在石头擂臼前,抱着一个石头擂臼锤子,舂去谷壳,给每个孩子装一袋子大米。舂大半天谷子,祖母很累,就自己捶捶腰身。村庄的女人们都说:“大娘子啊,你哪还像个张半县的闺女。”
祖母嫁过来,被村庄的人们称为王大娘子。时间长了,有感于祖母的宽厚和聪慧,他们去掉了王字,直接叫大娘子。
祖母的小儿子后来读了技校,在鹤壁一矿机电科,也算是有口饭吃。二女儿读了卫校,在县城里当妇科医生,祖母跟着她,一辈子算是世事安稳岁月静好。小女儿考大学的时候,虽然在政审时遇到了一点儿麻烦,终因小土地出租属于团结对象,被郑州大学数学系录取。
小女儿离开村庄到郑州大学读书的时候,祖母忽然发现了祖父的好处,说:“你把几十亩地赌完了,吸完了,落了个一生一世的轻松,几个娃子们也轻松了。”
我年少时,祖母从县城回到老家,拍拍樟木箱子说:“不是你爷赌博吸大烟,这个箱子早就是别人家的了。”
我问:“为啥?”
祖母说:“你爷不吸大烟不来赌,咱们的八十亩麦田稻田一分不少,还有梨园桃园,至少要被划为富农。土地会被没收,家具会被没收,哪儿还会有这口樟木箱子。人啊,浪荡一辈子,有浪荡一辈子的坏处,也有好处。金银财宝瓦上霜,土地家业也都是瓦上霜。早上起来瓦上白白一层,太阳一出来,就化了,就没影了。咱们家那几十亩麦田,还有梨园桃园,在你爷的手里,就是瓦上霜啊,赌场里抬手眨眼间,就没了。”
有一年,我看见了祖母耳朵上的细孔。就问:“奶奶,谁把你的耳朵扎了个窟窿?”
祖母笑着说:“那是戴耳环和耳坠的,是我妈用小米捻出来的。”
我读过一些小说也看过一些电影,明白戴耳环和耳坠的是两种人,一是老地主的女儿们,二是国民党女特务。
我问祖母:“你是个地主老太太?”
祖母说:“不是。”
我说:“那耳朵上咋会有戴金耳环的窟窿眼儿?”
祖母粗粗笑了一声,说:“过去是,后来不是了。你爷在赌馆里,把自己的银圆装进了别人口袋,把地契也裝进了别人口袋。我就不是地主老太太了。”
我终于明白了祖父说的“我的银圆在别人的口袋里”是什么意思。
后来,生产队每年每人分八十斤小麦,我们一家七口人,分五百多斤小麦,晒干拣净后,只剩四百来斤,全部装到樟木箱子里,也装不满。过年煮的肉,母亲会锁在樟木箱子里;老母鸡下的蛋,也锁在樟木箱子里;走亲戚的果子和饼干,也锁在樟木箱子里。
那口樟木箱子啊,曾是我们家的物资库。
樟木箱子的用途在岁月里不断改变,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前些天,我给樟木箱子拍了张照片,发现贴在箱子上的五谷丰登四个字,已经镌刻入木纹里。我把图片发在朋友圈,很快有人问:“卖吗?”
我说:“不卖。”
他说:“不卖就朽了。”
我说:“朽了,也是一个家族的骨头。”
其实一个家族的记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不会朽的。
德国镜子
祖母的老嫁妆里,还有一面德国镜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西部的县城,都有照相馆。很老的坐式相机,德国货。县城的商铺里,也有零零星星的德国货。殷实人家的闺女出嫁,嫁妆里有德国物件,是很荣耀的事。
祖母嫁过来后,樟木箱子挨着界墙放。她打开樟木箱子,取出德国镜子,抻开两条明亮的镜腿,稳稳地摆在樟木箱子上。
祖母搬一张枫杨木椅子,坐下来,对着德国镜子梳妆。祖母当时19岁,又是张半县的女儿,对镜贴花黄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过了一些日子,祖父把祖母的脸盆架子放在堂屋的门旮旯里,脸盆架子上放着一个在当时属于奢侈品的搪瓷洗脸盆。
脸盆架子是土漆加桐油漆过的,黑明透亮。祖母的德国镜子,两条腿中间各有一个位置相同的孔,祖父在门旮旯钉了一根钉子,穿过镜腿的孔,把镜子挂在墙上。早上洗脸时,祖母就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
中国的镜子多是圆形的或方形的,德国镜子是椭圆形的,很像符合中国审美的女子的脸。那时,村庄里很多女人是没有镜子的,她们和祖母熟悉之后,就会站到祖母的鏡子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村庄的女人们说:“大娘子的镜子是德国货,买这个镜子,要花多少钱啊?”
祖母是个低调的人,从来没说过这面镜子的价钱。
镜子在门旮旯里挂了很久,大概从1929年祖母嫁过来一直挂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1945年春,我家堂屋的屋脊被日军炸弹击中,烂了一个很大的窟窿,那个德国镜子却安然无恙。祖母四月份离家逃难,八月份回来,一眼就看见了门旮旯里的镜子。她用手拭去战争的烟云和尘埃,镜子依然明亮如新。那年祖母35岁,面对镜子里经历过战乱的自己,她说:“老了。”
祖母说的老了,是跟1929年嫁给祖父的时候比。经过16年生活的磨砺,祖母已经忘掉了自己是张半县的女儿。
祖父修好堂屋的屋脊,日子又回到了战争前。国民政府提供的小麦种子,村民们要去西峡口领取。大脚的祖母,跻身于男人们的队伍里,去西峡口背麦种。几十里路几十斤小麦种子,祖母硬是和男人们一样背了回来。
此时的祖母,年轻时代的光华已经全部烟消云散,完全成了一个地道的村庄女人。挂在门旮旯的德国镜子,也只是祖母生活的点缀,早上洗脸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自己而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祖母离开村庄到县城里生活,那面德国镜子,留在了老家的门旮旯里。我母亲继承了这个镜子的使用权,她站在德国镜子前说:“这个镜子好啊,不走相。”镜子里的人不像自己,我们叫走相。祖父曾说过:“这个德国镜子,十块银圆呢。那个时候,西峡口中学的老师一个月才五块银圆。”
祖母到了县城,住在一条胡同中间的房子里。她没事的时候,就坐在胡同口看人来人往。时间久了,祖母的一双眼睛就如同镜子,能照出各色人等的本来面目。
这个胡同,住了七八户人家,职务高低不同,在祖母眼里,都是挣几个买粮食买衣服的钱而已。对门的纪局长,祖母直呼其名。住在胡同最里面的桑局长,祖母也是直呼其名。他们两个称呼祖母为“王大娘”。
1967年的一天,桑局长戴个高尖帽子回来了,脸上抹了黑墨汁。祖母看到了,问他:“我看你是个好人啊,谁给你戴个高尖帽?”
桑局长说:“你对门。”
祖母问:“纪黑子?”
桑局长说:“是的。”
祖母说:“纪黑子也是个好人啊。”
祖母让桑局长坐到椅子上,把自己做的米酒舀了小半碗,添了白糖,加了开水,递给桑局长说:“喝碗浮子酒。”
我们这儿把自己做的甜米酒,叫做浮子酒。开水加糖冲一碗,米团子漂浮在碗里。
桑局长喝完浮子酒,把碗递给祖母,茫然地失声痛哭起来:“王大娘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碗浮子酒。”
过了半个月,祖母对门的纪局长也戴个高尖帽子回来了,和桑局长之前戴的一模一样。脸也抹上了黑墨汁,也和桑局长的一模一样。祖母问他:“你是个好人啊,谁给你戴的高尖帽子?”
纪局长说:“桑树娃子。”
平时,人们把桑局长叫作桑树娃子。祖母说:“桑树娃子也是个好人啊。”
纪局长问:“好人?”
祖母说:“你俩都是好人。”
纪局长说:“王大娘你不懂。”
祖母也让纪局长坐下,也冲了一碗浮子酒,递给他说:“纪黑子,喝碗浮子酒吧。”
纪局长喝完浮子酒,扑哧扑哧哭了:“王大娘啊,你这碗浮子酒,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老纪和老桑又都做了局长。河南豫剧三团的常香玉到县城里唱豫剧,一票难求,祖母却有两张戏票。一张是桑局长买的,一张是纪局长买的。
祖母的大女儿在清华大学党办的时候,祖母第一次到北京,一个人径直跑到了清华大学党办。党办的一个年轻人说:“你一个人能摸到这里,不简单。”
祖母说:“只要认识一个字,想到哪里都能到。”
“哪个字?”
祖母说:“女。”
那个年轻人问:“为啥?”
祖母说:“不上男厕所。”
祖母的这个段子,在清华大学党办很是轰动。我大姑回老家讲这个段子的时候,惟妙惟肖。
祖母晚年时,有一天在老家的门旮旯里,对着德国镜子端详了一会儿,说:“除了老,我的大样子没有变。”
祖母的德国镜子还在,只是斑斑驳驳了。我把它装在樟木箱子里,扣上盖子。
我把祖母的日子,都装进樟木箱子了。我总想,那个镜子是有记忆的,它看到的祖母,是不死不老的。
补记:1985年,祖母对我说:“找找张伯园吧。”祖母的父亲早就无影无踪了,她也没抱多大希望。一天,我在《河南日报》上看到省政协一个副主席叫张伯园,但是他的年龄比我祖母还小。祖母至死,都不认为自己的父亲死了。她说:“没有看见的死,不是死。”
责任编辑 申广伟
——基于黄金分割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