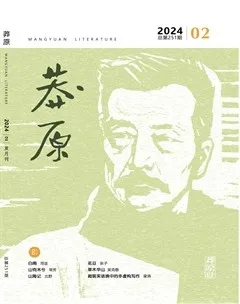烟与糖
陆铭晖
糖
糖,是一种使人皈依于自我的輔助剂;黑色包装盒,彩色文字,如梦境的叠印,一板上有十颗,绿色或者粉色,原产俄罗斯,看不懂的西里尔字母,她把它从包里拿出来摆在桌上。
那是一只白色的手提包,白色肩带,金色带扣与拉链;她身上的一切,除了头发眉毛和眼睛,大体都是白色的。冬天,一件白色的羊毛衫,脖子上白色的丝带,她的鞋不是白色的。
她笑的时候眯眼睛,不露牙,把手肘支在吧台上。法国人让她试试学调酒,她就从高脚凳上下来,鞋跟触及地面,绕着吧台走了一圈,让法国人手把手教着分辨不同的瓶子,如何拿起、倾倒、转动勺子,切一片柠檬。酒吧里烟雾缭绕。
男人们在抽烟,法国人和邻座的中国男人,白盒子的中南海免税,与打火机叠放在一起,汉字标识正对着前方。她见到的绝大多数男人好像都抽烟。法国人给她递了一支,她摆摆手,打火机在两个男人的手里流转,哗嚓哗嚓。
她是从两年前的夏天,塞维利亚的雨季开始吃糖的,欧洲和糖让她变了很多,这是件好事情,比如失眠不会再来,那些来自感觉过剩的失眠,由糖不遗余力地填补了。两年前在塞维利亚,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邀请她跳一支弗拉明戈舞,结束之后给了她一颗糖,一颗她早已忘了是什么样子,却认为从此拯救了自己生活的糖;棕发男孩的公寓里养了一只绿色鹦鹉,在她献出自己的初夜时,那只鹦鹉在窗台上咯咯地重复着西语的“甲虫”一词:escarabajo,塞维利亚的街上便下起欢快的小雨。
从清晨的白色床单上醒来,她第一次体会到投奔幸福的感觉,花洒喷涌而出的热水划过皮肤,水雾攀上玻璃,棕发男孩青色的眼睛朝她笑,嘴里叼着一颗糖,床头柜上还零星有两、三颗糖。她的小名就叫糖,因为从小笑起来很甜。有一张照片,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上拍的,头上戴着一顶生日帽,七岁。她的生日在春天。
在得到第一颗糖之前,三年前,那个时候她还不戴隐形眼镜,不化隐隐约约的腮红,不在脖子上系丝带,不抽烟,现在也不抽。白色手提包里放的是艾司唑仑片,解决失眠的唯一办法。她是个感觉动物,自认为拥有比任何人都更敏感的嗅觉系统,更能体悟类似爱、自由、浪漫或幸福的味道,这些味道一旦诉诸文字便会立刻被中和,烟消云散;诉诸药物和香烟也是一样的。她试过不同的药物,从塞维利亚回来之后,氨酚曲马多、枇杷露、立健亭、氯硝西泮、布洛芬或咖啡,最后发现只有糖管用。刚开始是偶尔尝一片,后来每天睡前都要吃;上海能买到的糖比塞维利亚的差了不少,东京的就还不错,这时的她一天差不多得吃两三片。
她是两个月前到东京的,理由自己也说不清楚——追着感觉——在涩谷这家开在天台边的酒吧,朝外走两步就能看见城市夜空。店老板是法国人,客人也是外国人居多,讲英文——她的日语不好——这间酒吧就成了她每周必来的地方。
法国人能讲好几种语言,说早十年的时候,他游遍了世界,在欧洲开的是一辆皮卡车,在美洲坐飞机穿越雨林,到中国是二〇一〇年,一五年来的日本,一直待到现在。他说话的时候手舞足蹈,圆片眼镜在鼻梁上跳来跳去。她说,她也总梦想着环游世界。
酒吧的吊灯是暖黄色的,暖气灯立在屋子一角,红漆的墙面,在她的白色背影上镀一圈金。
酒调好了,她捏着高脚杯回到座位上,双脚离地,龙舌兰日出,在彩色杯垫的衬托下显得尤其漂亮。法国人也夸她:“你是我在东京见过的最美的姑娘。”她笑了,说自己是个中国女孩,讲英文的口音还没脱去西班牙语的痕迹,她用手指把糖从锡板上摁下来,手指的指甲贴片也是白色的,像一颗颗小月牙。粉色的糖落在手心,一颗,两颗。
一颗落进法国人手心,另一颗停在她的舌头上。她想起了些什么,“好久不见。”拿起盒子在邻座的中国男人面前晃了两下——
“吃糖吗?”
烟
他在抽烟,从踏进酒吧到现在,接连抽了有四根烟。白色烟头,抽完就扔进一只金属烟灰缸里,刺啦一声,烟头熄灭的声音使他安心,好像自己抽烟就是为的这个。
十七岁,那是他下定决心抽第一支烟的年纪,比许多人都晚上一点儿,没什么不好的;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严密考量,唯独抽烟不是。在家乡大街上徘徊时他曾想,我十七岁了,应该做些十七岁该做的事情——傍晚总有那么一帮无所事事的青年,叼着烟,向路过的女孩耍流氓,向男孩找碴儿——被拦下来借钱的时候他想,我必须得抽烟。
变化对他而言是个比较陌生的词,她把那盒糖在他面前晃了晃,对他而言,包装上五颜六色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变化。糖片是圆形的,但不是理念中那种圆,球体。小时候他梦到过上帝,上帝是一个球体,他推着它走在故乡的黄土路上,到一处曾被土方车撞倒的柱子边,醒来。球没了。
他把烟当作镇痛剂,以健康为代价,缓释一切最为经济有效的办法,无论是悲伤、愤怒、焦虑或者失眠,还是偶尔难以抑制的感觉,拥抱的欢愉、行走的冲动。香烟说再等等,赋予迟滞的权力,把灵魂从嘴里吐出来。现在他二十三。
在四年前南下的绿皮火车上,窗外飞过一行行田野房屋,车厢连接处是乘客聚集抽烟的地方。他的烟盒空了,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孩递给他一支兰州,浅黄色烟盒,过滤嘴里有陈皮爆珠。铁轨的尽头是上海南站。女孩离去时在烟纸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第三位到第五位是三个0。
电话拨通的第二天,他们在苏州河边相逢。戴黑框眼镜的女孩一直在哼一首歌,不告诉他是什么。他们淋着小雨沿苏州河畔走过一段,轮番抽完最后一支烟;香烟把他的神经弄得迟钝了,也许浑身都迟钝了。酒店的房间在高处,十三楼,窗外是河水倒映着的灯光;他们焦急而迟钝地试图完成那些动作,一无斩获,感官也延宕,打开窗子透气,拆开一盒兰州,燃尽之后再试一次。
延宕中持续,太阳照进窗帘缝隙,戴黑框眼镜的女孩说,早上好。他也说,早上好。未然的愉悦,她的热情令人始料未及。上海的冬天不下雪,呼出的雾气凝结成露,他们在苏州河边手牵着手,看远处泥沙船排出的尾气。他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也是烟:燃尽的煤灰,摩托车的排气管,热力厂的烟囱,父亲一边鼓捣打不着火的发动机,一边隔着三层楼同母亲吵架,他跑到小巷里撒尿,浇化一摊雪。
她把手缩在羊毛衫的袖子里。窗户开著。他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转身去把窗户关上;她的手心攥着两颗糖,说,尝尝吧。
他又把烟续上,用力吸了一口。不吃糖,不是因为什么原则问题,只是他不想吃糖,除非它能让他像柯勒律治一样写出不朽的诗篇,否则他想不明白吃糖的意义在哪里;直抵血液的即时感觉,感觉过剩是有害的,不是永恒,没有永恒。打火机在手里开开合合,法国人说他那儿还有一盒七星,酒吧的抽屉里还卖各种各样的烟,这是他第一天来就知道的事,虽然他的英语不好。
他看着她把一颗糖放进嘴里,就那么含着,喝一口酒,冲着他吐了吐舌头,糖就待在舌头上。
法国人还在说环游世界,他只象征性地点头,对四处走动没有兴趣,东京是思量过很久的选择,这种思量久久不能消散,化为疑虑,为什么?把烟头熄在金属烟灰缸里时他又想,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
糖
糖的包装盒上贴着一张日文标签,上面写的是“不得饮酒服用”。
她乐于追从不确定性,从庞大事物的身边溜走,违逆语言在我们身上构建的枷锁;罗马字使她快乐,就像一颗颗蹦蹦跳跳的糖丸。十六岁时,母亲在厨房煮粥,每天往父亲的碗里拌一小撮白色的糖,那种糖比白砂糖要细,细小如霜,她站在边上看着,母亲就蹲下来,微笑,摸着她的头告诉她自己支持她的一切选择。又说,你爸爸是个窝囊废,只会张嘴说话闭嘴抽烟。她听了只是眨了眨眼睛。
第一个选择是默许体育老师把手伸进她的衣领。十七岁生日的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过后,阳光穿透云层爬上窗台,储藏室里无人光顾。她在等待下一步动作,麻雀停留枝头,她闭上眼睛把自己当成一只亟待拆开的礼品盒;手指在触碰到乳头的前一刻停止了动作。她笑了,体育老师把手抽了出来。母亲说过,男人都是畏首畏尾的窝囊废。
她觉得有趣,一场游戏的开始,把在储藏室发生或没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班主任,坐在凳子上低垂脑袋,掰自己的手指;班主任是个一惊一乍的中年妇女,像上了发条似的在教室里一圈圈徘徊,承诺不会再让她受到伤害,告诫务必三缄其口。她点了点头,成年人的认真总是那么可笑。同学们早就知道了这件事,管她叫“那个女孩”;体育老师被学校开除,离开时,对着她鞠躬,班主任挡在了她面前。
或许男人都是这样,他们是一群谨慎过度,只会担惊受怕的动物,哪怕是在塞维利亚,那个给了她一颗糖的男孩也是。他公寓的抽屉里有一把手枪,西班牙不禁枪,夏末,他们一道去树林里打玻璃瓶,那是一支小口径的柯尔特手枪,银灰色,子弹抛壳的声音清脆。棕发男孩站在她背后扶着她的手,解除保险、上膛、瞄准、发射,绿色的酒瓶在远处爆裂,里头还盛着雨水。她摘下耳罩,转身说:
“我打中了!”
他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松开她的肩膀往后退。她忘了自己手里还拿着枪,笑嘻嘻地对着他:“怎么了?”
棕发男孩指了指她手里的枪。
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只不过是太高兴了,拿枪的手腕甩来甩去,西班牙人的脸色却比铁还青,说如果刚才枪走火了,那她就等于亲手送他去见上帝。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他如此认真的表情,说:“你的认真叫我害怕。”跳舞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男人归根结底是理性动物,只会和语言相生相依。西班牙人把枪收起来了,她还没有摸够。回去的路上开一辆绿色小轿车,他双手扶着方向盘,嘴里滔滔不绝地说。西班牙语的音节短促迅捷,从她的一只耳朵进去又从另一只溜出来,隐约只能捉到几个词,手枪、生命、死亡和他的上帝,你在听吗?
“你把假期给毁了。”她说。
他说:“好吧好吧。”
她想吃糖,副驾驶的抽屉里有糖,到她抵达西班牙的第五个月,糖吃得越来越多,不由自主,一把抓了三颗,看着西班牙人手足无措地把车停在路边,糖撒落到地上。“你吃太多糖了。”
大约是因为这个,每次把糖放进嘴里时,她都会想起那把银色柯尔特手枪,西班牙人说的“死亡”一词:La Muerte,阴性,好像死亡是一个女人。把她和棕发男孩分开的不是死亡,她想,而是死亡这个词;塞维利亚的冬季,独自离开白色床单和公寓楼,披一件白色羽绒服在街上走,鹦鹉的最后一句话:escarabajo。死亡总会和每个人擦肩而过,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糖在她的舌头上化开。法国人将三个子弹杯端上吧台,咖啡、甜酒加黑朗姆,喷枪点燃杯口,幽蓝的火;她似乎想到了什么,问法国人,“法语里的‘死亡怎么说?”
“Mort. La mort.”
“敬死亡。”她说,等待杯口的火焰熄灭。
烟
“挣扎。”
他的脑袋里闪过这个词的时候,手指正扭转玻璃杯沿转动里面的冰块,冰块在威士忌海沉下又浮起,挣扎;世界很小,世界就是那么个玻璃杯,曾经岚也是这么说他的,一个挣扎的人,他想说她也是。法国人把点燃的酒推到他面前,糖说:“敬死亡。”一饮而尽。
他是在三年前的冬天得知那个消息的,岚在宿舍吞服了三分之一瓶安眠药企图自杀——岚就是苏州河畔戴黑框眼镜的女孩——那时他的心情就是没有心情,不悲伤也不快乐。走在西藏路桥上时,他说:“她大概希望可以不再挣扎。”事与愿违。
自认为姗姗来迟的忏悔,哪怕知道岚的选择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他也自认罪孽深重,无知而无力的罪孽。那时他们分手已有两个月,耽于迟钝,很多东西始终未能完成——她跟着一个穿褐色马甲的男孩走了,那个害她吞食安眠药的人就是他。深秋,艺术集市,潮湿的法桐叶铺满人行道,他记得很清楚,潮湿季节烟雾是往下沉的,最后一支兰州,看他们的背影往天桥上走,转过头他就遇见了三年前的糖,白色羊毛衫和白色手提包。
白色的一切和她黑色的眼睛,这么些年来唯一没变的东西,那只手提包挂在吧台下方的钩子上,大衣在墙角。他同食道里返来的气体做了会儿斗争——朗姆一直烧到胃里——闭着眼睛,问法国人要了一支七星。
她的声音隔着一张凳子传过来:“真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也在抽烟。”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他就隐约知道她是个危险事物,从眼睛里看出来的。哈姆雷特的台词,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它的感化;他的目光扫到这一段。
她喝了一口龙舌兰日出,说:“你没怎么变,想知道那时我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吗?”
挣扎,不是这个词,他把挣扎写在脸上,过粗的眉毛,黑色风衣像大号垃圾袋,香烟熏红眼睛,仿佛活着要费很大力气。
他皱着眉头抽烟,把烟嘴咬得扁平,好像在同它做殊死搏斗,踩灭时也是,非镶入砖缝不可。那是深秋的上海,艺术集市的尽头,手里捧一本莎士比亚,他习惯用机警的目光打量世界,看见岚和那个穿马甲的男孩登上人行天桥,路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时候白色的她走过来,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他打量了她一会儿说:“那是你男朋友吗?”
世界的表象再简单不过,现在他们走了,他和糖留在了这里,集市尚未结束,大约得持续到子夜。他们一前一后走着,漫长夜晚开始唯一的选择,一盏盏小灯连成一片;烟火不断,他觉得畅快多了,她也抿着嘴笑,一段梦一般的经历,作为一个迟钝的人无须多求。她坐在路边吞了半颗艾司唑仑。
“秘密。”穿马甲的男孩是不是她男朋友,秘密,就像多年后在东京见面,很多事情她不会告诉他一样,秘密。他的脑袋里塞了一大堆问题,比如当年她为什么不辞而别去了塞维利亚,后来为什么又来了东京;比如那年秋天在上海的事她还记得多少;比如艾司唑仑片刚放进嘴里是什么味道,她现在还失眠吗?
他抱着一大堆未知的问号抽烟,一切问号都指向同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感觉。他离感觉很远,就像在做出某一个他自己也无法相信的决定之后,坐在地铁上与糖戴同一副耳机,那时他也仍旧感到自己离她很远。
他的罪孽也来源于迟钝。
童年,当父亲骑上摩托车前往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时候,他正把一只猫从四楼阳台扔下去。
母亲在隔壁哭完,过来与他说:“跟我走吧。”
他摇了摇头。
得知岚服安眠药时他也是这么回答糖的。西藏路橋,把脖颈埋在衣领里,糖说:“岚自杀了,你难过吗?”风把苏州河的气味搅动,自杀在她的嘴里是个多么轻的名词。
摇头或许是她想要的答案,因为她笑了,同她谈到死亡时的笑容相似。她的笑容会让你忘记一切,把灵魂勾走,是比香烟更让人丧失嗅觉的东西,他想;她很美丽,此时此刻,她把两颗糖置于手心,粉红色的圆片,酒吧的灯光影影绰绰,他把打火机拿在手上开了又合,终于开口问她——
“糖是什么味道?”
糖
糖的成分表:食品添加剂,山梨糖醇,硬脂酸镁,阿斯巴甜(含苯丙酸钠),安赛蜜,苹果绿铝色淀,天然薄荷香料,槟榔精粉。
对她而言,远是唯一一个叫人兴致盎然的男孩。她是个感觉动物,感觉,用这两个字涤过脑叶,只在极少数风平浪静的时候会想,“感觉”这个词是否也是语言的一部分?放一片糖在舌底。远是冒险家——她来东京的原因:远在横滨有一台银色机车。
奥利瓦爱他的上帝,那个也许是出于无聊把语言赐给我们的,Dios,他一定是个无聊的家伙,否则夏娃也不会偷吃苹果。奥利瓦——那个把糖递给她的男孩,当一样事物的名字得到确定,它的一切趣味便烟消云散——手臂上纹着一只十字架,就像那个春天,戴黑框眼镜的岚给她看的那只十字架挂件一样。
她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远的。春天的河边,岚是一个热情过头,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分享给初识一天的朋友的人。岚甩动自己的手腕,银灰色十字架在月光下一闪一闪,告诉她自己的男朋友是块雷打不动的石头,迟钝而顽固,所以她悄悄地逃走了;她的名字叫岚,山雾的意思,日语意思是狂风骤雨。六个月过后,岚会在寝室的床上服下三分之一瓶三十三颗阿普唑仑,救护车会驶进校园,为她施行洗胃手术,在她见到上帝之前把她拉回人间。
她抿着嘴笑,对岚说喜欢这个名字。
“远就不一样。”岚说,“他是个爱冒险的人。”
远穿褐色马甲,棕皮鞋,骑一辆蓝色电瓶车,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布置好一切,夜灯、枕头、收音机和低温蜡烛,还有一只存放安全套的小盒子,虽然他几乎用不上它。冒险是个多义词,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险,医生说他精子活性不足,它有一纸远洋航行的宣言。
她站起来,让柳叶抚过自己的脸,听岚讲她和远的故事,闭上眼睛,就像那些故事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样,微笑,看岚指着河对岸的树林;春天到来时,成群结队的柳絮会把河道两岸填满,滚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犯戒,远喜欢把皮带拴在她的脖子上。迟钝的他不会知道,哪怕知道也无妨,他不认识远,只会被困在语言的囚笼里四处打转。岚说这些时眼里闪着懵懂无知的光,是月亮。
糖是什么味道?她也说不清楚,那不是用味道能够解释清楚的感觉,就像远,在得到第一颗糖之前,味道最接近糖的东西是远。她不喜欢用幻想这个词来表达:并拢双腿,让蜡油在大腿缝隙中爬过——多幸福的岚。从那天起她开始热衷于购买贴颈项链,丝制的或者皮制的或者布制的;坐在咖啡厅捧着一杯馥芮白,她的对面就是岚和远,远的眼睛很好看,笑的时候像个没长大的男孩;她想到远的手上抓着绳子的另一端。
酒吧的音响里在放日本老歌,抱いてくれたらいいのに(抱紧我就好),她想,有人说过,拥抱会上瘾。他又点了一根烟,和法国人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聊天,好像聊到了忏悔,法国人叼着烟,用夸张的手势画十字;她低下头笑,看着自己的手指。也许她该把各种真相告诉他,奇怪的念头,那是她自己的事,夏天跟踪岚到河对岸的树林、到卫生间、到法语系上了锁的教室,用相机拍下她和远交叠在一块儿的样子。那时她的脑袋里或曾闪过这样的念头:从某一刻开始她已罪孽缠身——一句话恐怖地回荡在颅底,究竟是哪一刻?十七岁时被体育老师抱住的时候。她的目光盯着桌上的糖。夏娃吃下果子的时候。按下快门时,孤独与兴奋一并涌来,不知孰先孰后。
她把照片导入电脑,藏匿在磁盘最隐秘的文件夹里,看着缩略图上模糊不清的两块白色,孤独。这一系列动作重复到了深秋,她跟着远和岚去了艺术集市,并在花坛边意外遇见了他,和岚说的一样,他是一个沉默迟钝的男人,手里捧着一本莎士比亚。她走到他身边,悄无声息。夜晚的莫干山路,他们看着岚和远走上天桥,在马路的另一头变小,正在抽烟的他坐在绿化带边缩成一个球。
她也坐到绿化带边,吞下半片艾司唑仑,他问:“这是什么?”
她说:“药。”时间过去很久。
他抱了她一下。
舌底的糖化完了。
烟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为什么来了东京?
东京是个奇怪的地方,闭上眼睛,身处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用身上的毛孔感受、想象,你的脑海里会出现不一样的图景,上海纽约巴黎佛罗伦萨,全世界的集合,充满不确定性。他曾在原宿的街头见过一身素白的日本女孩儿,站在一杆路灯下,等他经过时,走上前小声对他说只要两万日元,他双手合十弓着腰逃走;万圣节就要来了。
他看见她又吃了一颗糖,并把盒子朝他晃了晃:“真的不尝尝吗?”
他不是第一次琢磨她的微笑,也不是第一次一無所获。那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在静安寺,他把一枚硬币往香炉的顶上扔,屡试未果,站在台阶上发呆时,他抬头看向上海的玻璃高楼,他想抽烟。她说,抽吧。他说:“你男朋友和岚,他们去了哪儿?”她却说:“那不是我男朋友。”他说:“去了哪儿呢?”她说,不知
道,然后笑了笑。
“合法的,”她说,“至少在这儿。”
三年前的告别来得很突然,又像是命中注定,那时她的脸上也总挂着难以捉摸的微笑。在得知岚出事的第二天,他已决心把岚忘掉的时候,糖的离开让他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该往哪里去,下意识地蹲在河边抽烟,用水果刀削一只苹果。柳树下站着那个穿褐色马甲的男人,名字好像叫远;苹果皮落进泥潭,上海是一个泥潭。
上海是一个泥潭,他的人生是一个泥潭,这就是为什么自己会来东京的原因,如此简单。
他接过她手里的糖说,好吧。
问题还是在的,关于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会有突如其来的拥抱,这是个小问题,大问题是,为什么他选择了挣扎?神经放松,一颗冰块释放气泡。糖刚落到舌头上时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像西瓜霜含片,微甜,舌根发麻。她在微笑。
岚从医院出来时像变了一个人,这是他听说的,未曾求证;他没再见过她。河边,远双手插兜,向他走过来,马甲背后一支不知名的鸟的羽毛,他看着他,左手拿着苹果和刀,右手翻找香烟;远蹲下来,后颈呈现在他面前,像死囚受刑时的姿势。
无所作为是一种罪,一种卑微到连地狱大门都无资格踏入的罪,这是他草草翻阅《神曲》得出的结论之一,很奇怪,因为在这片生养他的东方厚土上,无为其实是种美德;无知、中庸、隐忍、宽恕、无为……善良的人类。他不知道远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他的刀尖离远的脖子不过三十厘米的时候,或许有过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刺进去,看看血是什么颜色,闪烁在语言中的死亡和亲眼看见的死亡或许不同;可他凭什么觉得自己掌有审判的权力?眼前的远捡起石头扔进河里——他大概连自己做错了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敢说自己知道,仅仅是纵容自身的动物性就足以降罪于之吗?远指着河面上漂浮的柳絮说:“试过把它们点着吗?”
他的右手找到了烟,削苹果的刀落到地上,烟延宕一切。远抬起头说,多谢。
“点着柳絮的时候,它们会瞬间烧成一片,然后瞬间熄灭,过程不过两三秒。”
他无数次在脑袋里构想那一情形,铺满河岸的火,和一个不需要他来宽恕的唐·璜一块儿抽烟。现在,喝一口威士忌,他问法国人:“你犯过罪吗?”
法国人说,二十岁时,抽烟烧了自己家的房子,这也是他为什么决定环游世界。很好的冷笑话。
沾上罪孽有时候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动作,把糖放在舌头上,等待融化,不知不觉。他想,现在他罪孽缠身了,然后呢?叛逆无法令他快乐,就像童年把一只猫扔下阳台,过不了五分钟他便开始哭。当然,如今他不那么擅长哭了。头晕,糖在血液里苏醒,喉咙深处一直到舌根都有些发麻,像感冒,像会厌处有一个圆球在生长,那种绝对理念的圆,任凭如何吞咽都无以撼动。母亲可能有罪,出轨了一个戴无框眼镜的胖男人,胖男人给了他一台蓝色的变速自行车作为收买;父亲的罪则是暴虐,摩托车吐着烟停在雪地里,父亲用脚把它踹倒。
她说:“你的脸红了。”
“我赌他一定抽不了大麻。”法国人说,“行了,别逗他玩儿了。”
他说,我还清醒着呢。现在他要出去透透气,那颗糖就像是魔鬼,难以捉摸的西里尔字母,粉红色的圆片;法国人在擦一只高脚杯。她说:“你口水都滴下来了。”
糖
烟草燃烧,飘出来一缕缕丝线,在灯罩下聚散,然后凝结成云。
她扶着他到露台上时,涩谷的街头正举行万圣节集会,年轻人自发组织,穿着稀奇古怪的万圣节服装,从一块写着“涩谷不是万圣节会场”的白色立牌下鱼贯而行,她猜想里面会不会有远。
糖就是这样,第一次吃它的人多半会晕得半死不活,重则上吐下泻,歇一阵儿就好了,二十分钟。他躺在一张红色沙发上,说想把自己的脑袋拔下来。“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上帝在我的嗓子眼儿这儿,我快把他吐出来了,可是我还有好多没有忏悔的。”他把嘴张大,“你能看见他吗,告诉我他是什么样子,告诉我他是不是无所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和我说话,告诉我。把我的烟拿过来。”
她笑了,许久以来第一次不自觉地笑,他的喉咙里当然没有上帝,只有一颗糖。走到吧台旁边,法国人拿了一包未拆封的七星递给她,喝一口白兰地,白色的包装盒上有许多金色的星星。她靠在沙发扶手边,看着嵌进沙发里的他,嘴角滴着口水,正抬手够她手里的烟。
她说:“傻瓜吗?”
他说:“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个傻瓜,打从记事的第一天起,我的脑袋里就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个傻瓜,你不是吗?给我烟。”
她撕开烟盒的封条,想到自己已很久没仔细端详过一支烟,烟盒内白色烟嘴的排列方式就像是糖。在她按动鼠标,把文件夹里的照片传入互联网的那个下午,这辈子最平静的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又是一、两个小时,转发量是一串数字。她第一次单独把远叫出来,从远的手里接过一支烟。她闭着眼睛,坐在河岸上等待远的手指或嘴唇。而远所做的只是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眼睛像在说,他知道她的心思,傻瓜。
“物竞天择,大傻瓜欺骗小傻瓜,小傻瓜欺骗小小傻瓜。”他把打火机放在胸口,“给我一支烟吧。”
她不说话,把一支烟叼在唇边,摊了摊手,打火机。
他哈哈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
从远的微笑开始,烟的味道比药还要苦。远说,岚正在哭呢。
塞维利亚,奥利瓦将弹匣退出柯尔特手枪,把子弹一颗颗扣落在桌面上的声音让她想起阿普唑侖,一口气吃下三十三颗是什么感觉?塑胶软管从口腔探入,直抵胃中灌注洗胃液是什么感觉?或许时隔多年,她仍旧嫉妒岚所拥有的那些体验。躺在白色床单上看着奥利瓦把手枪放回抽屉,她说:“把柯尔特M1911塞进嘴里会是什么感觉?”
奥利瓦说,肯定比不了他裤子里的那支枪。
醉生梦死,是这么个说法,奥利瓦把一颗糖放在上面,她就把它整个含在嘴里。醉生梦死;她知道它不会让她真的死去,只能无限逼近死亡的真实。岚还在医院时她去看望过一回,坐在床边对着岚笑。岚沉默寡言,唯一的一句话是:“现在大家都认得我了。”
哗嚓,火焰跳动,她看着缓慢燃烧的烟丝,纳一口烟在嘴里,闭眼,低头用嘴堵住他的嘴,把烟雾传过舌尖,睁开眼睛看着他。
“为什么?”他说。
她说:“还给你的。”
他说:“我可没对你做过这种事。”
“我知道,”烟灰落在她的白色裙子上,“我不抽烟,给你了。”
他说,谢谢。
露台上很冷,她得回屋里去了,起身时他拉住她的袖子:“为什么?”
香烟不适合她,朦胧延宕的雾气,熏得她眼睛发疼,脑袋也晕乎乎的,她在玻璃门前站了片刻,说:“是我害岚吃安眠药的。”
他微笑着说:“我知道了,然后呢?”
她说:“你不恨我吗?”
“有时候我也很残忍。”他对着烟头说,“岚活下来了,不是吗?我们也都活着,活着是最好的事情。”他松开她的袖子,朝着屋里的法国人招手:“活着真好,对吧!”
糖
法国人在吧台后似乎总能找到事情做,譬如现在,他正用一只电烤盘在后厨烤羊排。她经过时闻到了羊排的味道,然后径直往楼上走,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照了会儿镜子——不知道为什么下眼的妆花了一些——关上小窗,移步在马桶上坐了一会儿,面前的瓷砖倒映她的轮廓。她捂着脸,眼泪冒出来。
过了几分钟,外面的街上变得吵吵闹闹,有听不懂的日语,摩托车开过,远方飘来呜哇呜哇的警笛声。
糖还剩下三颗,倒在手心,一股脑儿放进嘴里,融化,她数着自己的心跳,到第六十下的时候提起裙子打开卫生间的门。她闻到楼下的羊排烤煳了。
街上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人在奔跑,叫嚷,救护车走走停停,鸣笛,红色蓝色的光,法国人站在露台上,往外探出半截身子使劲看。她问:“街上怎么这么吵?”
“Il a sauté(他跳下去了)!”法国人的声音在发抖,“Il a sauté!”
她听不清法国人的话,音响的声音太大了,也许,抱いてくれたらいいのに,烤焦的羊排还在滋滋叫呢。Il a sauté.糖在她的舌头上舞蹈,法国人一边喊着她听不懂的话,一边转身往楼下跑。她不想看露台外发生了什么,他跳下去了,准确地说,他尚在糖的迷雾中,摇摇晃晃起身,倚在栏杆上看万圣节集会的时候失去重心,掉了下去,变成一个摔扁了的男人,上帝正从他的嘴角流出来,烟头滚向一边,围拢的人群里有各种各样的鬼怪,渋谷はハロウィーンイベントの会場ではありません(涩谷不是万圣节会场)。
她张开手臂开始在木地板上跳舞,感受半支香烟的尼古丁与糖在血液中会合,把时间延长,听,歌曲渐弱,远骑着一辆银色川崎摩托像子弹一样划过海滨公路。点燃,不,她嚼碎了一支烟,手指寻找大腿皮肤下糖走过的踪迹。那里是少女时代,父亲死在一个春天,临死的时候面色蜡黄,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眼眶干裂;母亲说他是抽烟抽死的。跳舞,离开奥利瓦的时候,她掐死了那只成天在笼子里说西班牙语的鹦鹉,escarabajo,鹦鹉断气前还在重复,尸体被她放在抽屉里的柯尔特手枪边上;合上抽屉,她就这样在冬天塞维利亚的街上,穿着一件单衣跳舞,雪落在头顶。像糖。
随着对讲机的噪声,几个穿警察制服的日本人走上台阶,法国人跟在后边,他们用叽里咕噜的日语问了她些什么,法国人就翻译,他们问:“他跳下去之前,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她想了一会儿,看着威士忌酒杯里融化的最后一颗冰块,说:“‘我出发了。”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