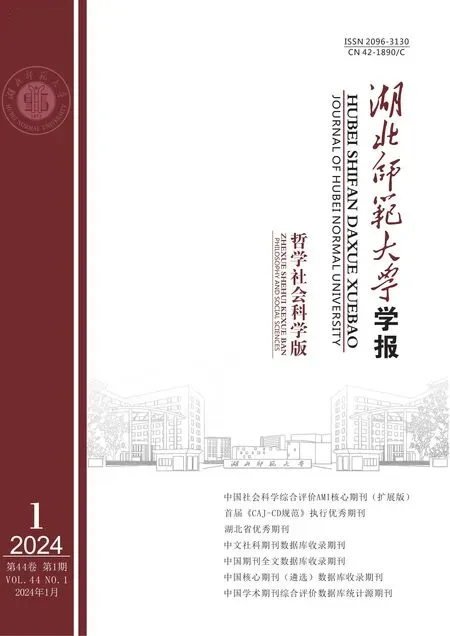文字分蘖生义及其价值研究
黎千驹
(湖北师范大学 离退处,湖北 黄石 435002)
引言
关于文字分蘖生义,前贤时彦曾有过不少类似的论述,只是提法不同,并且分析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例如:
马文熙先生(1987)提出了“词义裂变”说,他指出:“词义运动还存在着另一种方式:词义裂变,即构成本义的异意义素在言语实际的影响下,逸离非加和状态,裂变成两个能独立运用的义位,这两个义位分别与整个词形或某一构件相关。词义裂变是汉语词义运动的特异方式。例如:郝氏谈及的‘景’,《说文》云:‘日光也。从日,京声’,而‘景’又训‘大’‘明’,郝氏于‘大’‘明’义项的产生的解释,既不同于段玉裁的引申说,也不同于朱骏声的假借说,而是另辟蹊径,云:‘景从日,故训明,从京声,故又训大’,将义项‘明’联系于‘景’的构件‘日’,‘大’联系于‘景’的构件‘京’,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词义裂变。”[1]
董琨先生(1994)提出了“兼义造字”说,他指出:“兼义造字的意思,恰如字面所说,就是形体所显示的意义是非单一的。一个字形本身,就可以体现不同的意义,代表一个以上的词。或者起码可以说,这类汉字的单个形体往往孕育着表示一个以上的汉语词义的能力。”董先生认为汉字兼义造字的方式,大致分为“单相的整体型的”和“双相的分体型的”两种,他指出:“单相的整体型的:即一个字的全体部件共同表现某些意义,亦即词义蕴含于全体部件之内。”“双相的分体型的:即一个字的不同部件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亦即词义蕴含于不同的部件之中。”[2]
郝文华先生(2018)提出了“字义蘖变”说,他指出:“一般情况下,合体字整体的意义应该不简单地等于其字符意义。但一些汉字,受各种因素影响,可能脱离表示整体意义的轨道,仅仅表示其字符的意义。也就是说,合体字的字符突破了整字表示某词义系统的常规,使整字在某些场合仅表示与字符相关的意义,字符的意义就从整字义中蘖变滋生出来。”[3]
董琨先生所说的“兼义造字”的第二种造字方式“双相的分体型的”,郝文华先生所说的“字义蘖变”,皆与马文熙先生所说的“词义裂变”大致相当,他们皆发现了词义滋生的一种新方式。然而他们的论文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失之简略,例如:马文熙先生所举“词义裂变”之字只有“景、受、纠、秉、祥、振、祖、扬、疾、次”等;董琨先生所举“双相的分体型的”兼义造字之字只有“幾”和“利”两个字;郝文华先生所举“字义蘖变”之字只有“耆、罔、莫、鲜、半”等。二是所举之字尚有可商之处,下面分别以三位先生所举的一个字为例。
马文熙先生认为,“‘受’的两个逆向义位‘授’‘受’正是词义裂变的结果。”
按,甲骨文“受”字象上下手持舟之形,其中的“舟”象盘之形。《周礼·司尊彝》:“皆有舟。”郑玄注引郑司农云:“舟,尊下台,若今时承盘。”即托盘。“受”字从上面的角度往下看,是一个人用爪将舟授予他人,表示“授予”义;从下面的角度往上看,是一个人用又(手)接过上面爪授予的舟,表示“接受”义。由此可见,“受”的“授予”义与“接受”义,都是由形符构件“爪”“舟”“又”组合而共同表示的意义,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而不存在马文熙先生所说的“词义裂变”;或者说马文熙先生关于“词义裂变”的定义值得商榷,他认为“这两个义位分别与整个词形或某一构件相关”,按,说“这两个义位与某一构件相关”,的确是属于“词义裂变”;而说“这两个义位与整个词形相关”,则难以视为“词义裂变”,因为这两个义位并非是从整个词形中分裂出来的,而都是由整个词形所显示出来的。这倒是合于董琨先生所说的“单相的整体型的”汉字兼义造字的方式。
事实上,不少专家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受”字所表示的这两个意义的。例如:唐兰先生说:“从古文字来看,一字两读的方法,很古就已有了。例如:‘受’字,在古文字里画出两只手传递一只舟,上面的手,表示受予,下面的手表示承受,这一个字应属两方面,后人怕没有分别,把受予义加上手旁作‘授’,表示这去声字和上声的‘受’是不同的。”[4]杨树达先生说:受字“象一人拿手授舟,别一人用手接受之形。《说文》履字下说舟象履形,舟不一定是船。字形既然兼包授受两方的意义,所以金文用受字也具其两面的意思。……《说文》训‘受’做‘相付’,依然是授予的意思。后世用加旁的授字做授予的用法,受字便专做承受义用了。”[5]卜辞“受”字“从二又从舟,盖象甲以一手授舟,乙以一手受之,故字兼授受二义。”[6]
董琨先生认为,“幾”的“微小”义源于部件“絲”;“‘幾’的另一个部件是‘戍’,本身是个‘从人持戈’的会意字,其形与兵象、战事有关,所以含有‘危殆’的意义是不难想见的。……‘幾’的形体的不同部件蕴含了不同的词义。”[2]
按,“幾”的“危殆”义并非其部件“戍”单独表示的,因为从文献资料来看,“戍”并无“危殆”义;从合体字的结构来看,从“戍”之字也没有“危殆”义。其实“危殆”义是由“幾”的形符构件“絲”和“戍”组合而共同表示的。“幾”字从絲,从戍,何以具有“危殆”义呢?《说文》:“幾,微也,殆也。从絲,从戍。戍,兵守也。絲而兵守者,危也。”这就告诉人们“从絲从戍”是表示发现细微的征兆而用兵把守,这是有危机之感,所以“幾”具有“危殆”义。
郝文华先生认为“鲜,从鱼从羊会意,本义是味道美好,但整字可仅仅表示‘鱼’的意义,如《论语》(按,应为《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3]
按,“鲜”的本义并非是“味道美好”,而是鱼名。《说文》:“鲜,鲜鱼也,出貉国。”[7]段玉裁注:“按,此乃鱼名,经传乃叚为新鱻字,又叚为尟少字,而本义废矣。”[8]《说文》:“鱻,新鱼精也。从三鱼,不变鱼。”段玉裁注:“按,此释从三鱼之意,谓不变其生新也。引申为凡物新者之称。……许书‘玼’下云‘新玉色鲜也’,‘党’下云‘不鲜也’,其字盖皆本作鱻。凡鲜明、鲜新字皆当作鱻。自汉人始以鲜代鱻。……今则‘鲜’行而‘鱻’废矣。”[8]
本人(1997)曾提出“分蘖引申”说,认为“这是合体字中不同的形符与声符分别显示不同的词义特点而产生的引申。”[9]现在看来,“分蘖引申”这种表述不太准确,因为该合体字中的两个义项之间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因此,我们现在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字分蘖生义”,并且重新定义为:文字分蘖生义是指合体字中不同的文字构件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其中某个文字构件除了与其他文字构件组合而共同表示某个意义,又单独表示另外的意义。这样就使得某个文字表示两个以上的意义,并且这些意义之间互不关联、互不统属,即没有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这种在同一个合体字中由不同的文字构件而产生出不同意义的现象,就好像某些植物的分蘖,即植物发育时在幼苗靠近土壤部分生出分枝,因此我们称之为“文字分蘖生义”。由文字分蘖而产生的意义叫“分蘖义”。
自马文熙先生于1987年提出“词义裂变”说以来,至今已30多年,而学术界对此研究尚无多大进展。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文字分蘖生义现象作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文以《说文》所收合体字为研究对象,搜集到具有“分蘖生义”现象的文字共70余个。我们从汉字形体结构的角度将文字分蘖生义分为会意字的分蘖生义和形声字的分蘖生义等两种类型。下面我们以《说文》所收合体字为研究对象,辅之以《汉语大字典》[10]和《汉语大词典》[11]等工具书对相关字词的释义,并且参考前贤时彦对相关文字形音义所作的考释,来分类阐释文字分蘖生义现象,探讨文字分蘖生义理论的学术价值。限于篇幅,因此每个小类只举一个字为例。
一、会意字的分蘖生义
会意字(含会意兼形声字)的分蘖生义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其中一个形符又单独表示乙义;第二,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其中一个形符又单独表示两个以上的意义;第三,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分别由不同的形符表示;第四,会意字的本义由一个形符表示,乙义则由另一个形符表示。
(一)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其中一个形符又单独表示乙义
“辟”的本义是“法律;法度”。《说文》:“辟,法也。从卩,从辛,节制其罪也;从口,用法者也。”这个意义是由形符“卩”“辛”与“口”组合而共同表示的。《管子·宙合》:“故谕教者取辟焉。”尹知章注:“辟,法也,取为规矩也。”
“辟”又具有“罪”义。这个意义与“辟”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辛”(按,实则从“”)。“”的本义是“罪”。《说文》:“,辠也。”从“”之字皆有“罪”义。例如《说文》:“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重省声。”“妾,有辠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从女。”“辛”也有“罪”义。《说文》:“宰,辠人在屋下执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因此“辟”字无论是从“”,还是从“辛”,都具有“罪”义。《尔雅·释诂》:“辟,罪也。”[12]《国语·周语上》:“土不备垦,辟在司寇。”韦昭注:“辟,罪也。”
(二)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其中一个形符又单独表示两个以上的意义
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而其中一个形符有时候又单独表示两个以上的意义,并且这两个以上的意义之间并无关联,但分别与该形符所具有的不同的词义特征相关。
“昆”的本义是“同;共同。”《说文》:“昆,同也。从日,从比。”徐锴系传:“日比之,是同也。”[13]这个意义是由形符“日”与“比”组合而共同表示的。扬雄《太玄·攡》:“理生昆群,兼爱之谓仁也。”范望注:“昆,同也。”
然而“昆”又具有“光明”义。这个意义与“昆”的本义无关,而是与其形符“日”相关联。段玉裁注:“从日者明之义也。”《文选·扬雄〈甘泉赋〉》:“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李善注:“昆或为焜。”按,本作“昆”,孳乳为“焜”。
“昆”又具有“大;盛大”义。这个意义既与“昆”的本义无关,也与“昆”的“光明”义无关,但也是与其形符“日”相关联。这是取“日”之光辉盛大的词义特征。《广雅·释诂二》:“昆,盛也。”[14]古时西南少数民族称其大种曰“昆”。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从“昆”声之字有的具有“大;盛大”义,例如《玉篇·鱼部》:“鲲,大鱼。”[15]
“昆”又具有“混同;浑然一体”义。这个意义与“昆”的本义无关,也是来源于其形符“日”。段玉裁注:“今俗谓合同曰浑,其实当用昆,用。”《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按,帛书乙本《老子》作“昆成”。
综上所述,“昆”的“光明”“大;盛大”和“混同;浑然一体”等义皆与其形符“日”相关联,它们分别取自“日”所具有的不同的词义特征,但这三个意义之间并无关联。
(三)会意字的本义由形符与形符组合而共同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分别由不同的形符表示
“奄”的本义是“覆盖”。《说文》:“奄,覆也,大有余也,又欠也。从大从申。申,展也。”段玉裁注:“覆乎下者,往往大乎下,故字从大。”这个意义是由形符“大”和“申”组合而共同表示的。《诗·鲁颂·閟宫》:“奄有下国,俾民稼穑。”郑玄笺:“奄犹覆也。”
然而“奄”又具有“大”义。这个意义与“奄”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大”。“奄”字从“大”,因此“奄”也具有“大”义。《说文》:“奄,大有余也。”《玉篇·大部》:“奄,大也。”《诗·大雅·皇矣》:“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毛传:“奄,大也。”
“奄”又具有“急遽;忽然”义。此义与“奄”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申”。按,“电”“申”古同字,皆写作“申”。甲骨文和金文“申”字皆象闪电之形。例如《说文》:“虹,螮蝀也。状似虫。从虫,工声。……籀文虹从申。申,电也。”段玉裁注:“电者,阴阳激耀也。虹似之,取以会意。”后世在“申”字的基础上增加形符“雨”,遂孳乳为“電”字。《说文》:“電,阴阳激耀也。从雨,从申。”“申”既象闪电之形,而闪电迅速,因此“申”作文字构件时具有“急遽;忽然”这一字素义。“奄”字从“申”,因此“奄”也具有“急遽;忽然”义。《广韵·大部》:“奄,忽也……遽也。”[16]《楚辞·九辩》:“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洪兴祖补注:“奄,忽也,遽也。”
“奄”又具有“久”义。此义与“奄”的本义无关,然而也是来源于其形符“申”。“申”象闪电之形。闪电伴随着雷鸣,经久不息,因此“申”作文字构件时具有“久”这一字素义。“奄”字从“申”,因此“奄”也具有“久”义。《诗·周颂·臣工》:“奄观銍艾。”郑玄笺:“奄,久。” 这个意义也写作“淹”。《汉书·礼乐志》:“神奄留,临须摇。”颜师古注:“奄读曰淹。”
(四)会意字的本义由一个形符表示,乙义则由另一个形符表示
会意字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合并几个相关的字而构成的新字。这几个相关字在会意字里成为形符构件,会意就是把这几个形符构件的意义加以联系,从而表示一个新的意义。由此可见,会意字的意义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符构件的意义组合而共同表示的。上面所举会意字的本义无不如此。然而也有特殊的情况,即某个会意字的本义并非由两个形符构件组合而共同表示的,而是由其中一个形符表示,乙义则由另一个形符表示。
“君”的本义是“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其中“君,尊也,从尹。”是指“君”的“尊”义来源于形符“尹”。《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君,发号,故从口。”是指“君”的“发号”义来源于形符“口”。对此王筠阐释甚明。王筠《说文释例》:“有会意字而所从之字各自为意必不可会意者,许书亦两分说之,不肯勉强扭合,闻疑载疑也。‘君’下云‘尊也,从尹’,此释尹字也。君、尊、尹三字声相近。又云‘发号,故从口’,此释口字也。君字尹口二义,不甚连贯,故许说两对立文。设以在口部而曰从口从尹,则是为君者,尚口也。即如小徐‘从尹口’,又是所治者口也。(人部‘伊’下云‘尹,治天下者’,训尹以治)文义皆不可通。许君说字,必揣圣人制字之意不肯执见成之字,随文说之。遇难说者,比不牵合。今之君子见其字上尹下口,即曰从尹口,亦曾念二字之不相附属乎!”[17]
二、形声字的分蘖生义
形声字的分蘖生义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乙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第二,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第三,形声字的本义由形符单独表示,乙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
(一)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乙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
王筠曰:“‘帝’下云‘从丄,朿声’。此声之全不取义者,与江河一类,正例也。”[17]王筠认为声符不表义的形声字为形声字的正例。我们所说的“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是指此类形声字的形符不能单独表示字义,而只能表示字义的类属或关联;声符表示读音,同时也具有区别字义的功能。以《说文》木部所收的形声字为例:
一组:“李,李果也。从木,子声。”“桃,桃果也。从木,兆声。”
二组:“桢,刚木也。从木,贞声。”“柔,木曲直也。从木,矛声。”
三组:“杠,床前横木也。从木,工声。”“桯,床前几。从木,呈声。”
“李”与“桃”皆从木,这只能表示它们都属于木类,而形符“木”不能单独表示“李”与“桃”的字义,它们分别与声符“子”和“兆”组合之后,才能显示出意义;“桢”和“柔”皆从木,这只能表示它们都具有木的某种属性,而形符“木”不能单独表示“桢”与“柔”的字义,它们分别与声符“贞”和“矛”组合之后,才能显示出意义;“杠”与“桯”皆从木,这只能表示它们都属于木制品,而形符“木”不能单独表示“杠”与“桯”的字义,它们分别与声符“工”和“呈”组合之后,才能显示出意义。换言之,声符“子”和“兆”就是“李”和“桃”字的区别字素;声符“贞”和“矛”就是“桢”和“柔”字的区别字素;声符“工”和“呈”就是“杠”和“桯”字的区别字素。如果没有声符的区别功能,而仅仅依据形符“木”,则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字的意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所以我们说“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下面具体分析此类形声字的分蘖生义现象。
“格”的本义是“树木的长枝条”。《说文》:“格,木长皃。从木,各声。”徐锴系传:“亦谓树高长枝为格。”这个意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木”相关联。司马相如《上林赋》:“夭蟜枝格,偃蹇杪颠。”
然而“格”又具有“至;来”义,这个意义与“格”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声符“各”。“各”的本义是“至;来”。《师艅簋》铭文:“王各大室。”《竞卣》铭文:“白屖父皇竞各于官。”“格”字从“各”声,因此“格”也具有“至;来”义。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各,古格字,故从夊。夊有至义,亦有止义,格训为至,亦训为止矣。”《尔雅·释诂》:“格,至也。”《尔雅·释言》:“格,来也。”《礼记·月令》:“(孟夏)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郑玄注:“格,至也。”
(二)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
有时候,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另外两个以上的意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并且这两个以上的意义之间并无关联,但皆为该声符所具有的意义。
“抗”的本义是“抵御;抗拒”。《说文》:“抗,扦也。从手,亢声。”这个意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手”相关联。《荀子·臣道》:“有能抗君之命。”杨倞注:“抗,拒也。”
“抗”又具有“高”和“举”义。这两个意义与“抗”的本义无关,皆是来源于其声符“亢”。“亢”的本义是“颈项;咽喉”。《说文》:“亢,人颈也。”徐锴系传:“亢,喉咙也。”《汉书·张耳陈馀传》:“高曰:‘所以不死,白张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责塞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岂有面目复事上哉!’乃仰绝亢而死。”“亢”由本义而分别引申为“高”和“举”。段玉裁注:“亢之引申为高也,举也,当也。”《广雅·释诂四》:“亢,高也。”《庄子·人间世》:“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陆德明《经典释文》:“亢,高也。”[18]《谷梁传·僖公十六年》:“五石六鷁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范宁注:“不遗微细,故王道可举。”“抗”字从“亢”声,因此“抗”也具有“高”义。《方言》卷七:“抗,高也。”[19]《淮南子·说山训》:“申徒狄负石自沉于渊,而溺者不可以为抗。”高诱注:“抗,高也。”又具有“举”义。《广雅·释诂一》:“抗,举也。”《礼记·文王世子》:“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
(三)形声字的本义由形符单独表示,乙义则由声符单独表示
我们在上文中已指出:“形声字的本义由整字表示”,是指此类形声字的形符不能单独表示字义,而只能表示字义的类属或关联;声符表示读音,同时也具有区别字义的功能。上面所举形声字的本义无不如此。然而也有特殊的情况,即某个形声字的本义并非由形符与声符组合而共同表示的,而是由其中的形符表示,乙义则由声符表示。
“魁”的本义是“食勺”。《说文·斗部》:“魁,羹斗也。从斗。鬼声。”段玉裁注:“斗,当作枓,古斗枓通用,枓,勺也,抒羹之勺也。”这个意义来源于其形符“斗”。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榆》:“十年之后,魁、椀、瓶、榼、器皿,无所不任。”
“魁”又具有“大;壮伟”义,《广雅·释诂一》:“魁,大也。”这个意义来源于其声符“鬼”。从“鬼”声之字有的具有“大;壮伟”义。例如《说文》:“嵬,高不平也。从山,鬼声。”《广雅·释诂四》:“嵬,高也。”《说文》:“隗,陮隗也。从阜,鬼声。”按,“陮隗”表示“高峻不平貌”,《玉篇》:“隗,高也。”《说文》:“傀,伟也。从人,鬼声。”《广韵·灰韵》:“傀,大皃。”《荀子·性恶》:“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杨倞注:“傀,魁伟,大貌也。”“魁”字从“鬼”声,因此“魁”也具有“大;壮伟”义。《吕氏春秋·劝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高诱注:“魁大之士,名德之人。”
三、文字分蘖生义理论的学术价值
文字分蘖生义理论对于文字学、词汇学和辞书学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有助于深化对汉字形体结构的认识,有助于探求文字的意义及其理据,从而丰富文字学理论;有助于分辨词的固有之义与通假义,有助于掌握多义词纷繁的词义系统,从而丰富词汇学理论,有助于辞书编纂。
(一)有助于深化对汉字形体结构的认识,从而丰富文字学理论
在造字之初,每个汉字的形体都是依据它最初所要表示的词义来绘形的,即所谓“据义绘形”。这一特征在小篆以前的古文字阶段尤为显著。由此可见,汉字的字形与词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然汉字是“据义绘形”的,那么它的形体就会带上意义信息,即“因形示义”。这就使得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成为可能。或者说,汉字的这种“据义绘形”的表意特征为“因形索义”的训诂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所谓“因形索义”,就是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单音词的本义的训诂方法[20]。本义就是指能够直接解释字形并且在实际语言中被应用的词的最初的意义。因为只有本义才能与字形直接切合,才能体现汉字的造字意图。
一般来说,某个汉字往往是为记录语言中的某个词而造的,因此,一个汉字往往只表示语言中的一个词;然而有的汉字是为记录语言中的两个以上词而造的,当某个字形所取象的是两个以上不同的事物,所表示的是互不关联的两个以上的意义时,这个文字实际上是用一个字形来表示两个以上不同的词,即“同字异词”,或曰“同形异字”“异字同形”“一形多用”等。前贤时彦早已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例如,王国维先生说:“长官谓之正,若政,庶官谓之事,此庶官之称事,即称史者也。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21]黄侃先生说:“清世戴震创求本字之说,段玉裁注《说文》,遂壹意推求本字。惟本字、本义实不易断……缘初期象形、指事字,音、义不定于一,一字而含多音,一形而包数义,如一一推寻,亦难指适。且古时一字往往统摄众义,如拘泥于一形一义,而不知所以通之,则或以通义为借义。”[22]杨树达先生说:“甲文多同形异字”[23],“吾人已知囗为古方字,然则甲文田字所从之囗为何字乎?曰:此即经传之祊字也。”[23]“要知道甲文中异字同形的例子很多,譬如壬字与示字同作工。”[24]“古文亯字,后世分化为享亨烹三字。”[25]然而前贤时彦所说的“同字异词”现象,往往是就某个文字的整个字形而言。我们在这里所要补充的是:所谓“同字异词”现象,不仅仅是就某个文字的整个字形而言,也可以就某个文字的整个字形与其文字构件而言,即整个文字字形表示某个意义,而其中的某个文字构件又可以表示另一个意义;或者某个文字中不同的文字构件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并且这些意义之间互不关联、互不统属,即没有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它们都是直接从文字构件中产生出来的意义。我们已在上文对众多会意字和形声字的分蘖生义现象作了阐释。由此可见,明确这种特殊的“同字异词”现象,有助于深化对汉字形体结构的认识,从而丰富文字学理论。
(二)有助于探求文字的意义及其理据,从而丰富文字学理论
一般而言,汉字的意义包括本义、引申义和假借(通假)义。黄侃先生说:“凡字于形、音、义三者完全相当,谓之本义。于字之声音相当,意义相因,而于字形无关者,谓之引申义。于字之声音相当,而形、义皆无关者,谓之假借义。”[22]《说文》正是抓住字的本义来进行说解,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词义训诂的问题,也就为人们辨别假借提供了依据,也为探求词的引申义系统提供了依据。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叙注》中指出:“许之为是书也,以汉人通借繁多,不可究诘,学者不识何字为本字,何义为本义。……故为之依形以说音义,而制字之本义昭然可知。本义既明,则用此字之声而不用此字之义者,乃可定为假借,本义明而假借亦无不明矣。”
然而,随着人们对汉字结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从而发现了这样的现象:某个汉字具有某义,但这个意义既非本义,也非引申义或假借义,并且这个意义与该字的本义不相关联。那么,该字的这个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其得义的理据又何在?如果我们用“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来解释,那么这个意义产生的来源及其得义的理据,则可涣然冰释。例如:
“武”的本义是“与军事、战争有关的事”,跟“文”相对。《说文》:“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武者,兵事也。”这个意义是由形符“止”与“戈”组合而共同表示的。于省吾先生说:“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10]《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然而“武”又具有“足迹;脚印”义。这个意义与“武”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止”。“止”的本义是“足;脚”。《说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按,甲骨文和金文“止”皆象足形。《说文》:“走,趋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徐锴系传:“止则趾也,趾,足也。”《广韵·止韵》:“止,足也。”《汉书·刑法志》:“当斩左止者,笞五百。”颜师古注:“止,足也。”“止”(足)行走则必然会留下足迹,因此“止”作文字构件时有的具有“足迹;脚印”这一字素义。甲骨文和金文的“武”字都象上戈下足之形。“武”字从“止”,因此“武”也具有“足迹;脚印”义。《尔雅·释训》:“武,迹也。”《广雅·释诂》:“武,迹也。”《诗·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楚辞·离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缕”的本义是“麻线”。《说文》:“缕,线也。从糸,娄声。”这个意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糸”相关联。《孟子·滕文公上》:“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
然而“缕”又具有“积聚;增多”义。这个意义与“缕”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声符“娄”。从“娄”声之字有的具有“积聚;增多”义,例如《说文》:“瘘,颈肿也。”颈肿则意味着脖子积聚病菌而增粗,即淋巴结核。“薮,大泽也。从艸,数声。”“数”从“娄”声,亦有“积聚;增多”义,《说文》:“数,计也。从攴,娄声。”计数则意味着不断增多;“薮”从“数”声,本义是“大泽”,即水之所积聚之处。“缕”字从“娄”声,因此“缕”也具有“多;详尽”义。《文选·枚乘〈七发〉》:“虽有心略辞给,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李善注:“缕,辞缕也。”
由此可见,对于上述文字中本义之外的某个或某些义项,如果我们仅仅依据文字学中通常所说的“本义”和“引申义”的理论去解释其词义产生的缘由和得义的理据,则往往使之穿凿附会。如果我们运用“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来分析多义词中的某个或某些义项产生的缘由和得义的理据,则可涣然冰释。由此可见,“文字分蘖生义”理论有助于探求文字的意义及其理据,从而丰富文字学理论。
(三)有助于分辨词的固有之义与通假义,从而丰富词汇学理论,有助于辞书编纂
词具有本义、引申义和通假义,如何区别一个多义词中的某个义项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或通假义呢?黄侃先生指出:“凡字于形、音、义三者完全相当,谓之本义。于字之声音相当,意义相因,而于字形无关者,谓之引申义。于字之声音相当,而形、义皆无关者,谓之假借义。”[22]从表面上看,一词多义使得多义词的各义项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然而实际上并非杂乱无章。一词多义大多是词义引申的结果,而词义引申是按照一定的方式、一定的规律进行的,从而形成一个脉络分明而井然有序的词义系统。然而往往也有这种现象:一个多义词中的某个义项既不是本义(如果不采用“双本义”的话),也不是引申义,并且也不是通假义,但它的确是该词本身所固有的义项,于是有的学者便对该义项曲为之说而视为引申义,或滥用通假而视为通假义。这种现象在辞书编纂中屡见不鲜。下面以辞书中将某些文字固有之义(分蘖义)而误为通假义为例。
《汉语大字典》“凌”字条:2.通“陵”。逾越;超过。
《汉语大词典》“凌”字条:5.渡过;逾越。
按,“凌”的本义是“冰”。《说文》:“凌,仌出也。从仌,朕声。凌,或从夌。”此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仌”相关联。《楚辞·大招》:“冥凌浃行,魂无逃只。”朱熹集注:“凌,冰冻也。”
然而“凌”又具有“超过;经过”义。这个意义虽与“凌”的本义无关,然而这个意义来源于其声符“夌”。《说文》:“夌,越也。”徐锴系传:“越,超越也。”段玉裁注:“凡夌越字当作此,今字或作淩,或作凌,而夌废矣。《檀弓》:‘丧事虽遽,不陵节。’郑曰:‘陵,躐也。’躐与越义同。”从“夌”声之字有的具有“超过;经过”义,例如:“陵”的本义是“大土山”。《说文》:“陵,大阜也。从阜,夌声。”《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然而“陵”又具有“超过;经过”义。这个意义与“陵”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声符“夌”。“凌”字从“夌”声,因此“凌”也具有“超过;经过”义。《广韵》:“凌,历也。”《吕氏春秋·论威》:“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高诱注:“凌,越也。”
由此可见,《汉语大字典》认为“凌”的“逾越;超过”义是通假义,通“陵”,盖误;《汉语大词典》将“凌”的“渡过;逾越”义项视为“凌”的固有之义,而没有处理为通假字。这是对的。
《汉语大字典》“極”字条:(二)jǐ 通“亟”。急。
《汉语大词典》“極”字条:極2 jí 通“亟”。急速。
按,“極”的本义是“屋脊的栋梁”。《说文》:“極,栋也。从木,亟声。”“栋,極也。从木,东声。”段玉裁注:“極者谓屋至高之处。”这个意义是由整字表示的,并且与其形符“木”相关联。
然而“極”又具有“急;急速”义。这个意义与“極”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声符“亟”。“亟”的本义是“急;急速”,《说文》:“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徐锴系传:“承天之时,因地之利,口谋之,手执之,时乎时,不可失,疾也。会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人生天地间,手口并作,敏疾成事也。”[26]从“亟”声之字有的具有“急;急速”义,例如《说文》从“亟”声字共四个,其中就有两个字的本义是“急”。《说文》:“革亟,急也。从革,亟声。”“,疾也。从心,亟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与急字谊同音别。”“極”字从“亟”声,因此“極”也具有“急;急速”义。《荀子·赋》:“出入甚极,莫知其门。”杨倞注:“极……急也。”
由此可见,《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皆将“極”的这个义项视为通假义,通“亟”,盖误。
(四)有助于掌握多义词纷繁的词义系统,从而丰富词汇学理论,有助于辞书编纂
当今语文辞书对多义词义项的排列一般为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这无疑是科学的。然而过去由于没有“分蘖义”之说,于是往往导致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将某个分蘖义视为引申义,却又苦于找不到该意义的得义理据,即该意义是如何由本义引申出来的,于是在引申义的排列顺序时,对该义项的排列似乎显得有些随意性;第二,将某个分蘖义视为通假义,于是将该义项置于通假序列(如上文所举“凌”和“極”字)。下面以“物”字为例来分析其词义系统。
(一)“物”的本义是“杂色牛”。《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为什么“物”是“杂色牛”呢?这是因为“物”从“牛”,因此“物”是“牛”;“物”从“勿”,《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遽称勿勿。”段玉裁注:“九旗之一也。‘州里’当作‘大夫士’。”这种旗帜是用杂帛制作的,因此“勿”具有“杂色”这一语素义,当它作为构件与“牛”组合为“物”字时,就把“杂色”这一语素义带了进来,由此可见,“物”实际上是“从牛,从勿,勿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因此“物”的本义是“杂色牛”。王国维《释物》云:“《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案,许君说甚迂曲。古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诗·小雅》曰:‘三十维物,尔牲则具。’传云:‘异毛色者三十也。’实则三十维物,与三百维群、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谓杂色牛三十也。”[21]
(二)“物”又具有“万物;物体”义。这个意义与“物”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牛”。《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礼记·中庸》:“诚者物之终始。”郑玄注:“物,万物也。”“物”由“万物;物体”义向具体事物方向延展而引申出众多的意义:
1.人是“万物;物体”之一,因此“物”引申为“人;众人”。《左传·昭公十一年》:“晋荀吴谓韩宣子曰:‘不能救陈 ,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杨伯峻注引顾炎武曰:“物,人也。”
2.鬼魅精怪也是“万物;物体”之一,因此“物”引申为“鬼魅精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长桑君)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司马贞索隐:“服之三十日,当见鬼物也。”
3.物产也是“万物;物体”之一,因此“物”引申为“物产”。《周礼·天官·太宰》:“九曰物贡。”郑玄注:“物贡,杂物鱼盐橘柚。”
4.万物生长的环境也是“万物;物体”之一,因此“物”引申为“社会;外界环境”。《礼记·乐记》:“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孔颖达疏:“物,外境也。”
5.事情也是“万物;物体”之一,因此“物”引申为“事情;事务”。《左传·襄公三年》:“建一官而三物成。”杜预注:“物,事也。”
6.人们所说写的内容皆与万事万物相关,因此“物”引申为“事物的内容;特指文章或说话的实际内容”。《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7.既然是万物,则其种类必然繁多,因此“物”引申为“种类”。《周礼·地官·牧人》:“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孙诒让正义:“物犹言种类也。”
(三)“物”又具有“杂色的旗帜”义,为古代九旗之一。《周礼·春官·司常》:“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郑玄注:“通帛为大赤,从周正色,无饰;杂帛者,以帛素饰两侧。”这个意义与“物”的本义无关,而是来源于其形符“勿”。由上文所引《说文》对“勿”的说解和段玉裁的注可知,“勿”的本义是“大夫、士所建杂色的旗帜”。“物”字从“勿”,因此“物”也具有“勿”的“杂色的旗帜”义。《周礼·春官·司常》:“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帅)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其中的“旗物”为同义连用,“大常”“旂”“旃”“物”“旗”“旟”“旐”“旞”“旌”皆是“旗帜”,是为“九旗”。“物”由“杂色的旗帜”义向不同方向延展而引申出众多的意义:
1.“物”向区别性方向延展,王、诸侯、大夫、士等级不同,其所建旗帜亦有别,其名称不同,并且旗帜上所画的图画亦有别,以此作为区别的标志,“物”以其“杂色”之旗帜作为标志,因此“物”又由“杂色的旗帜”之“杂色”义素引申为“标志;记号”。《左传·定公十年》:“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杜预注:“物,识也。”
2.“物”向颜色方向延展,“物”由“杂色的旗帜”之“杂色”义素引申为“颜色”。《周礼·春官·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郑玄注:“物,色也。”
3.认识物类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观察其颜色;或者说观察物类的颜色是辨识物类的重要方法,因此“物”由“颜色”义引申为“辨识;观察”。《左传·昭公七年》:“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杜预注:“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远近之宜。”
下面我们再来看《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物”字条对其词义系统的排列顺序。
《汉语大词典》物:1.杂色牛。引申指杂帛。2.古代九旗之一。3.泛指万物。4.与“我”相对的他物。5.指具体的或个别的物品。6.种类。7.事务,事情。8.事物的内容、实质。9.颜色。10.标志。11.辨识;选择。12.人;众人。13.特指鬼魅精怪。
《汉语大字典》物:1.杂色牛。2.牲畜的种类、品级。3.形色。4.杂色的旗。5.客观存在的物体。6.社会、外界环境。7.哲学用语。8.物产。9.人。10.神灵;精怪。11.古代举行射礼时,射者站立处。其范围事先画定。12.标记;记号。13.特指文章或说话的实际内容。14.典章制度。15.选择;观察。16.法律用语。
相比之下,“物”字的义项排列顺序是否显得有点杂乱呢?如果我们运用“文字分蘖生义”理论,在词义序列当中将“分蘖义”的概念纳入其中,这样既可找到“物”字的每个义项得义的理据,又可以有条不紊地展现“物”字的词义系统,从而使得语文辞书对其各个义项的排列更具层级性与合理性。
——以“人”“彳”字部为例
——以满洲里学院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