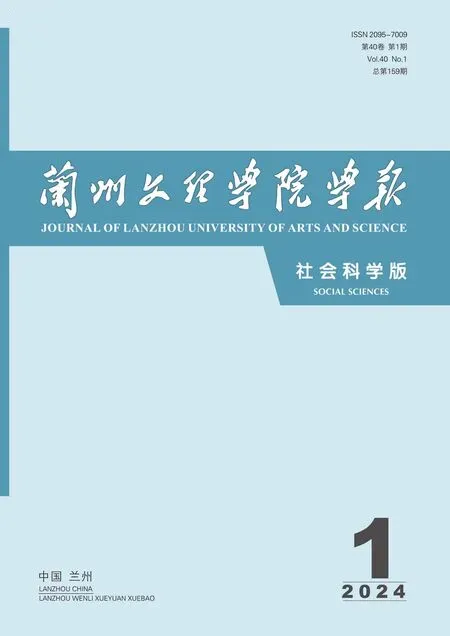何延华小说中乡土的书写与乡愁的守望
彭 文 鼎
(甘肃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甘肃 兰州 730000)
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到鲁迅笔下的故乡,对于乡土的依恋、回忆、回归、守望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书写中永不枯竭的源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一缕乡愁是赓续中华文明的根魂,是在全球化的现代潮流中华夏儿女独特的精神标识和的文化基因。乡土中国,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承载着故乡明月映照的乡愁,承载着天涯游子的思念,也承载着嬗变的阵痛,叛离的痛楚,还有深沉的反思与回望。许多中国作家,用饱含情感的笔端描绘出一幅幅牵人心魂的乡土画卷,成为文学天空中不凋落的星辰。甘肃籍藏族女作家何延华的小说无疑是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创作中具有独特风格值得细读的佳作,其中对乡土的书写与乡愁的守望在乡村振兴视阈下具有特殊的精神感召力,如同阿玛尼卿雪山下一缕带着青草气息的微风,轻柔而沁人心脾。正如程金城先生所言:“作为一位八零后作家,何延华从小生活在多民族群体聚集和传统文化氛围中,不同于都市文化和互联网背景下成长的八零后情感世界。”[1]何延华所熟悉的生活、所用心感受的世界让她的作品如同草原上带着露珠的格桑花,生动、鲜活,把根扎在乡土的大地上,所以散发出清凉沉静的芬芳。
在何延华的小说中,乡土自然具有神性和灵性,和生活在自然中的万物,包括人,有着某种深刻的精神感应和联系。无论是雪山、河流还是草原,都不是静态的景物,而是具有人格和情感的存在。在何延华的小说中,有情的乡土自然是故事叙述展开的独特背景。
何延华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乡土女性。她笔下的乡土女性更多地留存了乡土自然所禀赋的女性美,她们不是受到新思想洗礼的大写的人,她们虽然聪慧美丽但却走不出家的羁绊,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唯独不是自己,但却又在种种身份和责任中找到了独一无二的自己,她们是中国乡土女性的写照,她们无法像娜拉一样出走,也不会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抛家弃子去追求爱情,她们隐忍而顺从,她们用对万物的爱对家庭的爱约束自己的言行,从不放纵,因为对她们而言,生命是一场修行,限制她们自由的锁链都被她们用一生的时间和信念打磨出温润的光华。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以‘现代’为中心的巨大转型。”[2]在中国乡村社会以“现代”为中心发生巨大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传统乡村秩序的瓦解和传统乡村伦理的变化,都给乡土最后的留存带来挑战。城市化的进程中,乡土的温暖让人怀念,乡土的凋敝令人悲凉,温暖和悲凉所形成的张力赋予了何延华小说独特的魅力。何延华的作品中对乡土的细腻书写、对乡愁的真情守望具有打动人心的温度,这种温度也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一、乡土自然的书写
在何延华的小说中有许多对乡土自然的细腻描摹,乡土自然仿若徐徐展开的画卷,成为一个个或温暖或悲凉或诙谐的故事讲述的背景。在何延华中篇小说《拉姆措和拴牢》的开篇有这样的描写:
沿着黄金草原往里走,巍巍雷帝雪山耸入云端,起伏的余脉一直绵延到甘青交界的黄河边。雷帝雪山庄严肃穆,半山腰以上一片雪白,脚下是五月新鲜的黄金草原。一条源自雪山深处的小河,唱着初夏赞美诗,一路闪烁地流下来,把雪山和草原分成了两个世界[3]。
庄严的雪山巍巍耸立,五月的草原充满生机,一条闪烁的小河将雪山和草原分为两个世界。优美动人的初夏藏乡景色不仅是故事展开的画布,同时也是关于人物内心神性与人性的隐喻。一个是肃穆悲悯的神性的世界,一个是悲凉又温情,挣扎又留恋的人性的世界。拉姆措面对智力缺陷的大姑子拴牢给她带来的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桎梏,无边无际如影随形的痛苦把她推向崩溃的边缘,人性在苦难的泥沼中挣扎,而神性散发出莹莹柔光,让灵魂得到救赎。婆婆改嫁,丈夫常年外出打工,被婆家驱逐回娘家的大姑子拴牢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连便溺都无法自控,照顾她的重担落到了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拉姆措身上,拉姆措独自承担这样的苦难,心中常常有不同的声音激烈交战,因为拴牢的存在她本该幸福风光的生活变得黯淡无色,她渴望摆脱,渴望追求幸福生活。智障的大姑子拴牢仿佛枷锁“拴牢”了拉姆措,让她没有办法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她无数次想要遗弃她,但却始终不离不弃地照顾她。当拴牢坠河时有一瞬间她感到自己可以解脱了,但却又奋不顾身去把拴牢救回岸边。一半是雪山,一半是草原,一半是圣洁的神性,一半是苦难的人间。雪山和草原是两个世界,却又彼此依存,就像平凡又善良的拉姆措,她抱怨、焦虑,对着毛驴哭诉自己人生的不幸,但她依然对万物满怀仁慈,在带着拴牢去工地的途中,她把油饼掰开揉碎,转几个圈撒在草丛中,给那些小昆虫们一顿丰盛的施舍,再把剩下的四个都给了拴牢。正是这样一种对人物内心的撕裂挣扎敏锐地捕捉,让对于拉姆措精神世界的描摹如同雪山映照的草原,更加广阔和丰富。
拉姆措和拴牢,这一对苦命又幸运的女人在雪山脚下的草原上相依为命,彼此救赎,直至拴牢为了救拉姆措而永远离开。雪山和草原在季节的流转中从初夏的明丽步入深秋的萧瑟。在何延华的小说中,乡土自然与在乡土上生活的人们始终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共情,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阐释的“有我之境”,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创作视角,“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自然与人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学创作的特殊视角而魅力悠远。始终与主人公拉姆措共情共鸣的乡土自然,是滋养主人公拉姆措心灵的厚土,她的坚韧善良和对万物的悲悯是在雪山草原的滋养下绽放的最美的心灵之花。
在《三月之光》中,何延华这样描写三月的乡土:
在那荡漾着料峭微风的清晨,雷帝雪山山顶首先披上了一层金红的霞光。天空渐渐由金红变为浅蓝,再由浅蓝变成鸽子蛋般淡淡的青绿,田野河流中那超尘绝俗的宁静也渐渐被俗世生活的喧嚣打破。清丽春光把村庄笼罩起来了[4]。
在这样一片生机盎然的春光中,冰雪初融鹅黄初露,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作者讲述一个平凡家庭几十年曲折跋涉的历程,聪慧美丽的母亲和懒惰愚钝的父亲,磕磕绊绊的生活和对幸福永不言弃的向往,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平凡人家的悲喜,生活就像那山间小路蜿蜒曲折,在雪山、田野、河流和三月清丽的春光中缓缓铺陈,情景交融的乡土自然书写意味悠远,三月之光,照亮平凡人对幸福的追求与希望,也每每给这个故事中的家庭在落入低谷时带来希望。时序流转,冬去春来,三月之光象征着希望,象征着奋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效法自然,自强不息的精神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母亲的人生中,面对懒惰愚钝的丈夫、穷困潦倒的家、一双稚龄的儿女,面对劳苦终日没有止境的生活,母亲从来没有想要逃离,而是如同温顺的黄牛拉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在三月的春光中耕耘,最终收获了幸福的生活。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何延华的笔下,乡土自然哺育了祖祖辈辈在大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也充满了神性,具有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与人与万物之间有一种神奇的精神感应。自然景观并非是单纯的物,而是具有人格化特征,象征着自然秩序、道德规约以及古老的传说、不渝的信仰和某种精神力量。在《狼虎滩》的叙述中“菩萨保对世间一切有情众生都怀着一种敬畏、美好而纯洁的感情”[5]。在菩萨保解救落入沼泽的天马时,他从雪山雪峰的形象和传说中山神的故事受到了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和鼓舞;同样,当拴牢落入河水中时,拉姆措也由雷帝雪山的形象感受到道德力量的不可抗拒。
在何延华的小说中,关于乡土自然的书写比比皆是,优美细腻的笔触下,万物皆有神性、人性与灵性。肃穆的雪山,广阔的草原,河流与天地间,人与万物充满温情地相依,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自然地习惯把口中的食物与蚁虫、野狗分享,尊重一切生命。何延华笔下的乡土自然既是自然的景物,也是和人物共情的自然,同时也是人物质朴高贵精神世界的映照,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对乡土自然的书写成为何延华小说的显著特征。
二、乡土女性的书写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何延华在创作的过程中对女性的生命历程有着特殊的关注和洞察,她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丰满生动的女性形象。何延华笔下的女性并非充满了独立意识和性别觉醒的新女性,也不是经济社会地位不逊于男性的都市女性。何延华更钟情于描写那些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传统乡土女性。
拉姆措无疑是其中非常打动人心的一位女性。她为了追求爱情,嫁给了栓牢的弟弟,把丈夫的阿姐视为自己的亲人,智障的拴牢给拉姆措带来无数“磋磨”,但拉姆措不离不弃照顾她,爱护她,虽然无数次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是还是坚定地要照顾拴牢一辈子,“只要我活着,绝不会抛下她”。拉姆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生活的磨难让她比实际年龄更显老,比她大三岁的拴牢看上去比她还要显得年青,但她纯洁高贵的心灵让她像雪山一样圣洁美丽,夏工头也为她的善良和勇气打动,动情地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这种付出和牺牲并不是为了外界的荣誉和肯定,就算让全国人来向她学习她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为了照顾便溺不能自控的拴牢,她的双手没有一天是干净的,但她却依然没有抛下拴牢,只是因为自己心中的不忍。这种战胜自利的本性,无私牺牲和奉献的人格特征,为了心中的善良和不忍放弃自我的人生观,更多地契合中国传统女性的特征。拉姆措自觉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成就了更完美的自我、获得了更大的幸福。拉姆措的矛盾和痛苦是乡土女性在人间的修行。而对于感情的克制和忠贞,是拉姆措内心的另外一场修行。拉姆措丈夫常年外出打工,自己与智障的大姑子拴牢在一起生活,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渴望温暖,渴望关爱,渴望两心相悦的交流是包括拉姆措在内每一位女性内心深处最迫切的需求。正值盛年的空巢妇女拉姆措不仅引来像黑牛这种光棍汉浪荡子的觊觎,她的美丽,能干,她对弱者的怜悯、对自然的亲近也引来工头夏川的尊重和好感。拉姆措无疑是爱慕夏川的,但她鄙视像春芽那样对感情不加约束的行径。当被老阿妈奚落时,春芽为自己辩护的话句句落在拉姆措心上,拉姆措和春芽一样承受着日日夜夜的孤独,但拉姆措知道自己终究和春芽不一样,因为“我懂得羞耻”。拉姆措把感激和爱慕深藏在心底,把认认真真在工地厨房里做好做饭的工作作为对夏川的报答,在心底希望自己做的热面片能够让夏川的胃感到温暖已经是大胆到让她自己感到羞愧的念头,她的言行被理智牢牢约束一丝一毫都不会像同为留守妇女的春芽那样大胆逾越。拉姆措无疑不是一位敢爱敢恨的现代女性,她把爱恨都藏在心底,爱恨如果是如同夏日烈阳一样的火焰,那么她内心的道德感、对自我的约束和隐忍就仿佛洁白的云层,让爱恨的炽烈经过云层的过滤变得更加美好、柔和、持久而打动人心。
《三月之光》中的母亲是何延华笔下另一位美丽聪慧却命运多舛的乡土女性。母亲经历了一个贫寒的童年,她向往美,向往丰富幸福的生活。但母亲却在最美的青春年华被长相漂亮会吹口哨的父亲蛊惑,落入了一地鸡毛的婚姻。天性浪漫的母亲,以为父亲是一个浪漫温暖的归宿,但事实上父亲却成为母亲苦难的源泉,婚后的生活就像虎狼滩的沼泽一样,一点一点企图吞没母亲对幸福的向往,而三月的春光,周而复始点燃这位乡土女性的希望。学缝纫、挖虫草、养羊养兔养鸡、开饭馆……母亲从青春到暮年一直没有停歇追求幸福生活的脚步,哪怕是一次又一次与成功擦肩而过,一次又一次跌入生活的谷底,“这个家里,事无巨细,样样重担,都落在她一个人肩上,父亲只是老天给她派来,捣乱,捅窟窿的”。她面对着不成器的丈夫和贫寒的家庭,从来没有放弃和逃离,而是忍耐地无悔地肩负起生活的重担,拉扯着老老小小和没出息的丈夫,艰难地在通往幸福富足的路上跋涉。她就像大地一样,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在春光的召唤下永远能够孕育幸福与希望。
在《酸卓玛和甜扎西》中,正值妙龄的美丽姑娘卓玛因为要照顾患病的阿爸,照顾贫寒的家,她不能像其他女孩一样打扮好自己去跳锅庄,去和心上人约会唱歌,她把属于少女的心情藏在心里,甚至把炽烈的爱情埋在心底,对钟情已久的扎西也冷言冷语。为了要照顾阿爸不拖累别人,她决心永远不结婚。幸而她遇到了痴情的扎西,在历经曲折后彼此互诉衷曲,结为眷侣,扎西和卓玛共同照顾生病的阿爸,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无论是《拉姆措与拴牢》中的拉姆措,还是《三月之光》中的母亲,抑或是少女卓玛,何延华笔下的乡土女性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际遇和人生经历,但她们大都对家庭有着深深的眷恋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对于自己的亲人、家庭她们可以奉献出自己的青春、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理想。当面对亲人的时候,她们像温顺的羔羊几乎逆来顺受,但面对生活的苦难她们又不屈不挠像百战不屈的勇士,她们像草原上的花儿向往阳光一样向往幸福,她们像扎根乡土的植物,坚韧地生长,把希望的枝叶向天空伸展,也为自己所爱的人撑起一片荫凉。
她们固守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勤劳、坚贞,她们温顺地侍奉老人、相夫教子希望能在最苦的生活中用双手酿出甘甜,但她们并不保守,她们向往外面的世界,她们往往比身边的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能够更勇敢地面对熟悉的乡土之外陌生的广阔世界。但是,保守封建的思想像锁链一样束缚着这些勇敢聪慧的女性,乡间的舆论也常常对她们的奋斗充满了恶意。不论是《三月之光》中的母亲,还是《乔庄新年纪事》的小兰,她们都是为了改变家庭贫寒的窘境、渴望富足幸福的生活而出门打工,但却都受到了恶意的揣测和质疑,被怀疑是“跟着别的男人私奔了”。尤其是《乔庄新年纪事》中的大丽,母亲早逝,为了帮父亲抚养弟妹去城里餐厅打工挣钱,但作为一个闺中女孩去了乡亲们眼中的“花花世界”而被舆论所不容,成为名声不好婚嫁受到歧视的对象,最终在重重压力之下只能选择和先天畸形的“雏脖”结婚,最终酿成了自杀未遂、精神失常的悲剧。
何延华笔下的乡土女性从乡土的清风流水中汲取生命的芳华,她们像乡野间的植物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论在何种境况下都用尽全力去生活,她们的生活有悲剧也有喜剧,同样都质朴、热烈。
三、乡土的温暖与悲凉
在小说集《嘉禾的夏天》后记中,何延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脑海里清晰的浮现出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我一点一滴感受和挖掘着它的光亮和价值,愈是深入愈是迷恋,就像深深地眷恋着母亲[6]。
何延华对乡土的情感和眷恋让她让她对乡土的感悟和描摹入木三分。因为细致入微的体察,何延华笔下的乡土格外真实,乡土的温暖与悲凉都在她笔端的娓娓倾诉中流淌。
何延华笔下的乡土充满了令人眷恋的温暖气息,缓慢而轻灵的时光化为光影清风,掠过肃穆的雪山、清澈的河流、无边无际的草原、万物生长充满希望的田野,还有熊熊燃烧的灶火,美味的青稞、土豆、酥油,善良的老阿妈和淳朴的姑娘……乡间的人情格外醇厚,拉姆措会不离不弃地照顾智障的大姑子拴牢;打工的媳妇儿会把挣来的钱尽数交给家里的老人;横眉立眼的屠户也会给村里生病的穷人送去一罐免费的肉汤一块炖肉……古朴憨拙的农庄有一种别样的宁静安详和温暖,村里的人亲如一家,不论春种秋收、红白喜事还是天灾人祸都紧紧地彼此依靠,相互帮助,将朴素的日子温暖执着地向前推进,渡过一个个人生的难关,迎来一个个人生的春天。中华文明所根植的农耕文明就像温暖的乡土,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打动心灵的魅力,何延华对乡土的温暖书写是对乡愁执着的守望。
在现代化城镇化潮流的裹挟之下,青壮年乡民从像候鸟一样去城镇打工往来奔波,到像断了线的纸鸢,杳无音讯,乡间留下的是老人、妇孺,乡土的温暖渐渐凋零,对现实的关注,对弱者的关怀,对乡愁的守望,在何延华笔下有了温润绵密的质感。在《拉姆措和拴牢》中,拉姆措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村庄:“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人们一过完年,就出门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些学生娃和老汉。”[7]当春芽流露出对工头夏川的爱慕受到老阿妈斥责时,她为自己的辩解也是对留守妇女困境的控诉。
在《乔庄新年纪事》的开篇描绘出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原本世代种田畜牧,但这几年因为“城里活多,挣钱的门路广”所以庄里的男人们就像追逐花源的蜜蜂一群一群飞进了城里,空了的乔庄就像一个偏瘫患者,一个暮年女人,一方死水池塘或者一块缺水的庄稼。桑吉草的丈夫或许是一群人的缩影,像无根的飘蓬,最终彻底抛下了妻儿离开了乡土,越飘越远。
《乔庄新年纪事》的结尾,落寞得如同一声悠长的叹,而相比起乡村人口的迁徙和表面的凋敝更令人痛心的是传统道德秩序的坍塌。醇厚的乡俗民风受到冲击,乡民原本清晰的道德观念道德约束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变得淡薄甚至沦丧。《三月之光》中,开在岔路口的饭馆也让这淳朴的一家面临道德选择的岔路口,本分经商还是邪门歪道就像两条岔路,一条坎坎坷坷通往幸福,一条纸醉金迷走向深渊,幸运的是当他们接受了生活沉痛的教训终于在又一年三月的春光里找回了淳朴的初心,变得更加成熟。但在《嘉禾的夏天》中,大林的父母忍受不了贫寒的生活各自远走他乡,他们遗弃了可怜的大林,也遗弃了大林的祖父。祖父病重的时候,祖父的养子麦积叔叔也置之不顾,即便是祖里的长辈三番五次地劝说施压,麦积还是没有拿出一分钱,最终,大林的祖父病逝,大林成为了孤儿……《乔庄新年纪事》中桑吉草的丈夫也在进城挣到钱后无情地抛弃了桑吉草母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金钱和利益的巨大诱惑驱使下,乡土的传统和礼俗被藐视,道德规范被挑战,何延华笔下悲剧中痛苦的泪水仿若洗濯灵魂的清泉雪水,让人清醒,引人深思。
在《乔庄新年纪事》中,何延华用“并非结局……”作为最后结尾部分的小标题显然是寄寓了深意和希冀,小林和三个孩子站立村头,扯长了脖子,像大小四只哼猴,眼望远方一动不动的身影是无声而悠远的呼唤。乡土大地是中华民族的根魂,当乡土成为风中萧瑟的空巢,乡愁呼唤游子的回归和城市文明的反哺。那守望的身影,魂牵梦绕的乡愁,是对乡村振兴最热切的呼唤。
四、结语
何延华的乡土书写以扎根乡土的姿态,仿若蓝天映衬下的绿叶,清新自然,在书写人生艰难的同时用心表达真善美的尊贵。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厚重的传承和独特的魅力,何延华的创作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文脉,不以新奇的写作技巧博人眼球,而是以优美的语言,质朴的表达,让作品呈现出像春草河流一样蓬勃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8]何延华的小说作品无疑是符合这个评价标准的,虽然从作者所处的年龄阶段和创作阶段而言,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巅峰,但她目前的作品已然如清风阳光,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
何延华的乡土书写基于对乡土的深情、对人民的热爱,用心创作是一种高贵的创作方式,也是作家最为可贵的操守。何延华的乡土书写基于微观的人物生活,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乡土人物的命运展开,用一叶知秋、见微知著的手法映照一个大时代的变迁,从而更贴切生动地感受时代的脉搏。对于乡土自然的独特感知、对乡土女性的深刻理解让她笔下的乡土格外迷人,在她的作品中对乡土的深情书写和对乡愁的执着守望更有着一种润物无声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