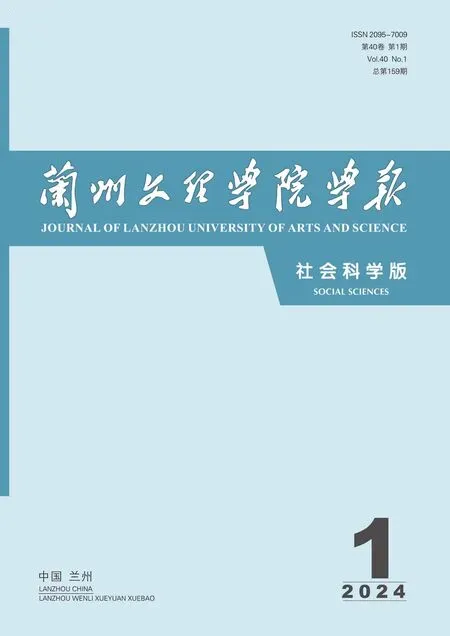从空间的联结到联结的空间:一个鲁东郊区集市的空间重构研究
刘 念,李 建 宗
(青海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我国传统集市深度嵌入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在地方社会的运行与整合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因此,针对集市的研究往往呈现出多层次、跨学科的特征。追溯中国集市研究学术脉络,则不难发现施坚雅(G.W. Skinner)的巨大影响力。施坚雅批判地吸收了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廖什(A. Lösch)、杨庆堃、杨懋春与费孝通等国内外学者的市场研究成果①,从实证调查资料中提炼中国集市空间层级的结构特征,追溯集市时空结构形成的社会过程,展现了中国市场在社会研究中的范式价值[1]。施坚雅将地理与经济因素视作形塑中国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而文化、政治等因素则被放置在市场结构的背面,体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2]。追溯施坚雅模式理论基础——“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则可以发现,该理论以理想地表假设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将空间归为一种可被精准量化及模型化的研究客体,在高度模型化的理论中,空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各类空间在堆叠中所呈现的统一性被极大地简化与遮蔽了。施坚雅曾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中对中国乡村基层集市的未来发展做出过预测:“传统时代市场体系的‘发展’所依赖的密集过程使市场区域的面积随着新集镇在这个地区的不断增加而持续缩减,而集镇转化为现代贸易中心所依赖的过程却使市场区域的面积随着旧市场的关闭而不断扩大。”[3]施坚雅认为,中国农村“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与“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的辐射范围会不断增加,并最终在基层市场的消亡中转化为现代贸易中心。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集市的发展状况显然要复杂得多,物质性与结构性空间远不足以展现集市空间的全部面向,更无法完整解释集市存续的原因,集市空间在抽象的结构空间之外还有一个广阔而复杂的世界,它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现的场所,那么它也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对抗场地。”[4]
当今学术界对社会空间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列斐伏尔的理论框架,其对空间的总体性的阐释以及对空间实践的阐发彰显了空间主体、本体与客体的三元辩证关系,拓宽了空间研究的现实可能。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始终伴随着这样的现实底色:“自然空间(natural space)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虽然它当然是社会过程的起源,自然现在已经被降贬为社会生产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质了。”[5]空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空间的历史可被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区分与命名,这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社会空间的现实支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伴随社会空间急剧变迁。今天的集市空间呈现出强烈的“断裂感”,这种断裂感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现实性的。从历史上看,乡村集市扎根于自然经济而存在,而城市则是市场经济与政治、文化的中心。与乡村相比,城市往往更具行政势能优势,城市周边的乡镇及其市场体系在城市发展规划过程中常常扮演着被整合的角色,许多乡村集市空间也从原来的地方中心变成了需要被整合的边缘。从现实角度看,集市中的实践个体往往会同时受到现代市场规则与传统社会关系的影响。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集市实践主体可以时刻在文化圈与贸易圈的中心与边缘间流动[6],集市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空间生产过程变得更为复杂。面对这一现实,空间所关联的丰富理论资源以及当代社会空间理论对空间辩证性的关照让集市空间有了连接“城市—乡村”与“实践主体—社会空间”这两组对立概念的可能。空间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同一性关系被进一步强调,实践主体与作为实践对象的空间之间的连接则以生产之名获得了可被观测的支点。
本文将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市郊集(化名)为例,梳理这一地处城市外缘空间的传统集市社会空间的重构脉络。集市所在的市郊镇背山靠海,近年来,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显著。市郊集兴起于清中期[7],1949年以前,在地方经济发展与居民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1949年以后,市郊集转型为以政府主导的物资交流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集市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快速扩张,并于1991年、2004年及2016年三度位移,目前集市位于城市郊区城乡结合地带地铁站旁的一片空地中。市郊集于2012年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媒体力量的介入以及地方交通建设让集市知名度大幅提升,城市消费者已日益成为集市消费主力。
二、集市之外:集市连接的空间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TheRiseofTheNetworkSociety)中提出了“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概念。在地方空间中,人们的实践与地域性紧密相连,空间的形式、功能与意义都在物理空间框架内展开。在流动空间中,流动是“支配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8]。空间被接入了一个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网络中。“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纳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市郊集连接空间的部分特征。
(一)连接地方空间的集市
市郊镇依山傍海,极具区位优势。一位居住在距市郊镇三十多公里外山区的村民曾回忆自己20世纪60年代的赶集经历:
俺赶集都说个“前七后八”,从藏马庄走到塔山顶有十七里,从塔山顶到集上有十八里。塔山顶上棵白果树(银杏树),算是个神树,这片有不少人去拜。俺去集上一般带着花生、嘎子(葛根)和烟叶子,换人家的海货,拿着这些海货再带着去六汪卖,六汪也是个山埝(山区),俺去那卖海货换地瓜干养孩子。俺刚去赶市郊集的时候在路上碰见过个择驴蹄子的,他是东王家夼村的,俺家离那也近。他看俺几个是新来还过来跟俺搭话哩,说现在集上咱山后头(塔山西)的人来得多了,人家欺负不着咱了。那择驴蹄子的说话办事儿真不糙,俺村这几个赶集的碰上他就和他一块儿,咱山后头的人在集上碰着了都能拉拉呱。俺那时候赶集得跟大队请假说回娘家,要不逮着了就是投机倒把。还有个离俺家近的集叫市美集,市美集没那么些海货,自行车这些稀罕件也没有。俺也上市美卖货认得的人就多了,有一回俺嘎子卖贱了,俺兄弟又找的熟人要回来,还跟人打仗哩,得为(因为)我卖贱了。集上的人跟俺说,那是叫贩子买了,人家在市美买了再上市郊集卖。孩子他爷(父亲)愿意上市郊集直接卖给使嘎子做渔绳子的,不容易卖贱②。
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中将集市分为“基本集”和“辅助集”,“基本集”用于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消费和生产的普通需要”,辅助集则“既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但同时也供给生活中的特殊需要”[9]。通过访谈对象的陈述,大致可将市美集视作“基本集”,将市郊集视作“辅助集”。市郊集的特殊地位源于其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与优越的交通条件,尽管市郊集辐射空间内人们的生产性质与生活方式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但在赶集人心中,这一空间并不是一个在意义上完全均质的空间。在市郊集的辐射空间中,塔山是一个重要的坐标,它不仅是地理的高地,更是意义与经验的高地。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的意象就是地方的认同,而对其意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展开思考,就是理解地方认同的前提条件。”此外雷尔夫还提出“意象能够在具有意义的事物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里提供较为稳定的秩序,所以意象可以被人们用来诠释信息与指导行为。”[10]赶集人的地方认同与作为地方意象的塔山深刻绑定,这并不只是赶集人对特殊客观现实产生心理映像的结果,它还反映了赶集人指向实践的能动目的。“前七后八”正是一种依附于塔山而传播开来的行为指导,它构成了赶集人对赶集路上的空间的稳定认知,帮助人们理解自己的空间位置。塔山这一意象借助“白果树”符号以及“前七后八”等地方经验而流传开来,成为市郊集辐射空间内的地方认同分界点。
集市是一个充满竞争性与流动性的场域,赶集人需要在博弈中争取自己的位置。“择驴蹄子的”正是基于这一需要而唤醒了其他山后赶集人的地方认同,由此,“山后头的”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延伸到了集市,在集市空间内形成了一种地缘差序格局。赶集人对地方的认知与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相互绑定,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构成形塑市郊集社会空间的重要力量。而随着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塔山以西的农民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郊集满足调剂余缺或谋生的需要。今天市郊集的农民摊主更多来自丁石洼、琅琊、大村以及高戈庄等周边村庄③。山后赶集人基于地方认同而生产出的那片社会关系空间已然从市郊集中消失了,集市所连接的社会空间逐渐转至城市区域。
(二)连接流动空间的集市
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今天的市郊集无疑更具流动性。2018年底,市郊地铁站投入运营,每到“逢四逢九”赶集日,便会有大量城市居民乘地铁赶集,13号线地铁也因此被当地人戏称为“赶集专线”。此外,网络媒介的影响进一步扩散,吸引了大量城市消费者。与地方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与流动性让它在制造关系方面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媒体不发达时期,人们需要通过亲临集市或者口耳相传的方式才能获得有关集市的经验。而在今天的集市中,网络空间支撑起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论及的“跨距离互动”,交通建设则为保障“现场卷入”互动提供了现实条件[11]。
流动性提升给集市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辐射空间异质性的提升。前现代社会集市辐射范围内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较强同质性,区隔集市参与者的主要变量为人们的地方身份自觉。当市郊集与城区关系加深后,城乡生产关系的差异给集市场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发生在集市中的空间博弈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城乡关系格局。以波普金(S.Popkin)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者认为:“小农是一个在平衡长短期利益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的合理的生产抉择的人。”[12]伴随地方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与城市消费者的介入,具有更高消费能力的城市消费者愈发受到摊主们的重视。目前市郊集由私营企业进行管理,市场化管理方式催化了集市摊贩对盈利的需求,在此层面上,城市对乡村市场、经济与文化上的整合已然发生。正如卡斯特所言:“由于我们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由于经验关联于地方,因而抽离了权力,且意义逐渐与知识分离。结果是两种空间逻择之间的结构性精神分离,构成破坏社会沟通渠道的威胁。”[8]39
流动空间构建了市郊集参与者新的实践逻辑,进而也引发了集市权力关系洗牌。集市买卖双方博弈状况是观测集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窗口,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对摩洛哥塞夫鲁集市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就关注到了买卖双方的博弈方式,他认为集市中的信息往往呈现出系统性的稀缺和不对称,“照顾老主顾”与“砍价”行为是缩减信息搜集成本以及抵御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手段[13]。前文中访谈对象所描述的那个“货卖贱了”的事例也是集市信息不对称的体现,但在地方空间中,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一系列地缘或血缘关系的交叠使双方始终处在一种非正式监督之下。但在今天,买卖双方的博弈环境已然变化,笔者曾在集市中目睹过两次买卖纷争。
第一次为海鲜干摊主与消费者的纷争。一位外地消费者通过向其他摊主询价的方式发现自己买的鱼干在产品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每斤售价比其他摊位多出二十余元,消费者决定退货,但遭到摊主拒绝,消费者无计可施。第二次为海鲜摊主与一位年轻消费者的纷争,消费者发现摊主使用了“鬼秤”。摊主提出以退货作为解决方案,但消费者并不满意,同时要对摊位进行录像并在网络社交平台曝光,海鲜摊摊主向该消费者郑重道歉并赠送了一袋舌头鱼,消费者就此作罢④。
不同于传统地方社会的集市,在今天的市郊集中,多数消费者并不会成为“老主顾”,“一锤子买卖”已经成为大集上做生意的新常态。在监管相对松散的情况下,摊主们的逐利动机得到了继续伸展的空间。在另一事例中,海鲜摊摊主对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有着清晰的认知,信息的流动性为城市消费者提供了新的的权力来源,谁掌握了流动空间的话语权,谁就可以在集市场域内占据更高的权力位置。在集市参与者的实践过程中,流动本身已然是实践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流动中愈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对相关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也产生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当然,对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的区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分析,为的是更清晰地梳理重构集市空间的变迁过程,现实中的市郊集始终是一个混杂多元的空间。也正是在这种多元空间格局背景之下,集市中不同主体的实践活动呈现出愈发分化的趋势。
三、集市之中:日常与非日常的实践
(一)实践中的消费者
现代市场体系对包括空间在内的资源整合的需要已然成为影响市郊集参与者的实践逻辑的重要现实背景。大卫·哈维认为:“资本跨越地球表面的地球流动,极大地突出了那些可能吸引资本的空间的独特品质。把各种社群跨越地球带入相互竞争的空间的收缩意味着地方化的竞争策略,以及意识到了使一个场所变得特殊并赋予它一种竞争优势的特质的增强了的感受。这种反应更加强烈得多地留意场所的证明,在一个日益同质化却分裂的世界之中建立和标明自己独特的品质。”[14]这一点也体现在在市郊集空间中,集市入口处的巨大招牌以及集市中充斥的“传统”“特色”等字眼,都在试图彰显市郊集的时间厚度与空间特殊性。
集市的南侧邻近公路与地铁站,是消费者进入集市的一侧,俯瞰集市时可以明显发现集市南侧与北侧的人流量与摊位数对比状况。集市南侧摊位主要售卖海鲜以及包括海鲜烩饼、羊肉汤和炉包等特色小吃,摊主们对食材进行现场加工,消费者们则在摊位旁的桌上品尝刚出锅的小吃。段义孚认为:“地方是运动中的停顿,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会停留在一个能满足某些生物需求的地方,停顿使一个地方有可能成为一个感受价值的中心。”[15]依靠品尝特色小吃这一实践活动,地方要素穿透人们的感官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地方作为一种感受被进一步强调,这使集市小吃格外受到城市消费者的欢迎。据常年赶集的摊主介绍,市郊集的海鲜烩饼、羊肉汤以及炉包摊位在附近地铁线路开通后便呈现出明显的扩容趋势。满足了城市消费者需求的南侧集市空间也将城市消费者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一并固定在了这个位置上。
20世纪60年代的集市参与者大多对集市中商品的使用价值有着深刻而完整的认知,集市是嵌入于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生产生活经验在心中勾画出商品生产与使用的价值链条。而现代市场中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则往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历经漫长产业链的商品以完善而又多元的面貌呈现于消费者面前。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相比,商品交换价值更能被其生产端与销售端所体认,现代消费者在面对浓缩了繁复生产工序的商品时则更是无力完整感知商品背后生产者们的实践意义。现代市场的消费者们已日益习惯于对商品意义的片面化思考,齐美尔所阐述的“文化悲剧”已经普遍地发生了[16],在此社会背景之下,贴近生产实践全貌的农村集市的特殊性得以成立。
一位市郊集的年轻消费者曾这样表达过她对赶集的看法:“我感觉海鲜烩饼做法挺家常的,味道也没让我特别惊艳,这边的东西也没便宜到哪去,就是看看热闹感觉挺有意思的。”⑤笔者在市郊集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城市消费者们类似的表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地消费那些被媒体与市场所塑造的符号,琐碎与悬浮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而集市这样一个可通过城市消费者们所熟悉的消费方式抵达的他人日常生活空间,无疑可以成为城市消费者们脱离日常的理想空间。城市消费者出于对非日常实践的需求而倾向于选择能带给他们更多实践感与新鲜感的商品,继而有选择性地为集市空间注入了经济活力。除此之外,集市中城市消费者们的消费行为本身也具有文化属性与象征意味,伴随着城市消费者们的消费实践所一同到达集市的还有现代消费文化。在这个消费符号的生产与复制变得异常容易的时代,集市中的摊主并没有太多与之抗衡的动机。
(二)实践中的摊主
相对应地,市郊集南侧摊主有着明显的服务于城市消费者的意识,笔者曾向从前赶集的老人询问早年市郊集售卖海鲜烩饼与羊肉汤的情形,但许多老人对这两种小吃十分陌生,经过详细沟通,老人们才理解到:海鲜烩饼其实是“烩火子”,而羊肉汤则与早年“馇锅子肉”类似。摊主们主动远离容易使城市消费者产生理解障碍的相对传统、具有地域性的农业社会文化语境,重塑了自己的语言。列斐伏尔曾这样阐释过异化:“异化是一种与‘他性’关系的结果,这个关系使我们成为‘其他’,即与这种‘他性’的关系改变了我们,把我们与我们自己撕裂开。”[17]以现代消费文化为他性,列斐伏尔所论述的“异化”已经在市郊集中深刻地发生了。雷尔夫认为,地方的本真态度意味着“人对地方的意义、象征与特征能够给予真切的回应”,[10]124地方的非本真态度,即“无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则意味着“对地方的深度象征意义缺乏关注,也对地方的认同缺乏体会。”[10]131对于城市消费者而言,接触这些被切断文化语境的语言往往意味着他们无法在集市空间内部获得所谓“地方的本真态度”。在网络空间中,市郊集进一步与“人间烟火气”“网红打卡地”和“非遗大集”等易被复制的去语境化流行符号绑定。这些符号的传播为摊主带来了实际收益,令摊主们也纷纷加入到了对符号的复制中,在脱离日常社会性的空间下,消费者们难以经由被斩断文化之根的语言抵达真正的“地方”。
市郊集北侧商品仍以农副产品、低价工业化产品以及农业生产工具为主,更能展现农村消费面貌。北侧摊主对商品意义的理解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相关,他们往往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有着深刻感受。笔者曾在集上目睹过几位年轻的城市消费者在北侧摊位购买衣物的场景:摊位售卖的是农村集市中常见的衣物,这些衣物的样式有别于城市年轻消费者以往的服装审美。几位年轻消费者选择了几件颜色鲜艳的秋裤和花坎肩套在了身上,随后边互相打趣边拍短视频。而摊主则不断强调衣服实用耐穿,最终两方达成交易。摊主与消费者各自的日常生活经验间有着巨大隔阂,集市流通商品原本连续地嵌入于买方与卖方日常生活的意义链条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斩断了。如果将时间线继续延伸,可以预见,随着当地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农民消费者所形成的市场会继续缩小,而市郊集原本连接农民消费者与摊主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空间也将进一步萎缩。
四、结语
市郊集对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的联结体现了其历史面向的空间变迁,而当下集市内部的社会空间秩序则可被视作是城乡社会空间关系的映射。现代化进程中,集市等传统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与现代性日常生活产生紧密联动,这一过程始终包含着历史因素,只是这种历史因素不是历史传统的直接继承,而是不断再生产着的社会现实的重构因素[18]。在理解如今同质化、碎片化特征愈发显著的社会空间时,对“连贯”与“断裂”的阐释应当成为理解空间历史过程的一体两面。
从集市外部视角出发,进入集市的城市消费者有着理解具有意义与历史积淀的“地方空间”的需要,人们对碎片化、同质化的日常生活的抵抗正逐渐成为滋生多元社会空间的土壤。集市空间流动性的增强为消费者多元身的份建构提供了条件,而集市也在当代日常生活的缝隙中找到了生长空间。从集市内部视角出发,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摧毁了维系传统集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集市逐渐成为现代市场体系的一环。集市服务于乡村地方社会的属性不断地被市场逻辑所冲击,逐渐“脱嵌”于地方社会居民原生的生产生活需要,集市的“市场性”不断地挤压和摧毁着“地方性”的空间,也消耗着传统集市发展的可能性。总之,当代传统集市社会空间转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平衡和融合外部“地方性”期待与内部“市场性”需要的过程。
【注释】
① 参见[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施坚雅以克里斯塔勒与廖什所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划分了中国市场层级。相关内容参见施坚雅前书第5-11页。施坚雅在研究中多次引用杨庆堃在《华北地方市场经济》中的论述,吸收并改进了杨庆堃对中国集市的结构划分。相关内容参见施坚雅前书第8页、第57页注释12。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强调了基层市场在整合地方社会与廓清集镇辐射范围等方面的作用,同时提出“市镇共同体组织”将充分适应中国农村未来转型发展,施坚雅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人民公社的现实影响。相关内容参见施坚雅前书第152-153页。施坚雅在分析中国经济单位与政治单位分布位置关系的过程中批判地吸收了费孝通在《中国绅士:城乡关系论文集》中对驻防镇与集镇关系的论述。相关内容参见施坚雅前书第9页、第58页注释15。
② 访谈对象:FXA,女,82岁;访谈时间:2023年1月30日;访谈地点: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饶子阿村。
③ 根据笔者田野调查资料整理得来。
④ 此处内容为笔者对田野调查资料的概括。
⑤ 访谈对象:FX,女,22岁;访谈时间:2023年2月19日;访谈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