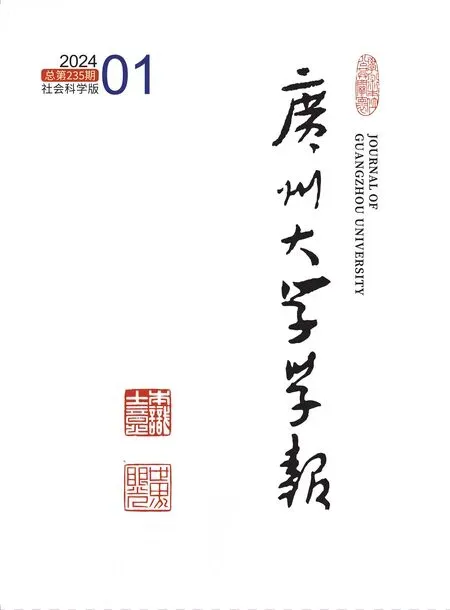主体·时间·空间:新媒介文艺生成性研究
别君华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浙江杭州 311121)
就新媒介文艺出场的社会历史语境而言,在新媒介、新技术的不断推动下,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状况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作为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趋势,新媒介日益组织起一系列文化生产和消费。同时,这一新的符号环境、感知环境、社会环境也构成了新媒介文艺生产的语境,新媒介作为新的支配性媒介为文艺生产现实、观念、实践带来了新的技术意向与文化尺度。但是长期以来,媒介问题即使在新媒介文艺理论研究中也未占据核心位置。与其说新媒介一直被视为跨媒介书写技艺的载体,毋宁说其内在生成性构成了当前文艺生产的技术尺度与重组逻辑。由于对日常文艺实践活动、现象牵连到的技术范围及其作用程度过于熟悉,我们往往将这种技术构造的生活世界、文化系统视为“自然的”,而缺乏必要的以媒介技术的意向性为起点的研究。
技术的意向性表明,技术不是中性的,它自身的意向性决定了我们体验外部世界时感觉材料的方式,此时技术形式的重要性高于媒介的具体内容。媒介技术哲学通过“媒介的偏向”这一理论探讨不同媒介结构与人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从伊尼斯《传播的偏向》对媒介的时空偏向、口头偏向、书面偏向的探讨,到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对媒介感官偏向的划分,我们发现,媒介的“任何意向结构,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由技术的意向结构所规定的这种价值取向,我们也称为技术的逻辑”。[2]
既有研究将“虚拟真实性”[3]“交互性”[4]“存在论”[5]“交往性”[6]等确立为新媒介文艺的内在偏向。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德勒兹的“生成”理论,创造性地将“生成性”确定为新媒介文艺的技术意向,通过考察生成如何作用于主体、时间和空间三个构成新媒介文艺生产域的基础锚点,进一步揭示新媒介文艺生产实践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深层逻辑,批判地介入媒介技术的当代经验,进而推动文艺创新。
一、生成:新媒介技术的意向性
什么是生成?“生成”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的哲学与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德勒兹几乎全部的思想与写作都与生成密切相关,他提出的“游牧”“欲望机器”“无器官的身体”“逃逸线”“褶子”“解辖域化”等一系列重要概念,都与他对“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的偏爱息息相关,这些概念反映了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富有流动性的特质。
生成性美学思想的意义首先在于对柏拉图主义及其模仿论的颠覆。柏拉图认为,现实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而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实隔了三层”。相对于古希腊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的传统而言,生存论否定了生成具有一个确定的源头作为基点,因而也就否定了真实/虚假、理念/现实这类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及其预设,从而使得后结构主义肯定差异、流变和多样性的生成性美学成为可能,也为审视、阐释、批评当代新媒介文艺提供了新的维度。
如何生成?实际上,“生成”与“欲望”这一具有反本质、反总体、精神分裂式朝向的本体息息相关。“欲望”是“流”,世界上一切存在皆不过是生成生命(becoming-life)过程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7]德勒兹反对传统西方哲学从主观心灵的角度看待欲望,而是将其视作客体。欲望“不是匮乏,它由连接组成”[8],物质性的欲望生机勃勃地扩张自身,创造性地寻求与周围任何客体的连接。
正是欲望机器的生命流,赋予了生成以主动性,生成就建立在欲望之流不断“解辖域化”的基础上。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试图对不同社会体制控制欲望的方式做历史分析:通过法律、契约和官僚制度手段,欲望被编码为总体化的、同质化的、静态的、理性的俘虏,而不是真实流动的饱含生命力的欲望本身,这一操作过程被称为“辖域化”。而将生产欲望从社会枷锁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被称为“解辖域化”,它努力摆脱固定辖域的束缚,旨在创造流变、跨界、联结、蔓延、生成、创造和突破的一系列可能。
“块茎”是展开“生成”的具体形态。在与瓜塔里合著的《千高原》中,德勒兹用“块茎”作为“解辖域化”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关于生成性、流动性和多样性的后现代理论。“块茎”一词来源于植物学,从形象上看,块茎如同铜钱草的须根,向四面八方延展,它没有固定的范围、方向,只有不断衍生差异、不断奔流出生命力、不断生成多元化的连接、不断溢出并寻求连接。在德勒兹看来,居于社会边缘位置的妓女、拾荒者、飞车党、精神分裂者是块茎,大自然中的草场、蜂群、狼群、蚁群是块茎,文学中卡夫卡、普鲁斯特、尼采的文本也是块茎,造型艺术中的立体主义也是块茎,块茎通过完全粉碎内部空间来探索多重形象的表现力:爆炸性的空间感以无法抑制的推动力溢出画面,成为连结多重时间观和空间观的手段,这是立体主义绘画中的块茎式空间。
德勒兹以“块茎”来抵御西方传统哲学偏向总体化、层级化、中心化、统一性的思维模式,因而其反面则是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思维典型“根-树结构”。德勒兹认为,传统西方哲学具有这种根-树状的知识构成方式:“心灵按照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支)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由镜子所提供的),而这些知识都扎根于坚实的基础(根)之上。”[9]128传统西方哲学以根-树结构限定并约束着自身向各个方面的连接,而与此不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的线的非层级化系统,它通过随意性的、不受约束的关系同其他线相连接。[9]111总之,块茎无处不在,块茎既在这里,也在那里。在媒介文艺生产域中,主体、时间、空间借助新媒介向各个方向不断生成,从传统域限中生机勃勃地奔流而出,以块茎形态流动、溢出、连接、结合,再流动、再结合为具有生成性的主体、时间、空间形态。
实际上,新媒介正是具有生成性的意向结构。对于新媒介的技术基础而言,建立在维纳“控制论”和“信息论”基础上的信息技术为计算机技术革命提供了一套操作原理,因此几乎所有社会系统都可转化为信息的输入、处理、输出、反馈的信息系统,推动着人类技术和文化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今日社会的每一重要活动都正被带入控制论原理的指导范围之内。通过计算机进行的‘信息处理’,正迅速成为我们技术文化的标志。”[10]
从新媒介具体构成形态来说,互联网就是联接电脑和服务器的网络的集合,能够通过全球通用的协议传送和接收。首先,新媒介的生成性在于它是“万网之网”,它将一点对一点和多点对多点的各种传播类型汇聚于同一空间,从而富有弹性;其次,新媒介是“万媒之媒”,它将过去曾出现的所有媒介,包括口语、文字、图片、视频、广播、电视机、录像机、手机等全部囊括其中,旧媒介没有消失,只是以组合式进化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新媒介世界中。从媒介的后视镜看,任何一种媒介都是前一种媒介的延伸,前一种媒介成了后一种媒介的内容,因此集合此前所有媒介的网络就是多种媒介杂交产生质变的结果,网络媒介生产了形式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的媒介符号,构成集以往媒介之大成的“元媒介”。作为“容器”技术,新媒介着眼于促进数据、信息的流动,但数据向哪里如何流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学者张先广的描述颇具启发性:“块茎中的每个节点同时是信息的搜索者、截获者、处理者、生产者、窄播者和传达的对象,流经每个节点的是来自所有地方却又不是来自任何特定地方的由数字化的文本、图像和声音组成的连续的信息流,因为赛博空间是个非域之境(atopia)。”[11]互联网构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促进不断连接、不断流动、不断溢出的生成性“星系网络”。
媒介界面的更迭几乎总能引发媒介文化的转场效应。文艺生产的文化偏向与媒介技术的意向性紧密关联,几乎任何一种技术都对应着相应的文艺属性。也就是说,从传统媒介向新媒介的转换,规定了新媒介文艺生产域的诸种要素的价值内涵。具体而言,不同的媒介形式具有与其技术意向结构匹配的文化编码方式,如林文刚所说:“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12]文化是技术意向性的后果,正是基于此,麦克卢汉才提出“媒介即讯息”[13],伊德称之为“技术对世界的暗藏转化”[14]53。富有宗教仪式感的口语文化、理性的注重个体书写的书面文化如此,平面的机械复制的电子文化、生成性的多元链接的新媒介文化亦然。
新媒介文艺生产与诸种文化实践相互牵连,如学者周翔和李镓所指出:“传统的媒介逻辑本质上是一种以时间面向为主导、以传播效果为目标的单向技术逻辑,而网络化逻辑在很大意义上是基于日常生活的以空间面向为主导的多元实践逻辑。”[15]包括跨媒介叙事、IP、融合文化、参与式生产、圈子文化、网红文化、粉丝社群在内的文化集合被称为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在这一系列相互交叉的文化表征集合之中,新媒介也生成其自身。唐·伊德认为,属于用具的存在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由此那件用具才能成其所是。工具成其所是的这种领域是复杂的,充满了牵连(involvement)或交叉关系(cross-relations)。其次,这些交叉关系具有所谓工具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或由工作规划规定的指引(reference)。用具是“为了作……”的东西。这种“为了作”的结构中,有着从某种东西指向某种东西的指派或指引。[14]35总之,新媒介以块茎的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效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界文艺生产,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同步关联。生成构成了以信息技术为根本的网络社会结构、组织、关系、文化的内在基础,为新媒介文艺提供了生产、叙事、展演乃至资本转化的场所。同时,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不断展开的实践又进一步增强了其自身的生成性活力。
对于新媒介文艺而言,新媒介的生成性前所未有地丰富了文艺的内涵,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新的文艺类型。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的民主现实主义文化观,新媒介文艺可以被定义为新媒介介入生产的文艺活动,可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现实空间中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3D打印甚至生物媒介等各种新媒介与传统绘画、雕塑、装置、行为、影像等各个艺术范畴深度融合的新兴科技艺术;另一类是传统文艺类型在新媒介空间的延伸、拓展,包括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综艺、网络电影、短视频、直播、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等,几乎所有伴随新媒介出现的文艺类型都属于新媒介文艺的范畴。在文艺实践上,新媒介生成性激活、调动起诸生产要素的能动性。具体而言,新技术形势下诞生了一批全新艺术家主体,包括机器人在内的“物”艺术家和深具媒介技术意识、观念的艺术家,新媒介技术正与人类构建起别具新意的联系,人-物交互、物-物交互的生产模式已然兴起,已有的人-人生产模式也正在转变。新的媒介技术改变了人与物的角色,使之成为融合文化的参与者广泛地参与融合文化的生产过程,并在多元异质主体之间创造充分互动的可能。在文艺观念上,美学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领域。一方面,依赖媒介、装置,艺术已经无限扩张、泛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与生活、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心灵与感官、技术与人文、静观与参与等一系列曾在文艺史上二元对立的观念在生成性作用下逃逸而出。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和接受的观念已经植根于具有生成性的媒介化新现实。学者黎杨全认为,在新媒介文艺中,“虚拟生存体验并不是直接体现为网络文学的内容,而是其‘结构’,即剥离掉内容之后的‘骨架’或形式,是从打怪得宝、种马后宫等各种欲望现实背后折射出来的世界想象、虚拟时空关系、主体的多重性与非中心化、网络社群与虚拟人际交往等”[16]。他的观点总体性地概括了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文艺观念已然发生更迭的现实情况。现今,新媒介文艺美学已经转移到感知领域,并开始转向以感觉为核心的生产。
为进一步揭示新媒介文艺的生成性,本文从主体、时间、空间三个层面展开讨论。
二、人机间性主体:生成性主体
在智能媒介、生物技术崛起并渗进社会生活的语境下,人类生命活动及其与科技、自然、物、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类应如何重新思考和处理自身与其他非人类物种或物之间的共存关系,成为人类纪的忧患命题。早期的控制论理论家维纳、哈拉维、斯蒂格勒以及众多的后人类理论家,都将技术的楔子插入到主体之中,通过聚焦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动摇了先前从未被质疑的主体概念。
主体地位的正式转变出现于后期现代哲学。自尼采以来,后现代哲学家就开始对中心化的、总体性的、二元对立式的主体观进行反思和批判。福柯是反对现代主体的英勇斗士,他拿起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武器,向被权力和话语双重规训与建构的历史性主体发起猛烈攻击,而后回到古希腊的理性主体,完成了先破后立的后现代主体观。德勒兹作为代表性的后现代哲学家,一直批判性地反思近现代主体,这也成了他拒斥传统理性的中心支点,他和福柯一样试图消解理性的、统一的人本主义主体,通过精神分裂分析法进行了一系列重铸新主体概念的尝试,包括欲望主体、无器官的身体、块茎、褶子等一系列后现代主体概念,都是他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主体概念反对被现代制度和话语限定与编码的中心的、一致的、再现的主体,偏爱差异化、多元化、解辖域的、逃逸的、散播的、不断生成的主体。现代性主体总是在僵硬的二元对立的“克分子线”下被分割和构建,克分子线将诸如上帝/平民、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君/臣、父/子分作次第有序的两端,而“逃逸线”打开了裂缝,将缺口扒开成欲望奔流的瀑布,鼓励欲望主体的连接行动。因而,生成哲学拒斥人类中心主义,即以人作为基本存在的观念。
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德勒兹正式提出了“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这一生成主体概念。“无器官的身体”是去本质化的身体,它消解了现代性的符码,使自身生成为一种游牧式欲望机器。它由物性化的有强度的力和能量构成,“是生成的场所,是欲望的生产、流通和强化的场域,能引起解辖域化、逃逸和生成运动”[17]。德勒兹和瓜塔里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肯定欲望身体的生产性:“欲望与客体是一回事:是机器,一台机器的机器。欲望就是一台机器,欲望的客体就是另一台与欲望相连接的机器。”[18]欲望机器不是隐喻层面上的,它实质就是一部积极的生产性机器,间断性和非连续流动运行,总是“在它自己充沛的能量的驱动下去寻求常新的连接(connetion)和展现(instantiation)”[9]96,同物质流及客体以及别的欲望机器建立随机的、多样化的、片段性的块茎式连接,“将自身弥漫、展现于整个社会领域,从而化生一切社会关系和现实”[19]。因此,欲望身体总是生产的、能动的、不断渴望与异质物连接的,它敞开了身体的边界,通过“生成”的方式对传统人类主体解辖域化。
在德勒兹看来,文学是这种自由解放的主要力量,因此他赞赏卡夫卡超现实主义文学中对人与动物二元域限的超越:人与甲虫、鼹鼠互相解辖域化,成为一种处于流动之中的连接。而当代新媒介文艺更是一个具有生成性的场所,男人/女人、成人/儿童、人/机器在网络空间铺展为等级界限消除的马赛克平面,借助技术之力,相互链接生成为新的结合物——跨性别者、成人化的儿童、儿童化的成人、类人化机器、机器化的人。
马克·波斯特把对主体的考察置于信息方式和交往方式之中,认为不同媒介意向结构的信息方式塑造了不同的主体。在口语文化阶段,主体的建构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自我包嵌在总体性的语音氛围中;在印刷文化时期,印刷文字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形成了这一时期二元对立逻辑的中心,在此结构中建构的主体是理性的、逻辑的和稳定的,与客体世界是一种主体和对象的二元对立的稳定关系;而在电子文化中,由于信息方式的不确定性和符号化,主体呈现出去中心、不稳定、流动性和多重性特征。因此,具体媒介情境的变化,引致主体在实践中被历史性地构建。对于新媒介生产域而言,新型主体以能动的行动者形象脱离肉态身体束缚,性别、阶层、年龄等传统社会固定不变的东西在新媒介交互中变得悬而未决,“自我建构本身变成了一项规划”[20],人成为媒介的产品。
在此,可以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形容,“媒介是人的延伸”逆转为“人是媒介的延伸”。也就是说,传统媒介、初级新媒介致力于对人体进行延伸,而当下则是紧密结合人体对媒介进行延伸,个人逆转为小型媒介组织装置。因此可以说,人已经成为技术的规定物,技术能动地“吸纳”人与自身结合为新组织,人与技术溢出人与物二元对立的边界,相互吸引、相互连接。正如技术自主论者埃吕尔所认为的那样,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即技术超过了某个临界值,那么它就会变成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组织,人类开始回应他们创造出来的技术的命令。德勒兹关于电影观看过程中人体与电影符号间形成的“精神自动机”的概念就是一种自我组织,因为“精神自动机”是由有机体和光构成的新型回路,人观看电影时的反应不再是由屏幕给予的,而是光、神经信号、人体脉搏的系统生成的“自我组织”,它既不能简化为生物性,也不能简化为科技性的控制论主体,它是一个模糊了二元对立界限的概念。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现实是由人类(意义、文字、讲述、机构、标志)与非人类事物(病毒、生物化学、免疫系统)持续相互影响的网络构成的,而非从意义中分离出来单独思考事物,或者从事物中分离出来单独思考意义”,网络并非被动的客体,它是帮助不同组成部分不管是人类、机器还是动物建立联系的装置,因此网络不仅仅因为人类的行动而行动,针对那些“对于我们而言可用的技术形式,拉图尔提出了对于非人类能动性的概念,来对抗我们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发现的对于能动性的人文主义理解”。[21]同样,斯蒂格勒也提出了超越二元对立的技术观,他认为:“在物理学的无机物和生物学的有机物之间有第三类存在者,即属于技术物体一类的有机化的无机物。这些有机化的无机物体贯穿着特有的动力,它既和物理动力相关又和生物动力相关,但不能被归结为二者的‘总和’或‘产物’。”[22]
而这就指向了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的主体生成性问题。在新媒介技术条件下的主体可视作人机间性主体,人与媒介技术两座欲望机器相互解辖域化,突破了自身(人类、机器)的界限,生成为“无器官的身体”,表现为构成“人+新媒介”的解辖域化的身体。问题是,为什么新媒介与人两类异质体能够构成新的身体?生成性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不论是人、动物还是其他物质都可以构成身体,身体是充斥着各种能量的集合,任意两种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力的关系都可以构成一个身体,甚至兰花和黄蜂也可以构成一个解辖域化的身体。因为新媒介主体的边界是敞开的,所以它既可以释放欲望的能动力,又能够吸纳新的异质物与它连接生成新的主体装置。因此,人与电脑或者人与手机、屏幕、智能芯片都可以结合为一个解辖域化的身体。“无器官的身体”是一个充满差异力量的界面:一方面,“无器官的身体”使意识可以脱离身体物理空间的界限,游牧在地球村的任何角落,获得身体在场、意识缺场或意识在场、身体缺场的新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人的身体可以与新技术结合为“人体+技术”的新装置,甚至通过电子脉冲连接人的意识激活外在设备进行信息交换(如脑机交互),生成“后人类”赛博格形象。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媒介的崛起与普及,对现阶段人机融合的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媒介性质来看,“传统媒介只是人的肢体的一般性延伸,与人体之间不能形成赛博格,而电磁、电子技术可以作为神经系统的延伸,与人体之间可以构成信息系统”[23],支持肉身神经脉冲与智能媒介电子脉冲直接进行数据交互。为凸显智能媒介相较于传统媒体在促进人机融合方面的能动性和有效性,本文将人与智能媒介融合的复合装置定义为“智媒态赛博格”,智媒态赛博格承接了后人类理论视野中主要的赛博格话语,在英文中“赛博格”意即“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人们多将赛博格理论追溯至唐娜·哈拉维借助控制论、信息论形成的技术女性主义思想。首先,赛博格是机器技术与动物、人类结合的混合编码装置,多存在于电影、文学等虚构领域,随着新科技革命进程的推进又广布于20世纪后期的人类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传播实践中。其次,赛博格强调技术对人体加工形成的增强效果,即外部物质通过与身体的嫁接能够延伸身体的部分功能,或超出肉身具备的综合能力,例如电影《毒液》中外星物种与普通人体嫁接形成对人类肉身功能的增强效应。主体、客体、物种、种族、类别是“赛博格”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基础与产物,赛博格这一概念混合了人类与非人类、有机物与无机物、碳基和硅基,拉近了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使之相互渗透,通过混合一系列边界,释放不同部分的能量促进人类进化,如同海勒所说:“信息、控制和传播,三大强力要素联合行动,将会造成有机体和机械体前所未有的综合。”[24]因此,智媒态赛博格以人与智能媒介的跨界融合为特征,突出了在智能媒介的加持下人机间性主体生产力的增强。
在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文艺生产主体不仅包括人类、智媒态赛博格,还包括智能物,微软小冰、洛天依、苏小妹、ChatGPT等新型主体,他们介入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等新媒介文艺类别,形成人机间性生产。人机间性的艺术生产方式拓展了人类艺术家的创作界限,为新媒介艺术生产赋能。
因此,借助新媒介的生成性,主体生成为网络社会千高原上的游牧者,通过充满力的强度的游牧运动,始终保持着与其他人、媒介、作品的连接。主体摆脱了一切僵硬空间的限制,通过解组自身创造出一种充满变化的实验式生活,它不停地运转着,生成了新媒介文艺生产关系的总和。
三、星丛时间:生成性时间
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人们通常以分、秒、小时、天、月、季度、世纪来丈量时间,似乎所有事物在客观的时间刻度上都标注了自身的位置,所以更多时候我们认为时间是自证的和理所当然的。但是,时间并非单一的、客观的,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丰富多样,在日常生活程序中建立起的时间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感知概念,时空存在于人类的感知中。而且,时间概念一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时间思维的基本范畴是由社会决定的,相同的时间单位暗示着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他人共同承认的社会秩序中。
在对媒介与时间关系的探索中,技术哲学家芒福德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论证到,现代生活中与机械相关的时间概念出自寺院而非上帝的规程,因为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社会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和血腥残杀,此时世俗世界的人们对于秩序有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首先体现在寺院的秩序上。公元7世纪,教皇要求寺院的时钟每24小时敲7次,人们依此建立起规定无误的祈祷时间,人们的活动在时钟的安排下得到协调,时钟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分离开。到公元13世纪,机械时钟被发明出来并逐渐普及,人们的作息活动以时钟为准。在这个进程中,来世和永生逐渐淡出人类活动的兴趣中心。随着新时空观念的普及,人们普遍的时间意识也建立起来,以时钟为准划分时间的抽象框架上升为人们思考和行动的参照点。进入18世纪后,许多哲学家也试图用钟表机械装置来解释人们的生活,人的生活和工作被认为是通过技术的形式塑造出来的。因此,按照芒福德的观点,时钟而不是蒸汽机成了现代工业最关键的机器。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在通过钟表计时的后基督教文明世界中,“由于我们一直按照这些时间单位行事,它们就成了我们意识的基本框架的一部分,是我们主观地将它们变成了绝对的现实。而社会以同样的方式暗中建构了我们世界观的基础”[25]。现代性主张的进步时间,像一串念珠、一条直线,是秩序井然线性排列和不断向前发展的,不能折回也不能拐弯。
漫长的媒介技术进化过程中隐含着不断演化的时空辩证关系,如同“媒介即讯息”提醒我们的,任何媒介都在我们个人和社会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这种新的尺度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时空感知层面。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时间征服空间的阶段。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出现多次终结了以往不同媒介阶段主导时空的感知方式:“在赛博空间出现之前,终结已经多次出现——电报、电力、电话、广播和电视都有它们自己的关于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终结的故事以及革命性预言。”[26]
生成性的新媒介再次革命性地为“地球村”引入了新的时间尺度,自钟表发明以来的“一串念珠式的”线性时间转换为几何式结晶的星丛时间。在新媒介作用下,现实时间与虚拟时间交汇,空洞的抽象的垂直时间转换为异质的具体的水平时间,体现为本雅明式的“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构成的“历史的星座”[27]。与此对照,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将网络社会的时间抽象化为“无时间的时间”,在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无时间的时间”并非等同于时间的消失,而是时间的空间化转折,展现为“按照时间密集排列或根据顺序的瞬间而即时排列的社会行为的先后顺序”。[28]此即本文提出的生成性时间,现代艺术家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福楼拜等对于时间同时性的偏爱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媒介星丛时间的预言。诗人艾略特在晚期的代表作《四个四重奏》的《燃毁的诺顿》一诗中写到:只有通过时间才能征服时间。新媒介时间正是过去时间、现在时间和未来时间在当下这一刻的汇聚,至此时间完成了自身的结构化,从一串链珠转为一束星丛。
新媒介时间结晶化之处,正是新媒介文艺生产实践的展开场所。借助新媒介技术,“数据处理成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顺序在一个特定的空间经验下可以被挪动甚至逆转”[29]。生成性时间增强了时间弹性,为新媒介文艺生产提供了调度的便利。人们即使在同一时间点上,也能够同步处理过去在不同时间刻度处理的事情。例如,多屏共生的媒介消费允许在同一时间点上同时打开电视、手机、IPAD、智能音箱;并且,人们即使使用同一部手机进入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也可以同时打开多个页面,意识分流到不同场景之中,时间的生产力呈倍数增加,人的意识在同一秒钟于不同的空间中参与行动。
除此之外,星丛时间又在线性时间秩序外生成“中间时间”。中间时间是指从一个时间节点到另外一个时间节点之间的时间,诸如出租车时间、地铁时间、飞机时间这类在线性时间下几乎没有生产力的中间时间也获得了“时间生产力”。新媒介的持续生成能力(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不断生成)将人们从必须固定的书房、咖啡馆中解放出来,对顺序时间的微观协调顾及到对文艺生产活动的精确调节。德塞都将其称作“弱者战术”:“弱者在占领强者的空间的同时,将惩戒性和工具性的时间转换成自由的和具有创造性的时间。”[30]
除却时间生产力的增殖,生成性时间也带来了深度时间意识弱化的问题。这一状况不仅表现在游戏、网络小说等通俗文艺作品对时间秩序的打乱和重组上,同样体现在智能媒介作品中,甚至成为艺术家热衷于表达的主题。比如在2016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城市博物馆-时空扭曲的记忆”项目通过挪移、叠加、植入,将“白塔寺再生计划”的几个特定情景粘贴至威尼斯年展给定场景之中,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唤起参与者强烈的时空异位感,在文本的延异中生成更具陌生化的审美体验。本文认为,此类注重对时间进行技术化“处理”从而获得新的时间体验的新媒介文艺作品,体现了生成性的星丛时间意识。
四、游牧空间:生成性空间
媒介文艺生产域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化,新媒介不仅生成了新的时间,也带来了新的空间形式,即生成性的游牧空间。新媒介一旦介入便开始借助其生成性对传统媒介生产域封闭的条纹空间进行摧毁,迫使其从僵硬的、密闭的、中心化的空间溢出为弹性的、开放的、去中心的平滑空间。这一动态的摧毁和生成过程循环往复,永不停息,构成游牧的网络“千高原”。
新媒介游牧平滑空间被麦克卢汉称作“声觉空间”,麦克卢汉认为:“电子技术发现了同步和声觉的组织原理,再现了西方的西塞罗,就像计算机再现了东方的《易经》。”[31]声觉空间是一圈圈边缘敞开的环形波动,没有自己所偏爱的焦点,它没有固定的边界,始终处于流动之中,一刻不停地生成自身特定的维度。具体而言,游牧空间实质是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征服、差异空间的生产与异质空间的创造来增强新媒介空间的生产力。
首先,游牧空间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媒介化实现对物理空间的征服。在这个类型中,游牧空间征服、延伸了地理意义上的地域空间,这种地方空间通过“节点”与流动空间相连,带动坚固的“地方”进入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的流动空间之中,两者交汇为环绕“地球村”的“空间流”。空间的生成性使“空间感”弱化,网络瞬间到达的速度肢解了物理空间的束缚力。
其次,随着对物理空间的征服的完成,游牧空间技术的注意力转移到“差异空间的生产、空间之间的吸纳与兼容以及对自由时间的争取”[32]。游牧空间“乃是经由信息流动形成的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33]。简单地说,流动空间是通过生产实践建立起的“空间”,例如文学社区中对话的传播行为就构建了流动的“地方”。流动的空间不仅包括电子和电信电路,还有围绕这些电路及其辅助系统进行同时性社会实践建立起来的全球化网络“地方”节点。因此,通过差异空间的生产,新媒介在物理空间之外建立起差异化的生产空间。
再次,以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技术为代表的游牧空间技术擅长创造异质空间。这一点在后文的案例中有详述。当然,不管是真实世界的延续还是一个新的世界,新媒介空间“都被生产为现实空间的重复并通过其内生力实现网络空间的增殖”[34]。对新媒介文艺生产而言,不论是对物理空间的征服、差异空间的生产还是对异质空间的创造,游牧空间都为跨媒介叙事创造了可能。
在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不仅网络文学借助游牧空间进行跨媒介生产,还有纪录片、电影、游戏也都借助“IP”进行跨媒介叙事和文本故事的再生产。就网络文学而言,《甄嬛传》《琅琊榜》《盗墓笔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仙剑奇侠传》《魔道祖师》等诸多文学作品均被改编为跨媒介作品,跨媒介衍生叙事“成为不同媒介空间中甄选故事元素,优化文本构型逻辑,重构故事时空的重要叙事方式”[35]。这在中国网络玄幻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玄幻小说无疑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网络文学类型,打开任何网络文学网站,玄幻小说都处在最重要的位置,网络作家收入排行榜上居于前列的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等也均为玄幻小说作家。近几年来,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IP剧的热潮,玄幻小说更成为影视剧改编的热门对象,从郭敬明的《幻城》、萧鼎的《诛仙》到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都已经以影视剧的形式和观众见面。不管是小说、影视剧、电影还是游戏、主题乐园,跨媒介叙事展开的每一个媒介空间都对应着同一文本的一种叙事模式和文化指向,几乎每个新文本都对其展开详尽叙述,都对整个故事贡献了价值。也就是说,通过跨空间的叙事集聚,文本的“理想”表述才得以展开、完成。正是这种跨媒介、跨文本、跨文化的游牧叙事使文学超越了单一的媒介单位,通过游牧空间的协同叙事“实现对传统媒介文本间的修复、整合、拓展功能,进而建构一个宏大的故事世界”[36],展开了故事的内部空间,丰富了作品中的故事叙事维度,使作品在物质、时空、符号、感知乃至文化层面得以扩展。
除了传统的网络新媒介空间,虚拟现实技术为跨媒介叙事开拓了更具表现力的异质空间,其适用的作品主题范围更广,沉浸性、代入性、互动性更强。早在2016年,达利博物馆就推出了《达利之梦》VR体验,这是一次达利《对米勒〈晚祷〉的考古学回忆》的虚拟之旅。作为沉浸式新媒介,这些异质空间的跨媒介叙事实质是对达利作品的再创作与新诠释。又如,英国国家剧院沉浸式故事工作室与加拿大国家电影委员会合作的Draw Me Close,这部作品用VR、动画结合表演让人们沉浸在儿子对母亲的回忆中,观众被置于儿子的位置,能够与母亲进行即刻的互动。这是虚拟现实异质空间进行新媒介文艺叙事的独特之处。再如,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的标志性游戏项目《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将电影《加勒比海盗》中各个巨型场景无缝连结,为游客提供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借助新媒介产生的新感官体验与此前欣赏的媒介文本体验相融合,让观众在头脑中产生了新的文本阐释之间的嫁接。或许,“嫁接的意义在于,它能让两个被嫁接的东西存在意义的对撞,借助于这种对撞使得意义增殖”[37]。
美国文化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认为,跨媒介叙事是一种融合文化,融合文化作为新媒体时代媒介文化的一种范式转换,并非单指技术层面不同媒体形式的融合;相较于以往对媒介融合技术层面的强调,融合文化代表了一种文化变迁,“因为它鼓励消费者获取新信息,并把分散的媒体内容联系起来”;在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欣赏者可以任意文本为切入点进入到文本消费中来,在更广范围内推动对文艺作品的消费;并且“融合的发生并不是依靠媒体设施,它发生在每个消费者的头脑中,通过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来实现”。[38]生成性空间的跨媒介叙事是人们充分参与、彼此交流的结果。如此,新媒介文艺作品作为开放性文本,总是处于一种生成性状态,它邀请消费者积极参与到新内容的创作、传播和分享过程中。
生成性代表了当今时代媒介文化的一种范式转换,传统媒体时代独家垄断的作品内容如今在不同的媒介渠道中流通,自下而上的参与文化与传统自上而下的传播形式相结合。“传统框架正被涌现中的实验性、激进性企图所推翻,因而研究目标是在发展着的技术中重新掌握叙述艺术。”[39]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叙述”的社会,文艺作品不断地通过传播媒介来流传各种叙事和文本,呼唤欣赏者通过媒介空间中的游牧完成对文本的解读与再生产。
总体而言,游牧空间使物理空间上的临近性让位于沟通的同时性,距离的远近和身体的在场与否不再是媒介生产的难题。但不论是流动空间还是固定空间,都作用于人们的身体感知和意识感知,我们应当从生产角度理解不同空间概念的张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成性的新媒介使得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转向虚境,由亲身体验转向媒介体验。
五、结 语
新的主导性媒介隐喻着新的文化偏向。在当下媒介化时代,透视新媒介技术的技术意向,能够为我们思考新媒介文艺生产提供有效的切入点。在“流动性”“交互性”“存在论”“交往性”等新媒介内在偏向的研究论断之外,本文引入德勒兹的“生成性”这一技术哲学和美学思想,以关照新媒介文艺的技术意向。
在经历了口语文化、文字-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之后,我们进入了以生成性为根本偏向的新媒介文化阶段。新媒介的生成性使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的主体、时间和空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机间性主体”这一新的后现代主体替代了现代性主体,“星丛时间”支配了工业时代的时钟时间,“游牧空间”几乎废除了地方空间,新的主体、时空又重新规定了文艺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者、消费者、媒介乃至文本都在新的生产域下重新生成。反之,新媒介文艺也在种种生成实践中生成自身。
不仅如此,理解生成性的意义还在于可从当下的文艺生产语境转换中发现那些尚未浮现的潜在趋势。这些趋势为思考正在展开的智能化文艺生产以及元宇宙文艺问题提供了启示。
然而,依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强调新媒介的技术意向及其文化后果,但从未站在技术决定论的立场上讨论这一问题。新媒介文艺具有技术性,但技术自身并不会构成新媒介文艺发展的全部力量。我们更加乐于考察媒介技术意向变革带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现实经验的诸种变化,以及其中蕴含的关涉未来文艺如何发展的可能。此外,虽然生成性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力量,然而新媒介文艺发展又始终与资本紧密结合,因此对于生成性问题的价值判断,则需要放置在具体的文艺事件中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