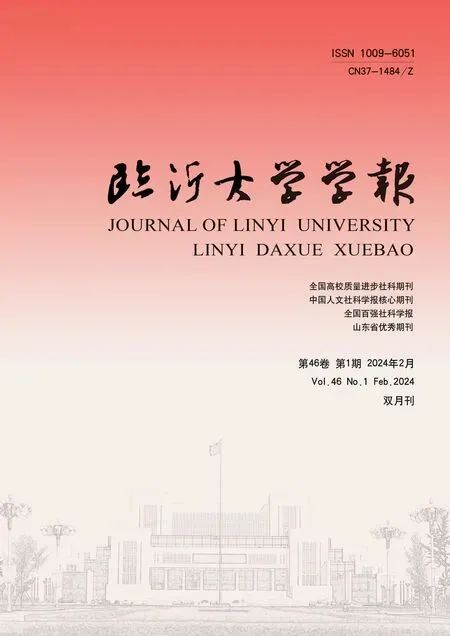论孔子对“天命”的知与未知
王春华 于联凯
(临沂大学 a.沂蒙文化研究院;b.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历代注《论语》者及其他专家学者立足于孔子对“天命”的“知”,对何为“天命”、何为“知”的问题做了大量探讨与诠释,为此问题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资料。 但是,以今观之,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实际上有虚夸的成分,孔子对“天命”并未完全知晓与把握,有些事情现代人也没有搞清楚,更遑论当时的孔子了。以下将对孔子对“天命”的知与未知进行具体分析。
一、“天命”含义及孔子对“天命”的认知
“天命”是一个具有多层面内涵的词语,其大致产生于宗教迷信盛行的夏商时代。 当时的治国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假托自己是尊奉皇天上帝的命令而统治人间,也就是说上天给他某种命令或使命,故谓之“天命”。应该承认,当时的治国者对于“天命”是有某种程度的虔诚的,但到后来,这种虔诚越来越少。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天命”的认知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样看来,“天命”一词有唯心主义色彩,但又并非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一般来说,孔子所谓的“天命”,应包括宗教层面、人事(政治)层面、自然层面、道德与文化传承层面等多种内涵。
(一)宗教层面上的“天命”及孔子对“天命”的认知
“天”“命”“天命”这些词语在我国出现很早,其最早出现时是从宗教层面上使用的,具有丰富的内涵。
1.春秋以前对“天命”一词的使用及其含义
《尚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皋陶谟》)“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誓》)“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盘庚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泰誓上》)“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泰誓中》)“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这些句子中的“天”就是指能决定人间一切的人格神,“天命”就是上天的命令,或释为上天给予的使命。
西周时期,“天命”的含义仍与夏商时期相同,但西周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商朝的灭亡,深切体会到“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和“小民难保”(《尚书·康诰》)的问题,因而改变了殷代唯信天命而罔顾小民的政策,实行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政策。
2.孔子对宗教层面上的“天命”的认知
孔子祖上为商朝王室的后裔,故其祖上以“天”为人格神的宗教意识也深深影响了孔子的天道观。 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首先是指宗教层面上的“天命”。
①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竈,何谓也?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
②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 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 无臣而为有臣。 吾谁欺?欺天乎? 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 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论语·子罕》)
③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论语·泰伯》)
①②③中的“天”都是指能够决定人间一切的“皇天上帝”。 ①是说如果得罪了天,那一切都完了,即使祈祷也没有用。 可见天的威严是何等厉害。 ②是说由于天有如此的威严,所以不敢欺“天”。 ③是说只有天最大,人间的帝王也必须遵循它。 由此可见,孔子心中是有一位最高的人格神存在的。
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这一句是说,由于有“天”这位最高人格神的存在,所以君子必须对其“命”(命令、使命)表示敬畏,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得好。
⑤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
⑥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⑦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 命也;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论语·宪问》)
⑤⑥⑦主要是讲孔子自称自己是“天命”的代表人物。 ⑤是说周文王死后,上天把文脉(文化传承)的掌握权交给了自己,自己就是天下文脉的主掌者,匡人也无可奈何。⑥是说自己是天德的主掌者,桓魋一类权臣奸臣亦无可奈何。 ⑦是说“道”的行与废都是由“天命”决定的,而自己又是天命的代表,所以公伯寮一类的小人物对自己只能无可奈何。
总之,以上例子说明在孔子看来,“天命”的确是存在的,是决定人间一切的,而自己是天命赋予的文脉方面的代表和主掌者,这就是孔子在宗教层面上对“天命”的认知。
(二)人事层面上的“天命”及孔子对“天命”的认知
“人事”,即人类之事或人间之事。 恩格斯说过:“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 ”[1]859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事有规律的发展;而自然界的历史,只有在人产生之后才被认识。从科学观点来看,所谓宗教层面上的“天命”,也是人事的一部分,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上帝神仙,世间一切都是人自己创造的。孔子的一切活动都在人事范围之内,所以“天命”为伪,人事为真。 但是为了叙述问题方便,我们还是将人事与宗教划分为两个层面考察。
人事诸种事务的中心就是政治。至春秋晚期,即孔子生活的时期,政治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王权的衰落和诸侯权力的膨胀,与此同步的是天命代表者由原来的“周天子”下降为“诸侯”,进而降为“大夫”“陪臣”,出现了“政逮于大夫”和“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现象。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 是谓近女室,疾如蛊。 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良臣将死,天命不佑。 ”(《左传·昭公元年》)这里的“天命”虽然仍是指上天之命,但其指代已由天子转换为晋侯,这表明当时天命的代表者已由“天子”降为“诸侯”。另外,晋侯之病重也不是什么鬼神的作用,而是起居不节、道德不修等人事变化造成的。
郑(国)大夫裨谌在评论子产得政时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避)子产?……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 不然,将亡矣。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里,郑子产显然成了“天命”的代表,应属“政在大夫”之列,这一方面说明了“天命”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表明“天命”实际就是人事。“善之代不善,天命也”,换言之,“善之代不善”,这是人事的变迁,而不是天的作用。
赵简子与史墨讨论孔子所在的鲁国的人事变化情况时说:“季氏出其君, 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 ”史墨在讲了一通辩证法之后,说:“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里同样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天生季氏”,即天命的代表已由鲁侯转换为季氏;二是这种变化是鲁君世从其失与季氏世修其勤的结果,即不同人为的结果,也就是说天命的变迁也是人事变迁的结果。
总之,“天命”的下降实质上也就是人事的变迁,对于这种天命下降与人事变迁的发生,孔子是有较明确的认知的。 例如,他曾总结“天命”下降与人事变迁的情况,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又针对鲁国的情况,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论语·季氏》)这里所谓的“礼乐征伐”即国家内政外交的大事。 孔子认为如果国家统治秩序正常,像西周初年,国家内政外交的各种大事是由天子决定的;如果王权衰落,则这些大事就变为由诸侯决定了。孔子根据亲闻亲见的王政衰微、诸侯力政的现象,指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这里主要是指齐、晋二国的情况。 齐国自齐桓公称霸之后,先后继之者有齐孝公、齐昭公、齐懿公、齐惠公、齐顷公、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齐悼公、齐简公十人。 齐简公被陈恒(田氏)所杀,齐平公继位,平公二年(前479年)孔子去世。 自齐桓公至齐平公是十一公,孔子所说的“十世希不失矣”,因为这话是在齐平公继位之前讲的,从齐桓公之后的齐孝公开始到齐简公正好是十世。 晋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关于大夫的“五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主要是孔子根据鲁国情况说的,自季友专权经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共五代,之后出现了阳虎等家臣专权的情况,权力层层下移。
孔子不仅对这种天命下移、人事变迁的总体状况有一定认识和了解,而且他还力图阻止和改变这种情况,使诸侯称霸、天下分裂的情况尽快结束,恢复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局面。 另外,由于孔子本人处于“天命”下移、王权衰落的时代,所以,这种变迁也在他身上显现出来。 他常以天命代表自居,宣称“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而未受到任何惩罚,这正是天命下降、王权无力的表现。
(三)自然层面上的“天命”及孔子对“天命”的认知
“天命”除包括宗教层面和人事层面的内涵之外,还包括自然层面的内涵。天,就是大自然,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地、人三者是相同的。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新的自然物,人受到各种自然规律的制约,是无法离开自然界的;历史虽然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两部分,但人类史是无法离开自然史而存在的。从这一点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与“天命”息息相关的。 前人已认识到这一点,如《中庸》开篇便称“天命之谓性”,即言天所生成的就是人的“本性”,宋代朱熹注此句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这里的“本性”是指人的生物性,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是不矛盾的。 皇侃在注释《论语》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时,亦曰:“谓天为命者,言人禀天气而生,得此穷通,皆由天所命也。”(《论语集解义疏》)邢昺注此句曰:“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禀受者也。 ”(《论语注疏》)其意也是人禀天气而生。 朱熹注“五十而知天命”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以上三家在注“天命”时都强调了“天”对于“人”产生的作用。 这与从宗教层面上对“天命”的理解不同,这里的天(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具有了实质性的内涵:人禀受自然之气而生,天(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人,人是自然的成果,也是自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标志,在这方面,孔子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是后人在诠释他的“天命”观时做出这样的分析,应该是符合孔子本意的。
另外,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佐证。例如,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语丛》:“有天有命,有地有形”,“有天有命有形”。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天、地”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只有天地的存在才能产生人的生命。据研究,这些简牍应该是孔子之后二传或三传弟子(在孟子之前)的作品,这些弟子在“天命”方面的认识,应与孔子相同或相近。
对“天命”的自然层面的分析,不仅包括对“天”与人性命关系的探讨,而且也包括对自然规律的探讨,如自然界四时更替,万物生长与死灭规律,风、雨、雷、电、地震、火山等自然现象对人类的危害等问题。
孔子对“天命”的自然层面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他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虽然不会讲话,但春、夏、秋、冬四时该来就来,该去就去;万物该生长时就生长,该繁茂时就繁茂,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应该说,孔子对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有了朦胧的认识。
“天命”的自然层面也包括人之为生物体的发展规律。《黄帝内经·素问》之《生气通天论篇》指出:“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这里的“天命”就是指天(自然)所给予人的生命,属于“天命”的自然层面。
为保持“天命”,必须注意饮食起居、养生等方面,孔子对这一点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他注重养生,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把品德修养与之结合起来。 如《论语·乡党》曰: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色恶,不食。 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 不时,不食。 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酱,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惟酒无量,不及乱。
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姜食,不多食。
祭于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言,寝不语。
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内经》上所讲的“谨和五味”的范围。
与养生同步, 孔子还很注重环境的优化和生态的保护,“子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即体现了这种精神。注意环保的弟子高柴说,“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家语·弟子行》),孔子对此表示赞扬,将注重生态优化与道德修养结合了起来。如上所述,天就是大自然,天、地、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具体而言,人所处的生态环境及其客观变化也属于天命的范畴,因此,孔子优化环境和保护生态的思想,也是其天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道德修养与文化传承层面上的“天命”及孔子对“天命”的认知
前文引用的《尚书·皋陶谟》已有“天命有德”的说法,且在我国民间,人们经常使用“天地良心”“伤天理”等词语,可见无论是地位最高的治国者还是民间都早已认可“天命”具有道德层面的含义。
孔子多次以“天命”代表自居,其中十分重要的标志就是“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的自我认定,认为上天把修德的重任放到了他的肩上。
虽然,在涉及“天命”时,孔子自称“天生德于予”,把道德看作“天命”的一个层面,但道德毕竟是“人”的道德,只有依靠人的具体践行才能存在与发展,而不可能总是与虚无的皇天上帝放在一起,因此,在孔子看来,道德有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内容与多方面的社会功用,并与“人”时时刻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孔子认为高尚的道德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依据。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美德是立身的依据,而占据道德核心地位的“仁”,是人必须时刻遵循的,所谓“依”就是须臾不可离,必须时刻依靠的。 其次,孔子认为道德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志。 例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这里的“刑”,即“型”,有典范之意;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是美德的重要内涵之一;又,“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泰”即安详稳定、大度,这些都是道德的内涵。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兹不一一列出。最后,孔子认为由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出现了“知德者鲜矣”(《论语·卫灵公》)的状况,所以,孔子竭力主张要“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要修德从善、强化修身,认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孔子大力倡导修身,以使自己成为仁德之士。
孔子对道德的认知,并未停止于修德本身,而是把个人修德与治国安民联系起来。 例如:“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这里明确指出,修德首先是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之人,但这不是最终目的;修德的第二层次是“安人”,根据儒家“亲亲为大”(《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的原则,这个“安人”应是使自己的亲人(包括身边的人)安乐;但这仍不是最终目的,修德的最终目的是“修己以安百姓”,但这个目的,即使尧舜也很难达到。
孔子把个人修德与安顿管理百姓联系起来,提倡以德治国,反对对百姓的强取豪夺、横征暴敛。 孔子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执政者自身首先要注重修德;当然要达到德治目的,其他人也都要注重修身。 后来的《大学》《中庸》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修身为何必须“知天”,质言之,是因为在古代一些人看来,仁、义、礼、智、信、善、顺、勇等美德都是“天德”,是上天给予人间的,人们要修身,必须学习和接受上天给予的这些美德。 朱熹注《中庸》第二十章君子“不可以不知天”时指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故又当知天”(《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就是说人间的礼和美德皆来源于天,故应该知天尊天,这与孔子当初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这种认识是唯心主义的。道德是人们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不是“天生德”,而是人生德。 孔子把道德的产生归之于天,这就限制了他对道德的本质与功能的正确认识。
《论语·子罕》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被围于匡地时,遇到了危险,意识到周文王死后,文脉即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到自己肩上,这是天命,所以匡人不能奈何自己。 这里既表现了孔子的宗教意识,是孔子对商、西周时期天命思想的继承,同时也表现了孔子对文化传承的自觉认同。
在文化传承的层面,孔子有着丰富的思想和多方面的践行,在这方面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首先,在文化传承、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孔子具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论语·先进》记曰:“子张问善人之道。 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善人(指虽然不能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类人物并驾齐驱,但也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人)如果不遵循前代圣人的思想轨迹,也不可能登堂入室,这种观点包含着对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萌芽。恩格斯在论述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过程时曾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 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1]775这里所阐述的就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即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但是它的产生又往往是借鉴先前的某种思想资料为其理论形式和出发点的,如果没有这种先前的思想资料,新的思想文化也很难产生。以此来考察和衡量孔子的“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论断,不难看出,它正是对上述规律中部分内容的朦胧认识,应该说这一点是弥足珍贵的。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2]为此,我们应该认真梳理与总结孔子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论述,使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与之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发展。
其次,在如何才能做好文化传承,即文化传承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方面,孔子也是有所认识的。 文化传承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既要重视实际,又要重视自己的声誉、名声。孔子认识到这一点,指出君子必须既重实又重名,这样才能做好文化传承事业。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孔子十分重视个人品德、能力的培养。另外,孔子还很重视声誉的培养,认为君子应该有好的品德和能力,但也必须重视声誉,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声誉都毫不关心,抱无所谓的态度,那对文化传承也不会有什么积极性。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论语·阳货》),认为君子会担心死后而名声不显,如果四十岁仍有恶名,那一辈子也就完了。 因此,君子必须重视自己的名声,当然好的声誉是在重视实际的基础上取得的。
再次,在各种历史文化思想资料的整理保存方面,孔子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为新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他“删诗书,定礼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四),搜集和整理“六经”,为保存古代文化资料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在文化人才的培养方面,孔子也有重大建树。 文化传承的基础是要有一大批人才,如果没有这些人才,文化就无法传承下去。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建立私人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为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孔子对道德、文化层面上的问题知之甚多,有很大贡献,但也有若干根本性问题,他尚未知晓与把握。 例如道德、文化等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的活动的成果,并不是什么“天命”产生的。 另外,关于道德、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孔子也未弄明白,只能归之于“未知”之列了。
(五)孔子对“天命”与梦关系的认知
先秦时期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人们对做梦一事缺乏正确的理解,一般认为是灵魂出窍,与天帝、神及已死的或正在生活的人们相交游,因而产生了各种传说。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当时朝廷设有占梦中士二人,史三人,徒四人”,专门为周天子和达官贵人解梦,可见当时解梦是周朝上层的一种政治活动。其中,梦者与天地及其他尊神的交游,往往被视为“天命”的征象。
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了若干与梦相关的涉及“天命”及人事变动的事例。如《艺文类聚》引《周书》曰:“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梓化为松、柏、棫、柞,寐觉,以告文王。 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艺文类聚》卷七十九灵异部下)《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三亦引此段,但文字有不同。 《礼记·文王世子》载:“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 ’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 ’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 吾与尔三焉。 ’文王九十七乃终。 武王九十三而终。 ”以上两例都是讲人间的帝王与皇天上帝交往而受“天命”之事,另外,朝廷使用重臣,有时亦利用梦的形式来宣示。如《伪古文尚书·说命上》记述商高宗任用傅说的事,即是由高宗先梦见他要得到傅说,后才派人去寻找的。还有《庄子·田子方》记述,周文王在找到姜尚后“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于是假托梦见了自己的父亲王季,王季命他任用姜尚,然后周文王把这个梦告诉众大夫,扫除了任用姜尚的障碍,姜尚受到重用。 以上说明运用梦而宣告某事,不过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为政者的一种手段。 孔子对于这种手段也是深谙其道的,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由此话中可以推论出孔子在“衰”之前是多次梦见周公的。
除梦见周公外,孔子临终之前,亦曾有梦,他说:“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礼记·檀弓上》)《家语·终记解》有基本相同的记载。 孔子临终前的梦,预示了他的生命即将结束,也预示他所承担的“天命”、人事等使命的终结。孔子在这里称他“梦坐奠于两楹之间”,是向弟子及其他人表示,这是其祖先或其他神灵向他提示的。 因为殷人的停灵的位置是两楹之间,即堂屋正中;夏人殡于东阶之上,即殡于主人的位置上;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即殡于客人位置上。 孔子的这个梦,显示了他与其祖上或其他神灵的关系。
总之,孔子虽然有若干唯物主义的倾向,但在“天命”与梦的关系上,仍然保留了较强的宗教理念。
二、孔子对“天命”的怀疑与未知
孔子虽然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但实际对“天命”尚有一定的怀疑,对“天命”中的许多问题也难以知晓与把握。
关于孔子对“天命”的怀疑,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认为天命不可违,君子应该“畏天命”,因为“天命”具有规定人间一切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天命”的自然层面,即“天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他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对与天命密切相关的鬼神,表现出了一定的蔑视态度,如,“樊迟问知。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聪明智慧在于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使民众遵循大义、把握正确的道路上,对鬼神一类不必得罪,但也不要过于亲近,这表现了他重民而轻鬼神的倾向。又,“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平时对“鬼神”一类的事,连谈也不屑谈。又,“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祷久矣。 ’”(《论语·述而》)邢昺《论语注疏》认为:“此章记述孔子不谄求于鬼神也。 ……子曰‘丘之祷久矣’者,孔子不许子路,故以此言拒之。 ”实际上,孔子所谓“丘之祷久矣”,其潜台词是“我祈祷已经很久了,但仍然要患疾病,所以,向鬼神祈祷是没有什么用的”,表现出了对鬼神的怀疑。 又,《论语·先进》曰:“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同样表现了孔子重人事、轻鬼神的精神,当然,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的进步思潮是一致的。
如前所言,“天命”实际上也是人事,或说是人事中涉及政治大事的部分,孔子对这部分内容虽然有所知,但未必能了解和把握其核心和关键问题。例如,孔子看到了春秋时期的王权衰败、诸侯称霸和礼崩乐坏,但对这种状况缺乏正确的理解,他只能以西周初年天下一统的局面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看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等上层建筑的改革需求,因而虽然感受到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只有恢复西周初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才是正道。实际上,这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因而孔子在政治上四处碰壁,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天命”趋向的未知。
在“天命”的自然层面上,孔子知之更是不多,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如自然界的发展究竟是怎么产生了人这种生物,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气候、天体运行等)究竟是怎么具体影响了人的生存发展,自然历史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宇宙究竟是什么,等等,孔子恐怕难以作出较有质量的回答,当然我们无意苛求前人,许多问题当代人也回答不好,孔子的“不知”“未知”是可以理解的。
在道德、文化方面孔子颇有建树,但社会经济因素与道德、文化因素之间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辩证关系,如何表述清楚,这在孔子当时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 但在这方面,孔子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如《论语·子路》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这是孔子提出的发展民间经济文化的一幅蓝图,为什么在人口繁盛之后要发展经济使之富起来,富起来之后又要发展文化教育,在孔子心中,对这几种社会发展因素间的关系,应该是有某种认识的,但孔子没有表述得很清楚,所以,孔子在这方面也只是略知一二或知之不深。
关于“天命”与梦的关系,通过“梦”的形式说出某种天命,这不过是统治者愚弄群众的手段,并非什么天意,当时连阅历不算丰富的颜回,都表示怀疑。 据《庄子·田子方》记述:文王在欲任用姜太公时,“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于是假托其父季历托梦欲用姜尚,使众大夫不再质疑。 颜回针对此事,曾说:“文王其犹未邪? 又何以梦为乎? ”意思是文王要办此事难道还做不到吗? 为什么要托先君之梦呢? 孔子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他不说破此事,正是因为他也要通过梦的形式以达成某种愿望。孔子在这件事上的不知,是故意为之,但对梦与“天命”的关系,孔子仍缺乏科学的见解。 虽然如此,孔子“梦见周公”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士人都以梦见孔子为荣,借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而抬高自己,如郑玄、谯周、刘勰、王通等都是如此。
关于孔子自述的对世界认知发展的不同境界,《论语·为政》 记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是孔子晚年自述一生经历的认知境界,它对今人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也不少。如“三十而立”,冯友兰先生曾谓之“功利境界”[3]57,实际上,“三十而立”,主要是道德、学业和世界观的初立阶段。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尧曰》)因此,“三十而立”应是知晓和把握各种礼的阶段。
“四十而不惑”,朱熹释为“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简而言之,即知事物之其然,因此,能分辨各种不同的事物而不致被各种假象迷惑,故曰不惑,这是深入认知世界的表现。 冯友兰先生曾谓之“道德境界”[3]57。
“五十而知天命”,已在前面作了分析,孔子对“天命”的不同层面认知情况不同,有知有不知。 朱熹释此句为:“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四十而不惑”是知事物之其然,“五十而知天命”是知事物之所以然,即知晓事物发展的规律。 实际上,孔子五十岁时,可能对若干事物做到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但若说对世间一切事物皆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六十而耳顺”,即言六十岁时耳根子很清静,由于自己处事得当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可闻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即七十岁时处事从心所欲,也不会违反规矩了。以上这两条,冯友兰先生曾谓之“天地境界”[3]57。美则美矣,无奈事实并非如此,孔子晚年大故迭起,孔鲤死、颜渊死、子路惨死,使孔子痛感天要塌了,再加上“河不出图”“洛不出书”,麒麟受伤,使孔子感到自己的路要走完了,不由得涕泪沾襟,这哪里还是“耳顺”“从心所欲”的样子,所以,事实并不像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的那样。
孔子虽然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是他的认识受到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受到整个人类认识能力和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制约,他对世界(包括各个层面上的“天命”)的认知,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有知之较深的,有知之甚少的,因此,要完全做到“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踰矩”是不可能的。
结语
“天命”是一个内涵丰富、具有多方面意义的词语,以上我们将之划分为宗教层面、人事层面、自然层面和道德文化等层面并进行了分析。 宗教层面,归根到底也是一种人事活动,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人间活动,它是古代为政者利用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导致民众愚昧的状况,而采用的特殊治理方式。孔子对“天命”“鬼神”有所怀疑,但又不能完全冲破宗教意识的束缚。在人事层面上,“天命”所反映的不是一般的人事活动,而是涉及国家治理的方向和大政方针的事务。 孔子是清楚这一点的,“五十而知天命”主要是说,他到五十岁时,由于阅历的加深,已经看清了如何治理“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乱世了,已经明白了自己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了。 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体会到孔子讲这些话时,是颇有傲视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的。 但可惜的是孔子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有开倒车之嫌。
自然层面上的“天命”就是天之命于人者,特指天(自然)所提供的生成人的条件,这是一个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决的科学命题,孔子不可能有更多的认知,只能是略知一二而已。
在道德层面上,孔子提出了“天生德于予”和“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观点,认为道德与文化皆源于天,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落后的认识。除这一点外,孔子对道德、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文化传承的条件及传承的意义等都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另外,孔子把做梦与“天命”联系起来,这与当时的流俗是一致的。
总之,孔子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与实际情况是有相当距离的,孔子五十岁时,对“天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说在某些层面上有所了解,但其未知者甚多,已知者亦非完全正确。 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述而》)实际情况未必能如此,这不是因为孔子不努力、不聪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方面和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孔子所处的时代限制了他。从认识论看,一个生命个体,无论其主观条件如何优越,也只能认识世界的一部分,或说一个点,而不可能认识得非常全面,人类只有通过世世代代的不断努力,才有可能认识世界的更多方面。对“天命”这一命题的认识也是这样,它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继续探讨,我们深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天命”的认识必然会更为全面与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