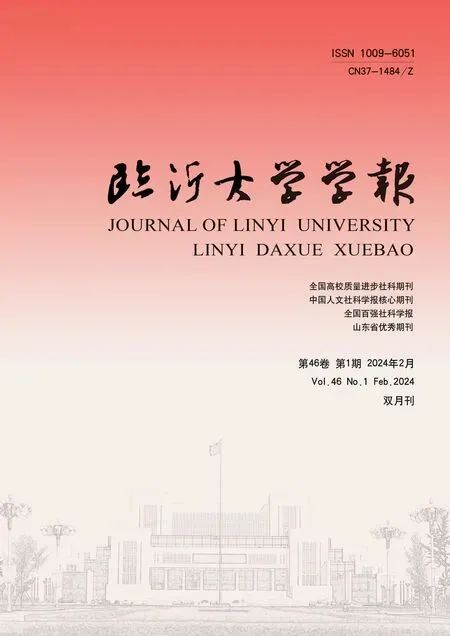南社小说家与民初小说报刊的生存、演进
王双腾
(山东警察学院 专业基础教研部,山东 济南 250200)
清末最后十年间,小说报刊成为小说的主要物质载体与传播媒介,其经营状况与办刊理念左右着同一时期小说的生存环境与演进路径。受辛亥革命、癸丑报灾等事件的影响,小说报刊在民国初年经历了由低谷到复兴的曲折发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学运动近十年的时间里,南社小说家或主办小说报刊,或担任小说报刊的编辑与撰稿者,成为维系、引领民初小说报刊生存、演进的中坚力量。
一、落潮中的坚守者
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报刊业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时局的刺激下,一度出现办报热潮。①这一时期创刊的报刊多为政治色彩浓厚的各级政权机关报,小说报刊并未随之走向繁荣。1909 年,《月月小说》停刊,标志着清末最后十年间小说报刊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自此直至1913 年癸丑报灾,只剩下清末创刊的《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仍勉力维持,其余的小说报刊无一幸免。 在1912—1913 年发行的《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中,南社小说家包天笑、周瘦鹃等是重要撰稿者,他们提供的小说作品使仅存的两份小说报刊得以生存,从而在保存小说报刊这一清末民初小说最为重要的物质载体的同时,继续着对小说艺术技法、价值取向方面的探索。
1912—1913 年的《小说时报》刊载了包天笑译著的《血印枪声记》《欲海情波》《百万磅》《新桃花扇》四篇小说。 《血印枪声记》叙写佐舍夫罗德波尔侦破“黄室案”,《欲海情波》讲述鲍尔敦查理与亦敌亦友的司德芬出海航行,两篇小说分别延续了包天笑在清末便已涉猎的侦探小说、冒险小说。《百万磅》《新桃花扇》与《儒林外史》等中国古代讽刺小说一脉相承,包天笑的冷峻审视与客观描摹再现了吴敬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1]的讽刺艺术。《百万磅》根据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译改而成,讲述了主人公“我”意外卷入两位富豪的赌局后,手握富豪所赠百万磅大钞在伦敦生活一个月的奇幻经历。 小说叙写“我”在餐厅结账时,店主人见了“我”的百万磅大钞,先是“身体如石化一般,呆呆不动”,过了半晌,方才“惊醒”,说道:“这也不打紧,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我眼光很精确,像你老先生这样的大财主,那有不信用的道理? ”[2]寥寥数语间,世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新桃花扇》讲述疁溪老人意外获得了一册扇面,“扇面上非书非画,都是七八个桃花瓣一般的粉红斑……每瓣旁边都有数字写着,如十四、廿五、三十、十六、十九、廿一等”[3]3。 小镇上的一众文人视此为珍宝, 而这些扇面实际上是好色的胡大爷用来记录与其交好的女子的 “交契册”,“桃花瓣”则是这些女子“嘴唇上的胭脂印在扇面上的,旁注数字都是当时的年龄”[3]3。为圣人立言的名士精心品鉴的“宝物”竟如此污秽不堪,即便作者本人不发一言,小说所写人物与事件的不和谐已然将现实社会纲常礼教的崩坏尽数显露。《海滨消息》是包天笑发表在1913 年《小说月报》中的一篇书信体小说。 现代文学研究者将中国近代出现的书信体小说视作五四时期大量译介西洋小说的成果,1922 年4 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这一过程的标志性事件。 事实上,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使“我手写我口”成为时代风尚后,中国近代书信便逐步抛弃古代书信板滞僵硬的程式化套语与务求“辞达”的语言标准,转变为“纯粹的私人随便道款曲的文字”[4]。与中国近代书信的散文化倾向相呼应, 南社小说家包天笑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便已开始书信体小说的创作实践。 《海滨消息》由三封千余字的长信叠加而成,叙写了“我”、秋航、翠娟三人的情感纠葛,其形式与内容均已为现代意义上的书信体小说。 包天笑以一位女性的口吻倾诉情感,虽将缱绻柔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却无法摆脱从男性视角揣摩女性心理的局限。 小说中的“我”与秋航本是青梅竹马,只因秋航生病时翠娟对其悉心照料,“我”便陷入深深自责而致书与秋航分手。 温顺、多情的女主人公使《海滨消息》在激烈的商业小说竞争中赢得大量男性读者的青睐,但近乎懦弱的性格却是男性作者强加于女性的臆想。随着五四时期丁玲、庐隐、冯沅君等女性作家的崛起,包天笑等人“男子作闺音”时对女性的病态书写最终为时代所淘汰。
周瘦鹃在1912—1913 年的《小说时报》中发表有《六年中之拿破仑》《鸳鸯血》《孝子碧血记》等九篇小说。周瘦鹃的哀情小说与明末清初兴盛的才子佳人小说一脉相承,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则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更趋多元。《六年中之拿破仑》是周瘦鹃在民国初年哀情小说的代表作,讲述了拿破仑滑铁卢兵败后,在流放地圣希利纳岛度过的生命中的最后六年。拿破仑的事迹自1830 年代引入中国后, 其与众多女子的风流韵事引起周瘦鹃等职业小说家的强烈兴趣。在《六年中之拿破仑》中,拿破仑因思念故国妻儿“独立露华风里,目注洋中。不少瞬,泪亦涔涔而落”[5]9。 雄才大略、英姿飒爽的一代英豪被塑造成一位苦情的“可怜人”。周瘦鹃的哀情小说在延续才子佳人小说男女爱情悲剧的同时,将传统的书生形象置换为拿破仑等现代英雄, 从而借助西洋文学的全新素材使板滞僵化的才子佳人小说重新焕发活力。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将男女爱情视作人伦纲常的附庸,周瘦鹃坚信:“世界上一个情字,真具着最大的魔力。 ”[6]以这种唯情主义思想为引导,周瘦鹃将男女间的情欲抽象化、审美化,使“情”上升为与家国之恋同一层次的精神信仰。小说中的拿破仑无法忘怀的,一是妻子约瑟芬,一是故国法兰西。发妻之恋与故国之思交织缠绕,周瘦鹃始终拿捏着二者间的微妙平衡,两条感情线索齐头并进,最终在拿破仑弥留之际一并推向高潮。 “皇帝(拿破仑)又呼曰:‘我上帝……约瑟芬……吾儿……法兰西国民……军士……法兰西……’‘法兰西’语甚模糊而皇帝呼吸已绝! ”[5]11在故国之思的恢弘中融入发妻之恋的细腻,周瘦鹃以此将拿破仑的英雄末路与铁汉柔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六年中之拿破仑》属于周瘦鹃哀情小说的早期作品,此时的周瘦鹃因推崇唯情主义而将“情”视作生命的全部意义,以致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旦感情不顺,便以死亡的方式将这种不圆满推向高潮。 这种为营造“哀情”而刻意制造的悲剧,使“情”在抽象为一种精神信仰后失于空洞,整篇小说的思想意蕴因此停留于男女恋情的单纯哀悼而无法得到更高层次的升华。周瘦鹃在《六年中之拿破仑》中不吝笔墨地描绘圣希利纳岛的美妙风光:“岛边树色,绿如罨画,波荡愁痕,遥岑作凄碧之色,而大西洋中白浪澎湃,似亦作哽咽之声……”[5]4拿破仑对妻子的思念放置在如画的美景中,情与景相得益彰,艺术氛围愈加幽远缥缈。 周瘦鹃的哀情小说由此在打破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结局的同时,凭借清新婉约的语言风格使其笔下的爱情悲剧并不表现得颓丧、消沉,而是如一曲悠扬的挽歌,在对真情与挚爱的苦苦追寻中,洋溢着诗情画意。《八万九千镑》讲述了银行家曼约翰驾驶飞机运送八万九千磅巨款的故事。飞机起飞后,周瘦鹃写道:“那时薄云卷罗,斜晖微黄。我身上一身衣服,也好似染作淡黄色。幸亏晚风甚平,所以我飞艇也很平稳,宛如挂在空中……天已入晚,月光如银,下照大地,好像一个琉璃世界。我在月光中疾飞而去,驾雾腾云,真好似羽化登仙,心里非常快乐……”[7]工笔画般的白描笔法在摆脱哀情小说固有模式的束缚后显得更加洗练。无论是描摹风景,还是记录行踪,周瘦鹃平实质朴的文笔总能在亲切自然的叙说中传递出一种自然恬淡的美。 他的小说由此摆脱了报刊小说的粗糙,将故事性、艺术性大幅提升,在歌颂男女爱情的同时,传递出南社小说家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精致的审美品位。 1912—1913 年,周瘦鹃另于《小说月报》发表了《磨坊主人》《大仲马之大著作》《科西嘉童子》三篇小说。其中《磨坊主人》是一篇讲述普法战争时期法国老人披亚古勃勒被德军囚禁后点燃自家磨坊向村民传递敌情,自己不幸牺牲的故事。小说结尾写道:“少顷,磨坊中都已着火,(老人)觉火焰垂及其身,犹力自支拄,危立如故。挥手向德人,朗声呼曰:‘法兰西万岁!’”[8]法国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样板,“法兰西万岁”的呼号既表达了中国民众对于国家走向共和的兴奋,同时也显示出周瘦鹃等南社小说家心系民主、捍卫共和的政治意识与价值判断。在此后的“二十一条”等政治事件中,周瘦鹃等人以笔为武器,创作出一系列警醒国民救亡图存的爱国小说,而在共和伊始便极力推崇爱国主义的《磨坊老人》可堪此类作品的先声。
1912—1913 年间,凭借《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两份小说报刊有限的创作平台,包天笑的讽刺小说、书信体小说,周瘦鹃的哀情小说、爱国小说等,均为民初小说艺术技法、价值取向的探索做出了有益尝试。除包天笑、周瘦鹃两位小说大家外,南社小说家许指严、宋一鸿、徐枕亚、杨天骥、姚肖尧、林万里等同样为1912—1913 年的《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创作了数十篇小说。 有赖于南社小说家的辛勤耕耘,两份小说报刊在辛亥革命后政治报刊的挤压中得以延续,从而填补了近代小说报刊在清末与民初的两个繁荣期之间的短暂空白。
二、消闲取向的引领者
袁世凯北洋政府组建后,不断以行政,甚至暴力手段加强对国内舆论的监控。严酷的政治高压最终引发了1913 年的癸丑报灾,中国新闻业随即由辛亥革命后的“黄金时代”跌入谷底。②与新闻业的满目疮痍相反,癸丑报灾后的小说报刊一派欣欣向荣,种类之繁、数量之盛更甚于清末最后十年。③南社小说家周瘦鹃、王钝根、包天笑、陈栩、蒋箸超等均是癸丑报灾后小说报刊再度繁荣的重要参与者。
《小说时报》历经癸丑报灾后延续至1916 年11 月停刊,在近3 年的办刊过程中,包天笑、周瘦鹃、陈栩、尤翔、李作霖等9 位南社小说家为之提供30 余篇小说。 《小说月报》于1921 年由沈雁冰接任主编后,被用作“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而与南社分道扬镳。 在癸丑报灾至1921 年8 年的办刊过程中,许指严、周瘦鹃、包天笑、王蕴章、闻野鹤等25 位南社小说家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110 余篇。 除《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外,癸丑报灾后另有一大批全新的小说报刊问世,南社小说家依然是这些新兴小说报刊的主要参与者。例如《中华小说界》于1914 年1 月创刊,1916 年6 月停刊,办刊期间共发表周瘦鹃、包天笑、徐枕亚、胡怀琛、李中一等13 位南社小说家的著译小说近60 篇。 《小说海》于1915 年1 月创刊,1917年12 月停刊,办刊期间许指严、尤翔、江瑔、成舍我、姚肖尧等20 余位南社小说家为之提供小说50 余篇。创作、翻译小说的同时,南社小说家还以主编或编辑的身份经营小说报刊。例如《礼拜六》由王钝根、周瘦鹃主编,1914 年6 月创刊,1916 年4 月休刊,仅周瘦鹃便为《礼拜六》创作小说80 余篇,王钝根亦发表有10 余篇小说。除周瘦鹃、王钝根外,陈栩、钱葆珍、姜可生、王蕴章、胡怀琛等30 余人亦为《礼拜六》提供小说110 余篇。 《小说大观》由包天笑担任主编,1915 年8 月创刊,1921 年6 月停刊。 在六年的办刊过程中,除包天笑本人创作、翻译小说20 余篇外,周瘦鹃、陈栩、叶楚伧、闻野鹤、贡少芹等10 余位南社小说家在《小说大观》中发表小说近50 篇。 通过在小说报刊领域的活跃表现,南社小说家已成为癸丑报灾后小说界的中坚力量。
癸丑报灾后,“上海发行之小说,今极盛矣,然按其内容,则十八九为言情之作”[9]。 言情小说的兴盛缘于以消闲为主导的小说创作风尚,南社小说家参与的小说报刊是消闲小说创作风尚形成的重要催化剂。 1913 年11 月《游戏杂志》创刊时,主编王钝根与陈栩在《序言》中毫不讳言旨在消闲的办刊理念:“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故作者以游戏之手段,作此杂志,读者亦宜以游戏之眼光读此杂志。 ”[10]1914 年5 月,《小说丛报》创刊,徐枕亚执笔的《发刊词》将以消闲为主导的小说创作理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流,难言经世文章;茶酒余闲,只供清谈资料。滑稽讽刺,徒托寓言;谈鬼谈神,更滋迷信。 人家儿女,何劳替诉相思;海国春秋,毕竟干卿底事? ……嬉笑成文,莲开舌底;见闻随录,珠散盘中。 凡兹入选文章,尽是蹈虚文字;吾辈佯狂自喜,本非热心励志之徒。”[11]1914 年6 月6 日,王钝根、周瘦鹃共同创办了《礼拜六》。王钝根撰写的《出版赘言》堪称消闲小说创作的宣言书:“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 ……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故有人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 ”[12]王钝根将小说与“买笑”“觅醉”“顾曲”相提并论,这种视小说为娱乐工具的办刊宗旨,成为以消闲为取向的小说创作理念在小说报刊领域的具体映射。 癸丑报灾前后是中国近代工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上海等近代大都市的繁荣催生出市民阶层娱乐消遣的强烈需求。 面对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以言情小说为代表的消闲小说无疑是最为契合的小说形态,南社小说家主办或参与的《游戏杂志》《小说旬报》《礼拜六》等小说报刊则成为消闲小说创作热潮走向市场的重要媒介。
南社小说家能够成为民初小说报刊消闲取向的引领者,这在清末小说界革命后便已露出端倪。 1907 年,针对梁启超等人重政治而轻文学的小说理念,黄人指出:“小说者,文学之顷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 ”[13]黄人的发声成为周桂笙、包天笑、王蕴章等南社小说家在清末最后十年间力图从理论上恢复小说娱乐属性的缩影。随着上海等近代大都市的繁荣催生出以消闲为取向的创作思潮,小说在其诱导下逐渐沦为博人一笑的娱乐工具,此时已成为小说报刊主要经营者的南社小说家被裹挟在商业化浪潮中而无法置身事外。 为追逐商业利润,周瘦鹃等人通过强调小说的趣味性来迎合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其小说创作因此渐趋脱离现实而呈现出明显的斧凿之痕。周瘦鹃对此颇为坦然:“那天花板和帐子顶都是吾制造小说的机器,坐着望了天花板,一阵子胡思乱想,一篇小说就打成为草图了;躺着望了帐子顶,一阵子胡思乱想,又是一篇小说打成草图了。 ”[14]如此“胡思乱想”而成小说充斥着随意的情节与专断的叙事,作品中好端端的人经常突然丧命,病入膏肓的人眨眼间平复如初,毫无瓜葛的男女能够硬扯在一起,原本好好的一对也可能瞬间阴阳相隔。 例如《画里真真》是周瘦鹃发表于1914 年12 月《礼拜六》第29 期中的一篇小说,讲述主人公秦云在美术馆见到一副美人图后,对画中美人相思成疾,不久病亡。画像中的真人林宛若听闻此事后大为感动,遂至秦云家中哭祭,立誓终身不嫁,此后“每值星期六日,必一归摘花至秦云墓上……越十余稔”[15]。 又如1917 年周瘦鹃为《南社小说集》创作的《自由》,小说讲述张俊才、沈淑兰本是一对大学时代相恋的情侣,两人因毕业分离,沈淑兰嫁与林伯琴为妻。 此后,张俊才意外担任林伯琴编辑《中国百科字典》的助手,与沈淑兰重逢,旧情复燃。林伯琴因醉酒坠楼导致重伤,弥留之际希望玉成二人,张俊才、沈淑兰则在悟彻红尘后双双进入天主教堂修道。 周瘦鹃创作此类作品时几乎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他根本不关心,或者根本不想去关心小说为谁而作的问题,其所在意的仅仅是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制罗列出一系列难以置信的故事来吸引读者。 面对市场竞争的残酷与商业利润的诱惑,周瘦鹃等人迫于生计最终无奈屈服,而随心所欲的创作方式与轻薄浮浪的处世态度也为南社小说家最终与鸳鸯蝴蝶派的合流埋下了伏笔。
三、现实担当的呼号者
消闲小说的兴盛显示出癸丑报灾后文学对政治的厌倦与疏离,但并不意味着小说就此舍弃对现实的关注。 小说即便未能成为小说界革命描绘的救世良药,但一概否定小说的政治价值,单纯视作博人一笑的娱乐工具依然失之偏颇。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混乱依旧,人们因此重新审视梁启超等人赋予小说的“新民救国”“改良群治”等政治功能。包天笑在《小说大观》的《宣言短引》中,通过虚拟主客问答,力图对小说的现实功用重新予以正名:“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 客曰:‘否! 子将以小说能转移人心风俗耶?抑知人心风俗亦足以转移小说。 有此卑劣、浮薄、纤佻、媟荡之社会,安得而不产出卑劣、浮薄、纤佻、媟荡之小说?供求有相需之道也。’则将应之曰:‘如子所言,殆如患传染病者,不能防护扑灭之,而反为之传播菌毒,势必至于蔓延大地,不可救药,人种灭绝而后止。 人即冥顽,何至自毒以毒人哉? ’”[16]姚民哀为《小说季报》作序时大声疾呼小说创作不应放弃对现实的关注:“河山萧索,世变已亟。《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传》曰:‘《诗》亡而后《春秋》作。’今《春秋》已亡,则吾侪有笔有舌,岂终甘喑哑以死?不讬之于说部,赴将奚讬!”[17]《小说大观》《小说季报》聚焦于小说文体功能的讨论,由《民权报》文艺副刊演变而来的《民权素》则直言不讳地抨击癸丑报灾后的黑暗政局。 《民权报》于1912 年3 月1 日创刊,是革命党人抨击袁世凯独裁专制的重要阵地,主编戴季陶甚至提出“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④的口号,《民权报》因此在癸丑报灾中惨遭查封。 1914 年4 月25 日,曾任《民权报》副刊编辑的蒋箸超搜寻残存的稿件与创作力量,整合成《民权素》继续出版。 在创刊号的序言中,蒋箸超痛悼《民权报》的夭折:“《民权》之可传者,仅小品乎哉?皇皇三页纸,上而国计,下而民生,不乏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之作。惜乎!血舌箝于市,谠言粪于野,遂令可歌可泣之文字湮没而不彰传。不若雕虫小技,尤得重与天下人相见。 ”[18]同为《民权素》重要参与者的徐枕亚在控诉袁世凯高压政治的同时,誓言以小说延续“民权”的种子:“昆仑崩,大江哭,天地若死,人物皆魅。 堕落者,俄顷梦死者,千年风雨恣其淫威,日月黝而匿采。是何世界还有君臣?直使新亭名士欲哭不能,旧院宫人无可言说! ……不痴不聋,难为共和国民! 无声无臭,省却几多烦恼。 ……然而我口难开,枯管无生花之望。人心不死,残编亦硕果之珍。是区区无价值之文章,乃粒粒真民权之种子! 零星断碎,具五族之雏形。 感慨悲歌,结千秋之遐契。 ”[19]癸丑报灾后南社小说家对于小说报刊的全方位介入,一方面源自职业小说家对于商业利润的自觉追逐,另一方面则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面对政治高压的无奈趋避。商业利润的诱惑使南社小说家成为消闲小说热潮的重要参与者,趋避政治高压的无奈则使南社小说家不甘沦作唯利是图的写手,面对全社会男欢女爱的纸醉金迷,依然倔强地追忆着共和的愿景,甚至以搏命的姿态向黑暗现实发起冲击。 南社小说家参与的小说报刊由此进入消闲娱乐与关注现实的双向演进轨迹。
癸丑报灾后小说报刊在消闲与忧国间的左右摇摆, 同样体现于南社小说家的创作中。周瘦鹃“言情之作居什九,然多哀艳不可卒读”[20]。 透过缠绵悱恻的男女苦恋,一介书生忧心国运的激愤成为哀情小说的底色。 1914 年7 月,周瘦鹃在《礼拜六》第5—6 期连载小说《真假爱情》中,通过郑亮与陈秀英、李淑娟姐妹二人的两段恋情,探讨了爱情的“真”与“假”。小说讲述了爱国青年郑亮在武昌起义中投笔从戎,却未能得到未婚妻陈秀英认可的故事。 陈秀英挽留郑亮:“革命军中多了你一人,未必就会打胜仗。 少了你一人,也不打紧,未必就会打败仗。 你又何苦来呢? ”[21]郑亮断然拒绝,两人就此分手。 郑亮临行时邂逅了陈秀英的表妹李淑娟。李淑娟欣赏郑亮的义举,对其暗生情愫。武昌起义胜利后,郑亮凯旋,与李淑娟喜结连理。成婚之日,李淑娟勉励郑亮:“郎君你娶了吾,别忘了祖国。吾虽然望你爱吾,吾也望你爱祖国。 ”[22]郑亮由此对李淑娟愈加钦慕,陈秀英则一人孤独终老。 《真假爱情》的故事情节不乏斧凿之痕,但周瘦鹃通过简短的叙事充分阐明了自己心中衡量爱情的标准:郎情妾意不应与为国尽忠冲突,美满的爱情是对爱国者最好的褒奖。 这一思想在周瘦鹃的其他哀情小说中也有体现,例如1915 年6 月26 日发表于《礼拜六》第5—6 期的《为国牺牲》,小说讲述顾明森大尉虽然深爱自己的父母妻儿,但国家危难之际仍然奔赴战场。一次战斗中,顾明森大尉只身面对敌人的炮火, 生死关头虽然脑海中不断浮现家人的身影,“心儿几粉裂,直欲失声而呼”[23],但依然摒弃思恋,慨然赴死。 爱情与豪情相生并存于郑亮、顾明森大尉等人物形象中,面对恋人与祖国的抉择,这些人物以身许国的大义凛然显露出周瘦鹃等南社小说家性格中的刚性因子。 慑于政治高压,这种刚性因子在癸丑报灾后一度潜藏于哀情小说的哭悼中,但现实的黑暗一旦突破隐忍的底线,书生报国的义愤便不再拘泥哀情小说的叙事而如火山爆发般喷薄而出。 1915 年1 月,日本向中国悍然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北洋政府虽虚与委蛇,但受制于羸弱国力,仍然被迫接受部分条款。 1915 年5 月9 日,中日签署《中日民四条约》,一时间举国哗然,民怨沸腾。周瘦鹃闻讯后义愤填膺,当即创作《亡国奴之日记》,讲述积贫积弱的中国被六国瓜分殆尽,“四万万黄帝之裔”无奈听任异族蹂躏的惨状。 周瘦鹃在小说附记中写道:“吾又自问,问吾祖国其已亡也耶? 然而此中华民国四字,固犹明明在也!吾祖国其未亡也耶!则一切主权奚为操之他人?而年年之五月九日,奚为名之曰国耻纪念之日? ”[24]同周瘦鹃的虚拟影射相比,王钝根节取报纸新闻整理而成的《国耻录》堪称“二十一条”事件的“实录”。从1915 年5 月22 日开始,王钝根在《礼拜六》中开辟《国耻录》专栏,全方位展示中日双方就“二十一条”交涉的整个过程,希望以此唤醒国人,共同挽救危局。 《国耻录》开篇写道:“中国对日交涉失败,人民愤痛,莫可名言,军人学子,甚至自尽。 呜呼哀哉! 孰谓中国人民甘心为亡国奴耶? 然而痛者自痛,嬉者自嬉,彼冥顽无耻之官吏,吾不屑论。 ……国而忘家,公而忘私。 祛旧弊,振新机。 兴学育才,整军经武。 人人心中有国耻而耻乃可雪,人人心中有仇敌而敌无可乘。 楚虽三户,犹能亡秦! 岂我中华,遂沦永劫? ……万众一心,坚持到底,中国前途,庶几少免于凌辱。 ”[25]《国耻录》连载于《礼拜六》第51—53、55、58 期,前后持续近两个月。 《礼拜六》创刊之初,主编王钝根便确立了“趣味第一”的办刊理念,并由此聚集了周瘦鹃、包天笑、许指严、徐枕亚、陈栩等一大批消闲小说大家,甚至以消闲娱乐为宗旨的“鸳鸯蝴蝶派”亦被称作“《礼拜六》派”。 但正是这份被五四新文学家批评为“以靡靡之音,花月之词,消磨青年的意志”[26]的消闲杂志,却在国家沦丧之际拿出整整五期的篇幅,向中国民众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而发出这声呐喊的周瘦鹃、王钝根等又曾在癸丑报灾后掀起消闲小说的创作热潮。 消闲与忧国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矛盾地统一于南社小说家的创作中。 这种矛盾既是癸丑报灾前后的社会政治环境所致,又是小说家个体的有意为之。正如1913 年9 月王钝根为《自由杂志》作序时所写到的:“自由谈者,救世文字而非游戏文字也。虽或游戏其文字,而救世其精神也。慨自时局纷乱,约法虚设,所谓言论自由者,孰则能实践之? 或徇于党见,或困于生计,或屈于权威。 虽有慷慨激昂之士,欲为诛奸斥佞之文,在势所不能,在情所不便,乃不得已而托于游戏文字以稍抒其抑郁不平之气,而彰善瘅恶之义务,亦于是乎? ”[27]新民救国的激昂呐喊与消闲娱乐的缱绻柔情由此双峰并峙于南社小说家参与的小说报刊中。
辛亥革命至新文学运动的近十年间,包天笑、周瘦鹃、许指严、王钝根等通过小说创作与编辑小说报刊成为小说界的中坚力量。 1912—1913 年,南社小说家支撑起仅存的《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从而保存了清末民初小说最为重要的物质载体。面对癸丑报灾后大量涌现的小说报刊,南社小说家一方面掀起消闲小说的创作热潮,另一方面极力维持小说对现实的关注。 有赖于南社小说家的辛勤耕耘,民初小说报刊在消闲与忧国的二重变奏中曲折前行,成为中国小说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环节。
注释:
①方汉奇先生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一百多种,陡增至近五百种,总销数达四千二百万份。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676 页。
②方汉奇先生统计:“综计在1912 年4 月至1916 年6 月共四年零两个月的袁世凯反动统治时期,全国报纸至少有七十一家被封,四十九家受传讯,九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二十四人被杀,六十人被捕入狱。 从1913 年的‘癸丑报灾’,到1916 年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而实行的对舆论的残酷压制,全国报纸的总数始终只维持在130—150 种上下, 几乎没有增长, 形成了民国以后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低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720 页。
③据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统计,仅1914 年一年,刊载小说的报刊便达近百种之多。
④胡道静记载:“是年(1912 年)五月十七日,财政部与四国银团订垫款合同,《民权报》于二十日载‘反对外债’论说时评,公共租界捕房即控以‘毁谤袁总统、熊希龄、唐绍仪、章炳麟’罪,请廨出票,在二十二日把戴氏(戴季陶)捕去。 六月十三日宣布堂谕,谓‘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惟值此过渡时代,国基未固,尤贵保卫公安。 该报措辞过激,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询明,着罚洋三十元’。 戴氏出狱后,在其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载《胡道静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0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