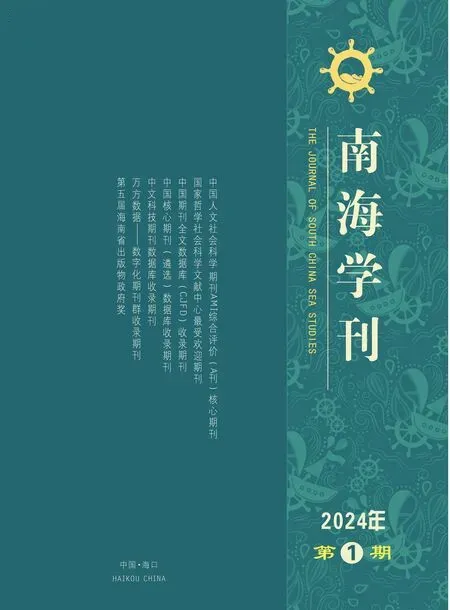理学视域下的为政之道:以丘濬政治观为中心的解读
朱 彤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号深菴,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人,人称“琼台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永乐十九年(1421),丘濬出生于琼山县府城西厢下田村。由于父亲早逝,丘濬自幼在祖父丘普以及母亲李氏的教导下,博览群书,立志举业[1],可谓是“少孤力学,天资过人”[2]。正统九年(1444),丘濬在广东乡试中举。景泰五年(1454),丘濬会试中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仕宦生涯自此而始。丘濬一生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官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位极人臣。丘濬逝世于弘治八年(1495),享年七十五岁,赠太傅左柱国,谥文庄。丘濬一生不仅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其本人更是“性嗜学”,甚至在年迈时“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3]。就学术倾向而言,丘濬崇尚儒学,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虽然丘濬并未与当时的理学大家建立师承关系,但他始终恪守程朱之教,曾著有《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等书,精心整合了二程、朱熹等宋儒的思想精华,并且将自己对程朱理学的理解灌注其中,充分彰显了其以程朱理学为宗旨的治学态度。丘濬的理学著述在明代影响力颇大,以至于“天下人诵其文,家有其书”[4]。作为成化、弘治年间的一代名臣,丘濬的政治观有着鲜明的程朱理学色彩,他的诸多施政理念都是以程朱理学作为指导思想,其本人也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以下将通过君臣之道、礼治与国家教育三个层面,来探究丘濬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政治观。
一、丘濬对君臣之道的理解
君臣之道这一概念最初由孟子提出,强调君臣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道德关系和义务。君臣之道关乎着国家政权的运行,尤其是到了成化、弘治年间,当朝皇帝的能力与素养远不及国初几位先君,朝堂上贤臣的涌现也远逊于前代,君臣冲突时有发生,故丘濬的政治观首先体现在维系君臣之道的稳定与和睦。丘濬曾云:
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极。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启,以诒厥子孙者也。太康以逸豫灭厥德,则失其祖父所传之道,所传之道既失,则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为纲,小之为纪者,咸紊乱矣。纪纲既乱,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其底于灭亡也宜哉。[5]56
丘濬认为君臣之道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理”,尤其是对于君王而言,王位的更替始终是有“理”可循的,倘若违背此“理”,代代相传的君王之道自然也会由此断灭。显然,这一观点与程朱理学的基本理论相契合,故丘濬将君王本应遵循的“理”诠释为“纪纲”,强调君王的“政令之所行”都要以“纪纲”为依据,对此他又讲道:
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纪纲者,维持天下之具。”臣窃以为,所以立道而维持其纪纲者,修德又其本也。人君诚能修德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纪纲,则可以保祖宗之基业,诒子孙之远谋矣。[5]56
由此可见,丘濬认为君王“立道”的根本在于“修德”,为人君者唯有具备优良的道德修养,方能将其所践行的君王之道引入正途,以此来匡正“天下之纪纲”,也就是所谓的治国之“理”,进而令这种以德为本的君王之道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立道”即是“格物”,“正天下之纪纲”即是“穷理”,所以丘濬的这一观点其实是契合了程朱理学“格物穷理”之法,并且将之最终落脚于伦理道德的构建,丘濬也对此感叹道:“德之在身为威仪,发于外为声誉。德乎,德乎!其立纪纲之根本;而所谓不解者,又其保纪纲之节度乎!”[5]58
不仅如此,丘濬还特意强调了朱熹本人对于匡正“纪纲”的重视,其云:
自古儒臣论为治之纲纪,莫切于唐韩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为切至焉。伏望明主留神省察,奋发刚断,一正宸心,斥远奸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胜大愿。[5]60-61
由此可见,把“纪纲”当作王道之“理”并非丘濬独创,而是其对朱熹原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也再次反映了丘濬的政治观与程朱理学的融会贯通。
丘濬对臣子之道的理解同样与程朱理学相契合,他强调为人臣者须树立忠君观念,谨遵君命,将侍奉君王视为不可违背的天理,其云:
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违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则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则不足以继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则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5]81
丘濬指出君命乃“天之道”,是天命在国家政权中的体现,故臣子顺应君命实际上就是顺应天命,这就表明臣子之道与君王之道应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天理为依据。丘濬又讲道:
大抵天立君以为之子,君立官以为之臣,无非为乎斯民而已。盖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独理,而寄之臣;则是臣所治者君之事,君所治者天之事也。[5]112-113
据丘濬所言不难看出,君臣之道所应遵循的天命指的正是民心所向,一个国家之所以拥有君王,正是要以此来统领万民,君王之道的推行更是应该合乎民心。而臣子作为君王的辅助者,有着为君王分担政事的责任与义务,可以被看作君王之道的实际执行者,这就表明臣子之道的推行更应该循天顺人,这不仅体现在为君王分忧,还要时刻以人民利益为己任。
对于臣子而言,欲协助君王承袭天命,说到底还是要以德为本,与君王同心同德,对此丘濬说道:
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人君之任官,惟其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则用之。至于左右辅弼大臣,又必于贤才之中,择其人以用之,非其人则不可用也。人臣之职,在乎致君泽民,其为乎上也,必陈善闭邪以为乎君之德;其为乎下也,必发政施仁以为乎民之生。[5]108
丘濬指出为人臣者需兼具贤德与才能,尤其是身居高位之人更要竭忠尽智、秉节持重,无论是“致君”还是“泽民”都应当做到深仁厚泽,与君王共修德行,与人民休戚与共,在日常的施政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厚德载物,故丘濬亦云:“国之任用,所施所行者,无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岂有不治哉!”[5]110由是观之,臣子之道所应遵循的“理”,同样体现在以德为本,将个人修养与国家命运相关联,不断地提升政治素养,时刻把“为政以德”视为自己的政治信条。不仅如此,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居敬”工夫也在丘濬的君臣思想中有所展现,例如他曾讲道:
所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者也。是以人君为治,所以贵乎能修礼以达义。礼者敬而已矣。主敬以修礼,达之于天下,使其皆知其所当为者而为之,则义达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礼,则虚伪之气不作,而惟信实之道是体是行。[5]2481
丘濬认为君臣上下若能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怀有恭敬之心,对世间万物心存敬意,那么整个国家都会朝着河清海晏的方向发展,君臣之道的走向也将更加地合乎天道。君臣之间唯有“主敬以修礼”,并且将这种“居敬”的状态灌注于治国安邦的实践,方能实现“达之于天下”的远大宏图。总的来说,无论是君王之道还是臣子之道,都体现了程朱理学胸怀天下的价值取向,更是对天命的顺承,而天命中所蕴含的“理”正是体现在以德为本,程朱理学中的“居敬”“穷理”等道德修养工夫也同样可以适用于致求君臣之道。因此,丘濬所追求的君臣之道契合了程朱理学的政治理想,充分彰显了儒家以德治国的价值目标。
二、丘濬对“礼”的把握
在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之中,“礼”与“理”始终是一脉相承的,“礼”与君臣之道一样,都是天理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反映。礼治的发展关乎一个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风气的开化,牵动着封建政权伦理道德体系的构建,符合程朱理学的政治诉求。丘濬作为程朱理学的信奉者,同样将礼乐制度的建设与天理联系在一起,提倡以“礼”来维系封建伦理体系,他曾云:
礼乐之制作于圣人,非圣人所自为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气而为之耳。大率礼以地制,而其制也本其自然之形;乐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之气。气得其顺,则天亦应之以顺;形得其常,则地亦示之以常。[5]620
丘濬认为国家的“礼乐之制”虽是由圣人制定的,但其制定的过程亦有“理”可循,遵守了天道运转的法则。由于“礼乐之制”是圣人站在天地自然的高度制定出来的,因而都是天理的体现。世间万物本就各有差异,故礼乐制度的颁订应当顺天承命、因地制宜,遵循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切不可逆天理而行。尤其是对于“礼”而言,丘濬称“礼以地制”,这无疑与人类社会更为接近,所以“礼”的推行始终与社会秩序的运转息息相关。对此,丘濬还曾引用朱熹之言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其云:
《易·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六经》言礼之始,然经但言履而已。而说者乃以之为礼,何哉?朱熹曰:“辨上下,定民志也,是礼的意思。”……是以君子为治,莫先于定天下之志;欲定其志,莫先于辨上下之分;辨上下之分,而不见于践履之间,徒有其言,不可也。是以定为品级,制为节文,截然有威而不可犯,秩然有仪而不可紊,此履所以为礼欤。[5]635-636
朱熹将“礼”诠释为“辩上下”“定民志”,这就表明“礼”的制定源自天地之“理”,是上顺天意、下应民意之举,是一个国家政通人和的基础保障。丘濬对朱熹的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他指出欲行“君子之治”,必须顺天时、应地利、得人和,并且最终要落脚于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就要求施政者必须完善礼制,将国家的运行机制“定为品级”“制为节文”,以此来保障政治权威,规范社会秩序,彰显以礼治国的风范。因此,丘濬认为一切政令、法律皆出自“礼”,强调“天下之事,无一而不本于礼者”[5]644。他亦对许多施政者不重视礼制的态度进行了批驳,称其“顾以礼为虚文,而一以法令从事,岂知本者哉”[5]644,抨击了这种忽视礼教的舍本逐末行为。
鉴于“礼”对社会体系有着规范与约束的作用,那么势必会与人们的欲望产生对立,恰如丘濬所言:“礼则天理,所以防闲人欲者也。”[5]673丘濬认为欲望有好、恶之分,而恶欲的消除亦离不开“礼”的制订,对此他谈道:
盖以人心莫不有欲,而所欲者莫不各有所好恶,好恶得其平,则是人道之正也。故圣人因礼乐而示之以好恶之正,使民观其礼而知上之制礼,而不专事乎口腹也。[5]614-615
丘濬强调人皆有欲望,而欲望亦“各有所好恶”,唯有使恶欲得到抑制,方能唤醒善念,令心中的道德仁义得到充分地发挥,以此来修正个人行为,进而达到“人道之正”的效果。显然,这反映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丘濬亦云:“后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下民化之。此人道所以日流于邪淫,而世道日沦于污下也欤!”[5]615他指出君王若是任由自己的恶欲蔓延,无疑会造成治国无方的后果,以至于朝纲废弛、民生凋敝,终究为天理所不容。照此看来,丘濬举此例的目的,正是要提醒当朝天子应当以“礼”来规范自身,节制私欲,时刻遵守儒家的纲常伦理,从而令当朝天子匡正君心,走上励精图治的道路。
此外,礼制的推行亦与程朱理学的“居敬”工夫密不可分,丘濬明确指出:“礼者,敬而已矣。”[5]643他将“居敬”视作遵守礼制的先决条件,其云:
春秋之时,去先王之世不远,一时论治者,率本于礼;论礼者,率本于敬让。敬也者,礼之本也;让也者,礼之实也。存乎心者以敬,形于貌者以让。以此立义,以此为政,本乎恭敬之节,形为逊让之风,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长世也欤![5]664
丘濬认为“敬”乃“礼之本也”,无论是追求道义还是执政掌权,都要具备“敬让”精神,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既要保持恭敬、端肃的态度,同时又应当拥有一颗谦让之心,以“礼”为本,令这种“敬让”精神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以此来弘扬礼义,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保证,这也契合了圣人推行礼制的初衷与归宿。尤其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礼”与“敬”始终是具有同一性的,都能为政令的执行提供道德依据,对此丘濬谈道:
政之行,以礼为舆;而礼之行,又以敬为舆。不敬,则怠于礼;怠礼,则政不立,而驯至于乱也。[5]664
《春秋传》曾记载:“周内史过曰: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5]643丘濬所言基本借鉴了这一思想,先将“礼”视为国政之根基,又将“敬”视为“礼”之根基,这就进一步凸显了“敬”在礼制中的先导作用,把“居敬”工夫当作践行礼制的重要方法。此外,丘濬崇尚以“乐”来辅助礼制,其云:“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所谓六律五声八音者,察政治之具也。”[5]680丘濬认为“乐”同样是与“理”相通的,对此他讲道:
君、臣、民、事、物五者,该尽天下之理。一乐之作,而万理无不该尽。先王作乐,以一声寓一理。于其声之高下,而验其理之得失。觉其有失,则乘除抑扬以应之,使之必得其平,协比和谐,无相凌夺,然后反求于吾之政治……如此,则乐音与政事,常相流通。则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5]689
据丘濬所言不难看出,天下之事各有“天下之理”,而“乐”的制定正是对“天下之理”的诠释与表达。“乐”的作用体现在培养人的内心情感,注重以德化人,以此来促进道德观念的树立、伦理秩序的明晰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乐”是政治风气的映现,当政治清明之时,“乐”自然会悠扬悦耳,而倘若靡靡之音出现,那就意味着政治将趋于衰败。因此,“乐”的抑扬与政治的兴衰“常相流通”,只有令“乐”与天理相符合,才能创造出国泰民安的政治景象,进而实现儒家的治世之道。总之,在丘濬的政治观中,“礼”“乐”皆是天理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反映,二者并驾齐驱、相辅相成,不仅牵动着朝政的稳定与民心的凝聚,更是共同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构建出了一套完备的社会规范系统。
三、丘濬对国家教育的重视
中国古代的国家教育始终与政治挂钩,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国家教育的推行反映了统治阶级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主流,在塑造了士人道德修养的同时,亦为国家的官僚体系源源不断地培养着后备力量,时刻为政权的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尤其是自明王朝建立以来,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将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明成祖朱棣更是秉承父志,“命诸臣集《四书五经大全》,以训天下”[6],并且将之钦定为各级学校和科举考试的教材,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
丘濬作为一代名臣,深知国家教育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始终心系于教育制度的更新、教育风气的改善以及各级人才的选拔,故丘濬的教育思想无疑是其政治观的延伸和体现。毋庸置疑的是,丘濬的教育思想同样深受程朱理学的熏染,他认为国家教育的发展也是依托于天理,其云:
圣人观天之神道以设教,谓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当暖而暖,当寒而寒,无一时之差忒,不见其有所作为,自然而然,所谓神也。圣人体之,以设为政教,故下人观之,如见春而知其必暖,见冬而知其必寒,其暖其寒,皆其所自然。[5]1046
丘濬指出教育的设立源自“天之神道”,符合圣人的道德观。他通过四季交替而产生的气候变化形象地揭示了“设教”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当朝政与世风蒸蒸日上的时候,国家可以通过推行教育来延续这种优良风气,一旦世风日下,国家则可以通过加大教育力度来扭转衰败之风,恰如春暖冬寒,皆为自然法则。
天理呈现于人性之中即是伦理道德观念的树立,其根本则是着落于“性善”,这也表明对“性善”的致求同样也是国家推广教育的目的之一,丘濬就此谈道:
人之生也,性无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气禀所拘,物欲所蔽,不能无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无而今有者,拯救补塞之。如是,则师之教道立,而天下无不成之才矣。[5]1088
人皆有善,此乃天理使然,但其自身难免会遭受习气与私欲的侵染,故丘濬强调施教者应当为人师表,充分发挥教育的积极功效,以此来涵养心性,调节欲望,从而令人性趋于至善。显然,这也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观点的继承。
而对于求教的过程而言,主要是体现在客观知识层面的学习,这实际上正是反映了“格物致知”的方法,故丘濬亦云:
所谓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类。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为忠、信、孝、弟者。[5]1101
丘濬指出施教者所传授的知识既要囊括以“六艺”为核心的基本技能,同时还应该对儒家的道德标准有所涵盖。无论是“六艺”还是儒家的道德标准,都是“理”在人类社会中的显现,故受教之人应当以“理”为教,通过“格物致知”来到达“穷理”的目的,进而完成自身基本技能与道德标准的兼修。
对于如何开展国家教育这一问题,丘濬首先提倡应当充分发挥学校的作用,他称学校之教“根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来已有之”[5]1103,认为学校的教育内容源自上天赐予的禀赋,顺应了人之本性,是历代相传的真理。然而,丘濬注意到当时许多士子虽然置身于学校,却终日不学无术,缺乏勤学苦读的诚心,对此他惆怅道:
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学,方可以致其道。然今之士子,群然居学校中,博奕饮酒,议论州县长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饱食安闲,以度岁月,毕竟成何事哉?惟积日待时,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学者,亦多不务正学,而学为异端小术。中有一人焉,学正学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涂而废,而功亏一篑者,亦或有之。学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极,皆所谓自暴自弃之徒也。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5]1116-1117
丘濬不仅批判了“今之士子”在学校中荒废学业的行为,同时也对那些虽有好学之心,但又陷入异端之学或是不能持之以恒的学者深感惋惜。国家兴办学校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能够希圣希贤、明道济民的人才,这无疑与程朱理学“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相一致。因此,丘濬强调士子求学于学校必须“致其道”,既要坚守笃志好学的信念,又应当尊重国家兴办教育的初衷,在学校中业精于勤、潜心苦读,将追求圣人之道视为“致其极”的目标,切不可辜负施政者以教化人的良苦用心。
其次,丘濬认为开展国家教育离不开师道尊严,他指出师道与天理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云:
先儒谓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笃焉。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5]1129
显然,由于天地万物各有不同,皆需因材施教,师道便应运而生,这也表明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都具备成为圣贤的可能性,故为人师者要以德育人、循循善诱,求学之人更要将尊师重道视作天经地义的本分,保持温恭自虚的求学态度,诚心接受教诲。丘濬还列举了先儒投身教育事业的实例来印证师道正行的重要性,其云:“程颢在晋城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于其任,必大有所成就。”[5]1286又云:“朱熹在漳州,首以礼教化俗。”[5]1286可见良师的言传身教不仅关乎人才的培养,更有助于正一方之风俗。照此看来,无论是国家教育内容的制定还是师道的弘扬,皆是天人相应的必然结果,故丘濬感叹道:“程氏谓知道多少,皆由乎教,则学校之设,师儒之教,诚不可无于天下也。”[5]1135值得一提的是,丘濬本人同样致力于躬身弘扬师道,时人曾对此记载道:“昔丘文庄公为国子祭酒,以‘师道立则善人多’论试诸生。”[7]
此外,丘濬强调国家开展教育所使用的教材必须以程朱理学推崇的“四书五经”为基础。“四书五经”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权的建立与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导作用,尤其是《四书》中的《大学》与《中庸》,经朱熹编订、删减后单独成书,无疑是程朱理学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托之一。丘濬曾谈道:
孔孟之时,已有《六经》之说,而《四书》之名,则始于宋焉。所谓《四书》者,《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也。此数书者,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具也。学者必先读《四书》,而后及于《六经》;而读《四书》者,又必自《大学》始。[5]1210
丘濬认为《四书》宣扬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承载着士人精忠报国的政治抱负,故站在国家教育的角度,其重要性远胜过传统的《六经》。尤其是《四书》中的《大学》,凝结了儒学思想的精华,是程朱理学弘扬伦理道德与政治哲学的重要基石,对此,丘濬亦云:
小学由是而入德,大学本是以为教。圣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则《易》也,《书》也,《诗》也,《春秋》与《礼》也,《论》《孟》之与《中庸》也,皆所以填实乎《大学》一书。今日在学校,则读之以为格物致知之资;他日有官守,则用之以为齐治平均之具。[5]1210
显然,丘濬极力抬升《大学》在“四书五经”中所处的地位,认为该书浓缩了“四书五经”全部的思想精髓,蕴含着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对于求学之人而言,不管是初学时的启蒙还是稍微年长之后正式开始接受教育,都要把《大学》的内容当作读书求学的基础知识,当学有所成之后,更是要始终将“大学之道”视为治学或是施政的理论依据,故丘濬随即讲道:
我祖宗以学校育才,以经术造士。教之于学校者,以此经此书;取之于科目者,以此经此书。盖将资之以为辅治之具,而以是经是书之所载者,以敷布乎天下,使斯世斯民,皆皞皞乎雍熈泰和之域也。[5]1210-1211
《大学》所折射出的人生哲学涵盖了个人修养、家庭和睦、社会治理以及国家统治等多个方面,塑造了儒学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故丘濬提倡无论是开展国家教育还是开科取士,都要将《大学》作为最基本的教材,倘若国家所培养的人才可以入朝为官,协助君王辅政,那就更需要将《大学》看作“辅治之具”,以此来为国家政治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进而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由此可见,丘濬对国家教育的理解始终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这也与明王朝自建国之初就早已钦定的以程朱理学为本的科举指导思想相辅相成。
四、余 论
综上所述,丘濬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政治观主要体现在君臣之道、礼治以及国家教育三个方面,这实际上反映了其本人对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的认同与维护。自明成祖颁布《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以及《性理大全》之后,明代前、中期的经书注解都是以程朱理学为依据,并且将此钦定为各级学校的教材以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唯一标准,彻底地将程朱之学作为统一思想的理论工具,致使天下士人皆以程朱理学为宗,正如清代学者朱彝尊所描述的那样:“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8]自此,明代前、中期的诸儒“大抵恪守紫阳家法,言规行矩”[9]。丘濬身为辅君之重臣,加之又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自然会凭借着自己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加强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力。因此,丘濬对程朱理学的弘扬无疑会率先在其政治观中有所显现。
丘濬一生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此时的思想界正值心学思潮开始萌发,“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10]。与丘濬同一时代的陈献章已经在岭南广积门徒,开明代心学之先河,许多士子在读书乃至举业的过程中试图冲破程朱理学的藩篱,这一趋势无疑是丘濬不愿意看到的,故丘濬对心学思潮的兴起呈反对态度,例如他曾多次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渊,其云:
曾子之作《大学》,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子思得于曾子,孟子得于子思,一知行之外,无余法焉。周、程、张、朱之学,皆不外此。而陆九渊者,乃注心于茫昧,而外此以为学,是果圣人之学哉?[5]1113
又云:
蔡渊曰:“或者但见孟子有‘无他,而已矣’之语,便立为不必读书穷理,只要存本心之说,所以卒流于异学。《集注》谓:“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放心而已。”正所以发明孟子之本意,以示异学之失,学者切宜玩味。窃考其所谓异学者,盖指当时陆九渊也。至今学者,犹有假之以惑世废学,切宜痛绝。[5]1126
由此可见,丘濬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深恶痛绝,将之看作“异学”。他指出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过于重视本心的自然萌发,忽视了“格物致知”的工夫,倘若士人在治学与举业的过程中随心所欲,抛弃了“读书穷理”的基本方法,那就势必会陷入异端之学,进而偏离圣人之道。不仅如此,丘濬注意到心学与孟子的学说有着一定的渊源,他以蔡渊、朱熹的言论为依据,揭示了许多学者对孟子思想存在着片面理解。丘濬认为这些学者沉溺于“存本心之说”,过分专注于内心的发挥,从而导致了心学思潮的蔓延。所以,丘濬呼吁士人应当恪守“孟子之本意”,谨遵程朱传注,以免在学术道路上误入歧途,而他的这一观点恰恰反映了明代心学思潮的兴起与程朱理学对思想界的统治产生了直接碰撞。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来自心学思潮的碰撞并非始于正德年间阳明学的发端,而是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已经初见端倪,虽然这一碰撞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撼动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程度,但其力渐增,其势渐旺。因此,心学思潮的涌动只是造成这种碰撞的外因,而究其内因,则是要归结于明代前、中期程朱理学的日益保守与僵化。
——以《程朱阙里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