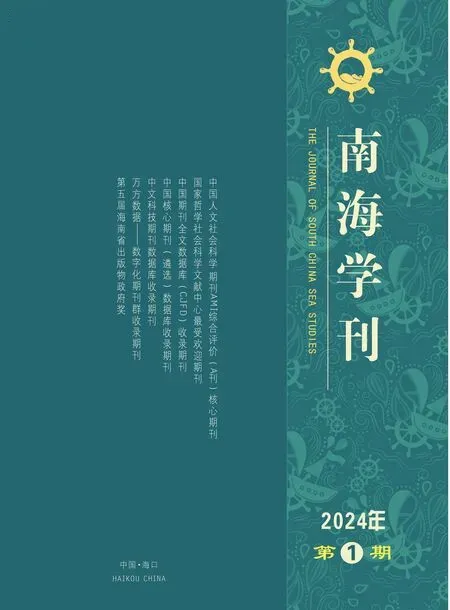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的法制完善
——以《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为视角
王一雯,李卫海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引 言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的见证与文化的传承,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物工作格局不断拓展,文物保护利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首次写入党的历史决议,“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成为全党意志[1]。
水下文物是我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目前国内水下考古按照“一南一北”方针,南方主要开展“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如广东“南海Ⅰ号”“南澳Ⅰ号”、漳州“圣杯屿”、上海“长江口二号”等沉船考古发掘工作;北方主要开展甲午沉舰课题研究,如辽宁“致远舰”“经远舰”和山东威海“定远舰”“靖远舰”水下考古工作等[2]。同时,随着我国深海载人潜水器技术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具备了深海考古作业能力,将在极大程度上拓展我们对深海文物的认识范围和程度。
2022年1月23日,第二次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修订后的《条例》在考古发掘、行政管理、文物利用、公众参与乃至国际合作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使水下文物的保护体系更为完善,进一步适应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的新形势。加强水下文物保护,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人类文明成果;同时,在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重视水下文物的保护管理对于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向多维、纵深发展意义重大,进而为全世界水下文物的保护管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条例》修订亮点纷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条例》的修订可谓是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的一次重大法制完善,内容上亮点纷呈,主要体现为水下文物的保护管理体制、执法机制、保护途径、保护理念等方面的更新完善。
(一)理顺水下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和执法机制
通过对《条例》此次修订前后的第四条(1)《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11年修订)第四条:“国家文物局主管水下文物的登记注册、保护管理以及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活动的审批工作。地方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水下文物的保护工作,会同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负责水下文物的确认和价值鉴定工作。对于海域内的水下文物,国家文物局可以指定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代为负责保护管理工作。”该条规定现已失效。《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下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水下文物保护工作。中国领海以外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水下文物,由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保护工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修订后的《条例》将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职责由登记注册、保护管理、考古勘探等具体工作变更为水下文物保护工作,涵盖了文物保护的全过程和多方面,强化了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责任;并将其职责所辖范围明确扩展至我国领海以外依法由我国管辖的海域,避免了原先海洋、外交、文物等多个部门齐上阵、职责划分不清的局面。同时,《条例》第四条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主体责任分别加以明确。针对水域的不同,赋予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相应的职责,强化了属地管理,使保护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此外,基于近年来海警力量的整合重塑,《条例》第十七条(2)《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文物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海上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水下文物保护执法工作,加强执法协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在水下文物保护工作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共享水下文物执法信息。”明确了海警作为海上执法力量在水下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定位,赋予其行政执法、治安管理和打击犯罪等权限。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对水下文物盗捞的执法打击力度,并且明确了责任主体,这在修订前的条例中是不曾有的。
修订后的《条例》构建起地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保护管理格局,形成了令行禁止、赏罚分明的行为规范体系,大大强化了实践层面上的可操作性,开启了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法治化的新篇章。
(二)确立了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
《条例》第七条确立了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进一步完善水下文物的保护措施(3)具体规定可分解为四点:一是明确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划定条件——水下文物分布集中、需要整体保护的水域;二是明确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准备工作——应当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包括有关部门和水域使用权人、专家、公众、有关军事机关;三是明确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具体程序——应当制定保护规划,标示范围和界线,制定并公布保护的具体措施;四是规定水下文物保护区内的禁止行为——禁止进行危及水下文物安全的捕捞、爆破等活动。。立法从划定条件、准备工作、具体程序和禁止行为四个方面建构起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的框架,体现了谨慎决策、科学保护的理念。2022年1月,山东省首次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基本确认为北洋水师旗舰“定远”沉舰残骸遗址,并划定了核心保护区和监控水域。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在未来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中将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三)拓展了水下文物保护途径
《条例》第九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初步建立了公众参与渠道:明文规定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渠道并向社会公开,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力量,同时明确单位和个人的水下文物保护义务;规定单位和个人发现疑似水下文物时应及时报告文物保护部门和举报危害水下文物安全的行为。
此次修订将举办展览、开放参观、科学研究等宣传教育方式写入《条例》(4)《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文物主管部门、文物收藏单位等应当通过举办展览、开放参观、科学研究等方式,充分发挥水下文物的作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水下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等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水下文物保护意识和参与水下文物保护的积极性。”,有利于最大程度上发挥文物的价值,体现了我们对扩大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决心,引导公众参与水下文物保护,增强社会公众的积极性。
(四)更新了水下文物的保护理念
在2011年修订的《条例》第九条(5)《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11年修订)第九条:“防止水体的环境污染,保护水下生物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不受损害;保护水面、水下的一切设施;不得妨碍交通运输、渔业生产、军事训练以及其他正常的水面、水下作业活动。”(现已失效。)中,文物保护必须让位于环保、保护自然资源和设施、交通运输、渔业生产、军事训练以及水下作业等,保护水下文物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水下文物的保护被置于靠后的位置。现如今,新修订的《条例》中已经没有了类似的表述,而是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水下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下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水下文物安全”(6)参见《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从经济发展优先、环保优先到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这一变化凸显了我国在保护水下文物理念上的更新和进步。
文物是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见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历史和文化愈发重视,精神文化需求愈发增长。保护文物不仅是保护国家财产,更是保护历史文化。在理念上提升文物保护的顺位,有利于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二、《条例》面临的挑战和难点
水域空间联结互通的特性无疑使水下文物的管理保护工作具有协同联动的特点,因而,与国际公约规定、通行做法有效衔接是提高我国《条例》适用性的应有之义。诚然,修订后的《条例》在管理体制、执法机制、保护理念和保护途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更新和进步,但是与国际公约及各国立法实践相比,《条例》仍然存在执行难点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保护对象及范围界定、所有权归属、管辖权确定、国家船只及飞行器的主权豁免等方面。
(一)与《联合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在重要议题上仍存在区别
《联合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通过。《公约》的宗旨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人类文明是其首要出发点。
1.保护对象
在保护对象上,《公约》采取了全面保护的标准,保护范围更大,不仅包括遗物、遗址和人的遗骸,还包括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以“水下文化遗产”这一称谓表述。《公约》中明确表述:“‘水下文化遗产’系指至少100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例如,2010年,在土耳其的Yenikap遗址出土了早期拜占庭时期最大的港口狄奥多西港。
《条例》界定水下文物,采取了重要性标准,保护范围仅限定在“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3],以“水下文物”这一称谓表述。从我国目前的水下考古成果来看,“南海Ⅰ号”“南澳Ⅰ号”“碗礁Ⅰ号”“华光礁Ⅰ号”“长江口二号”等沉船以及白鹤梁题刻都属于文物的范围。
同时,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变化可以看出,“水下文化遗产”的概念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这一概念来代替原有立法中的“水下文物”“沉船”“沉物”等概念[4],比如比利时、西班牙等。
从《公约》看,“水下文化遗产”涵盖的保护对象种类更多,但是在时间方面有距今100年的限制;从《条例》看,我国立法采用“水下文物”的措辞,未将遗址、遗骸、环境等纳入保护对象的范围,但是在时间范围上更广,没有100年的时间限制,只是将1911年后的部分无关的水下遗存排除。因此,《公约》与《条例》从措辞表述上反映出保护对象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
2.保护范围
《公约》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是从距今至少100年的时间往前溯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而《条例》则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时间节点——1911年,将“1911年以后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以及著名人物无关”的水下遗存予以排除,这一范围则是基本固定的。
我国的《条例》在保护范围上与《公约》并不完全契合,《公约》的规定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将近代以来更多的水下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围,有利于实现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
3.立法目的
在立法目的上,《条例》与《公约》存在较大差异。《公约》不处理所有权问题,“根据本公约采取的任何行动或开展的任何活动均不构成对国家主权或国家管辖权提出要求、支持或反对的理由”(7)参见《联合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第2条第11款。,根本目的是确保和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归属权问题。“泰坦尼克号”沉船被发现后,多国打捞公司都竞相打捞沉船上的文物,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却悬而未决。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自“泰坦尼克号”沉没一百年之日起,其残骸受到国际法保护。由于沉船地点位于国际海域,任何国家都不能声称对该地点拥有所有权。
而中国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对文物所有权有积极的主张和要求。我国立法的目的不仅仅是加强水下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更是主张和确保我国领水范围内和起源于我国的文物的所有权。因此在《条例》中对国家享有所有权、管辖权和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情形(8)《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三条:“本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所规定的水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其行使管辖权;本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水下文物,遗存于外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以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国不明的文物,国家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针对国家对水下文化遗产享有权利在立法上赋予依据。
(二)在水下文物所有权归属方面存在难题
1998年,德国一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了一艘波斯商船。这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世纪上半叶,运载众多陶瓷器、香料等从中国出发经由东南亚前往西亚、北非,出水的文物被一新加坡华商整体购买。同年,越南政府在金瓯角海域打捞了一艘清代雍正年间的中国沉船,众多文物被打捞出水,部分由河内历史博物馆收藏,其余则被拍卖。水下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归属这一问题不仅牵扯财产权利的保护,也关涉历史文明的传承,亟须重视和解决。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沿线国家共同开拓的海上交流的共享通道,唐、宋、元、明时期繁荣昌盛,船舶往来不计其数,因此在海上遭遇意外沉入海底的船舶也颇多。自20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国水域就不断发现我国古代沉船,这些沉船及其运载的大量文物的所有权归属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沉船原所属国、沉船所在海域管辖国、沉船文物原产国、沉船打捞者等。利益牵涉盘根错节、沉船文物价值巨大等原因都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困难重重。
1.国际立法各不相同
从涉及的利益相关方来看,处理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归属的理论方法主要包括三种,分别为主权先占主义、原权利人所有主义与来源国所有主义[5],在适用上各有优劣,各国遵循不同的标准,规定不一。从所处水域类型来看,内水和领海内的水下文化遗产无论来源国为何,大多归本国所有,一些国家甚至将这种沿海国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延伸至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1)早期国际惯例。早期实践中,很多沉船文物的归属都是依据“谁捞到,就归谁”的国际惯例。这一国际惯例不仅应用于国际水域,某些国家领海内的沉船文物也被打捞者据为己有。“谁捞到,就归谁”的国际习惯源于《发现法》(Law of Finds),这是海商法的一项古老原则,从大自然提供许多贵重物品的时代演变而来,这些物品可能包括鲸鱼或龙涎香[6]。《发现法》起源于普通法的财产法[7],基于对无主物的占有,将无主财产的所有权授予发现者或保管者,可追溯至12世纪英国法院的判例Armory v. Delamire(9)Armory v. Delamire (1722) 93 ER 664,该判例主要内容为一个清理烟囱的人发现了一颗显然是丢失的珠宝,英国法院授予其除了真正所有者之外的所有权。参见Kim Browne,Murray Raff. International Law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22, p.476.。习惯国际法的成立包含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客观因素,即一般国际惯行做法;另一个是主观因素,即法律确信[8]。发现并占有无主物的国际惯行做法和普通法中形成的法律确信,使得“谁捞到,就归谁”的国际习惯形成并固定下来。《发现法》也逐步应用于具有历史价值的沉船,其目的是将所有权赋予发现并占有遗弃财产的人[9]。《发现法》的适用必然假定所涉及的财产被遗弃,因此适用“发现者即物主”这一古老的原则。但是,“遗弃”这一情形很难确定。在极少数情况下,时间的流逝就足够了,但前提是没有原物主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利。从现实看,因年代久远没人打捞,就意味着该船被原物主遗弃了。
《发现法》明确授予发现者对打捞物的所有权。1983年,宝藏打捞者有限公司(Treasure Salvors,Inc)一案中,法庭对于1622年沉没的西班牙大帆船Atocha判决适用《发现法》,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主张对它的所有权,因而将其定性为被遗弃,并且确认宝藏打捞者有限公司获得第一发现者的所有权利。
(2)美国法律规定。1972年的《国家海洋保护区法》(National Marine Sanctuaries Act)规定,海洋保护区可位于美国内水、沉没土地、沿海水域乃至海洋水域,包括专属经济区;禁止破坏、损害或毁灭保护区内的水下文化遗产,禁止占有、出售、购买、进口、出口、递送、携带或运输违反该法获得的任何水下文化遗产[10]。1988年,美国通过《被弃沉船法》(Abandoned Shipwrecks Act),该法案规定这些美国领海内的沉船所有权归美国,并将所有权转移给沉船所在地的州。
(3)英国法律规定。1995年,英国的《商船法》(the Merchant Shipping Act 1995)规定,英国水域内无人认领船只的所有权归英王及其继承人,同时尊重沉船所有人和占有人的权利,除非英王及其继承人将此权利授予他人。
(4)比利时法律规定。比利时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法》第10条规定,在比利时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都属于比利时国家所有,但这一规定不妨碍原所有权人在证明其身份的情况下主张所有权[4]。
(5)联合国国际公约规定。通览《公约》全文,其并没有解决所有权问题,只是着眼于保护,确保和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公约》的首要和主要目的,“泰坦尼克号”沉船案便是最佳例证。
(6)我国立法规定。《条例》第三条规定,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的所有文物以及领海以外管辖海域内起源于中国和起源国不明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国家行使管辖权;遗存于外国领海以外的管辖海域以及公海范围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国家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可见,我国领水及管辖海域内起源国不明的文物之确权,《条例》秉持主权先占主义;外国领海以外管辖海域以及公海范围内起源于中国的文物,并不是完全秉持来源国所有主义,仅规定了国家拥有辨认物主的权利,保护力度不足。并且,辨认权利的行使依赖于文物所在国和文物来源国双方,并且在国家行使辨认权之后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仍不明确,在实践中无法实现对我国水下文物的有效保护。
2.“起源于中国”的内涵不明确
我国采取了根据来源国区分水下文化遗产的立场,此种立场是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的(10)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49条:“考古和历史文物 在‘区域’内发现的一切考古和历史文物,应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或处置,但应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权利。”第303条第3款:“本条任何规定不影响可辨认的物主的权利、打捞法或其他海事法规则,也不影响关于文化交流的法律和惯例。”。但是,此种立场在《条例》与《公约》之间、来源国和沿海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我国古代的航海活动起源较早,足迹遍及东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区,许多中国古代船只的残骸沉没在世界各地的海域。那些位于外国领海以外海域的沉船文物,一旦被中国政府认为“起源于中国”,就会成为存在潜在冲突的对象,外国的管辖权与我国的所有权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而《条例》与《公约》之间保护理念上的差异极有可能会加剧这种矛盾冲突。
到目前为止,“起源于中国”的内涵和定义还没有在中国的任何研讨会上得到确定[11]36。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有两种含义:如果是“具有中国国籍”,不论是作为船舶还是文物,都更容易被所在海域的沿海国所接受。但如果是“驶往或来自中国”或者“在历史上或文化上与中国有关”,那么,所在海域的沿海国可能难以接受,因为这就扩大了我国对水下文物主张管辖权和所有权的范围。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中对“起源于中国”的内涵进行有权解释,继而明确符合“起源于中国”的文物范围,从而对我国的水下文物形成有效的保护。
(三)总体上忽略起源于外国的水下文物
我国《条例》对于适用对象和范围,以水域、时间、价值等多重标准界定。《条例》第二条在界定“水下文物”时,将起源于外国的文物范围从所在水域上加以限定——中国内水、领海,即仅针对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起源于外国的水下文物行使管辖权,换句话说,我国对领水范围以外起源于外国的水下文物主动放弃了管辖权。我国近代的国门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的,海上交战、运输往来不计其数,因而我国水域内存在大量的外国沉船。在实践中,我国也几乎没有对外国的沉船进行保护和管理的实例,如2012年度青岛市水下文物重点调查工作中,1号沉船遗址初步推测极有可能是一战时期作为德国同盟国在青岛参战的奥地利“伊丽莎白皇后号”。该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工作目前仅停留在考古调查阶段,尚未实现对这一水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1.内水、领海范围内
内水、领海为一国主权所及范围,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的一切起源于外国的文物属于《条例》的适用对象,且《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其行使管辖权”。同时,《条例》第二条第2款又增加一限制条件——“不包括1911年以后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以及著名人物无关的水下遗存”,而这一限制条件可以将我国水域内许多外国沉船排除。“起源于外国的水下文物”范围不清晰,继而使管辖权的行使也变得不确定。由此看出,我国立法对于我国水域内外国文物的所有权问题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状态。
2.毗连区范围内
《公约》第8条顺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3条第2段规定,肯定了沿海国(缔约国)管理开发毗连区内水下文化遗产的权利。习惯国际法中关于毗连区的规定,构成了扩大沿海国管辖权的基础[11]29。但是,《条例》却为保护毗连区内的水下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相当约束的、有限的适用范围。《条例》第二条第2款将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的管辖海域内起源于外国的文物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换句话说,毗连区内只有起源于中国和起源国不明的水下文物才会受到《条例》的约束和我国的管辖。
3.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
《公约》第9条规定了缔约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的水下文化遗产的报告和通知义务,第10条更是以较长篇幅规定缔约国对于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概括而言:一是缔约国不得在《公约》许可之外授权开发水下文化遗产;二是为保护本国主权和管辖权不受干涉,缔约国可以禁止或授权开发水下文化遗产;三是有意愿的缔约国之间商讨如何有效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四是协调国要对上述缔约国之间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商讨进行协调。而我国的《条例》也同样为保护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的水下文化遗产设定了有限的适用范围,即起源于中国和起源国不明的水下文物。就《条例》的适用范围,归纳而言:一是遗存水域属于我国内水、领海;二是文物起源于中国或起源国不明。这两个条件满足其一即可管辖,但是都不涉及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起源于外国的文物。
实际上,《公约》规范了缔约国对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聚焦“如何保护”,而不论其所有权归属如何。表面上看似扩大了管辖权,实质上则是给缔约国设定了义务。而我国《条例》是在确定水下文物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进行管理和保护,以确定水下文物的起源国为首要条件。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本身是文化遗产大国,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瑰宝,自身的遗产确权与管理牵涉众多、纷繁复杂。目前起源于我国的水下文物保护和追索仍面临难题,在对本国文物尚未形成完善处理的情况下,对起源于外国的文物实施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并不现实。同时,存在的权属争议也难免引起国家之间更多的分歧和矛盾。
对于领水范围内的水下文物,无论是起源于我国还是外国,《条例》都赋予了我国管辖权。同时,立法中使用“起源”二字,表明立法注重水下文物的历史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国拥有被掠夺文物的所有权。而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只有起源于我国和起源国不明的水下文物才属于《条例》的适用对象,对于领水以外、起源于外国的水下文物总体上持放任和忽略的态度。但是随着我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加深度地参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应强化树立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的观念意识。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水下文物重见天日,必然也会发现起源于外国的文物,因此,始终忽略起源于外国的文物并非长久之计,有必要对我国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起源于外国的文物在立法上将确权与管理保护明确规范。
(四)回避国家船只和飞行器的主权豁免问题
国家船只和飞行器通常指的是在执行非商业性任务的军舰和其他政府船只或军用飞行器,《公约》规定的主权豁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经船旗国的许可,不得对“区域”(11)“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内的国家船只或飞行器采取任何行动;二是这些军舰和其他政府船只或军用飞行器没有报告发现水下文化遗产的义务。有的国家还针对此类国家船只和飞行器进行了专门立法,比如美国2004年的《沉没军用船舶与航空器法案》(Sunken Military Craft Act),该法案旨在保护所有美国沉没的军用船只和飞机,无论它们位于何处,并为位于美国水域享有“主权豁免”的他国船只和飞机提供保护[11]30。英国于1986年颁布《军事遗骸保护法》(Protection of Military Remains Act),该法案主要针对军用飞行器及船只的保护,一般通过划定保护区(protected palace)和受控制的遗址(controlled site)进行保护。
我国的《条例》未对国家船只和飞行器的主权豁免问题作出专门规定,未明确对于我国管辖水域范围内的符合水下文物条件的外国军用船舶和飞行器是否承认主权豁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尊重外国的主权豁免,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军用船舶和航空器是国有公船,但它们不仅是国家的财产,更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海上军事行动的基本工具,是国家的象征,因而具有国家的主权特性[12]。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在我国水域范围内存在大量起源于外国的沉没军用船舶及飞行器。随着海洋探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起源于外国的沉没军用船舶及飞行器将进入公众的视野,我国立法有必要对军用船舶及航空器的主权豁免和作为水下文物进行保护管理在性质确认、范围界定、处理方式等方面加以明确。
三、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的法制再完善
面对国内《条例》与国际《公约》存在的差异,面对各国在保护理念、保护制度等方面的不同,我国需要在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对水下文物的保护管理进行法制完善。同时,大量水下文物处于海洋环境中,对于现存难题,不妨结合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遵循包容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海洋观和治理思想[13],在制度建构和实践做法中加以完善。
(一)注意借鉴融合,健全保护体系
不论是相较于发达国家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相较于我国陆地文物的保护,我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都起步较晚。法国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从1961年颁布《关于确立海难残骸机制的法案》开始的[14];作为文化遗产大国的意大利在其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并于1969年设立“文物宪兵”保护制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的一些探险公司在我国南海和东南亚海域肆无忌惮地盗捞了我国大量的古代沉船文物,并在西方公开拍卖,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水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才在我国得到重视。我国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当注意借鉴国际已有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同时立足我国国情,实现相关制度规定的转化与融合,健全我国水下文物的保护体系。
首先,在名称界定上,我国立法应当考虑采用“水下文化遗产”的表述,将“文物”的范围拓宽至“遗物、遗址和人的遗骸以及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在扩大保护范围的同时,做到与国际接轨。其次,在处理文物所有权的难题上,需要先明确采用何种理论方法——主权先占主义还是来源国所有主义,从而对我国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起源于外国的文物所有权在立法上分别加以明确;针对外国水域内起源于我国的文物,应当秉持“民族主义”的核心立场,在尊重其国内法的同时,积极主张权利,实现对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一般情况下,民族主义是第一位的,文化遗产首先应满足其发源地人民理解自身历史的需要,然后它才能成为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15]。对于难以解决的复杂权属争议,我们应加强沟通协调,秉持合作共赢的态度,搁置争议,共同管理,努力使文化遗产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保护和发挥价值。
(二)协调利益衡量,完善保护理念
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建立了西北夏威夷群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养护区(Northwestern Hawaiian Islands Coral Reef Ecosystem Reserve),2006年该养护区被重新规划为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海洋保护区(Papahānaumokuākea Marine National Monument),聚焦该区域内一系列自然与文化资源的保护管理,涵盖珊瑚礁、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环境中的遗骸、夏威夷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12)关于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保护区的介绍见官网,http://www.papahanaumokuakea.gov/。。由此可见,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涉及科技、自然、文化等多个方面,应当置于海洋整体环境的大背景之下综合考虑,在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生态管理、科学探测、经济发展、旅游观赏等多个层面努力达到平衡兼顾。
同时,水下文化遗产的分布区域多与航路和港口重合,故常与海洋工程、航行、疏浚或拖网等作业,以及海洋保护区存在竞合[16]。此时,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比就地保护和出水打捞何种保护方式更为适宜,选择和采用最为适宜的保护方式;无论是原址保护——划设水下文物保护区,还是打捞出水进行考古研究和博物馆陈列,都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施工难度、生态保护、文物宣教等多种因素,实现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有机统一。
保护理念的更新完善不仅在于国家和政府,也要依靠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共识的与时俱进。这也意味着在公众参与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价值和享受方式上需要更多的投入,而不是将其仅仅视为一种经济商品,也要合理计算其娱乐、考古、历史、文化、社会和存在价值[17]。
(三)科学合理规划,拓展保护格局
海洋空间规划(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和多用途概念(multiple-use concept)的发展最近成为有效管理海洋空间中进行的多种活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18]。这启示我们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置于海洋空间的多维规划之中,通过对相邻资源的平衡兼顾和合理利用构建科学、高效的保护管理格局。因而,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开发和活动的海洋空间规划,是一种有效的手段[19]。同时,也要兼顾和保障军事用海、工程建设、科学考察、商业运输、水产养殖、资源开采等多种海域使用形式,将水下文物的保护管理融入海洋空间规划的各方面。因此,借鉴国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立法及具体实践,我国应考虑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新时代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中,置于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建设框架之下,致力于构建一个多维度、广覆盖、深层次的大保护格局。
(四)细化分工协作,统筹综合保护
2020年11月,我国海警在闽、赣两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盗捞水下文物案,缴获和追回沉船文物近700件,该案系我国海警侦破的首例非法盗捞文物案。我国海警集侦查、行政执法、防卫作战等多种职能于一身。《条例》中也明确规定了海上执法主体的职能要求,但是水下文物的保护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涉及文物、外交、科技、交通、军事、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必须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方能保证维护国家利益,保证大量的水下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条例》对于各执法主体在文物保护执法方面仅作笼统规定。因此,在国家文物部门与公安部门、海上执法部门之间的分工配合上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规定。各有关部门在共享水下文物执法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健全海上联合执法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联合执法的具体程序、各个环节的负责主体、分工协作的具体安排,从而完成对水下文物有效保护的力量整合与重塑。
(五)加强国际合作,形成保护合力
由于历史、地理、海洋环境等多种因素,水下文化遗产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因此,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是加强保护成效、完善保护机制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与东盟的文化区域合作中,中方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比如共同梳理“海上丝绸之路”史料和遗迹,联合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构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圈,实现和谐相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20]。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纳入中国与东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框架之中,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为了实现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可以签订双边、多边协定,或者对现有的协定加以补充,针对双边、多边水域内起源于对方国家的文物所有权归属问题制定明确具体的处理方法,也可以建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国际合作平台与规划项目。例如,比利时、德国、荷兰、波兰、葡萄牙、瑞典和英国七个国家合作共建的水下文化遗产管理数据库(Managing Cultural Heritage Underwater)在水下文化遗产监测、危险预警、考古价值预测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3)详见MACHU Report:Managing Cultural Heritage Underwater(January,2008),https://www.cultureelerfgoed.nl/publicaties/publicaties/2010/01/01/machu-reports-2007-2008-2009.。
同时,为了推动水下文物所有权的确权,《条例》规定了国家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而此项权利的行使也依赖文物所在国和文物来源国双方,双方有必要对辨认权利的具体行使程序以及辨认后的结果处理进行合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此外,相邻沿海国可以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等方式联合执法打击水下文物盗捞、走私,协力追捕,遏制犯罪,形成国家层面的整体保护合力,从而实现对水下文物的有效保护。
四、结 语
我国历史悠久,拥有种类数量十分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不仅有古沉船、水文石刻、古港口、古城市遗址,近现代沉没军舰也是水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域,因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遗存于水下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步入快轨,新兴的水下考古蹒跚起步,我国大量水下文物被外国人盗捞、继而贩卖牟利倒逼了我国水下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现如今,水下文物保护工作面临新的任务和新的形势。《条例》的第二次修订较之以前科学性、专业性加强,实践性、可操作性提高,立法理念、保护管理机制、执法体制等各方面亮点纷呈,对水下文物保护管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条例》在保护对象、立法目的等核心问题上与《公约》仍存在差异,在文物所有权的问题上仍面临立法上的难题,这都需要在未来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不断加以完善。
2021年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1]
文化遗产应该作为人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遗产的概念本身就要求尊重和保护个人和群体的特征[22]。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必须强化“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开放的格局审视和对待水下文物的保护管理事业。同时,全面推进涉海“软实力”建设,在关键性和战略性的国际治理议题中逐步提升以议题引领和规则创设等为进路的核心治理能力,多方面进一步实现文化遗产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现代化[23]。
水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无疑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一环,“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文化内涵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实际管理和有效保护具有深刻的启迪价值和重要的当代意义。未来,我们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并不断完善和更新立法精神、保护理念,将水下文物的管理保护置于经济、科技、自然、生态、文化等多维度协同的综合保护体系之中;同时,进一步完善保护管理体制,实现依法保护管理,并且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整体保护的合力,从而实现对水下文物的有效保护,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物保护利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