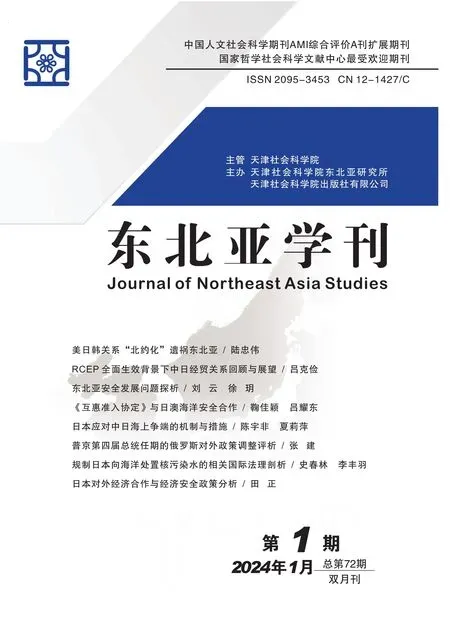规制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的相关国际法理剖析
史春林 李丰羽
内容提要: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问题,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有关风险预防、防止与减少及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海洋环评、可持续发展等规定,也暴露出国际法中相关规定在应对此类问题上存在规则不严密、适用局限性以及约束力度不足等缺陷。为了全面、有效规制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需要进一步做出有针对性的修订与完善,切实加强履约工作,充分发挥国际法作用,以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2023 年8 月开始,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周边国家的反对,引发了一场是否违法的国际讨论。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多项规定,但日本声称此次排放的核污染水是经过过滤处理的“干净”水,带有一定的迷惑性。笔者通过对《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的文本分析,阐释日本的违法行为,进而提出规制日本处置核污染水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日本核污染水处置问题的国际法讨论
2011 年3 月,日本福岛县因地震与海啸,造成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核电站泄漏。此后,东电公司在事先未与相关国家沟通和向国际社会及时告知的情况下,多次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如2011 年4月日本借口为了给高放射核污染水腾出存储空间,将1.15万吨所谓低放射核污染水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入海洋。特别是2021年4月日本在未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充分商议的情况下,又单方面决定将储存的处理核泄漏事故产生的130多万吨核污染水向海洋排放。根据同年12月东电公司提交的核污水排海实施计划,先对核污染水进行所谓的过滤与稀释,再通过新建的海底管道排放至约1公里之外的海域,全部排完约需30年的时间。而在稀释的过程中,每升核污染水需加入254 升干净的海水,这样最终向海洋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将会超过3 亿吨。①参见岳林炜、马菲:《多方呼吁阻止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日本政府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极不负责”》,《人民日报》2022年5月9日,第14版。2022 年4 月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NRA)同意了上述计划,并于7 月正式批准。东电公司在获得地方政府同意后开始全面建设排放设施,2023 年6月有关设施建成并开始试运行,8 月正式向海洋排放,截至11 月,日本总共排放三次共计2.3万多吨核污染水。
由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放总量大、排放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因此会严重影响海水质量,对海洋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水产养殖与捕捞等产业构成严重威胁。②Krati Gupta,Raj Shekhar,“Fukushima Radioactive Water Discharge Case:A Veheme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s,”May 4,2021,https://www.jurist.org/commentary/2021/05/guptashekhar-fukushima-international-law/[2023-12-10].而且,随着洋流、食物链等自然系统的循环,被污染的海洋食品最终会进入人体,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与身体健康,甚至还会改变人类的基因。③UN News, “Japan: UN Experts Say Deeply Disappointed by Decision to Discharge Fukushima Water,”April 15, 2021,https://news.un.org/ en/story/2021/04/1089852 [2023-12-10]; BBC News, “Contaminated Water Could Damage Human DNA,”October 23,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4658379[2023-12-10].因此,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这一做法,遭到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谴责与反对。比如,韩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韩大使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也表达了严重关切。①Sou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y, “Vice Minister Choi Jongmoon Summons Japanese Ambassador to Korea,”April 14, 2021, https://www.mofa.go.kr/eng/brd/m_5676/view.do?seq=321631 [2023-12-10]; Marianne Guenot, “Russia Joins China and South Korea in Expressing‘Serious Concern’at Japan’s Plan to Release Waste Water from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April 14, 202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ussia-japan-plans-fukushima-wastewater-nuclear-south-korea-china[2023-12-10].
迄今为止,日本对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并未认真给出后续说明,甚至还一直为自己的行为百般辩解。如2011 年4 月日本向海洋处置低放射核污染水后,辩称这是为了防止更大灾害而采取的相对合理的措施,是依其国内法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并不违反有关国际法。②参见张超:《日本排污入海内外皆不满》,《法制日报》2011年4月12日,第10版。但实际上,日本在未与周边国家协商与通报的情况下,擅自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是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不负责行为。特别是2021 年4月日本决定向海洋处置130 多万吨核污染水后,国际社会纷纷从国际法的角度批评日本的这一决定和做法。如中国明确表示日本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韩国指出日本的这一决定属于重大违法行为,绿色和平组织谴责日本的这一“暴行”决定违反了其应该承担的国际法义务。③Greenpeace,“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Discharge Fukushima Contaminated Water Ignore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April 13, 2021,https://www.greenpeace.org / international / press-release / 47207 / the-japanese-governmentsdecisionto-discharge-fukushima-contaminated-water-ignores-human-rights-and-internationalmaritime-law/[2023-12-10].但日本一再声称,此次排放的核污染水是经过过滤处理的“干净”水,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利用日本有关说法与做法所涉及的国际法来予以驳斥。
关于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的问题,不仅受到各利益攸关方的普遍关注,而且引发各国学界的广泛热议,特别是对日本的有关说法与做法是否违背1972 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简称《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展开了讨论。对于2011年4 月日本向海洋排放所谓低放射核污染水问题是否违法,目前国际社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日本的做法与《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的有关规定相悖,违反了基本义务,应受其规制。①参见李毅:《从国际法角度探析日本排放核废液入海问题》,《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2期,第40页。二是认为日本行为确实构成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所规定的倾废定义,但其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倾废,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倾废需经过严格储存、运输与选定特定的海域倾倒,而日本则是将核污染水直排入海,这种行为已凌驾于国际法之上。②参见蔡岩红:《日本向海洋排放核废液污染环境有违国际法,各国可视受害情况保留对日索赔权利》,《法制日报》2011年4月14日,第4版。三是认为不能认定日本排放行为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因为该公约所说的海洋倾废是指从船舶、航空器、海上平台或其他人造结构故意处置废物的行为,如果把日本排放行为对号入座,未免牵强。③参见郁志荣:《日本排放福岛核电站低放射性污水入海的法律责任辨析》,《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年第10期,第72页。
从2021 年4 月日本做出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的决定后,到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伦敦倾废公约》规定缔约当事国在向海洋倾废时,有义务采取任何方法防止跨界环境损害,不能违反一般法律原则,而东电公司处置方式违反了该公约有关对海洋环境污染进行有效控制与通报的规定,也不属于所规定的例外情况,因此可适用该公约规制;④参见马忠法、郑长旗:《日本决定核污水入海事件的国际法应对》,《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129—132页。二是认为该公约强调通过一定的运载工具作为倾倒条件,而东电公司通过新建管道向海洋排放属于陆源排放,不属于公约所规制的范围;⑤参见郭萍、喻瀚铭:《对放射性废物海洋处置国际法规范的审视与思考——以日本福岛核事故核污水处置为视角》,《学术交流》2022 年第10 期,第83—93 页;胡正良、李雯雯:《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的违法性与周边国家的危机应对》,《学术交流》2022 年第10期,第67—71页。三是认为东电公司的行为涉及违反该公约第1 条和第2 条及其议定书第3 条第1 款所规定的防止海洋污染的义务,但其具体排放方法是否满足倾废行为的法律要件可能存在争议,因此该公约有关规定在此事件适用性问题上存在讨论空间;①参见张诗奡:《福岛核污水排放方案的国际法义务检视》,《南大法学》2022年第4期,第6页。四是认为日本排放行为是否受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约束取决于其排放方式,但事实上目前国际社会对海洋倾废的定义必须予以修正。②参见程功舜、林赟:《海洋倾废视角下日本核废水排海决定的法律问题研究》,《未来与发展》2021年第12期,第55页。
由此可见,目前《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既有一定的法理依据,同时又有某些局限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笔者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究,认清日本排污入海行为的实质和违反公约及议定书相关义务的表现,揭示日本有关说法及做法的实质。在此基础上,针对该公约及议定书在规制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方面的缺陷,提出有关修订与完善措施,以便全面、有效规制日本的错误行为,更好地维护海洋生态、资源与环境安全。
二、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违反《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有关规定
为保护海洋环境、敦促世界各国共同防止由于倾倒废弃物而造成的污染,1972 年11 月英国政府召集的海洋倾倒废物公约政府间大会通过了《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简称《伦敦倾废公约》或《伦敦公约》,包括正文22 条和3 个附件。该公约于1975 年8 月正式生效,1996年11月通过的《1996年议定书》对原公约进行了较大的补充与修订,并于2006年3月正式生效。③参见危敬天:《国际海事条约的历史和现状概览》,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20页。日本作为《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缔约国,没有认真遵守有关规定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故意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把本来国内的污染危机推向了国际海域,违背了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有关宗旨、原则和具体规定。
第一,违反了关于风险预防的规定。《1996 年议定书》的序言指出,各缔约国应采取以预防和防止为基础的处理方法。第3 条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采用保护海洋环境不受倾废危害的预防方法,即有理由认为进入海洋环境中的废物有可能造成损害时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200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依据1972 年〈伦敦公约〉确定海上处置材料的适当性:放射性评估程序》,更是明确要求采用预防性方式。①参见余敏友、严兴:《论IAEA 在海洋放射性废物治理中的作用与局限——聚焦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事件》,《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5期,第12页。而当前日本却人为将核污染水直接排放至海洋,无法满足上述预防的法律要求,违背了合理预防的义务。对此,国际绿色和平组织首尔事务所表示,在目前还具有其他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违背了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事先预防等处理原则。②参见岳林炜:《“日本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很不负责任”》,《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1日,第15版。
第二,违反了关于防止与减少及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的规定。《伦敦倾废公约》的序言指出,各缔约国为确保对海洋环境进行管理并使其质量和资源不受损害,有必要采取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防止倾倒和排放等类污染。第1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有效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的一切来源,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防止因倾废而污染海洋。《1996年议定书》的序言指出,在防止和消除海洋倾废污染方面,有关国家应采取比国际公约更为严格的措施。第2 条规定,缔约国应保护海洋环境,使其不受一切污染源危害。因此,日本有责任确保海洋环境免受损害,也有义务采取措施有效防止与控制有关污染源。
日本违反了关于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核废物的规定。《伦敦倾废公约》第12 条规定,各缔约国保证为保护海洋环境免受各种来源的放射性物质污染而采取措施。为此,附件1 第6 款规定,禁止在海上倾倒强放射性废物。但该公约附件2 规定,如果缔约国有关单位事先申请并获得主管部门签发的特别许可证,同时考虑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有关建议,可向海洋倾倒未列入附件1 的放射性废物,即可向海洋排放弱(低)放射性废物。因此,2011 年4月东电公司借口为高放射性核污染水腾出空间,便向海洋排放了所谓低放射性核污染水,目的就是为了规避该公约对高放射性废物倾倒的限制,但其事前并未取得特别许可证,实际上仍违反了该公约的有关规定。1983 年在《伦敦倾废公约》第7次缔约国协商会议上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被暂时禁止,1993 年在第16 次缔约国协商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倾倒放射性废物的决议,并在附件1 的修订中得以体现。①参见《〈“伦敦公约”1996年议定书〉解读》,《中国海洋报》2006年6月30日,第2版。至此,一切放射性废物无论放射性高低,都被纳入了《伦敦倾废公约》禁止倾倒的黑名单之中,并在《1996年议定书》中再次予以确认。据此,日本负有不向海洋排放放射性污染废物、保护环境的义务。但2011年4月日本未采取任何预防与控制的必要措施,便向海洋主动排放了1 万多吨所谓低放射性核污染水,其主观故意及行为都严重背离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有关规定。由于这些核污染水中含有艳-137、碘-131等危害极大的物质,据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监测与检测报告显示,目前这些未经处理的核污染水对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质量的破坏已开始显现。②FAO,WHO,“Impact on Seafood Safety of the Nuclear Accident in Japan,”May 9,2021,https://www.who.int/foodsafety/impact_seafood_safety_nuclear_accident_japan_090511.pdf [2023-12-10].而目前日本声称向海洋排放的核污染水中,除氚以外的62 种放射性物质过滤后会被全部去除,是使用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净化过的处理水,③参见岳林炜、马菲:《多方持续批评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人民日报》2022年5 月24 日,第17 版;邢晓婧:《“洗白”核污染水排海,日本花了多少?》,《环球时报》2021年12月23日,第3版。以逃避有关法律义务。但日本这一说法并不属实,实际上日本所谓核污染水净化与稀释技术并不成熟,其可靠性、有效性、安全性及长期稳定性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该设备实际效果并不如东电公司所宣称的那么理想。目前只有三台设备,是由不具备核污染水处理经验与技术的东芝公司提供的。2013年为应对越来越多的核污染水仓促上马,东电公司事先并没有进行检查,便以试验运行的名义投产,直到2022年3月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才“检查合格”,其有效性并没有经过第三方评价或认证。因此,其技术上并不成熟,安全性也缺乏实际验证。该设备启用至今故障不断。如2021年9月东电公司宣布在设备中发现五个过滤器破损,且在部分过滤器附近检测到放射性污染源。④参见樊巍、曹思琦、单劼:《IAEA“日本排污报告”埋着这些雷》,《环球时报》2023年7月7日,第8版。由此可见,该设备处理效果并不稳定。而且,东电公司只片面强调处理过的核污染水中氚含量已达标,而故意忽视对其他放射性物质处理不足的事实。①Dennis Normile, “Despite Opposition, Japan May Soon Dump Fukushima Wastewater into the Pacific,”January 24, 2023, https://www.sience.org/content/article/despite-oppositionjapan-may-soon-dump-fukushima-wastewater-pacific[2023-12-10].日本国内外有关专家与组织进一步调查发现,处理过的核污染水中除氚以外,还存在碳-14、锶-90、碘-129、钴-60 等其他放射性同位素。对此,东电公司不得不承认该设备存在技术缺陷,在处理后的水中仍会残留碳-14、锶-90 等放射性物质。②参见吴学安:《日本核污水排海对海洋环境带来不确定性风险“日本不能再污染海洋,污染地球了”》,《防灾博览》2023年第5期,第45页。因此,在未来30 多年的时间,需要处理的核污染水数量巨大、成分复杂,很难确保不会发生事故或错误操作,而且该设备长期高负荷运行的性能与效率也会随着设备腐蚀与老化而进一步下降,从而加剧核污染水未达标的程度。
二是目前福岛核电站内储存核污染水的储水罐有1000 多个,但东电公司仅选取很少一部分进行检测,而且全部检测工作都是自行完成,并没有第三方机构监测与核实。同时,东电公司仅将核污染水中的铯137、钚等30 种放射物作为检测对象,只要这30 种放射物的含量低于限度,即被视为达标。如此自行检测与自定标准,其科学性、公信力无法取信于人。东电公司也承认70%以上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并不符合国内法对排放浓度的要求,需要二次过滤。③参见岳林炜:《日本核监管机构正式认可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引发各方强烈反对》,《人民日报》2022年7月27日,第15版。于是,2020 年9 月东电公司开始二次处理,但处理样本仅为2000 吨,不但采样数据严重不足,而且没有从存储罐底部高浓度沉淀物中取样。核污染水即使经过再次处理,仍无法去除钌、钴、锶、钚等放射性寿命更长且更危险的同位素。④Dennis Normile, “Japan Plans to Release Fukushima’s Wastewater into the Ocean,”April 13, 2021,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1/04/japan-plans-release-fukushima-scontaminated-water-ocean[2023-12-10].
三是东电公司所使用的辐射检测仪存在问题。如2022 年10 月东电公司在向公众展示所谓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安全性时,使用的是难以检测出放射性物质的检测仪。核污染水中主要放射性物质是氚与铯,其中氚会放射出贝塔射线,而当时使用的检测仪只能用来检测伽马射线,因此无法测出氚的浓度。铯虽会放射出伽马射线,但由于检测仪精确度较低,即便超标几十倍,仪器也不会有任何反应,以此来误导公众。
四是东电公司所谓的达标不等于没有、稀释不等于去除。即使通过稀释降低了核污染水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但放射性物质的总量并不会变化,因此污染海洋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因为,核污染水入海后会有很多生物对其中的核素产生富集,并通过逐级生物链把核素浓缩起来,最后通过海产品进入人体,其危害的放大效果十分严重。
另外,2023 年7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关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安全性的综合评估报告,认为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①参见岳林炜、杨沐岩:《“一家之言”不能成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护身符”“通行证”》,《中国能源报》2023年7月10日,第11版。于是,日本政府利用该报告大肆渲染核污染水安全无害,并强行启动排海方案。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该评估报告并没有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做出担保,无法成为日本排海的科学依据。
一是从职能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只是一个科技交流的平台,并没有放射性废物处置的权力,其本身并不是决策者,也不具有执行权与强制力。其对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的评估,是基于日本单方面委托而开展的,属于国际同行技术援助和咨询性质,并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另外,日本是否有权排放核污染水也不是由任何单一国际组织所能决定的,还需要综合考虑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其他具有监管权力的国际组织的意见。实际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只是促进安全、可靠、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国际组织,并非评估核污染水对海洋生态环境以及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长远影响的机构,对此并不能轻易下结论,而应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其他相关国际组织评估。
二是从程序来看,尽管日本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评估,但并没有体现出对该机构应有的尊重。实际上,日方早已预设了核污染水排海的结果,其排海计划一直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之前。如2021 年4 月日本宣布排海决定后,7 月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委托评估的“授权协议”。因此,日本邀请国际原子机构评估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而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三是从授权限定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范围受到日本政府严格限制,导致报告有关结论不完整、有前提,评估内容狭隘,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实质性问题并没有作出科学回答。首先,对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及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有效性和长期可靠性没有充分验证。其次,只对核污染水排海一种方案进行片面分析,并不包括对其他可替代方案的评估,没有办法经过对比证明这是处置核污染水最安全、最可靠、最佳的唯一选项。最后,对核污染水排海后的严重性与环境影响的可控性认识不足,未能全面评估核污染水排海后对生态环境系统的长期影响,也没有关于放射性核素在生物与人体内长期累积的内容,更没有后续审查与长期监测的安排。因此,无法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也就无法保证排海的实际安全性。
四是从评估方式来看,主要是基于日本单方面提供的信息、资料与数据进行评估。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未亲自取样,仅对日本自己有选择采集的少量核污染水样本开展实验室间比对分析。每个实验室仅测量25 升,而要排放的核污染水有130 多万吨。对此,有关专家指出:“无法从一个非常小的样本中提取数据,来预测超大容量的核污染水在未来几十年的走向。”①参见李曦子、李叶繁:《倾倒的恶意》,《国际金融报》2023年8月28日,第4版。而且,储存核污水的罐子很大,污染物比较浓的物质都沉淀在下面,而日本只提取了表面污水做样本。由此可见,日本取样的数量、方式等都存在问题。另外,参加此次评估的六家第三方实验室来自韩国、法国、美国、瑞士、奥地利和摩纳哥。除了韩国以外都是域外国家,并不是利益攸关方。因此,在信息准确性与数据真实性有待确定以及取样独立性与代表性不足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存在较大片面性与局限性。
五是从专家意见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虽邀请多国专家参与评估,但报告却未能充分反映所有专家意见,有关结论也未获各方专家一致认可。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曾就报告草案征求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则由秘书处决定。秘书处在收到反馈意见后,并没有再次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协商。而且,报告也未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或理事会的认可,缺乏权威性。另外,日本政府提前获得了报告草案,并提出实质性修改意见,对报告结论施加了不当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对报告结论是否客观公正的质疑。①参见钟声:《任何报告都无法“洗白”排海错误决定——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极端不负责任①》,《人民日报》2023年7月21日,第3版。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声称,福岛核电站处理水排海是日本政府的“国家决定”,证明排海的正当性属于日本责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既没有建议日本采用排海方案,也没有为日本排海方案背书,相关结论是基于日本制定的计划,并不能反映国际原子能成员国的看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国对利用这一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不承担责任。②参见刘洪亮:《违背道义责任,日本或于8 月排污入海》,《文汇报》2023 年7 月6日,第7版。这一免责声明也说明该报告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显示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污染水排海行为的保留态度。因此,该报告并不代表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批准,并不能证明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本身及其实施过程是安全的,更不代表认可在未来30 年时间内所有核污染水都能处理达标。同时,该报告也承认处理后的核污染水放射性物质的构成、对全球大气和海洋的影响、放射性物质在海洋生命体内的累积效果等都存在不确定性,并表示将建立监督机制,这恰恰证明核污染水排海的风险。③参见岳林炜、朱钥颖、林森:《日欲借IAEA 报告强推排海计划》,《环球时报》2023年7月5日,第16版。
对此,太平洋岛国提出,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国际协商不应局限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应通过《伦敦倾废公约》等平台开展磋商。④参见钟声:《强加核污染风险足见自私和傲慢——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极端不负责任②》,《人民日报》2023年7月27日,第17版。日本国内舆论也指出,该报告并不是对日本排海计划的“推荐”与“支持”,也不是许可证与挡箭牌,日本政府不应用该报告证明排海的安全性。⑤参见岳林炜、张悦、刘仲华、陈效卫:《“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只会给未来埋下祸根”》,《人民日报》2023年7月20日,第17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明确指出,该报告证明不了日本排海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安全性,保障不了监测安排的有效性。因此,不能成为日本排海的“护身符”与“通行证”。①参见李欣怡:《外交部发言人就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23年7月5日,第15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仍坚持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显然违反了上述禁止一切放射性废物向海洋处置的有关规定。因此,绿色和平组织日本事务所专家指出,日本行为首先是有违关于禁止故意向海洋环境倾倒核废料的《伦敦倾废公约》以及《1996年议定书》。日本作为上述公约和议定书的签署国,有义务履行禁止向海洋倾倒核污染水的责任。②参见马玉安:《后患无穷的自私举动》,《光明日报》2023 年6月3日,第8版。韩国阻止福岛核电站污染水排海对策委员会指出,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中禁止将放射性废物排入海洋的相关规定。③参见岳林炜、马菲、陈效卫:《“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将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人民日报》2023年7月10日,第15版。日本国内也对政府违反《伦敦倾废公约》禁止排放放射性物质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如日本《朝日新闻》社论指出,日本签署了《伦敦倾废公约》,但现在却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因此须向国际社会说明理由与今后措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众议员指出,日本是《伦敦倾废公约》的缔约国,却要违反不得向海洋排和核废料的禁令。日本参议院议员、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称,核污染水排海违反了伦敦公约有关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物质的规定。④参见张超:《日本排污入海内外皆不满》,《法制日报》2011 年4 月12 日,第10版;苏宁:《多方持续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法治日报》2023 年6 月26 日,第6版;岳林炜、李文:《示威者在福岛控诉核污染水排海》,《环球时报》2023 年8 月28 日,第2 版。
违反了关于防止海洋倾废跨界影响与损害的规定。《伦敦倾废公约》的序言指出,各缔约国有责任保证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为此,第6 条规定,缔约当事国不应允许将核废物出口到其他国家倾倒。《1996年议定书》第3条第3款规定,缔约当事国采取的行动不应使损害从环境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因此,日本负有避免跨界影响与损害的国际义务,日本在处理国内核污染水时应充分考虑对他国产生的影响,避免直接或间接将核污染水排放所造成的损害或危险转移到其他国家。
2011 年4 月日本将所谓低放射性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由于海水不断循环流动,目前已造成对其他海域的污染与损害。如2016 年加拿大在其西海岸的三文鱼身上检测到铯-134放射性元素,证明福岛核污染水已扩散到北美地区。由此可见,日本的行为已引起跨境环境损害,对其管辖之外的其他地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严重违反对防止跨境损害的国际义务。而目前日本再向海洋排放大量的核污染水,据有关模拟分析显示,核污染水七个月后到达韩国济州海域及其西海岸,三年后美国与加拿大太平洋海域将受到影响,①Ken O.Buesseler, “Opening the Floodgates at Fukushima,”August 21, 2020,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04/621.full[2023-12-12].十年后将蔓延至全球所有海域。对此,有专家明确指出,作为《伦敦倾废公约》的缔约国,日本完全漠视排污行为的跨境损害,执意作出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的决定,违反了不损害国外环境的国际法规则。②参见郭言:《日本转嫁核污染风险违反国际法》,《经济日报》2023 年7 月19 日,第3版。
但2011 年4 月东电公司在为排放所谓低放射核污染水行为进行辩解时,强调是为了给高放射核污染水腾空间,这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目前东电公司声称核污染水将达到储存罐上限的137 万吨,已无更多可利用的空地用于堆放新建的储水罐,因此向海洋排放是别无他法的唯一选择。③参见陈益彤:《日本强推“排污入海”做法极不负责》,《经济日报》2022 年7 月26日,第4版。由此可见,日本试图援引《伦敦倾废公约》的例外条款寻求免责的理由,以逃避公约的规制。但这些说法属于强词夺理,其排放行为并不符合特定紧急情况免予法律责任的条件。《伦敦倾废公约》第8条规定的“例外”包括两种情形,即由恶劣天气引起的不可抗力以及对人命或对船舶、航空器、海上平台及其他人工构筑物造成真实危险。在这两种紧急情况下,如果倾倒是防止威胁的唯一办法,找不到其他更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且倾倒造成的损失会小于其他办法的损失,则可进行不得已的倾倒。但缔约当事国在倾倒之前,应与可能受到影响的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协商,有关国际组织应向该缔约当事国建议应采取的适当程序。缔约当事国应在最大程度上遵循这些建议并向国际组织报告其行动,同时应将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
由此可见,2011 年4 月日本的排放与目前的排放都不存在由恶劣天气引起的不可抗力,也不属于不能接受的危险,因此其无权援引《伦敦倾废公约》的例外条款来主张免责。当时情况虽然紧急,但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不是排放,日本以其发达的经济与科技完全可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如建造一个大储蓄池或向人工浮岛和油轮转移、存储高放射核污染水,然后再用化学或生物等方法降解核物质的辐射性,而不是为了给高放射核污染水腾空间而去排放所谓低放射核污染水。
目前日本处理核污染水并非只有排海一个选择,以目前日均新增140吨核污染水计算,只需新建1.2 倍于现有规模的储水罐,就可存放未来30年所产生的150 多万吨核污染水。①参见冀勇:《对国际社会的正当合理关切置若罔闻,东京电力执意提交核废水排海申请》,《法治日报》2021年12月27日,第5版。而福岛核电站场址及福岛县周边地区有足够因核泄漏而闲置的空间,可向核电站外拓展用地,建设更多核污染水储存设施,这与其声称没有可存放储水罐的用地并不相符。但最后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却以需要大量时间沟通协调、工作量大为由拒绝了这一方案。除此之外,日本也曾提出地层注入、水蒸气加热释放、电解大气释放和地下掩埋等其他处置方案,而且这些方案能更有效降低污染风险。但最后这些方案都被放弃,究其原因是技术复杂、耗资与工程量庞大。如从经济角度来看,上述方案处置成本分别为180 亿日元+6.5n 亿日元(n 为选取合适地点所需尝试的次数,每次尝试花费6.5 亿日元)+监控费用、349 亿日元、1000 亿日元、2431 亿日元,而排海方案只需34亿日元。②参见胡正良、李雯雯:《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的违法性与周边国家的危机应对》,《学术交流》2022年第10期,第67—71页。由此可见,当前日本核污染水处置并不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排海,因为这是最经济也是最快速的解决方式。③Dennis Normile, “Japan Plans to Release Fukushima’s Wastewater into the Ocean,”April 13, 2021, https://www.science.org / content / article / japan-plans-release-fukushima-scontaminated-water -ocean [2023-12-12]; Alen J.Salerian, “Sample Records for Bacteria Produce Organic,”June 1, 2017, https://www.science.gov/topicpages/b/bacteria+produce+organic[2023-12-12].日本政府也承认其决策是基于便捷性和经济性,而非科学性和安全性,这表明核污染水排海并非唯一与最优选择。①参见郭冉:《从福岛核废水排海事件看国际法的现实障碍与未来走向》,《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12页。就算不得不采取排海这种办法,其在排海之前还需与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国家协商,但无论是2011年4 月的排放还是目前的排放,日本事前都没有同其他国家协商,因此并不符合第二种紧急情况。
第三,违反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的规定。《伦敦倾废公约》的序言指出,国家间应采取行动,刻不容缓,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第2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集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海洋倾废污染。第9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通过有关国际机构内协作,促进对有需要的缔约国提供帮助与支持。《1996 年议定书》序言更是明确强调了国际合作与协作的重要性,并对有关具体合作做了专门规定。
一是违反了关于事前信息通知的规定。《伦敦倾废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每一缔约当事国事前应向主管国际组织及其他缔约国报告有关情报及采用的标准、措施和要求。第4 条第3 款规定,如果缔约当事国倾倒了未列入附则1 所禁止倾倒的废物,还要报告主管国际组织。《1996 年议定书》第7 条第3 款规定,每一缔约当事国应事前向主管国际组织提供有关在内水中所倾倒物质的种类和性质的报告。另外,《伦敦倾废公约》第5条与《1996 年议定书》第8 条都强调,即使倾倒国遇到紧急情况,事前也应履行向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国家通知的义务。根据以上规定,日本在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上应向有关国家与国际组织履行事先信息通报的义务,并提供有关决策的科学数据与情报,使国际社会能够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并做好应对。
但2011年4月日本向海洋排放所谓低放射核污染水之前,并未履行信息通报的义务。后来日本才勉强承认,在排放前未及时向周边各国及国际机构进行通报。②参见李毅:《从国际法角度探析日本排放核废液入海问题》,《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2期,第40页。对此,韩国明确表示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的任何告知,因此要求日本提供相关决策的科学依据、证明资料,否则将追究其责任。俄罗斯也指出,日本公开的信息不充分,希望获得更详细的解释,并将其可能造成的威胁清清楚楚地告知有关国家。①参见张辛欣、罗沙:《日本向海洋排放核废液,中方关切》,《新华每日电讯》2011 年4 月9 日,第3 版;任虎、牛子薇:《日本核废水排海的责任:国际责任与预期违约责任》,《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57—61页。2021年4月,日本故技重演,在没有事先向周边国家通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对此,韩国明确要求日本应向周边国家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并向外界充分说明。②参见苏宁:《罔顾国内外关切,日本加快排污入海工程进度》,《法治日报》2022年7月25日,第6版。俄罗斯对日本在未提供足够官方信息的前提下做出排海决定表示担忧,希望其在相关问题上保持透明。③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Briefing by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Maria Zakharova,”April 13,2021,https://www.mid.ru/en/web/guest/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87881#28[2023-12-10].对此,日本回避关键信息问题,在周边各国及国际社会对其提出公开有关数据等要求后,日本采取在核污染水里养鱼的方式“自证清白”。
由此可见,日本排海在前,即使后来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进行了通报也只是形式上的告知,并没有实质性内容。而且,在有关事件被曝光后日本也不采取相应的补报措施,而是开脱责任,导致有关信息与数据公布不及时、不完整甚至前后矛盾。如东电公司屡有不良记录,隐瞒、虚报、漏报,而日本政府则极力包庇。日本甚至使用各种手段封锁消息,如自2011年以来,由政府牵头已召开数千场听证会讨论核污染水处理问题,但这些听证会从未向外界开放。特别是2014 年12 月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还根据《特定秘密保护法》,宣布不再接受国内外科学界调查与评估核污染水的相关数据,而由该委员会进行书面说明。④参见金莹:《日本福岛核事故五周年现状及未来挑战》,《当代世界》2016 年第10期,第53页。由此可见,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决策程序、处理过程与具体处置方案都缺乏公开性、透明性和民主性,违反了上述公约与议定书所规定的信息透明与事先告知的程序性义务。这是目前国际社会对日本最不满之处。
二是违反了关于相互协商的规定。《伦敦倾废公约》第6 条第4 款规定,缔约当事国海洋倾废程序应由各缔约国协商同意。《伦敦倾废公约》第5 条与《1996 年议定书》第8 条都规定,即便在紧急情况下,颁发倾废许可证之前,缔约当事国还应与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国家协商。而2011年4 月日本在事先未获得其他国家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便单方面向海洋处置了1 万多吨低放射核污染水,这是将国际事务内政化,严重违背了有关协商的义务。对此,韩国声称要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并要求日本应与有关国家主管部门开展更加充分的事前协商。①参见张超:《日本排污入海内外皆不满》,《法制日报》2011 年4 月12 日,第10 版。2021 年4 月,日本又在未与周边国家等利益攸关方充分事前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对此,中方指出,日本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就单方面决定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是一种极不负责的行为。俄罗斯也就日本在未与任何邻国主管部门磋商的前提下,就做出排放决议表示担忧。韩国更是明确要求日本核污染水在排海之前应征得相关国家同意,并将持续同日方进行沟通与协商。②参见冀勇:《对国际社会的正当合理关切置若罔闻,东京电力执意提交核废水排海申请》,《法治日报》2021 年12 月27 日,第5 版;王京滨、李扬、吴远泉:《日本环境外交的历史演进与决策体制——兼论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日本学刊》2022 年第3 期,第147页;岳林炜、马菲:《多方持续批评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人民日报》2022年5月24日,第17版。
三是违反了关于科技合作的规定。《伦敦倾废公约》第8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注意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协作。第9 条规定,要在训练科技人员以及提供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设备和装置等方面合作。《1996 年议定书》第13条规定,各缔约国之间以及各缔约国与有关国际组织之间要开展科技协调,并向有关国家提供支持,包括科技人员培训以及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设施、提供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和相应专门知识等帮助。据此,日本在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上有接受国际技术援助以及与其他国家开展技术合作的义务,应努力寻求有关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同时,国际上一些科技先进的国家也都曾表示愿与日本加强国际协作、分享有关经验,帮助其处置核污染水。目前,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都研制出了核污染水处理的先进装备和技术,可为日本选择其他替代方案或减少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提供技术与工艺支持。如加拿大与俄罗斯掌握了分离核污染水中氚的技术,但日本却对此视而不见。因此,积极寻求广泛的科技合作与其他更优的可替代方案,采用最有利于海洋保环的技术来妥善处理核污染水问题,才是日本的正确、明智之举。
第四,违反了关于开展海洋环评的规定。《1996 年议定书》附件2 序言要求对可考虑倾倒的废物进行评定,并对评定内容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这是确定处置方案的基础。另外,第14 条规定,评定的结果未能充分说明影响的,应对拟议方案做更多考虑。200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依据1972 年〈伦敦公约〉确定海上处置材料的适当性:放射性评估程序》,要求应严格评估标准与程序。①参见余敏友、严兴:《论IAEA 在海洋放射性废物治理中的作用与局限——聚焦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事件》,《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5期,第12页。由此可见,海洋倾废之前进行环评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2011 年4 月日本在没有任何事前环评的情况下,将所谓低放射性核污染水排放入海;2021 年4月又在没有公布海洋环评报告的情况下,再次单方面决定将核污染水向海洋排放。对此,太平洋岛国明确要求日本应执行独立可核查的科学评估,尽快提供太平洋岛国论坛科学家开展独立评估所需的数据,对核污染水排放进行全面环评。②参见岳林炜、张悦、刘仲华、陈效卫:《“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只会给未来埋下祸根”》,《人民日报》2023年7月20日,第17版。可见,日本并没有按照《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相关程序进行实质性的跨界环评,也没有公布任何对跨界环评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对于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构成了对有关国际公约义务的违反。
第五,违反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规定。《伦敦倾废公约》指出,海洋吸收及转化废物为无害物质以及使自然资源再生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因此《1996年议定书》的序言强调各缔约国应保护海洋环境并促进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养护。为了使海洋生态系统能够继续承受对海洋的合法利用并继续满足需求,必须采取新的国际行动来防止、减轻与消除倾废污染。
日本向海洋排放的核污染水中,所含的放射性元素需要很多年才能降解,不利于海洋生物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如核污染水中氚降到低风险大约需要100 年,其停留在人体内会产生持续损害遗传基因的风险。而碳-14 的半衰期为5370 年,碘-129 的半衰期则为1570 万年。①参见吴学安:《日本核污水排海对海洋环境带来不确定性风险》,《防灾博览》2023年第5期,第45页。对此,中国明确强调,日本应对全人类和子孙后代负责。②参见任虎、牛子薇:《日本核废水排海的责任:国际责任与预期违约责任》,《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57—61页。
总之,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多项规定。对此,国际社会形成了基本共识。澳大利亚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联合主席蒂尔曼·鲁夫、澳大利亚工商业领袖戴若·顾比都明确表示,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③参见岳林炜、张悦、陈效卫、刘慧:《“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所带来的危害将是全球性的”》,《人民日报》2023 年8 月10 日,第13 版;《国际社会持续反对日本推进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批评这一举动——“极其自私的算计”》,《人民日报》2021 年12 月15 日,第17版。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环境运动联合秘书长都强调,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的有关规定。④参见王慧、马菲、赵益普:《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启动核污染水排海——“日方悍然将核污染水排海是对人类未来的极大不负责”》,《人民日报》2023年8月25日,第16 版;岳林炜、张悦、刘仲华、陈效卫:《“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只会给未来埋下祸根”》,《人民日报》2023 年7 月20 日,第17 版;岳林炜、马菲、陈效卫:《“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将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人民日报》2023年7月10日,第15版。日本原子能资料信息室、日本山谷劳动者福祉会馆活动委员会也都指出,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违反了《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⑤参见岳林炜、王慧、郭梓云等:《各方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启动核污染水排海——“核污染水排海是一种暴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8月31日,第6版;岳林炜、马菲、李志伟:《国际社会持续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人民日报》2023年3月24日,第15版。
三、《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在规制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问题上的局限
尽管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的行为不同程度地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可以作为规制日本行为的国际法依据,但同时也应看到该公约及其议定书在应对此类问题上存在着规则不严密、适用局限性以及约束力度不足等缺陷。
第一,海洋倾废定义存在内涵狭窄问题,过分强调工具标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对海洋倾废概念的界定秉承了工具标准,强调倾倒是指从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将废物在海洋中故意处置,或将上述工具在海洋中故意处置,或从上述工具将废物在海床及其底土中贮藏。由此可见,该定义在海洋倾废的手段与方式上都做了限制,即强调专门借助特定的工具有意向海洋处置废物作为条件,使其管辖范畴主要限定在海上,而不包括从陆地向海洋直接排放废物的行为。这种对海洋倾废的机械界定,会将陆源污染、海洋工程污染以及海底资源勘探、开发等所产生的污染排除在海洋倾废范围之外。这会导致以下问题:一是这种工具标准会使同样来源于陆地污染源的海洋倾废和岸边排污相分离,成为两种不同的污染形式,进而人为地使海洋污染治理的法律主体、程序与方法有所不同。二是运载等工具只是便于形象解释海洋倾废的一种方式,而并非其最本质的界定。实际上,海上处置废物与岸边排污实质都是利用海洋空间及其自净能力来处理陆源废物,并不能截然分开。三是这种工具标准忽略了岸边排污对海洋造成危害的最终结果,存在避重就轻的问题。
由此可见,这种把来源相同、实质相同、处置结果相同的废物进行人为主观区分是不科学的,影响司法治理。日本关于核污染水向海洋处置方式曾考虑过两个方案:将核污染水通过油轮运到公海倾倒,或通过在岸边建设地下管道直接向海洋排放。日本最终没有选择成本更低的第一个方案,而是大费周章地在岸边建设管道来排放核污染水,在形式上排除《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对其直接适用,有以技术性手段规避法律义务与责任之嫌。①参见郭萍、喻瀚铭:《对放射性废物海洋处置国际法规范的审视与思考——以日本福岛核事故核污水处置为视角》,《学术交流》2022年第10期,第83—93页。如果单纯从字面定义来解释,按照上述工具标准,日本这种做法或将难以界定为海洋倾废行为,只能适用陆源污染的国际公约,即《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的蒙特利尔准则》。该准则于1985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虽对各国有关陆源污染控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其属于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1974 年的《防止陆源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则是区域公约,其适用范围具有明显的限定性,即仅适用于大西洋与北冰洋部分海域,这使日本钻法律空子有了可乘之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与科学界定海洋倾废的概念,对这种工具标准的狭隘定义进行修订,将对废物进行处置的海洋倾废与岸边排污这两种行为加以整合,凡是影响海洋生态环境的做法都应属于海洋倾废行为,而不要囿于以何种形式与手段进行处置,以利于对所有陆源污染进行统一规制、综合治理。
第二,海洋倾废地点存在适用范围有限问题。内海水作为海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处于有关海洋倾废国际法的管制之下,会对沿海国家与国际海域的环保问题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伦敦倾废公约》第3条规定,“海”是指除各国内水以外的所有海域。《1996年议定书》适用范围也不含内水,其第1条第7款同样规定,“海洋”是指除各国内水之外的所有其他海洋水域,显然这一规定有悖于内海水与外部水域连接及流动的自然属性。
实际上,一个国家在内海的倾废行为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污染。如日本在2011年4月将所谓低放射核污染水未经任何处理在沿岸直排入海,虽然是在其内海排放,但由于洋流的作用会对周边国家形成跨界污染。其行为并不符合《伦敦倾废公约》对倾废地点的要求,因而也就无法进行有效规制。而目前日本通过海底管道向距离核电站一公里之外的海域排放核污染水,该排放地点也属于日本的内海。①参见张鹏飞、刘训智:《国际法对日本核废水排海行为的规制及完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7日,第7版。日本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规避《伦敦倾废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对其追责,同时也是以内海为其国家主权的范围为由,回避与其他国家进行协商。
第三,某些规定存在模糊问题。《伦敦倾废公约》某些规定模糊、界限不明。如《伦敦倾废公约》附件1 第9 条、附件2 第1 条对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的规定,其中“痕量沾污物”(trace contaminants)、“大量”(significant amounts)等术语并不十分明确:究竟多大含量算“痕量”或“大量”,容易引起歧义,致使各国所制定的标准和衡量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在具体实践中难以协调,一定程度上影响公约的执行,也给责任认定增加了一定困难。
这样的模糊规定,为日本逃避有关国际责任提供了便利。如2011 年4 月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时,东电公司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核污染水的放射性浓度值,只是不断强调说这是低浓度的放射性核污染水。而据韩国监测,这些核污染水所含放射物的浓度超出日本国内法定排放标准的100 倍。①参见张辛欣、罗沙:《日本向海洋排放核废液,中方关切》,《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4月9日,第3版。日本所说的低浓度的放射性核污染水,显然不是一个准确的科学术语。日本为了安抚国际社会、逃避监管,极力宣扬其核污染水经处理后符合国际标准,甚至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并不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②Kyodo News,“Deputy PM Aso Repeats Claim That Treated Fukushima Water is Good to Drink,”April 16, 2021,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1/04/ccdf91e0cdde-aso-repeatsclaim-that-treated-fukushima-water-is-good-to-drink.html[2023-12-12].对此,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日本所说的“合格”是按照其自行订立的排放标准的一种说辞。③参见戴建华、杨楠:《日本核污水排放的国际舆论解析》,《当代世界》2021年第6期,第76页。日本认为,福岛核电站事故核污染水符合安全标准是无法可依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单方面标榜的所谓“安全性”也就不足以让国际社会信服。比如,据美国杂志证实核污染水处理后氚辐射仍会超标,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处理水中还存在其他超标的放射性物质。④Dennis Normile, “Japan Plans to Release Fukushima’s Wastewater into the Ocean,”April 13, 2021,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1/04/japan-plans-release-fukushima-scontaminated-water-ocean [2023-12-12];IAEA, “IAEA Follow-up Review of Progress Made on Management of ALPS Treated Water and the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Handling of ALPS Treated Water at TEPCO’s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Station,”April 2,2020,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20/04/review-report-020420.pdf[2023-12-12].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合作,在科学调查、实验、研究与论证的基础上,合理设置污染物含量的上、下限,完善海洋倾废及其损害的客观评定标准与程序,为衡量某种废物是否可向海洋处置提供统一的尺度,以减少有关指南的不确定性,为海洋倾废污染受害者的认定及追究污染者的责任提供科学、明确的法律依据。
第四,某些规定存在相互矛盾问题。如对于核废物在海上处置问题,《伦敦倾废公约》附件1 第6 条明确要求强放射核废物不能倾倒,而附件2第4 条则规定未列入附件1 的放射性废物可以倾倒。但强弱之分是相对的主观定义,这就为所谓弱放射核废物倾倒提供了借口。如2011年4月日本借口为了给高放射核污染水腾出存储空间,将1 万多吨所谓低放射未经任何处理的核污染水直接排放入海。上述公约自相矛盾的规定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又如《伦敦倾废公约》附件1 列出了完全禁止向海洋倾倒的污染物,而该公约科学专家组在1990 年制定的废物在海洋中倾倒综合评价程序的第l 部分虽也列出了禁止倾倒的各类污染物,但同时又强调如果对这些污染物进行预处理后,确信不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伤害则可允许倾倒,这就为那些所谓被禁止的污染物进行倾倒留下了空间。①参见樊一丹:《“伦敦倾废公约”中几个有争议问题的研讨》,《交通环保》1994年第5期,第28页。如2021年4 月,日本就声称其向海洋排放的核污染水经过处理后能达到“饮用水”的程度,并不会对海洋环境构成任何损害,其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有关法律的追责。
第五,某些规定缺少强制性。《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约束性条款较少不利阻止有关国家搭便车的行为,也不利于对违约行为进行有效惩处,从而给履约工作带来一定困扰。比如日本事先并未与周边各国及国际组织协商与通报,就擅自做出排海的决定,而且事后既没有向有关国家道歉,也没有向相关国际机构解释说明。日本如此行事跟《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在约束国家行为上的脆弱性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应引导与推动国际社会增加履约的硬性规定,有力规范与约束相关国家的行为,防范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所造成的破窗效应。
四、对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进行有效规制的几点思考
由于人类历史上的核事故如苏联切尔诺贝利与美国三里岛的核事故都是造成大气污染,而没有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这类事件,其排海及其引发的风险是个新问题,具有诸多不确定性。针对目前《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在应对日本处置核污染水问题上所暴露的局限,需对其加以重新审视。实际上,扩大《伦敦倾废公约》适用范围是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各缔约国协商会议讨论的焦点:一种观点是对现有公约进行完善、发展标准,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综合环保公约;另一种观点是重新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包括陆源污染在内的国际公约。这两种观点都体现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统一管制各国海洋倾废活动,从而使整个海洋生态环境大系统得以全面保护。①参见吕建华:《对海洋倾废概念立法修订的理性思考》,《环境保护》2011 年第12期,第39页。由于新的国际公约订立会涉及各国博弈问题,需要长时间的磋商。从立法成本、现实可行性及可操作性来看,可通过对《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有关规定进行完善,以弥补其在放射性废物海洋处置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的缺失及不足。②参见郭萍、喻瀚铭:《对放射性废物海洋处置国际法规范的审视与思考——以日本福岛核事故核污水处置为视角》,《学术交流》2022年第10期,第83—93页。因此,为了全面、有效规制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需进一步对该公约及其议定书做出有针对性的修订,全面加强履约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国的作用。
第一,正确理解与完善海洋倾废的定义。目前有关国家因对海洋倾废概念理解不同而出现歧义甚至发生争议,从而影响倾废污染的治理。因此,需要全面理解海洋倾废的本质含义,并对海洋倾废的概念进一步充实完善、统一认识。一是应重点强调海洋倾废定义中的“有意”目的。只要是有意识、有目的向海洋处置废物的行为,可以定义为海洋倾废。如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就是有意处置,理应受到《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的规制。二是应注意所有废物的来源。从海洋环保的整体角度出发,海洋倾废概念中如果不包括岸边排污等陆源污染,那么其内涵不可能完整。为此,《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的管辖范围应扩大,以便有效控制更多的污染源。因此,应将岸边排污的陆源污染行为纳入海洋倾废治理整体系统之中。三是应正确理解“倾倒”的方式。目前有学者片面强调“倾倒”的字面含义,把海洋倾废单纯理解为在海上倾倒废物。但实际上《伦敦倾废公约》在解释“dumping”(“倾倒”)的含义时使用的是“deliberate disposal”,即“有意处置、弃置”。显然,这种处置、弃置废物并非仅局限于在海上倾倒废物。因此,海洋倾废实际上包括了向海洋处置、弃置废物的各种方式,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在海上倾倒废物的行为。四是应突出倾废造成的污染结果。即依据有关废物是否造成污染与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结果来定义海洋倾废,这样岸边排污行为就可以被纳入海洋倾废治理的法规之中,避免同样来自陆地的海洋污染,只是由于排放工具与渠道的不同而造成管理体制、手段以及适用法律不同等问题,从而有利于海洋环境整体性综合治理,实现对海洋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的目标。①参见史春林:《东北亚海洋废物处置合作治理的法理依据及其完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1期,第65—66页。据此,无论是2011 年4 月日本向海洋直接排放所谓低放射核污染水,还是目前日本通过海底管道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有意行为,都可以用《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进行有效约束与规制,从而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另外,尽管日本通过管道这种陆源方式排放核污染水,试图逃避《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规制,但国际社会普遍将其建设的管道看作是《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定义中所说的海上人工建筑物,强调其仍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禁止通过海上人工建筑物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规定。日本无论如何粉饰,都改变不了其违反国际义务这一事实。②参见钟声:《日方不应为强排核污染水找“护身符”》,《人民日报》2023年7月6日,第17版。如有中国学者明确指出,《伦敦倾废公约》禁止通过海上人工构筑物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日本学者也指出,《伦敦倾废公约》禁止通过海上人工构筑物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日本作为《伦敦倾废公约》缔约国企图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明显违反了该公约有关规定。③参见柴雅欣、李云舒:《一倒了之,祸害全球》,《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 年8 月25日,第4版;岳林炜、张悦、陈效卫、刘慧:《“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所带来的危害将是全球性的”》,《人民日报》2023年8月10日,第13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反复强调,“《伦敦倾废公约》禁止通过海上人工构筑物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日方做法违背国际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禁止通过海上人工构筑物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规定。”①参见李欣怡:《外交部发言人就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23 年7 月5 日,第15 版;岳林炜、马菲、陈效卫、曹师韵:《各方持续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日本自私自利行为应该受到全人类谴责”》,《人民日报》2023 年7 月3 日,第15 版。
第二,加强对有关法律条款的解释。随着国际社会海洋倾废新问题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对《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中不完善以及与时代脱节的条文进行法律解释。比如,从立法意图与文义解释这两方面来看,即使日本通过海底管道排放核污染水也无法规避《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法律约束,仍然构成对相关国际义务的违反。一方面,从立法意图来看,《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公约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随意向海洋排放废弃物,保护海洋环境,各缔约国在加入该公约及其议定书时也是本着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目的。日本作为缔约国,不应违背《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基本意图。日本即使通过海底管道来排放核污染水,依然改变不了其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的事实,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来逃避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约束。另一方面,从文义解释来看,《伦敦倾废公约》第1 条就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促进对海洋环境污染的一切来源进行有效控制,以防止因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日本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自觉地对这一污染源进行有效控制。有效控制的方式很多,绝不能因花费最小、速度最快而一排了之。因此,日本应为其向海洋中排放核污染水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②参见戴宗翰、栾丹丹:《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的不法性及其责任追究》,《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23页。
第三,及时修订有关条款。一是为了增强有关条款的可操作性,可针对某些原则性与模糊性的条款进行细化,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二是对于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如自相矛盾等问题进行及时修订。三是对于一些建议性、劝诫性条款,改为义务性规定以及较为严格的执行条款,特别是应专门增加对拒不执行有关规定的给予警告或惩罚的条款,以加大对缔约国的约束力。
第四,加大有关条款执行力度。特别是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履约力度,从而有效规制日本的行为。
一是召集协商会议与特别会议。《伦敦倾废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每两年至少召集一次缔约国协商会议,并根据2/3 以上成员国的要求可随时召开特别会议。如针对目前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问题,可临时召开特别会议。
二是促进有关科技研究。《伦敦倾废公约》第14 条第4 款规定,应邀请适当的科学团体与各缔约国或主管国际组织协作,并就有关科技问题提供咨询意见。《1996 年议定书》第14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减轻和在切实可行时消除倾倒造成污染。如针对日本目前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问题,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可联合建立一个独立的放射性废物问题应对专家咨询工作组,从科技角度对放射性废物海洋处置危害、放射性废物海洋与陆地处置比较等方面开展研究。这样,才能对日本核污染水向海洋处置问题的安全性得出科学结论。同时,通过计算机模型建构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后污染扩散的路径、范围以及对生态环境损害与经济社会影响的程度、对人类发展与安全的潜在风险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为有关国家决策、风险管控、应急计划、公众教育等提供必要和可靠的科学依据。
三是加强全过程跟踪监测。《伦敦倾废公约》第6 条第1 款第3 项规定,若废弃物经过批准可向海洋倾倒,应记录所倾倒物质性质与数量以及倾倒的地点、时间与方法。第4 项规定,各缔约国应个别或协同对海域状况进行监测。第8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注意在监测方面协作。第9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提供监测所必需的设备和装置。《1996 年议定书》也做出了上述类似的规定。2011 年4 月,日本向海洋排放所谓低放射核污染水后,韩国就要求对其进行实地调查,俄罗斯要求在必要时对辐射情况进行检测。①参见张辛欣、罗沙:《日本向海洋排放核废液,中方关切》,《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4月9日,第3版;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Briefing by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Maria Zakharova,”April 13, 2021, https://www.mid.ru/en/web/guest/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87881#28[2023-12-12]。对此,有关国家与国际社会应不断完善联合监管程序,全面、系统加强对日本核污染水处置的全过程以及污染情况、程度、波及范围和影响后果等进行联合调查与监测,实现多角度核查与监控,而且不能任由日本单独决定,也不能听信其声称的所谓符合安全标准的单方面说辞。为此,有关国家与国际社会应成立联合调查组,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合作,对日本核污染水处置的全过程进行严密监管,同时还应邀请国际上具有权威调研资质的机构对其排放后风险进行长期监控及测评。
四是追究环境损害赔(补)偿责任。《1996 年议定书》第3 条第2 款规定,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缔约当事国应充分考虑公众利益,努力推行由倾倒者承担防止与控制污染费用的做法。第15 条规定,缔约当事国应按照有关对损害他国环境的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原则,承诺制定有关倾废所产生的赔偿责任程序,即当事人及其国家政府应支付因其倾废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及净化环境恢复原状所需的成本。因此,鉴于目前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会对周边国家、区域甚至全球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危害,日本东电公司及日本政府负有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受损国家未来可向日本提出索赔请求。对此,有关国家与国际社会应尽快形成一套完整的海洋倾废生态损失赔(补)偿机制。如可设立有关专项基金,使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合理的赔(补)偿,并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
五是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伦敦倾废公约》第10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制定明确责任以及解决因海洋倾废引起争端的程序。第11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制定因解释及适用本公约引起争端的程序。《1996 年议定书》第16 条规定,有关解释或应用本议定书所引起的争端,应通过谈判、调停、调解,或以争端各方能够接受的其他和平方式解决。另外,也可使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7 条第1 款中所列的程序,即通过国际海洋法庭、国际法院、仲裁庭与特别仲裁庭,或使用本公约附件3 中所列的仲裁程序解决争端。
由此可见,《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为解决日本处置核污染水所引发的国际纠纷提供了多种方式。首先,继续以外交手段谴责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的行为,对其排放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等问题进行批驳。其次,有关各方加强对话与谈判。基于国家主权平等与利益平衡原则,广泛开展国际对话与协商谈判,促使相关各方尽快达成共识,降低解决争端的成本。比如,对于当前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所引发的国际纠纷,有关国家可通过深入交换意见,商讨共同解决办法,尽量降低对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的危害,并为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资金保证与设备供应。再次,在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框架内提起动议。比如,有关国家可将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的争端提请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讨论与审议,做出相应的处理决议。最后,寻求国际司法救济。比如,针对当前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问题,韩国正着手搜集证据,将日本起诉至国际法院,或向国际海洋法庭申请临时措施及提起诉讼。①Thomson Reuters, “South Korea Court Fight over Japan’s Plan to Release Contaminated Fukushima Water,”April 14, 2021, https://www.cbc.ca/news/world/fukushimanuclear-water-1.5986603 [2023-12-12];Reuters, “Korea Aims to Fight Japan’s Fukushima Decision at World Tribunal,”April 14,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koreas-moon-seeks-international-litigation-over-japans-fukushima-water-decision [2023-12-12].因此,有关国家可联合起来对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的争端提起司法诉讼或仲裁,请国际司法机构做出法律咨询意见、申请仲裁或临时禁令。另外,受损的个人、企业等也可联合组成代表团,或请求国家代位求偿,或共同委托、授权一个实力雄厚的第三方专业权威机构代表当事人在本国或日本提起民事诉讼,为受害者进行调查取证、司法鉴定以及提出损失赔(补)偿。
第五,注意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在执行与完善过程中,应注意与其他国际法原则、条约规定以及国际判例等相协调,彼此互为补充,从而为海洋倾废治理建立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以便对日本目前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问题进行多重规制。比如,针对日本通报不及时的问题,除了适用有关海洋倾废国际公约的报告制度,也可运用《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对其进行规制。实际上,目前《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有关报告制度基本上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则具体要求一国核事故污染发生后,应将该事故及其性质、发生时间和确切地点等具体内容立即通知那些受影响的国家和机构,并尽可能迅速响应受影响的缔约国关于提供进一步情报和进行协商的请求,以尽量减少相关影响。
第六,充分做好应对之策,加强国际合作。中国有1.84 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作为日本近邻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后的直接受害国。根据清华大学有关模拟研究,日本核污染水在排入海洋240 日后会到达中国沿海。①参见郭萍、喻瀚铭:《对放射性废物海洋处置国际法规范的审视与思考——以日本福岛核事故核污水处置为视角》,《学术交流》2022年第10期,第83—93页。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应加强与国际社会共同采取措施防范应对。一方面,运用《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对日本进行驳斥。另一方面,制定科学的预警与应急预案。中国应根据《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的相关条款,做好防范与评估,及时启动风险预警与监测机制,加大索赔证据的收集力度并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为将来联合其他受害国追究日本法律责任提供基础,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益。
总之,2011 年4 月日本向海洋处置所谓低放射性核污染水以及目前向海洋排放大量的核污染水的行为,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同时该公约及其议定书在规制日本有关行为方面也存在法律漏洞与不足,影响约束力度与效果,使日本有可乘之机。为此,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有针对性地完善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有关条款,并加强法律解释与履约工作,为全面、有效规制日本行为提供有力的国际法保障,共同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