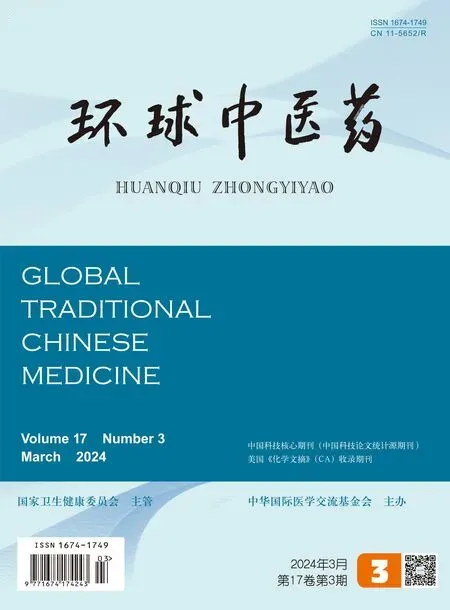探讨“主客浑受”理论在痛风慢性期中的应用
于汶仟 洑晓哲 刘媛媛 胡洁 田楚箫 任怡宣 梁素文 傅强
“痛风”病名最早见于朱丹溪《格致余论·痛风》:“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或卧当风,寒凉外搏……”该病在中医理论中通常归属为“白虎历节病”或“痹证”[1],多由外感风寒湿邪或饮食内伤所引起。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痛风发病率也明显上升,2019年我国痛风患病人数与1990年患病人数相比,变化率为175.6%[2],越来越多的人被痛风带来的疼痛及并发症所困扰。中医治疗痛风多从湿热论治,但很多痛风慢性期患者仅从湿热论治效果不显,且临床发现这类患者多存在体型消瘦、舌干裂等阴虚现象,这是由于病人素体阴虚或病程较长,湿热伤及肝肾之阴所致。
纵观历代医家学术思想,温病学派最注重祛湿与养阴并重,且近来“主客交”及其演化理论在疑难重症中的临床应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有学者[3]基于“主客交”理论探讨同样具有皮肤发热、关节病变最终累及多器官特点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中医病机及治疗,亦有基于“主客浑受”理论论治肺纤维化者[4],皆为病程较长且缠绵不愈之疑难病。而本文通过分析“主客交”与“主客浑受”之不同,发现薛雪在“主客交”基础上提出的“主客浑受”理论与痛风慢性期病机更为切合。笔者试通过探寻“主客浑受”理论与痛风慢性期之契合度,探讨运用薛氏三甲散治疗痛风慢性期的新思路。
1 “主客浑受”理论渊源及内涵
1.1 “主客浑受”理论起源于“主客交”理论
吴又可在《温疫论·主客交》中提出:“凡人向有他病尪羸……此际稍感疫气,医家病家,见其谷食暴绝……遂投参、术、归、地、茯神、枣仁之类,愈进愈危。知者稍以疫法治之,发热减半,不时得睡,谷食稍进,但数脉不去,肢体时疼……盖但知其伏邪已溃……不知正气衰微,不能脱出表邪,留而不去,因与血脉合而为一,结为痼疾也”,明确表示了素有他病而素体正虚之人感受疫气后原病加重,若医以杂药频试,或补、或泻、或滋、或散、或疏、或守,虽里证可去,然正气衰微不可托表邪而出,故邪气与血脉结合而为痼疾。其后又言:“客邪胶固于血脉,主客交浑,最难得解”,其意为此外感之疫邪与素虚之血脉胶结,即主客交浑于血脉,最难治疗。这一论述则体现了正虚邪实,主客相搏的发病思想[5],而其理论源于《素问·评热病论篇》“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等论述中,可见吴又可基于当时的疾病特点将古代理论进行了理论创新,并据此首创三甲散,而薛雪则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发挥,提出“主客浑受”理论。
“主客浑受”一词首见于薛雪《湿热病篇》第34条原文:“湿热证,七八日,口不渴,声不出,与饮食亦不却,默默不语,神识昏迷,进辛开凉泄,芳香逐秽,俱不效,此邪入厥阴,主客浑受。宜仿吴又可三甲散,醉地鳖虫、醋炒鳖甲、土炒穿山甲、生僵蚕、柴胡、桃仁泥等味。”析其释评可知,通过三组症状,即“口不渴”“与饮食亦不却”“辛开凉泄,芳香逐秽,俱不效”得知此病非阳明热盛上蒸心包、非腑实熏蒸心包、亦非热闭或痰蒙心包之证,实乃由于湿热“先伤阳分”,日久及阴,而致阴阳两困,气血呆滞,继而深入厥阴,灵机不运所致神情呆顿的表现,并仿吴又可而创后世所谓“薛氏三甲散”,强调引邪从阴出阳,活运气血。“主客浑受”其意为久留之湿热之邪与素体正虚之营血相混而成络脉凝瘀的病理状态。
1.2 “主客浑受”与“主客交”的区别
对比之下,薛雪在吴又可“主客交”基础上对其理论加以深入及扩展,提出“主客浑受”理论,将湿热日久之病位定于厥阴,认为“主”为人体之正气,不仅是血脉,更是人体正常气、血、津、液,“客”亦不仅为湿热之邪,更包括其所产生之痰饮、瘀血、结石等病理产物。有现代学者指出[6]“主客浑受”理论与“主客交”有两点最大不同,第一是对其“主”之差异:“主客交”为素有他疾而至身体羸弱,或久疟,或内伤瘀血,或吐血等,而“主客浑受”患者乃本病之因致虚,即“太阴内伤”,此亦为痛风慢性期患者病之根本;第二是“主客浑受”之“客”实为复合之邪,其中既有湿热所转化的热邪,又有病变过程中所形成之瘀血,其与《温疫论》“主客交”中所感之疫邪明显不同,而此更合痛风慢性期病理产物,于此两点,本文选用“主客浑受”而非“主客交”进行研究。
2 “主客浑受”理论切合痛风慢性期病机
2.1 脾虚酿生湿热,湿热耗伤肝肾之阴
“主客浑受”理论与痛风慢性期病因、病性切合,痛风慢性期患者病性虚实夹杂,具体表现为脾虚酿生湿热,进而导致肝肾阴虚,这与“主客浑受”理论相符。痛风是单钠尿酸盐沉积于关节及其临近关节囊、滑囊、软骨或皮下等部位引发的急慢性炎症和组织损伤,在临床上多见关节处红肿热痛或痛风石,甚者累积肾脏病变。现代医学将本病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原发性痛风病因不明,认为多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常与肥胖、糖脂代谢紊乱、高血压病、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等聚集发生。继发性痛风主要发生在肾脏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其他疾病过程中,或因服用某些药物以及肿瘤放疗、化疗等原因所致。对于痛风的早期阶段——高尿酸血症的病因之一则是嘌呤摄入过多,而研究表明食用高嘌呤食物包括红肉、海鲜等[7]确实对痛风的发生存在一定影响[8]。在中医理论中这些高嘌呤食物及导致肥胖、糖脂代谢紊乱等食物均可归属为“肥甘厚味”之品,过食肥甘厚味则易酿生痰湿,湿浊困脾,导致太阴脾虚,进一步影响脾之运化功能,或素体脾虚,脾胃运化失司则脾不升清、胃不降浊,故而湿浊中阻不化,郁久化热而为湿热,热为阳邪易耗阴血,湿为阴邪但其性粘滞,与热相结后更不易祛除,病情进入慢性期后最终导致肝肾之阴受损。《素问·六节脏象论篇》中有云“肾者……其充在骨”“肝者……其充在筋”,此“筋”则包括肌腱、韧带和筋膜,朱永涛等[9]通过现代超声技术发现痛风慢性期患者常有骨侵蚀、滑膜增生及双轨征等现象,也是痛风慢性期病人肝肾阴伤的体现。
“主客浑受”乃正虚与邪实胶结,其正虚者,太阴脾虚则为首发,正如薛雪在《湿热病篇》第1条原文自注中所说:“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素有太阴脾虚之人,水液运化失职,体内易留湿饮,若正值热邪相扰,则引热邪合化而为湿热。董锡玑[6]指出主客浑受之“正虚”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其人太阴素虚,二是湿热之邪郁久,既有其化热化燥,深入营血,灼伤肝肾之阴,又有部分湿热尚未尽化而继伤阳气,导致阴阳俱虚,正合痛风慢性期病因所致病性演变。
2.2 浊瘀互结于厥阴血分,日久累及全身
“主客浑受”理论与痛风慢性期的病位、病势及病理产物亦有相同,具体体现在二者均为湿浊、瘀血两种病理产物互结于厥阴血分,病情进一步进展可由局部累及全身终至饮食不进、神昏而亡。痛风慢性期患者脾虚运化失常,湿浊郁久而成湿热,有研究表明[10]高尿酸血症患者的实性性质状态要素中湿、痰、热状态要素居前三位,因此笔者认为尿酸可理解为“湿浊”,即食物消化过程中的代谢产物,若其不能及时排出,湿浊郁而化热,湿热之邪日久则入营血之分,深伏于藏血之脏,煎熬厥阴血分之阴津,则血液粘滞,血行受阻,故成瘀血,瘀血之形成又阻滞气机导致气滞,进而影响身体多处血运,日后发展为痛风肾、肾衰、尿毒症危及生命。此外,国医大师朱良春[11]主张痛风不应与“痹证”混为一谈,并独创性提出“浊瘀痹”,认为痛风乃湿浊与血结为浊瘀,滞于经脉,引起骨节肿痛,更直接指出痛风的病理产物为湿浊与瘀血。
薛雪在“主客浑受”条文后自注:“暑热先伤阳分,然病久不解,必及于阴。阴阳两困,气钝血滞而暑湿不得外泄,遂深入厥阴,络脉凝瘀”,可知湿热之邪伤人后,阴阳两困,气钝血滞,日久入于厥阴,其病位在于血脉[12],于是出现原文中“与饮食亦不却,默默不语,神识昏迷”,此之切合,不再赘余。
综上所述,痛风慢性期患者由脾胃虚弱,生湿内郁为湿热深伏厥阴血分,湿热与“人体正气”之血脉胶结难解,损耗肝肾之阴,浊瘀留滞于关节则引起疼痛,其“主”为太阴素虚,久及肝肾之阴,导致素体营血之阴受损,其“客”为浊瘀互结,二者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及病理产物高度符合,由此可得出“主客浑受”理论与痛风慢性期的病机相符合。
3 薛氏三甲散为“主客浑受”理论之代表方
“主客浑受”的主要机理在于本虚标实,其患者湿热之邪深入营血,内陷厥阴,损耗肝肾之阴,薛雪在《湿热病篇》对应条文后提出“仿吴又可三甲散”(即薛氏三甲散),其方中鳖甲、土鳖虫、穿山甲、柴胡、桃仁、僵蚕,攻补兼施,引热出表,祛瘀通络而护阴,正如许益斋所校释“鳖甲入厥阴,用柴胡引之,俾阴中之邪尽达于表;土鳖虫入血,用桃仁引之,俾血分之邪尽泄于下;山甲入络,用僵蚕引之,俾络中之邪亦经风化而散”。诸药合用,既可透阴分之热,又可逐血分之瘀,使湿热瘀邪与人体血脉剥离,正复邪祛,病得自愈。
4 薛氏三甲散组方思路适合痛风慢性期
薛氏三甲散内外合治,表里兼顾,在表可分别借鳖甲、柴胡、僵蚕领搜风之药入厥阴,经少阳,出太阳,使湿热经风而散,从表而解;在里可使浊瘀借桃仁润肠通腑之势从下而出,正适用于痛风慢性期邪伏厥阴,浊瘀互结之机,若能取法化裁、辨证加减则可为临床指导治疗痛风慢性期患者提供新方案。
4.1 入络脉,使内外之邪经风而散
痛风日久肝肾阴虚而生热,皮肤腠理疏松易受外邪尤其是风热侵袭,临床发现夏季很多患者因感受风热之邪而发作,方中山甲性善走窜而活血散结、搜风通络,血和则荣卫通畅,旧血得去新血自生,筋骨关节得以濡养;僵蚕气味俱薄,能入太阳肤表,祛外风而散风热,发散邪热兼以燥湿,引络中之湿从风胜之,血中之热从风散之,其消痰除癥、化痰散结之力相比同类草木药作用更强,另外,现代药理学研究[13]发现僵蚕可以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对于疼痛类疾病有治疗作用,对于痛风慢性期患者因外感而急性发作者多有良效。
4.2 入厥阴,滋肝肾阴而引邪出表
痛风慢性期湿热挟瘀,日久伤阴,若肝肾之阴充足则骨骼健壮,不易被侵蚀,筋膜濡润不易磨损。国医大师吕仁和[14]治疗痛风预防复发便提倡从肝论治,注重清利肝胆湿热、补益肝肾、疏肝健脾等,而方中鳖甲入厥阴搜邪热而护阴,柴胡引厥阴之郁热从少阳之枢转而达外更与此暗合,且从温病角度“引热外达”给人以启发。此外,前文提到痛风患者多由脾虚起病,土生金,金克木,脾土虚弱则肝木易旺,为减轻脾虚之势,抑制肝木过旺从厥阴入手亦十分必要,施今墨便常用“柴胡、黄芩”药对清泄肝胆之热,以缓肝木克土之势。临床中亦有运用鳖甲、银花“透热轻清,引邪出表”配伍滋肾阴、解热毒治疗痛风的成功案例[15],充分说明从厥阴出表论治痛风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鳖甲在《本草备要》中记载“补阴退热,咸平属阴,色青入肝”,且咸能入肾,软坚除癥,既补肝肾之阴,又有助于消除痰瘀互结之癥瘕。若患者有身体消瘦,夜间盗汗,腰膝酸软,舌红,苔少而裂,脉细数等典型肝肾阴虚表现,则可选择芍药、当归等入厥阴肝经之药以顾护阴血,亦可加入枸杞子、女贞子及旱莲草等滋补肝肾之阴,肝肾之阴充足则可濡润四肢关节,正气不虚,邪则不凑。
4.3 入血分,祛瘀通腑使邪出于下
痛风慢性期之浊瘀互结易成痛风石,且慢性痛风性关节炎常从浊瘀论治[16],对于久病之治,叶天士云:“久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通逐邪,”唐容川亦在《本草问答》中指出“动物之攻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之性,本能行而又具攻性。”因此,擅长运用三甲散加减治疗痰热与瘀血胶结之证的名中医郭贞卿[17]认为临床上用一般草木对症之药无效、或效不确切者,均可选加同类昆虫动物类药使用。薛雪方中土鳖虫入厥阴血分,逐瘀通络,且土鳖虫常潜伏在山野的树根烂草之中,昼伏夜出,正合痛风夜间加重之势;桃仁气薄味厚,可假阳明之路逐瘀下行。此外,“非辛香无以入络”(《临证指南医案·卷八疝》),辛味能行气活血,咸味能软坚散结,在痰瘀胶结之证中,以辛佐咸,既攻顽结,又畅气血,既利于痰浊排除,又益于气机恢复。于此,郭贞卿有两种方法:一是配伍以辛香之药,如香附、桂心、枳壳等,二是通过炮制手段使之具备辛香之味,如炒香枳壳、酒炒地鳖、土炒穿山甲。对于关节僵硬、变形的患者,吕仁和[18]亦常选用炮山甲、炙僵蚕、白芥子、皂角刺以化痰祛瘀散结,而名家常用之酒炒地鳖、土炒穿山甲、炙僵蚕等都是薛氏三甲散中的组成药物,可见“主客浑受”理论亦适用于痛风之瘀血证。
痛风多由湿热而起,对于体内湿热较盛患者不能只顾阴虚而不除湿热,湿热两邪所出异路:于热邪,前文提到方中鳖甲、柴胡可透热于外;于湿邪,则可考虑配伍利湿泄浊之药,使其由二便而出。现代研究表明一些清热利湿和通腑泄浊药如萆薢[19]、土茯苓[20]、虎杖[21]、金钱草、威灵仙等有很好的降尿酸作用。赵进喜[22]治疗痛风就曾提出分消湿热法,常用萆薢、土茯苓、虎杖、金钱草等代表药使湿邪从二便而出,临床证明确有疗效。证明“主客浑受”治疗痛风从大、小便而下之思路临床可行。亦有临床报道[23]采用发汗利小便之法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疗效确切者,认为使“热浊”之邪从汗孔、尿窍而去,则关节自得通利。
5 小结
痛风慢性期患者病情反复发作,正邪胶固、缠绵难解,中西医治疗周期均较长,是临床难治之病,在其病程中正虚邪实常同时存在,医者应根据虚实之不同表现辨证加减。笔者认为“主客浑受”理论以其脾虚为先,湿热伤阴,浊瘀互结,虚实夹杂的独特病机正合痛风慢性期病机,而薛氏三甲散以其“引邪外达、通下,兼顾补虚”的组方特色与治疗痛风慢性期极为相符,但其代表方更适用于痛风慢性期邪盛为主者,邪去之后还应重视顾护脾胃正气及肝肾之阴。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还应抓准正虚与邪实之间的关系,动态把握观察,邪实重者宜多通,正虚重者宜多补,重视“主客浑受”的临床意义,攻补兼施,以减缓疾病进展,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