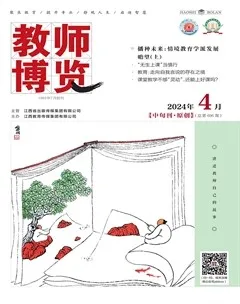漫游诗词话汉唐
刘梅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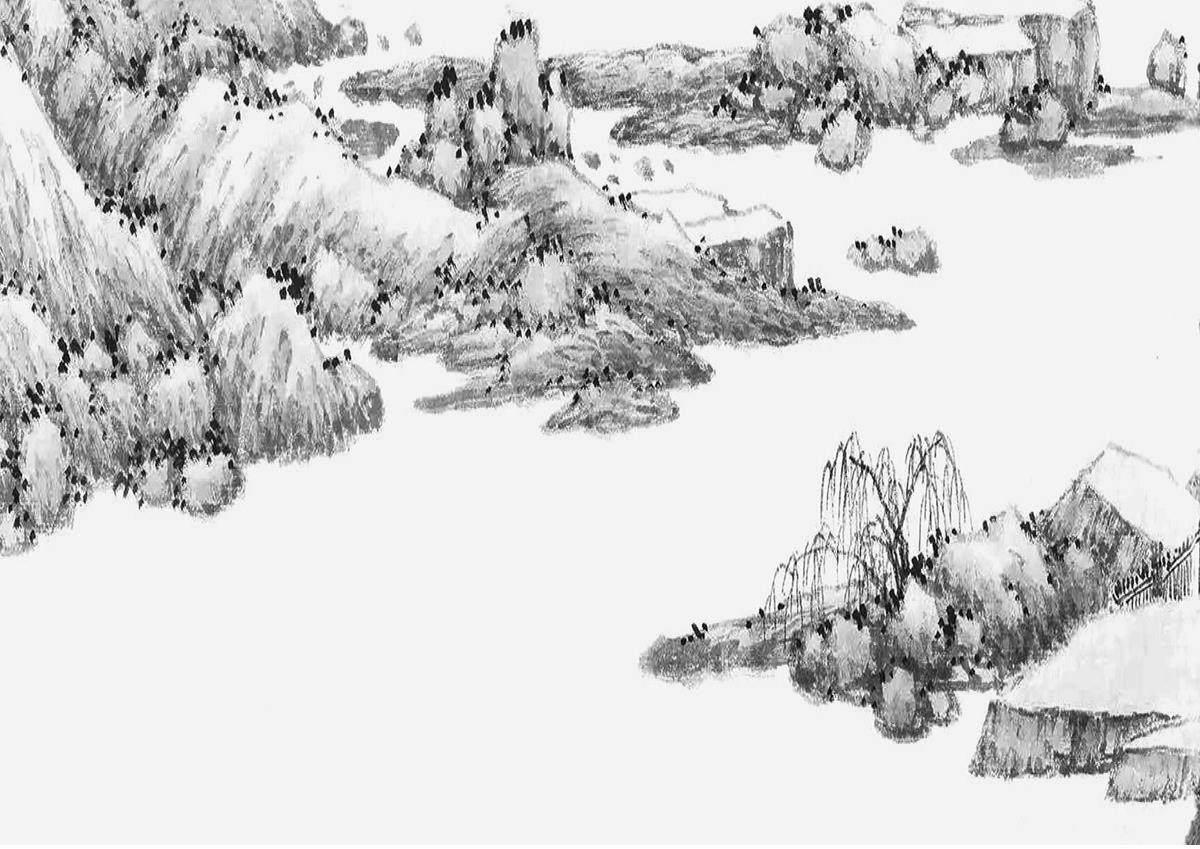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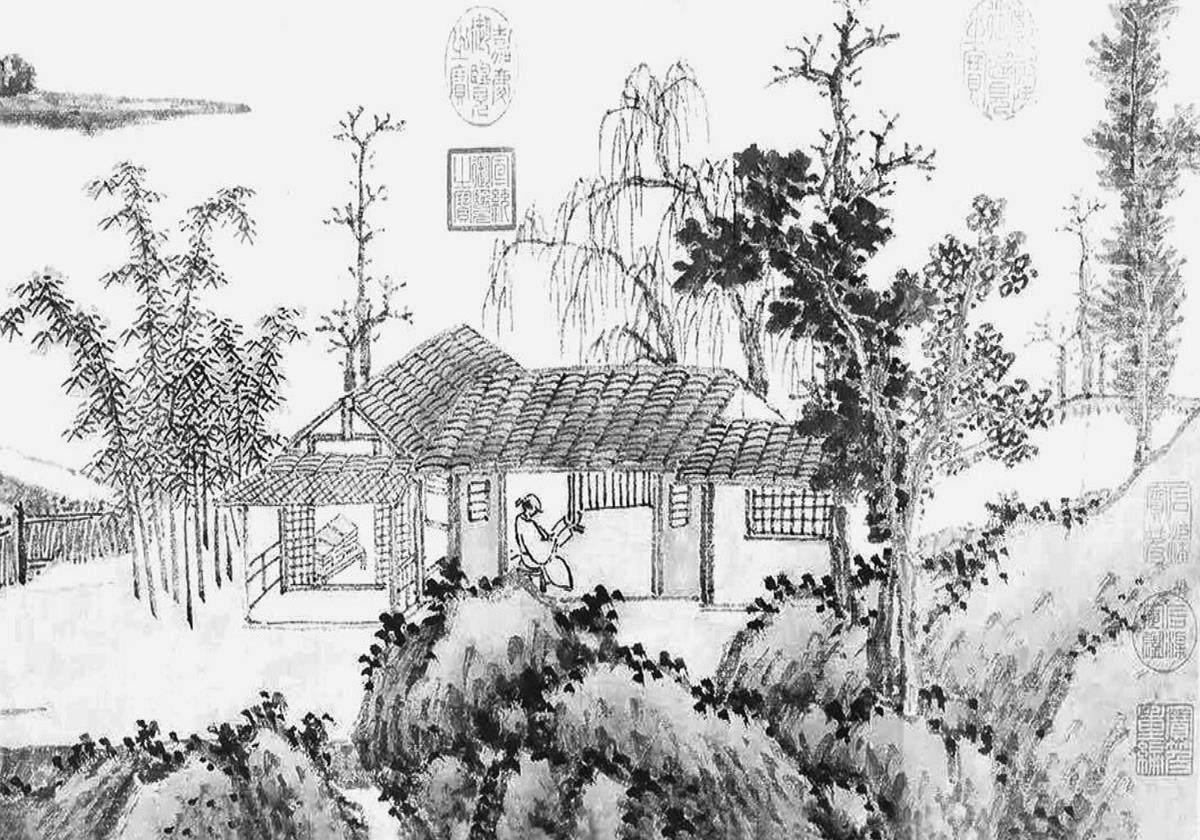

漫游古韵,我最爱这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生活在遥远东晋的王羲之,在千年以前便有了穿越古今的时空观照意识。人生代代无穷,趣舍万殊,静躁不同,但后人看待今人,一如今人看待前人。书圣感慨系之,寓悲叹于觥筹,于美景,寄予的是对生活的热诚思考。这份思考,今日我等视之,感同身受。
然悲喜同根,今之视昔,非独有“悲夫”一种慨叹。“悲”是给予“喜”的一种积极逆向的思考,所谓居安思危者便是其中的一种。今日漫游古诗词,领略笔墨情韵,其间亦有喜焉,亦需喜焉。比如唐人诗文,常见他们对古人古语态度之诚、回首之勤、践行之切。
历朝历代皆有热爱回首之人,唐代亦如是。在唐人抚今追昔的踪迹里,汉朝尤为受宠。我们从诗词中可窥见一斑。“汉皇重色思倾国”“秦时明月汉时关”“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汉家大将西出师”……
游历恢宏的唐诗王国,随意摘取几首诗来,我们便可以看到“汉皇”“汉关”“汉家”“汉将”等有关“汉”的词眼,而且这些“汉”词随着唐朝的发展在诗歌中不断“衍化”“繁殖”。汉家优雅曼妙的姿态在唐诗中随处可见,一如热恋中的人儿,一路依偎携行,又如传统中国的才子佳人相伴相生。唐朝的墨客才子们借助他们对古韵的热忱,高调地向世人表达着他们对汉朝真挚的敬意,这份浓厚且真切的“恋汉”情结在诗歌里一目了然。
“恋汉”,连诗仙李白也曾卷入这样的潮流。且看“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清平调·其二》),“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苏武》),“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塞下曲六首·其六》),等等。李白身在唐朝心在汉,诗仙笔尖热腾腾的仙气也不免要为“汉家”的地气让道。这份热忱不是“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恣意挥毫,更像千家万户对偶像时代的追崇,诗仙仅是泱泱大军里的一员。
自西汉建立到唐王开国,跨越时空八百多年。八百多年的光辉岁月,弹指一挥间,汉皇汉将乃至汉砖汉瓦不曾想到,他们会被八百多年之后唐王朝的一群妙笔生花的士子惦念。正所谓距离产生美,抑或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不妨跨越这两个朝代,去寻找其间的趣味。
膜拜者里不乏忠实的“铁粉”。“楚王云梦泽,汉帝长杨宫。岂若因农暇,阅武出 嵩。”此诗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汉武大帝的艳羡之情。在大唐,以皇帝为标杆,自上而下,对大汉钟情者比比皆是。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曾专门为汉皇写下溢美之词《汉武帝杂歌三首》:“汉武好神仙,黄金作台与天近。”“武皇南面曙欲分,从空下来玉杯冷。”“汉天子,观风自南国。浮舟大江屹不前,蛟龙索斗风波黑。春秋方壮雄武才,弯弧叱浪连山开。”诸多诗例,不一而足。有人说唐诗中的“汉皇”实指唐玄宗,究竟如何姑且不论,而韦诗中显而易见是一位文韬武略的汉武帝向我们走来。
当然,唐诗中不仅汉皇成了红人,汉朝的美人们更为唐诗增姿添色。比如李白笔下的赵飞燕:“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再有杜甫笔下的王昭君:“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她们一度成为诗人们争相吟咏的对象。就连“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北方佳人李夫人,也博得了大诗人白居易的青睐,为她专门写诗:“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白居易感怀李夫人的同时,也为汉皇增设了一丝儿女情长。其实,白居易对于汉皇的情感是复杂的,《长恨歌》开篇便是“汉皇重色思倾国”,给汉皇定下了沉湎声色的人设,也可以理解为暗讽唐明皇的曲笔。汉皇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唐诗中褒贬不一。清朝学者赵翼有评“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廿二史札记》),就是对汉皇文采的褒赞了。
唐诗里的汉人不仅是颜值担当,更是武艺高强。在唐詩中,汉朝的一批骁勇善战的人“复活”了。李广将军在王昌龄的笔下雄姿英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勇猛无敌的李广成为边塞诗人高适心中的慰藉:“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昔日驰骋沙场征战的将士们,走入唐诗,依旧神采不减当年——“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王维《老将行》)。走入唐诗的,除了汉朝的武官,还有文官,西汉的贾谊就是典范——“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李商隐《贾生》)。“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相比武官的勇猛威武,以文官入诗显得格调低沉了许多。相比盛唐诗人追崇汉时的勇武,晚唐诗人对汉朝文人则有惺惺相惜之意。
不仅是汉代将领入了诗,谦虚而好学的唐人还流连于汉朝的宫城古迹,就连汉代著名的“玉门关”“玉塞”也成了边塞诗的重要意象。如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又如白居易《长恨歌》中“太液芙蓉未央柳”的“太液池”“未央宫”,也源自汉朝的名称。
汉朝对于唐朝是一段过往的烟尘,但唐王朝自上而下将这段历史视域中的美人、沙场都照进了现实。唐太宗李世民曾语出良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借用这句话,似乎可以很好地揣摩唐人追随汉朝的意图。所以诗至晚唐,走过盛世的唐人们尤为追念远去的大汉图景。
以汉写唐式的“膜拜”,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追崇,其最高境界是精神的膜拜。唐王朝自上而下都有这样的格调。遥想汉室王朝,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艺术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文景之治”奠定治国根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思想新主流,“丝绸之路”更是开创朝代新格局。思想的兴盛,文学的恢宏,疆界的扩大……对于八百多年之后的唐王朝,无一不是闪耀在历史天空之中的璀璨之星。
仰观宇宙之大,唐朝之前的历史何其浩瀚。常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何唐王朝不尊夏、不尊秦?唐人言语里,隋的影子就很少。探其根本,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膜拜”不是单纯的膜拜,膜拜者也应有膜拜的“资本”。对唐人来说,高调的“恋汉”情结,正因为二者的实力相当,彼此志同道合,亦能镜照自我。
“恋汉”,巧借汉代,使得唐代诗人心中激荡着的英雄之气与万丈豪情得以喷发,让汉王朝盛世景观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得以重现,文人墨客们意欲表达自己身为唐朝人的骄傲与自信,这也为他们的浪漫情怀找到了言说的出口。“汉家飞将下天来,马棰一挥门洞开。”(《平蔡州三首·其一》)唐朝名将李愬攻蔡州擒叛贼,在刘禹锡的笔下化身为汉家自天而下的神人,身怀开天辟地之力,恰恰体现的是大唐王朝自上而下的强烈自信。
汉代国力强盛、幅员辽阔,其繁华鼎盛令后世士人为之向往。以汉代唐,镜照自我在于,朝代兴衰更替是一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唐诗中巧借汉人、汉事来发表对唐代统治者昏庸无能或者对统治者的举措失当的不满。不能直言,便以汉为典,曲意表达,这种诗歌含蓄蕴藉一说是诗歌研究最通俗的阐释。
唐人言汉事,是今之视昔,从中洞见的是跨越时空的大唐自信;我们读唐诗,亦是今之视昔,从圆融恢宏的汉唐美景里观赏了历史的轨迹。探其根源,可以说是唐诗成就了汉家风情,也可以说是汉家气概成就了唐人风貌。历史已然是历史,只是诗歌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洋溢着生命的热情,代代无穷式传承、吟唱,从而汇聚成为今人口耳相传的经典。在河流的两岸,汉唐不惧时光,相依相偎,一路欢腾。
(作者单位:安徽省庐江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