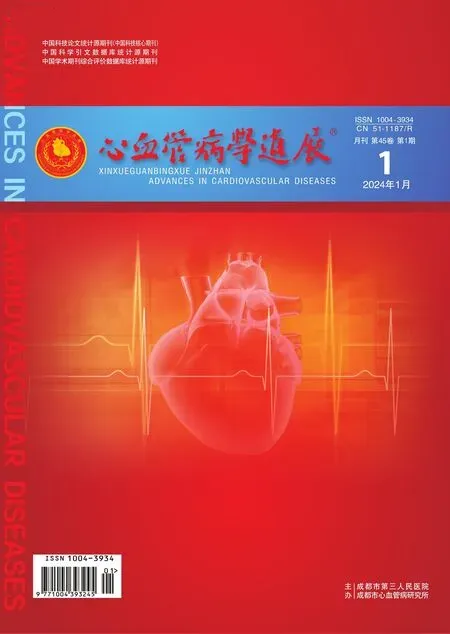房间隔缺损相关肺动脉高压机制及治疗进展
李思聪 罗勤 赵智慧 赵青 柳志红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北京 100037)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是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先天性疾病相关PH被归类动脉型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中。不同于其他亚型PAH进行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在CHD-PAH患者的病程中可观察到肺血管从早期可逆到后期不可逆病变发展的全过程,这有助于研究PAH独特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并有机会对患者进行早期干预,实现PAH的临床治愈。房间隔缺损(atrial septal defect, ASD)是常见的CHD,占所有CHD患者的8%~10%[1]。相似缺损大小的ASD患者的PAH严重程度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这突出了PAH发展的动态性和病因学的多样性,提示除了分流之外,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等在ASD-PAH的形成中同样重要。现围绕ASD-PAH的发展过程和危险因素对ASD-PAH的发生机制进行总结。
1 肺血管重塑的病理生理学
根据血流动力学特点,CHD-PAH分为动力型和阻力型。(1)动力型PAH期:患者存在PAH,但肺血管尚未发生严重病变,关闭缺损之后肺动脉压可降至正常。(2)阻力型PAH期:肺血管已发生不可逆病变,关闭缺损后,患者肺动脉压不能降至正常或反而升高,出现术后持续PAH[2]。动力型向阻力型的转变也意味着肺血管系统从可逆到不可逆的转化。
1.1 早期
流量增加结合可能导致压力增加的危险因素使肺血管系统发生血流扰动,血管内皮细胞所受剪切应力增加,一系列对流量敏感的基因上调[3]。早期生长反应因子-1是重要的核转录因子,可通过激活参与血管损伤的基因在内皮细胞中的表达以响应流体剪切应力[4]。血流扰动还能诱导p53表达上调,使内皮细胞迁移减少,并出现动脉内膜修复缺陷[5]。内皮细胞首先发生增殖和形态学改变,表现为动脉内膜的增厚,早期PAH以腺泡内动脉的弹性蛋白碎片为特征[6]。
1.2 可逆向不可逆病变的转化
持续的高流量和压力破坏了血管内皮屏障功能,导致血管弹性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激活、细胞外基质降解以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1释放,促进平滑肌细胞肥大和增殖以及新生内膜形成[7]。
凋亡与抗凋亡失调是PAH发展的重要一环,剪切应力的刺激不足以直接引起细胞增殖,细胞凋亡过程可诱导抗凋亡的发生,造成内皮细胞增殖。促凋亡基因p53在早期受剪切应力刺激表达上调,并在内膜病变过程中持续表达[5,8]。而抗凋亡蛋白B细胞淋巴瘤-2仅在来自严重内膜纤维化动脉的内皮细胞的不可逆性PAH中表达[8]。
炎症和血栓形成是通过内皮损伤后血小板和白细胞的黏附、活化以及凝血途径的二次激活而发生的。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弹性蛋白酶、肿瘤坏死因子-α、γ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1β参与新生内膜形成的增殖反应[9-10]。内皮损伤致血小板聚集能力增强以及促凝物质分泌增多,使肺小动脉内更易形成原位血栓,造成肺血管床容量显著减少[11]。
1.3 不可逆病变的形成
内膜重塑会破坏管腔表面,进一步扰乱局部血流,导致重塑的内膜层上再次发生血流扰动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纤维化新生内膜层的形成和管腔闭塞。自局部远端小动脉起始的变化将逐渐影响整个肺动脉血管床的结构和功能,最明显的变化是分支复杂性降低、外周肺小动脉闭塞、丛状病变以及继发于丛状病变的动脉扩张性病变[3]。
不可逆性PAH的典型病理表现为丛状病变和同心性内膜纤维化。丛状病变更频繁地发生在从大血管发出的侧支血管中,而纤维化往往会影响外周分支[12]。同心性的闭塞病变并不孤立出现,而是存在于丛状病变的近端。这提示丛状病变可能并不是静态的现象,而可能继续转变为由内皮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组成的管腔内同心状阻塞的紧密网络,代表了从动脉分支的近端开始并向远端发展的中间过程[13]。
2 ASD患者中PAH形成的其他危险因素
尽管存在相似的缺损大小,但ASD患者的PAH严重程度可能会有很大个体差异。此外,不同于室间隔缺损等三尖瓣后分流造成的高压与高流量状态,ASD分流引起的剪切应力增高往往不足以造成肺动脉压的显著升高,很少有发展成不可逆性肺血管疾病的趋势,这提示某些ASD患者可能合并其他危险因素才会最终发展成PAH。
2.1 低氧状态
生活在中高海拔地区的儿童孤立性ASD-PH的发病率为9.7%,高于低海拔地区(2%左右)[14-15]。低氧状态下,肺内动脉因肺泡缺氧而收缩,将血液转移到氧合较好的肺段,从而优化通气/灌注匹配和全身供氧[16]。然而,人类肺血管对肺泡缺氧的反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外膜成纤维细胞分化、特定血管平滑肌表型的存在与否、血管活性介质的上调或下调、氧敏感转录因子的剪接变体、生长因子的上调、Ca2+的致敏和Rho/Rho激酶信号级联反应都可能在血管对缺氧的反应程度中发挥作用[17-18]。因此,目前很难阐明低氧对ASD患者发生PAH的贡献。
2.2 唐氏综合征
PH与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 DS)患者死亡率升高相关,尤其是CHD患者。一项纳入 1 252例儿童的回顾性队列研究[19]确定DS儿童PH的发生率为28%,与无CHD的患者相比,患有CHD的DS患者后续发展为PAH甚至艾森曼格综合征的风险也显著高于其他CHD患者。DS患者易发生PH的原因可能与肺泡和肺血管发育受损、肺血管顺应性较低、内皮素-1水平升高等因素相关[20-22]。
2.3 基因突变
有遗传学研究[23]已鉴定出11个已知的PAH风险基因,遗传因素在CHD的发病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已知PAH致病基因在CHD的背景下出现突变,往往会导致与分流量并不相符的严重PAH。尤其是小ASD,其分流量不足以解释肺动脉压升高的严重程度。而引起心脏发育异常的基因突变通常影响多个器官结构的发育,因此患者常表现为一个综合征而不是单纯的心脏畸形,尽管并发PAH较为罕见,仍有一些病例报告描述了这种情况。
2.3.1 携带已知PAH致病基因的ASD患者
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receptor,BMPR)可识别并与骨形态发生蛋白结合。骨形态发生蛋白是TGF-β超家族的一类重要成员,在生物体中具有多种功能,包括细胞生长、分化、凋亡以及骨、软骨和其他组织的形成和修复。肺动脉平滑肌细胞中的BMPR2突变将导致对TGF-β的异常生长反应[24]。病理学检查已证实携带BMPR2突变的肺部比无突变的肺部具有更明显的内膜重塑[25]。Liu等[26]报道患有PAH的CHD患者的BMPR2突变率为7.2%,显著高于无PAH的CHD患者(1.2%)。此外,由于TGF-β信号转导对心脏发育和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PAH患者中突变携带者的右心室功能也比非突变携带者受到更严重的影响[27]。Du等[28]发现BMPR2通过DNA结合抑制因子和USP9X发出信号以驱动心脏分化,DNA结合抑制因子1和DNA结合抑制因子3表达的缺失导致BMPR2突变的CHD-PAH患者的心肌细胞功能障碍。异常细胞信号通路和血流动力学超负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促进肺血管病变的快速进展,将导致分流不明显的ASD患者出现严重的PAH[29]。
SOX17是在发育过程中广泛表达的转录因子保守SOX家族成员,在心脏发育、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中起核心作用[30]。在一项近期的研究[23]中,SOX17被确定为一种新的CHD-PAH候选风险基因,SOX17的变异参与了约3.2%的CHD-PAH病例。进一步观察发现,SOX17的有害变异在发育中的心脏和肺血管系统中高度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研究中儿童患者的大多数先天性心脏缺陷是单一的(ASD占比为33.8%),但多数患有严重的PAH,伴有右心室肥大和功能不全[23]。
TBX4基因编码的TBX4蛋白是基因编码转录因子T-box家族的成员,在四肢和呼吸系统的发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在PAH队列研究中发现,与成人患者相比,儿童TBX4突变的富集显著;与BMPR2突变携带者相比,TBX2携带者的平均发病年龄更小[31]。Zhu等[23]在256例CHD-PAH患者组成的队列研究中发现7例发病年龄<28 d~11岁的患者存在TBX4变异。
2.3.2 携带CHD相关基因的PAH患者
细丝蛋白A(filamin A,FLNa)是一种在体内广泛表达的交联蛋白,可将肌动蛋白交联成三维网络,后者在细胞迁移、形状变化以及应对潜在破坏性机械应力等方面发挥作用[32]。在与FLNa突变相关的多种疾病中,大多数患者都患有肺部疾病,例如肺炎和呼吸衰竭[33]。ASD、动脉导管未闭、PH、瓣膜病和动脉扩张都与FLNa突变相关[34]。Deng等[35]报道了1例患有小ASD的8个月患儿表现出快速进展的PAH,伴有明显的心力衰竭和低氧血症。该研究报道19例FLNa突变患者表现为早发PAH,其中6例患者出现发育迟缓,而所有患者均出现CHD。这提示FLNa突变患者的心脏畸形和肺部发育缺陷可能共同导致了PAH的发生。
位于2号染色体上的NKX2-5基因突变与ASD相关,患者通常还伴有传导功能障碍、心肌病、复杂冠心病和心源性猝死等症状[36]。Rozqie等[37]报道了东南亚人群中ASD患者的一种新的杂合NKX2-5变异,这种变异可能导致家族性ASD并发心律失常和严重PH。
ASD合并基因突变的患者往往病情进展较快,并发生与缺损大小和分流程度不相符的严重PAH。因此建议对于该类患者尤其是年龄较小者进行全面的基因检测,并考虑肺移植等更积极的治疗。
3 ASD-PAH患者的治疗策略
根据《2022 ESC/ERS肺动脉高压诊治指南》[38],将CHD-PAH分为以下4类:艾森曼格综合征、体肺分流相关的PAH、伴有小缺损/巧合缺损的PAH与缺损矫正后PAH。《2020 ESC成人先天性心脏病管理指南》[39]建议对于有右心室容量超负荷证据且无PAH或左心室疾病的患者,无论症状和年龄如何,均进行ASD封堵。对于非侵入性检查提示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建议行侵入性检查测量肺血管阻力(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PVR)以进行早期干预[39]。
对于与普遍的体肺分流相关的PAH患者的治疗依然证据不足。目前推荐PVR<5 WU的ASD患者,当存在明显的左向右分流时(即肺循环血流量与体循环血流量之比>1.5)可考虑关闭缺损[39]。对于PVR≥5 WU的患者,封堵后发生术后PAH的概率高,预后不良[40]。
对于PVR≥5 WU的患者,当靶向PAH治疗后PVR降至5 WU以下且存在显著的左向右分流时,可考虑行开窗ASD封堵[39]。修复治疗策略可能使某些初次就诊时被诊断为不可纠正的ASD患者获益。靶向药物已被证明可改善PAH患者血流动力学状态和降低死亡风险,在CHD患者中也同样适用[41]。然而,随着药物治疗后PVR的降低,分流的增加可能加剧右心室容量超负荷并加重肺血管重塑。在药物治疗后进行经导管开窗封堵术可能为患者带来良好的短期预后,且与药物的联合治疗表现出互补的优势,对PAH靶向药物治疗有反应且PVR降低和左向右分流增加的患者尤其如此[42-43]。开窗封堵术在缓慢减少分流、降低右心容量负荷的同时避免了因关闭缺损造成的血流动力学的剧烈变化。然而目前对该类患者进行治疗的证据等级较低,仍缺乏治疗后的长期随访研究。
艾森曼格综合征患者不适合接受封堵术,因为此时患者的心输出量取决于PVR显著升高情况下的分流。小ASD也无关闭缺损的指征。伴有微小缺损的PAH患者15年存活率为66%,而特发性PAH的15年存活率为38%[44]。小缺损可能允许晚期肺循环向体循环分流,减缓心输出量的进行性减少,对预后产生有利影响,这可能解释了这类患者与特发性PAH患者相比存活率更高的原因。
4 小结
ASD患者的左向右分流导致肺血流量增加是发生PAH的先决条件,通过凋亡、炎症和血小板激活等多种途径最终从动力型PAH转变为阻力型PAH。一些ASD患者的分流大小并不足以解释PAH的严重程度,他们的发病可能还与自身存在的PH相关的危险因素有关。ASD-PAH患者接受封堵与否主要取决于PVR的大小和分流的方向,近年来靶向药物的发展带来了修复治疗策略的兴起,能让原本无法进行手术的患者接受更积极的治疗,但仍需更大规模的长期随访研究来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