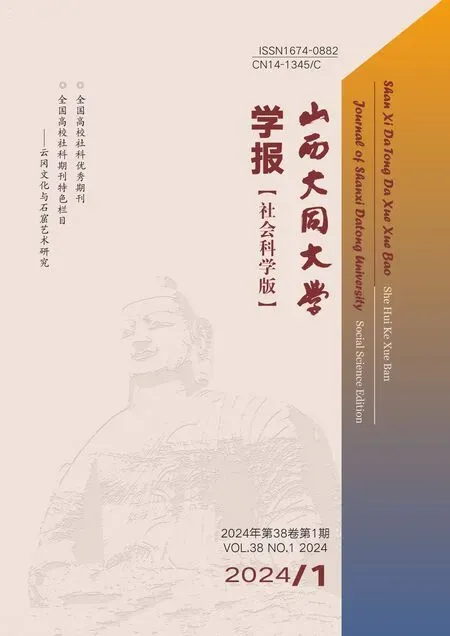强制管理制度的历史演进
史沛尧,樊新红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强制管理制度的近现代源起
普鲁士的强制管理制度最开始适用对象仅限于世袭财产以及不可转移给他人的财产,不过在后来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强制管理制度也可适用于一般不动产的强制执行,于是将强制管理视为是一般的执行方法之一。[1](P468)
1877 年《德国民事诉讼法》未规定强制管理制度。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在法律领域为了结束之前混乱无序的状态,统治者在原先各联邦既有立法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普鲁士作为该帝国中举足轻重的大联邦,其法律文化自然对德意志帝国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1877 年颁布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未将强制管理的相关规定囊括在内,在“对不动产的强制执行”一节中仅对执行法院的管辖权做了规定,同时规定具体的程序参见州法,[2](P42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并未有统一的房地产法律,[3](P1)在之后统一民法规定时,立法者决定通过制定专门法律的方式来规定强制拍卖和强制管理制度。[4](P187)
1897 年,《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颁布,《德国民事诉讼法》也加入了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另以法律规定之。可以说,《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第一次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强制管理制度做出系统而全面的规定。该法于1997年和2007年进行了两次修订,现行《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共三章,186 条,对强制管理的启动条件、效力等各项基本内容,以及管理人制度、收益的分配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并未将强制管理视作是强制拍卖或登记保全抵押的补充执行措施,而是赋予债权人在三种执行措施中任意选择的权利。既为债权人在不同情形下选择不同执行措施以实现债权提供了便利,也因强制管理不改变被执行标的所有权的特点,兼顾了债务人的利益。此外。修改后的《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已将强制管理制度的适用对象扩展至船舶这一特殊动产①,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以下简称《执行法草案》)在构建强制管理制度时,其适用对象仍仅限于不动产是否合理,值得深思。
同为大陆法系且构建了近代部门法体系的法国是否存在强制管理制度,尚不可考。就目前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而言,未见有学者将强制管理与法国法关联在一起,在对强制管理制度的比较法研究中也未论及法国法。
二、英国委任接管人制度
在英国,并没有强制管理制度一说,但由于在英国委任接管人制度中,接管人的职责在于妥善保管被接管的财产,收取孳息以清偿债务及执行所需的费用,且与强制管理一样不改变被执行标的的所有权,因此有学者认为,英国的委任接管人制度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强制管理。[5](P388)
1873年《司法法》颁布之前,英国的强制执行方法是与“令状”制度紧密相连的,主要包括向法院申请押记令、扣押收入令、第三方债务令等,而在众多令状之中并未提及“接管”或与之相关的执行方法。
随着《司法法》的颁布,英国国会开始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各项执行方法。在英国民事执行改革前,高等法院和郡法院的执行方法各不相同,《高等法院规则》第30 章“接管人”及第51 章“接管”,对委托接管人制度作了规定,[6](P24)同时,《1981 年最高法院法》第37 条和《1984 年郡法院法》第338 条、第107条赋予了法院委任管理人的权力。于民事执行改革后颁布的《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在第29次修订中增补了第69 章“法院委任接管人的权力”,统一了高等法院和郡法院委任接管人的程序。[5](P388)
与德国强制管理制度不同的是,英国的委任接管人制度不仅出现较晚,而且现在已经很少使用,因为“高等法院及郡法院只有在其他执行方法不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委托接管人”,[5](P388)甚至有英国法官表示,他没有碰到过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只有在执行债务人与其他人共有的抵押房屋租金收益、即将到期的租金、不宜用第三方债务令执行的债权及人寿保险等财产时才会用到。[6](P211)
可见,强制管理制度并非为大陆法系国家所独有,英国有委任接管人制度,在美国也存在财产的“接管”制度,且其适用范围极广。
三、日本强制管理制度的引入
日本明治政府于1890 年制定了《日本民事诉讼法》,该法是日本最早的近代民事诉讼法典,该部法典以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因此,与德国法一样将强制执行的相关内容规定在其中(该法第六编为“强制执行”)。而与德国法不同的是,日本民诉法在立法之初就对强制管理制度做了明确规定,[7](P298)即标志着这项发端于欧洲大陆的民事执行制度,以成文法典的形式传入到亚洲国家。
总体而言,《日本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对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承袭,因此存在大量“水土不服”的地方,1926 年日本政府对该法第一编至第五编的内容做了全面修订,而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日本政府对《日本民事诉讼法》第六编强制执行部分进行修订的计划被迫中断,[8]强制管理制度也因此未进一步加以完善。
此后,因日本立法者认为,“民法的抵押权等担保物权的实施程序不同于强制执行,应当由民法的附属法令来进行规定,遂于1898年制定了《日本拍卖法》”,[9](P8)二者共同构成了“旧”日本民事执行法体系。但这种将强制执行法归于民诉法典之一部分的做法遭到了学者的质疑,一种观点认为:就强制执行的性质而言,是非讼事件,而民事诉讼则是诉讼事件,二者性质不同,当然不能合并于同一法典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重在确定权利义务,而强制执行则重在权利义务的实行,二者关系不同,因此不能并为一法。[10](P215)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理由不同,但结论一致,即认为将来立法应将强制执行法从民诉法中分离出来,单独立为一个法典。顺应这种理论观点,1979 年日本制定了《日本民事执行法》,将《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所涉强制执行相关规定与《日本拍卖法》相统一,使强制执行制度体系更为合理。该法第三目为“强制管理”,延续并发展了《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强制管理的相关规定。
通过梳理日本对强制管理制度的引入和发展,可见直接“照搬照抄”他国法律规定的做法不可取。
四、我国初遇强制管理制度
(一)清末修律的确立 作为民事强制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强制管理从清末改制开始,随着近代诉讼法律体系的建立被引入我国。该项制度在我国最早现于清政府聘请日本学者松冈义正起草的《强制执行律草案》中,该草案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于不动产之强制执行依左列(下列)方法为之:一、强制拍卖;二、强制管理。债权者得声请并用前项所揭之方法。”该草案从第二百八十五条至第三百一十八条详细规定了强制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该草案对管理人制度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人的选任、职责、报酬、解职等内容,是对当时德国、日本管理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部草案虽然由于清朝的灭亡而未能正式颁行,但却为以后历届政府编纂更加完善的强制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的发展 北洋政府因循旧制,基本沿用了前清所修订之法律,对强制管理制度亦有保留。袁世凯上台后,于1914 年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开始制定其他法律法规。同年7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不动产执行规则》,该项规则虽仅有41条,但专设“管理”一章,对强制管理制度加以规定,同时,为补其不足,各省审判厅也自行拟订了与执行相关的各种章程、办法等。[11](P17)1920 年,为方便执行工作的进行,各省单独制定的执行规则、章程或办法被全部废止,另行颁布了《民事诉讼执行规则》,其中,在“不动产执行”一章中规定有“对于不动产之强制执行,以查封、拍卖、管理之方法行之”,[12](P324)至于该法律文本为何改“强制管理”为“管理”,精确原因不得而知,但回溯1914 年《不动产执行规则》,该规则就已有用“拍卖”“管理”代“强制拍卖”“强制管理”之做法,笔者猜测,可能是立法者力求用语精简所致②。但如松冈义正之言:“因系不动产,故言强制,以别于动产。”[10](P223)可以说这一时期删去“强制”二字的做法有失偏颇。
之后,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尝试构建中国完整的近现代法律体系。在对《民事诉讼执行规则》部分内容加以修正后,国民政府令准援用,并于1933 年颁布《补定民事执行办法》以使其更为完备。1933 年,基于“强制执行案件,往往经年累月,拖延不结,债权人既蒙损失,社会经济亦受影响”[12](P11)之原因,民法委员会开始起草《强制执行法》,并于1940年颁布施行。这部法律文本承袭北洋政府1920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执行规则》并融合了1933年出台的《补订民事执行办法》,仍将强制管理制度囊括其中,其七十五条规定:“不动产之强制执行,以查封、拍卖、强制管理之方法行之。”九十五条规定:“前条未拍定之不动产,债权人不愿承受时,应命强制管理。在管理中,依债权人或债务人声请得减价或另估价拍卖。”
(三)我国台湾地区的延续 我国台湾地区沿用了1940 年由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强制执行法”,而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变迁,该法自然无法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同时,为能应对数量激增的执行案件,实现迅速终结强制执行的目的,确保民众权益,[13](P19-23)我国台湾地区对该法律文本进行了多次修正。修正后的强制管理制度在管理人的选任上既不同于德国仅限于自然人,也不同于日本仅限于法人,而是对管理人的主体资格几乎不作限制(原则上不允许债务人担任管理人)。同时,在第五次修正时删除了“经二次减价拍卖而未拍定不动产应命强制管理,及再减价拍卖或另行估价拍卖”的规定,[13](P23)这是我国台湾地区对强制管理制度所做的一次调整与完善。强制管理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民事执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五、新中国对强制管理制度的再引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的规定,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均被废除,[14]强制管理制度也随之消失于正式的法律文本之中。虽然,沈阳市人民法院于1951年颁布的《民事执行暂行办法》中第八条③、1951 年的《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加强民事强制执行的指示》以及乌鲁木齐市人民法院于1952 年制定的《民事案件执行试行办法》均做出类似强制管理的相关规定,但其规定都较为笼统,无法构成系统的“强制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也步入了新的阶段。在执行领域,为应对财产种类的多样化,同时在执行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即应逐步调整落后的执行措施。而在1991 年《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执行实践中对查封财产的变价主要还是通过变卖方式进行,[15](P143)没有任何关于强制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过,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2条有关于“交付申请中执行人管理”的规定④,且可视作是强制管理制度在我国的又一次萌芽。2015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2 条(2021 年修订后的第490 条)除增加了不可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条件外,基本沿用了上述关于“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的规定。此外,于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5 条第2 款中提到的“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中所指的“其他执行措施”,在实务中多被解释为包含强制管理措施。⑤
事实上,自2000 年起至2022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以下简称《民事强执法草案》)在内,共八稿执行法草案均包含了对强制管理制度的专门规定。此次《民事强执法草案)》于第二编第九章,自第133—135 条分别规定了强制管理的适用情形、管理人制度和强制管理收益的使用。此次草案的出台可以视作是强制管理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回归”。
起源于普鲁士的强制管理制度,其适用对象由最开始仅限于世袭财产以及不可转移给他人的财产逐步适用于一般不动产,在近些年有了进一步扩张的趋势。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强制管理制度适用对象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将船舶、航空器纳入其中,以及是否应当将该项制度应用于更广泛的财产权利之中。2021 年7 月1 日《奥地利执行法》迎来重大革新,将强制管理制度的适用范围由传统的不动产扩张至对动产、存款等资金、债权等一切财产权利的执行。[16]此番改革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司法制度的革新与发展的表现之一。奥地利执行法的此次修订时间较晚,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等科技的飞速发展,法院的工作方式也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发生了重大革新,此种革新即为民事执行强制管理制度适用对象的扩张提供了可能。此前有学者认为,船舶或航空器只有在航行时才有收益的可能,但船舶或航空器航行时,执行法院难予控制,故查封后原则上即不准航行。“从而,关于船舶或航空器之强制执行,本法虽无禁止之明文,但依其性质,原则上仍以不准用关于强制管理之规定为宜。”[13](P405)现今有发达的全球定位系统,此种风险便可依科学技术有效规避,则对船舶、航空器适用强制管理制度并无不妥。强制管理制度适用对象范围的扩张俨然已成为该项制度在日后修改完善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此外,强制管理人的选任规定也随着强制管理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演进而异。其差别主要在于是否认可由债权人或债务人即与执行标的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担任管理人。日本学者板倉松太郎认为,强制管理人不适宜由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担任,应当由与执行案件无利害关系且通晓相关业务的案外第三人来担任,[17](P836)若由债权人或债务人担任管理人可能会存在管理不适当、恶意处分执行标的等不利于强制管理进行的行为发生。而《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第150b 条(1)的规定:“在农业土地、林业土地和园艺业土地的强制管理中,须指定债务人为管理人。”允许由债务人担任管理人,如此可省去管理人报酬等费用以及选任其他主体作为管理人而花费的时间,且由直接利害关系人担任管理人存在的弊端大多可以通过加强法院监管以避免。因此不应完全排除选任债权人、债务人等作为管理人的可能。同时,管理人应否仅限于自然人或限于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德国强制管理人条例》第1 条第2 款的规定:“强制管理人应是一个有业务能力的自然人,其资质和现有的办公设备能够保证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可见,在德国法上,强制管理人仅限于自然人;日本则恰好与之相反,依《日本民事执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执行法院于强制管理开始裁定应同时选任管理人。信托公司、银行其他法人,得为管理人。”在日本民事执行强制管理制度中,管理人不得为自然人。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抑或非法人组织,在管理人选任时应注重管理人的专业性,以期实现管理收益的最大化的目标。
最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管理制度都要求管理人提供管理账目,这一方面有利于法院、各方当事人了解具体的管理情况,同时也为法院行使监督权提供了条件。管理人的此项义务是民事执行强制管理制度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一环。
纵观强制管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这项执行措施随着近代民事执行法律体系的建立而不断发展完善并延续至今,在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执行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民事强执法草案》的发布标志着该项制度正式“回归”。但若对比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立法例,《民事强执法草案》仅有三条规定,不足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执行措施。对此,需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同时回应科学技术进步、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充实我国强制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以期发挥该项制度的真正作用,应对实践中的迫切需要。
注释
①参见《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第165条之(2)。
②根据1933 年《补订民事执行办法》第十七条:“执行处得依声请或职权,对于应拍卖之不动产,同时命行强制管理,或先命管理而后拍卖。”之规定,可知“管理”即为“强制管理”,并无二致。
③《沈阳市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暂行办法》第八条:“本院在执行时,得斟酌具体情况,使债务人继续经营其生产事业,以其生产品其所得利润陆续还债,或采取其他管理财产、收益等适当方法以其所得还债。”
④该条规定:“被执行人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的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
⑤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执复117号执行裁定书;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09执复15号执行裁定书;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5 执复85 号执行裁定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鄂执复175 号执行裁定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