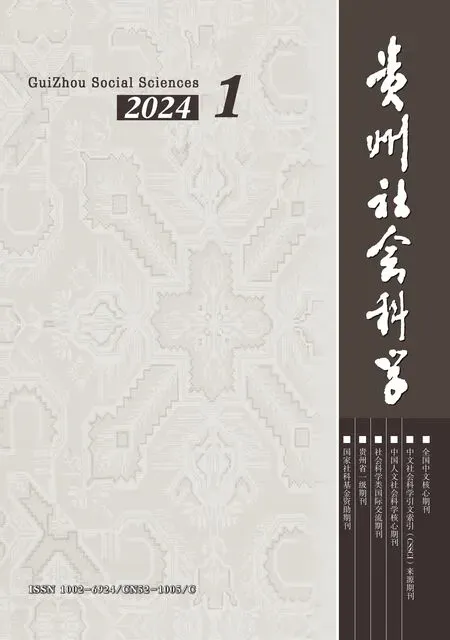唐合川郡界守捉的设置与名称书写变化
李新贵 杨 浣
(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一、引 言
贞观九年(635年),唐朝为平定吐谷浑所设置的合川郡界守捉(今青海化隆县德加乡附近)。该守捉名称书写的演变,恰好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对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的认知变化。由于合川郡界守捉从一开始就不在唐朝平定吐谷浑战役计划内,遂具有了临时设置的特点。这未体现在现存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反而对其名称有着不同的记载。《通典》曰:“合川郡界守捉,西平郡南180里,贞观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元和郡县图志》(简称《元和志》)省略“界”字:“合川郡守捉,(鄯)州南一百八十里,贞观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合川郡,今叠州。” 《旧唐书·地理志》(《旧志》)《资治通鉴》(《通鉴》)《新唐书·地理志》(《新志》)则省略“郡界”两字,分别记载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管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兵千人”、“(鄯州)南百八十里有合川守捉城”。无论合川郡界守捉名称如何变化,其位于西平郡即鄯州南一百八十里的位置是相同的。所以,唐末、五代、宋初的文献所记载的这个守捉是一个地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通典》《元和志》所载该守捉设置者是侯君集,设置时间是贞观(627—649年)中,后者还补充了“合川郡,今叠州”的内容。这段时期侯君集率部西渡黄河至鄯州,只有贞观九年这一次。《旧志》《新志》《通鉴》则将设置者、设置时间省略了。
前贤依据前引文献,一致认为合川守捉是唯一正确的名称。唐长孺先生沿袭《新唐书·兵志》“合川守捉”之名。⑥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同样称“合川守捉”,⑦当依《旧志》《新志》或《通鉴》所作推论。王永兴先生认为贞观九年侯君集率兵征战,所经乌海、星宿川、柏海皆在鄯州及九曲西南,而叠州合川郡(今甘肃迭部)与侯君集所经之地相距甚远,遂断言侯君集不可能在此设守捉城,鄯州西南180里的合川守捉与叠州合川郡无关,进而认定《通典》“合川郡界守捉”之“郡界”为衍文,《元和志》“合川郡守捉”之“郡”也是如此。⑧严耕望先生也持此说。⑨李智信先生认为合川郡在侯君集设置合川郡界守捉时称叠州,该州改名是天宝元年(742年)左右,与合川郡界守捉无任何关系。⑩
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两组。一、沿袭《新唐书》《旧志》或《通鉴》中的称谓,称“合川守捉”。二、合川郡界守捉之名与叠州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称之为“合川守捉”。这两组观点都注意到了合川郡界守捉名称的变化,却忽略了所处位置未曾变化的特点,因而未细致解读这些文献所记该守捉内容的差异,也未将这些差异纳入唐末至宋初时人对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认知变化视野中分析。而对唐平吐谷浑之役的记述,虽然注意到了贞观九年正月党项之乱,但未深入分析此次偶然事件对唐平吐谷浑之役造成的深刻影响,自然不能深入研究其间复杂曲折的情况与合川郡界守捉设置之间的关系。
二、唐军平定吐谷浑之役与侯君集部行军路线分析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八年十二月辛丑(634年12月28日)条详细记载了唐军在平定吐谷浑战役准备阶段,参战唐军各部的作战目标、战术、行军路线。“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
李靖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指向西海道(西海道以西海郡为名,该郡治今青海湖西吐谷浑伏俟城),侯君集也从长安出发西指向积石道(积石道以积石山为名,积石山今青海兴海西阿尼玛卿山),李道宗同样从长安出发西至鄯善道(鄯善道以鄯善郡为名,鄯善郡治在今新疆若羌),李道彦从岷州都督府(治今甘肃岷县)出发西向赤水城(今青海兴海东),高甑生从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出发西北至盐池(今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池),李大亮从凉州都督府(治今甘肃武威)出发西至且末道(且末道以且末郡为名,该郡治在今新疆且末)。从此可以看出,以李靖为主帅的唐军主要作战目标,是攻击吐谷浑之都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石尕亥乡铁卜加村西南)。为达成此目标,唐军实行了围歼战术,即李道宗、李大亮两部分别从鄯善、且末两道东进以防止吐谷浑西逃,侯君集、李道彦两部分别从积石道、赤水城西进以防止吐谷浑东出,高甑生部北上开赴盐池以防止吐谷浑南走。 这里明确说明从长安开赴吐谷浑战场的途中,兵部尚书侯君集担任的是积石道行军总管,《新唐书·侯君集传》记载亦同:“李靖讨吐谷浑,以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册府元龟》则不同。“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贞观九年,将讨吐谷浑伏乞(允),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总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并为之副。师次鄯州,君集言于靖曰:‘大军已至,贼虏尚未走险。宜简精锐,长驱疾进,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潜遁必远,山障为阻,讨之实难’。靖然其计。乃简精锐,轻赍深入。道宗追及伏乞(允)之众于库山,破之。伏乞(允)轻兵入碛,以避官军。靖乃中分士马为两道并入。靖与薛万均、李大亮趣北路,使君集、道宗趣南路,历破罗真谷,愈汉哭山,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轻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师,与李靖会于大非川,平吐谷浑而还。”
此时侯君集是主帅李靖的副手。《旧唐书·侯君集传》亦同:“时将讨吐谷浑伏允,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并为之副”。这可能意味着战前准备阶段侯君集是以积石道行军总管一职作战,后来战役进行阶段由于受到某种原因的影响,不得不改变原来指向积石道的行军路线,因而侯君集职务也从积石道行军总管转变为李靖副手。至此,可以看出平定吐谷浑之役中侯君集先后所任职务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新唐书·侯君集传》《资治通鉴》所记积石道行军总管,另外一个是《旧唐书·侯君集传》《册府元龟》所载作为李靖副手。《新唐书》书写具有“事增于前,文省于后”的特点,《资治通鉴》所记当受《新唐书》的影响。《旧唐书》“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这与《册府元龟》不纯取正史而直取实录、国史、诏敕章奏、诸司吏牍等原始史料,直接构成一脉相承的书写体系。因而,这两个系统关于侯君集所任职务之记载都是正确的,分别反映的是战前准备、战役进行两个阶段的实际情况。
贞观九年三月,鄯州会议后的战术、参战部队、行军路线都与之前不同,可资证明。这年闰四月癸酉(5月29日),李道宗部趁机击败库山(库山即库真山,今青海兴海县鄂拉山)毫无防备的吐谷浑之众,伏允率领可汗轻兵逃入莫贺延碛碛尾,唐军在此附近分兵。李靖、薛万均、李大亮从北路追击至鄯善、且末等地,侯君集、李道宗从南路沿着曼头山,经赤水(今兴海县境青根河—大河坝河)、破逻真谷(今兴海县曲什安河支流长水河谷)、汉哭山(今兴海县与玛多县交界之处的巴颜喀拉山口)、大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等地,五月抵达星宿川(今青海玛多县黄河沿)、柏海(今鄂陵湖),然后回师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平原)。
通观这次唐军平定吐谷浑之役,贞观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战前准备阶段有主力李靖部,配合作战的五部:东面侯君集、李道彦两部,西面李道宗、李大亮两部,南面高甑生部。贞观九年三月鄯州会议后,战役进行时缺少了李道彦、高甑生两部。由于这两部未直接参战,战前准备阶段实行的围歼战术在战役进行时不得不改变,以前的行军路线只能随之调整。侯君集部自然服从作战大局,遂改变了原来指向积石道转而配合李靖部的行军路线,指向《元和志》等文献所记鄯州。这是在战前准备阶段转向战役进行阶段的过程中,侯君集职务在《新唐书·侯君集传》《资治通鉴》为积石道行军总管,而在《旧唐书·侯君集传》《册府元龟》为李靖副手的原因。还需要明确从长安出发的侯君集部到鄯州的具体行军路线。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渭州(今甘肃陇西)至狄道县(今甘肃临洮),有两条道路通往鄯州。一条经兰州北上渡河,向西沿着湟水谷地。另外一条至河州分为两途:一经河州西北去经凤林关渡河,再经龙支城(今青海民和北古城),另外是从河州西去,至今青海循化渡河,经化隆北上便至鄯州(今青海乐都),合川郡界守捉就位于鄯州南180里、循化西北的德加乡附近。因此,侯君集部是选择最后一条道路开往鄯州的。
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行军路线,认为侯君集部行军到河州后,折而东南到洮州(今甘肃临潭),南下叠州(今甘肃迭部),随之西去经阿尼玛卿山东南等地,再西北至鄯州。从此西南经汉哭山去河源。侯君集部如此行军的原因,是学者将合川郡界守捉认定在叠州。这不仅有悖于《元和志》等文献对合川郡界守捉位置一致的记载,而且还将唐军平定吐谷浑之役战前准备阶段与战役进行阶段的行军路线混淆在一起了。即使按照战前准备阶段,也没有必要首先行军至河州后,再接着从此东南折向洮州。从洮州出发西向,就可直接到达侯君集起初行军所要行走的积石道。因此,欲弄清侯君集部是否行走叠州一线并于此设置合川郡界守捉,首先要明白岷州都督、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与利州刺史、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两部未参加围歼吐谷浑之战的原因,以及这两部在战役进行阶段从事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三、党项之乱与李道彦高甑生两部作战任务调整
李道彦、高甑生两部未参加围歼吐谷浑的原因,是贞观八年十二月末以李靖为首的唐军主力从长安向西行军过程中,遭到了叛乱党项的阻拦,不得不调整作战任务的结果。这次党项叛乱的具体时间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九年条记载:
春,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浑,杀刺史孔长秀。
《旧唐书·太宗本纪》有类似的记载:“九年春三月,洮州羌叛乱,杀刺史孔长秀。”《新唐书·太宗本纪》亦曰:“贞观九年正月,党项羌叛……三月十四日,洮州羌杀刺史孔长秀,附于吐谷浑。”虽然各种文献都未明确记载此次党项叛乱的具体日期,但一定距离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的贞观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不远。党项选定这个时期叛乱,一定是吐谷浑精心策划的结果,不仅叛乱的党项先后归属了吐谷浑,而且这年三月十四日洮州羌杀害该州刺史后也归属了吐谷浑。另外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洮州之境的羌族杀害的是洮州而非其他州的刺史。洮州,今甘肃临潭,是渭河谷地驿路西南经岷州(今甘肃岷县)进入九曲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从此通往积石道的便捷之路。因而吐谷浑于此策划叛乱,显然是有意阻止侯君集部从此行军至积石道。
吐谷浑的目的,并不仅局限于此,而是要阻止所有唐军向西进入吐谷浑的势力范围,进而打破各路唐军围歼计划。利用生活在吐谷浑与唐朝之间九曲内外的党项、羌叛乱,就是一件十分便利之事。不过,对这次行军道路上可能造成威胁的党项、羌,早在贞观三年唐廷已开始招抚,并陆续设置了桥(今青海泽库县城泽曲镇智和罗合古城)、西唐(今青海贵南县森多乡青羊禾古城)、西盐(今青海河南县宁木特乡龙干多)、嶂(今青海兴海县桑当乡夏塘古城)、祐(今青海河南县柯生乡)、丛(今甘肃玛曲县阿万仓乡哈尔钦和东南黄河北岸)、洪(今玛曲县阿万仓乡尕若村黄河南岸)、肆(今青海同仁县年都乎乡向阳古城)、玉(今青海贵南县沙沟乡查纳寺古城)、西沧(今甘肃碌曲县玛艾乡红科村)、轨(今四川松潘县上八寨乡阿基村)、西戎(今四川若尔盖县求吉乡麻藏沟口)、西麟(今若尔县盖达扎寺镇)、西吉(今若尔盖县包座乡唐热村南溪口)、诺(今若尔盖县嫩哇乡黑河牧场)、西集(今若尔盖县阿西乡阿西牧场)、阔(今四川红原县邛溪镇达合龙村)、蛾(今四川阿坝县求吉玛乡夏坤玛)、西雅(今阿坝县贾洛乡贾曲中游河口至贾曲桥一带)等十九个羁縻州。这些内附于唐朝的党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住牧今青海境的九曲之内,另外一部分住牧今四川境内在九曲之外,这些羁縻党项的各州都归属西戎州都督府(今四川若尔盖县求吉乡麻藏沟口)。如果前引《资治通鉴》所载“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完全属实的话,这次唐军行军途中,党项叛乱之地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
这些党项叛乱的地方,不仅是从长安出发的唐军主力李靖、侯君集、李道宗三部所经,也是李道彦、高甑生两部战前准备阶段所行。李道彦身为岷州都督府、赤水道行军总管,行军路线是从岷州都督府治所岷州出发沿着洮水谷地西行,所经之地有羁縻台州(今甘肃碌曲县玛艾乡红科村)、桥州,过此便至目的地。高甑生身为利州刺史、盐泽道行军总管,行军路线从利州刺史治所利州西北行,经文、扶两州,进入若尔盖草原,沿着大积石山山麓经都州(今青海都兰县城察汉乌苏镇东风村遗址)西北向,可至作战之地。
贞观九年正月九曲内外的党项叛乱之际,正是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率部从长安西进之时。突如其来的叛乱,打破了唐军多路齐头并进的围歼计划。原来所拟定的行军路线,不得不暂时做出相应的调整。贞观九年三月庚辰(635年4月6日)洮州羌杀害该州刺史后,乙酉(4月11日)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遂奉命平叛。直至这年七月庚子(8月24日),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仍在与叛羌作战,从而说明党项叛乱不久唐军就采取了保护主力西进的战术,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的作战对象与行军路线也作出了改变与调整。这次党项叛乱也改变了李道彦部的行军路线与作战任务。战前准备阶段,岷州都督李道彦是以赤水道行军总管的职务指向赤水城。结果,战役展开后,他最终行军目的地却至阔水(在今若尔盖草原),目的是为满足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主力部队的后勤补给,而唐军后勤补给出现的问题正是党项叛乱所致。这迫使唐廷不得不通过“复厚币遗党项”的手段,令党项引领党项首领、西戎州都督府拓跋赤辞至李靖部商量补给事。西戎州都督府属唐之松州都督府管辖的羁縻府,李靖亲自邀请拓跋赤辞至军营,一方面说明这已非通过正常手段所能解决,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拓跋赤辞极有可能参与了这次党项叛乱,唐军与拓跋赤辞歃血为盟可从侧面佐证此事。即使如此,李靖也要从拓跋赤辞处获取军需,可见这批军需对唐军是何等重要,李靖不得不为之派出大量唐军护送。而此次负责军需的李道彦却未遵守事先约定,遂在拓跋赤辞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袭夺数千头牛羊,结果引起党项怨恨,造成唐军死亡数万人的惨剧。
总之,贞观九年正月九曲内外的党项叛乱,打乱了唐军战前准备阶段各路围歼吐谷浑的计划,在保证唐军主力西进的宗旨下,随之对其他各部的作战任务、行军路线进行调整。利州刺史、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与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临时改变了开往盐池的行军路线,以及防止吐谷浑从盐池南逃的作战任务,不得不北上平定岷州都督、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辖区内的党项之乱。文献不载李道彦部平叛本辖区内党项之乱事,因当在此时高甑生已接替他的岷州都督职务,赤水道行军总管已被左骁卫将军樊兴接替,李道彦所受作战任务已转向唐军后勤补给。而高甑生仍兼任盐泽道行军总管,说明唐军围歼吐谷浑的计划至贞观九年三月仍未改变。
四、合川郡界守捉设置与侯君集部行军安全保护
既然贞观九年正月党项之乱导致了李道彦的岷州都督、赤水道行军总管职务分别被利州刺史高甑生、左骁卫将军樊兴替代,那么李道彦除负责唐军军需外,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旧唐书·李道彦传》《新唐书·樊兴传》《通鉴》等史料,均不载李道彦职务何时被替代事。与此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却很清楚。贞观九年三月,唐军主力到达鄯州并于此召开会议。三月庚辰(4月6日),高甑生率部平定党项之乱。闰四月癸酉(5月29日),李道宗部开始在“大军已至,贼虏尚未走险”情况下出击吐谷浑。这距离唐军主力到达鄯州已六十余天,吐谷浑不可能不知道。在获悉唐军到达的情况下,仍然未与唐军接战,说明伏允可汗对通过策划九曲党项叛乱以阻止唐军西进活动的自信,也说明唐朝主力因受粮草供给等方面的影响,不得不在鄯州与吐谷浑僵持两个多月。
虽然在得不到粮秣补充的情况下,唐军以偏师取得小胜,但在吐谷浑烧掉野草后,遂陷入“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的困境,从而再次证明是粮秣制约着唐军行动,这时李道彦仍未获得粮秣。唐之主力才不得不在鄯州按兵不动两个多月。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唐军四面围歼吐谷浑的计划迟迟得不到实施。否则,无法进一步解释樊兴代替李道彦行使赤水道行军总管职务,以及高甑生代替李道彦出任岷州都督仍然行使盐泽道行军总管的职务后,因没按照预期参战而均受处罚事。
闰四月癸酉(5月29日)实行分兵出击吐谷浑前,李靖并不想将歼灭吐谷浑的作战区域溢出战前准备阶段的范围,更未计划使唐军深入河源远距离作战。这必须在九曲党项叛乱之地寻找一处为唐朝提供粮秣补给的地方,西戎州都督府因远离叛乱党项的作战中心洮州,遂成为唐军选择的对象。不足之处,就是鄯州与西戎州都督府两地过远。即使今天,这两地之间最短的距离还有1134里。唐军自贞观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从长安出发至九年三月达到鄯州,1960里(约合今1764里)路程,至少用了63天,平均每天行军28里。每天以28里计算,1134里大约需要40天,这还不包括返回的时间。如果绕道黄河之西的阿尼玛卿山,则距离会更远、时间会更长。因而,闰四月癸酉(5月29日)唐军分兵出击吐谷浑,实是获悉李道彦军需运输失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问题是李道彦何时开始负责唐军主力军需?贞观九年正月,党项发生叛乱。三月,洮州叛羌杀害该州刺史,乙酉日(4月11日)高甑生率部平叛。因此,高甑生平叛党项事应是三月鄯州会议的结果。正是在此次会议上,高甑生代替李道彦出任岷州都督,樊兴代替李道彦出任赤水道行军总管。这两种职务解除后,李道彦开始负责唐军主力军需。解除职务之前的正月至三月间,李道彦还担负唐军主力西进安全的任务。如前所论,贞观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率领的主力从长安出发不久,即贞观九年正月九曲党项就发生了叛乱。在保护唐军主力西进的宗旨下,李道彦此时应很快承担了这三路大军西进侧翼安全护送的重任。正是这两个月护送主力西进过程中,李道彦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后勤工作才能,最终让其承担了唐军主力军需补给的任务。
李道彦的出色表现,还包括护送侯君集部从河州至鄯州之途设置了合川郡界守捉。首先分析地理形势。从长安向西翻阅六盘山经秦州(今甘肃天水)、渭州(今甘肃陇西)、兰州(今甘肃兰州)、河州(今甘肃临夏)至鄯州(今青海乐都)一千多里的路程中,越往西去防御力量越弱。秦州至兰州段的南面,有成(今甘肃礼县南)、宕(今甘肃宕昌)、岷(今甘肃岷县)、洮(今甘肃临潭)等州为之屏障,河州至鄯州段之西面向黄河南北的广袤区域,却亟待加强防守。这时从河州去鄯州仅有龙支县城,西去廓州仅有米州。两条道路之间的空旷地带,没有任何军政建置。这确定必须设置一个军事据点,保障侯君集部的行军安全。从河州经青沙山北麓至鄯州的交通线,成为可供选择之地。至贞观九年,遂在鄯州南一百八十里之地的青沙山北麓设置了合川郡界守捉。
其次,分析名称来源。贞观九年正月以来九曲党项叛乱的形势与唐军艰辛行军的情况,促使唐军考虑从河州至鄯州之途的安全。此时一直负责唐军主力侧翼安全的李道彦部,自然承担了侯君集部行军之途安全的任务。贞观九年,岷州都督府辖属岷、宕、洮、旭四州,无叠州。根据唐朝行军兵员构成,有优先从当地及邻近征发的惯例,且以州为单位确定征发数量、以州别为原则编制军队。岷州都督李道彦以赤水道行军总管身份奉命征讨,辖境各州自然在征兵范围,邻近叠州同样应列于其中。唐初,实行州县两级制。至《通典·州郡典》成书时,改为以郡为纲,故有“合川郡界守捉……贞观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的记载。“合川郡界守捉”之“合川郡”指叠州。杜佑讲得非常清楚,“叠州。今理合川县。……大唐为叠州,或为合川郡”。因此,唐初该守捉初置时应名“叠州界守捉”。
最后,分析设置者。既然是岷州都督李道彦设置,为何《通典》等文献记为侯君集?唐军平定吐谷浑之役,最终未实现战前阶段制定的围歼计划。从处罚结果看,李道彦所受最严厉,“坐减死徙边”,高甑生后因诬告李靖谋反才被判处“坐减死徙边”,樊兴则“以勋减死”而已。侯君集则不同,不仅立下战功,而且该守捉极可能是侯君集下令所置。这是现存文献记载设置者是侯君集而不是李道彦的原因。
纵观合川郡界守捉设置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从一开始其就未列入战前准备阶段的计划中,也没有列入战役进行阶段的计划里。该守捉是唐军面对九曲党项的叛乱,鉴于侯君集部去往鄯州行军之途的安全,结合当时从河州西北去鄯州的形势临时所设,因而具有了临时设置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合川郡界守捉之名变得扑朔迷离。
五、合川郡界守捉书写变化与西部边疆地理认知
从《通典》成书的贞元十七年(801年),经《元和志》的元和八年(813年)、《旧志》的开运二年(945年),至《新志》的嘉祐五年(1060年)、《资治通鉴》的治平四年(1067年),二百多年间,合川郡界守捉的名称经历了从“合川郡界守捉”“合川郡守捉”至“合川守捉”的演变,背后隐藏着这些书籍编撰者对唐之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认知的变化。
《通典》所记“合川郡界守捉”之名没有错误。该书有严格的编撰原则,历代沿革废置“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因而书中所记陇右节度使所属合川郡界守捉在内的十军、三守捉,绝非道听途说,“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清人也有类似的评价:“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有用之实学”,边疆治理上也有所体现。
道德远覃,四夷从化,即人为治,不求其欲,斯盖羁縻而已,宁论封域之广狭乎!……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露,动盈百轴,岂所谓撮要者乎!
杜佑明确反对拓边,与此相关的地理之幅员、因革、要害等都不是书写的重点。不过,对于唐朝边界是所取舍的,他希望维持在开元二十年(732年)前未拓边的情况,具体就是“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既然如此,首先必须如实记述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各郡至吐谷浑、吐蕃接界的情况。 西平郡(鄯州)“西至绥戎硖旧吐谷浑界一十里”“西南到宁塞郡广威县故承风吐谷浑界三百一十三里,西北到木昆山旧吐谷浑界一百九十五里”,临洮郡(洮州)“西南到吐谷浑界”,合川郡(叠州)“南至吐蕃界三十里,西至吐蕃界九十里”、“西南到吐蕃界七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七十里”。为使这些与周边民族接界之郡处于有备无虞的状态,明确以郡为单位补苴边界安全的方位与距离、补苴边界罅漏的时间与人物、保障边界安全的兵力或马匹数,同样显得十分必要。因而《通典》所记“合川郡界守捉,西平郡南百八十里,贞观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就是这种情况下的真实反映;“合川郡界守捉”之“郡界”,则是杜佑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边界思想的具体反映。这样书写的原因,就是希望唐之边疆回到其所主张“列州郡,俾分领”,没有节度使统辖的治理局面。
《元和志》则不同。李吉甫编撰旨的趣是军事攻守,“施于有备之内,措于立德之中”。具体言之,就是借助地理上的“攻守厉害”,达到供德宗皇帝“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的目的。
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指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
因此,李吉甫对唐之黄土高原西部边界各州的书写,侧重于历代军事攻守,明晰是否为吐蕃占领。鄯州“宝应元年,没于吐蕃”,廓州“乾元元年,陷于吐蕃”,岷州“上元二年因羌叛,陷于吐蕃”,洮州“广德元年,陷于吐蕃”。
随着《元和志》编撰旨趣转移至军事攻守,分布在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的所有军事据点不再以州为单位叙述,而是系于鄯州条下。凡在鄯州之境,均言在该州某方位,如“绥和守捉,(鄯)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凡不在鄯州之境,则说明其具体位置,如“莫门军,洮州城内”。这是以陇右节度使治所鄯州为中心进行的兵力部署,体现的是攻守态势。与此相关的内容,诸如兵力调动、地域来源,成为强调的内容。因而《元和志》补充了《通典》所未载的“合川郡,今叠州”,这里“合川郡”就是“合川郡守捉”之“合川郡”。所补充内容,旨在说明该守捉初置时驻守这里1000名士兵来源于合川郡。这不是随意地杜撰,“志(《元和志》)载州郡、都城,……皆本古书,合于经证,无不根治说”。
至于合川郡界守捉,《元和志》将其更名“合川郡守捉”后省略了“界”字,则是有意为之。《元和志》书写强调的是军事攻守,达到经略天下的目的,所以不会承认开元时期唐廷就不承认的唐与吐蕃西部边疆之界限,也不会承认基于唐之国家安全利益所占领的吐谷浑疆土。黄土高原西部边缘的鄯州(西平郡)、洮州(临洮郡)、叠州(合川郡)的书写,均不再像之前强调为唐与吐谷浑、吐蕃的界限。在这种已不再重视黄土高原西部边缘边疆地带书写的时代背景下,《元和志》再像《通典》记为“合川郡界守捉”,会显得特别突兀,也有悖于书写的宗旨。结果,《元和志》出现了“合川郡界守捉”的记载。
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短短的七十余年,北方更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频繁的政权更迭,自顾已经不暇,焉能再对唐之广袤疆土进行积极探索。这无形中影响了《旧志》编撰者对唐之地理空间的认知与编撰的旨趣。
盖德业有浅深,制置无工拙。殷、周未为得,秦、汉未为非。摭实而言,在哲后守成而已。谨详前代隆平之时,校今天耗登之数,存储户籍,以志休期。
这时对唐之疆域已不作出是非曲直的评价,只想找出盛唐时田赋的丰歉、人口的多寡,作为美好记忆而已。而对唐之黄土高原西部边缘的疆土,也是如此。这种背景下,文献鄯、洮、廓、叠等州的记载,主要叙述各州武德至天宝、乾元元年(758年)两个阶段天宝前后户、口的变化情况,以及从吐蕃手中收复后的建置沿革。虽然这里涉及到吐蕃,但很少提及吐蕃事,自然缺少了前引《通典》所记唐朝与吐谷浑、吐蕃厘清边界的内容,也缺少了前引《元和志》所载对于鄯、洮等州是否陷入吐蕃的叙述。
而对于陇右节度使辖属的军事据点,虽然《旧志》参考了《通典》,记载了兵力、马匹、衣赐,“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疋。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疋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但仅仅关注而已,并不像《通典》想达到“列州郡,俾分领”的治理目的。由于编撰旨趣的变化,《元和志》并未完全抄录《通典》这些军事据点的内容,只是有限抄录了兵力、马匹、衣赐,设置者、设置时间等都被省略了。结果,合川郡郡界守捉,从《通典》所记“合川郡界守捉,西平郡南一百八十里,贞观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至《旧志》时就被节录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官兵千人”。因省略“贞观中侯君集置”“合川郡界守捉”之“郡界”,造成了该守捉信息的不完整。陇右节度使所辖其他军事据点也存在类似情况,临洮军“在鄯州城内,管兵万五千人,马八千疋”,这很容易使人误认为从设置伊始,该军就在鄯州城内。事实却非如此,《通典》曰:“临洮军,开元中移就节度衙置,管兵万五千人,马八千疋”。
宋代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但北有辽国、西北有西夏的鼎立格局,造成熙宁(1068—1077年)开边前的大部分时间,无力于唐之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的开拓与经营。这也造成《新志》编撰者关注的重点是唐之户口盈耗、州县废置,以此作为国家治乱的借鉴而已。
考隋、唐地理之广狭、户口盈耗与其州县废置,其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矣。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德而不务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呜呼,盛极必衰,虽曰势使之然,而殆忽骄满,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这也深刻影响着宋人对唐之黄土高原西部边缘的认知,结果每个州更多的记载是州名、天宝户口、沿革、土贡而已。所表达的含义,无非作为“盛极而衰”的历史注脚罢了。《新志》所载的军事据点已分散记载在各州之下,成为让人凭吊的古城。“鄯州西平郡,……星宿川西有安人军。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军。西南二百五十里有绥和守捉城。南百八十里有合川守捉城……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沒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这显然是编撰旨趣转变的结果,即使《新志》编撰者参考了《元和志》,依旧未沿袭“合川郡界守捉”之名,仅记其方位、距离。虽然也参考了《旧志》,却未全部照录,只沿用“合川守捉”之名,亦未记载“管兵千人”的内容。以资政为目的的《资治通鉴》全部节录了《旧志》中所有军事据点的名称、方位、兵力或马匹之数,不过司马光已用其说明由此带来的“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的情况。
纵观合川郡界守捉的名称演变,可以概括为三个时期。《通典》中的合川郡界守捉表示唐与周边民族的边界。《元和志》中的合川郡守捉反映了编撰者重视的是军事攻守。五代至宋初合川守捉反映了编撰者对黄土高原西部边缘无力经营情况下剩下的只有往事追忆、作为国家治乱的鉴戒而已。所有这些名称变迁的背后,隐藏着编撰者对唐之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地理空间认识变化与以往知识的选择。
六、余 论
由军、守捉组成的戍守体系,是唐前期边疆安全重要组成部分。前贤主要从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角度出发进行了翔实研究,为今天深入探讨奠定了非常厚重的基础。不过,似乎未找到更切合这些军事据点的解读方法,以至于研究的过程与结果给人意犹未尽的遗憾。合川郡界守捉是唐军平定吐谷浑之役的产物,因此对其研究应与唐军平定吐谷浑的战前准备、战役进行、战役结束的过程充分结合起来。唐军因受吐谷浑精心策划的党项之乱影响,不得不行军途中临时改变了行军路线,调整了作战任务,转变了作战战术。该守捉的设置就受到这些要素变化的影响,从而证明合川郡界守捉之名并非错误,由此初步摆脱了基于传统文献对该守捉之名是非的争论。
对合川郡界守捉名称演变的考察,同样应摆脱仅基于传统文献的有限分析,而应将其放在黄土高原西部边缘这个大的地理环境、军与守捉组成的戍守体系中全面考察。从设置开始,该守捉就是唐人基于唐之主力在黄土高原西部边缘行军不安全临时应变的结果。设置以后,与以后陆续设置的其他军事据点共同构成唐之黄土高原西部边缘的防御体系。这避免了因单独考察合川郡界守捉可能得出的偏颇结论,而且符合《通典》《元和志》《旧志》《新志》《资治通鉴》等书籍编撰者从全局性视野考察所设定的编撰旨趣。而合川郡界守捉名称从唐经五代至宋初的演变历程,也是这段时期编撰旨趣变化的结果。
这也反映了编撰者对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地理认知的变化。安史之乱,这里为吐蕃占领。无论是《通典》还是《元和志》,都将这个地带视为《禹贡》雍州、梁州之域,说明在编撰者视域中仍为唐之疆土,因而才会从地方治理、军事攻守的角度进行书写。这是合川郡界守捉之名得以延续,进而改为合川郡守捉的时代背景。唐朝灭亡,继立五代的都城远离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其对当时政治、军事的影响再未像唐朝那般剧烈,《旧志》编撰者甚至对其是否为《禹贡》之域都未载。虽然《新志》还视其为《禹贡》雍州、梁州之域,同时也不忘强调被吐蕃占领的事实,但宋人所绘《太祖皇帝肇造之图》《太宗皇帝统一之图》就将其绘在界外了。无论是后晋还是宋人,都将唐之黄土高原西部边疆地带视为回忆、鉴戒之地,而不视为与其生活紧密相关之处,原来基于国家经略之区中的合川郡界守捉、合川郡守捉遂更名为合川守捉了。
注 释:
②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1页。
⑤《新唐书》卷40《地理志一》“鄯州西平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1页。
⑥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4页。
⑦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1—62页。
⑧王永兴:《唐代经营西北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
⑩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