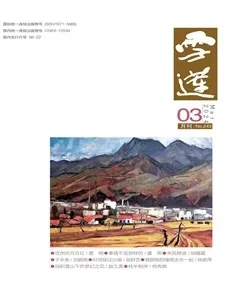一个人的银川
【作者简介】 计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刚需房》《半街香》,诗集《如果疼痛可以开花》《未来辞》。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文学艺术奖,银川市第二、三、四届“贺兰山文艺奖”,首届刘成章散文奖黑马奖等。
鼓楼和玉皇阁
城市在大张旗鼓地搞建设,到处都在拆,都在建。可矗立在城市中心的两个建筑却从来没人打过它们的主意。所有的拆建、改建都是围绕着它们而展开,就像一个家族的老祖宗,他无论多么衰老都不会有人想过遗弃他。这两个建筑在我眼里堪比北京故宫,它们就是位于解放街的鼓楼和玉皇阁。
其实我老家也有鼓楼,可年幼的我眼里只有这两座宏伟的建筑,其他的都抛之脑后。鼓楼和玉皇阁相距不远,它们在一条街的直线上,隔了大约几百米,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妈领我到处转着认路,这两座古建筑外表看起来差不多,都是那种故宫墙的颜色,都是琉璃瓦,门洞也是一样的青砖门洞。我妈教了我好多遍,我都记不住哪个是鼓楼哪个是玉皇阁,而我又是个不分东南西北的人,气得我妈回去给我奶说这孩子是个猪脑子。我奶回她一句,隨她妈。我妈听了气得踩着她的高跟鞋噔噔噔地下楼上班去了。
我奶又领着我去了一回街上。我俩站在鼓楼和玉皇阁之间的德隆楼门口,我奶对我说,娃,抬头看,那鼓楼的顶子是尖的,玉皇阁的顶子是平的,记下没?我站在老字号德隆楼的门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还真的是哎,我一下子就分清了哪个是鼓楼哪个是玉皇阁。记住它们是为了能从新华街回来的时候找到回家的路,分清它俩,我只要从玉皇阁一路往北就能到家了。新华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区,那时是唯一的最繁华,现在是最繁华的之一。四面八方来逛街的人如果没去一趟新华街,他就等于没来银川。家家户户条件都好起来以后,我们老家的人家里办喜事都要来这里购物、拍照。第一次来的人,几乎都要在玉皇阁或是鼓楼留一张影。后来在银川很有名气的士良照相,他的老板就是从在广场给人拍照开始发家的。
上学后,学校组织参观活动,我上过几次玉皇阁。走上几层陡峭的步梯,我趴在玉皇阁的栏杆前看到了我家的楼。现在没那么容易了,中间隔了无数新拔起的高楼,玉皇阁在它们跟前真的成了一个上年纪的老者,曾经的步梯摇摇晃晃,极少对外开放。当年的玉皇阁和鼓楼在大家眼里并不算个文物,它就是两座古建筑。在改革开放初期,到处都在搞活经济,连玉皇阁这样的古建筑都没有逃脱这股子浪潮。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组织我们上玉皇阁参观木乃伊,木乃伊怎么来到我们这的,我一点儿印象都没了。我现在脑子里记得的就是我们爬上了玉皇阁,在它最大的一间房的中间放着一具缠满白布条的尸体,远远看他的样子和我在电视里看到的一样。但近距离呈现在我眼前的这具木乃伊,看起来更像个做工粗糙的玩具,我们上来看他一眼还要收门票和参观费,门票五毛钱,参观费多少不记得了,那段时间的玉皇阁是创收的,管理员大姐的嘴咧得很大,让我想起我爸挣了钱咧着大嘴的样子。
鼓楼始建于1821年,玉皇阁的始建年代无从查考,史料上只有它重建的日子,在清朝的乾隆年间。从建筑时间看,它们必定是文物级建筑,承载了一方水土的兴衰荣辱。人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抓钱风暴期后,终于从它们摇摇晃晃的楼梯意识到了再这样下去,史料级文物就会毁于一旦。于是,在人为的干预下它们像大熊猫一样重点保护起来,在保证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对它们进行了修缮。从此后,我们只能在它的广场上奔跑玩耍,再没有登上它红色的满是裂缝的楼梯。
再后来,参加工作后,我出差去过很多城市,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座鼓楼,它们立在城市的中央,似一枚枚定海神针,保卫着一方人民的富裕安康。而玉皇阁我只在银川见过。
新华街和小吃街
解放街和新华街是平行的两条街,它们被鼓楼和步行街连接起来。
我最早来新华街是去那里的大众浴池。我在老家的时候洗澡不多,一年一次,年三十那天洗,平时都是洗洗头发,擦擦身子。在老家洗澡,是用我奶家的大铝盆,我们轮流坐到铝盆里洗,通常会洗两遍,第一遍狠劲地搓泥,第二遍细细地擦洗全身。我奶带孩子在我们那一带都是出了名的干净。我身上从没有像我的小伙伴们一样生过虱子,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我的发小她奶奶给她用篦子篦头上的虱子和虮子,我帮她奶奶把篦下来的虱子掐死。帮她篦一回虱子,我就会带一两个回去,晚上咬得我奶睡不好,半夜起来捉虱子,第二天再把我捶一顿。
我长到十来岁没进过澡堂子,不知道大家一起洗澡是什么概念。
我奶带我来银川的第二天我妈就带我们去洗澡。我奶没去,她腿脚不好,六层楼爬上爬下她实在吃不消。她一般上了楼就很少下去,所以她不喜欢待在这里,她其实每天都很憋屈,但为了她的三个孙女能安心上学,她每天都乐呵呵地忙着家务,所以我们都以为她很快活。
我妈在浴池窗口买票,售票员从小小的一个洞里面探出一双眼睛,对我妈说,三个丫头子两张票。我妈不乐意了,说最小的不是和我算一张票吗?我妈的言下之意是我们娘四人一共买两张票就行。售票员又探出眼睛来冲我妈说,墙上有尺,你看看你小丫头多高了?我妹听完一蹦子就站到了尺下面,果然比人家要求的身高高出了半个额头。我妈吊着个脸子买了三张票,一张票一块钱,不算便宜。后来涨到了两块,再后来我妈单位盖了职工澡堂,每个月发澡票,我们不用花钱洗澡了。
女浴室在二楼,一楼是男浴室。只要有男的上楼,会被守在楼梯口收票的大妈轰下去。大妈很敬业,从没有男的误闯过女澡堂。澡堂进门后是一排排柜子,用来放我们的衣物,一张票给一个锁子,那种小小的绿色的“将军不下马锁”。钥匙挂在一个红色松紧塑料环上,方便套在胳膊上,我妈担心我们弄丢了钥匙,她的胳膊上就套了三个环,看起来很像我们玩的那种弹簧拉环,我们仨羡慕地看着母亲的胳膊,恨不得一夜能长大。
那天去的是个周末,人很多,好像全银川的人都出来洗澡了。我妈只在柜子的最前排的最下面那层找到了两个柜子。这一排因为离淋浴头很近,大家都怕溅湿了衣服,所以空了出来。我是第一次见识了那么多陌生人的裸体,虽然都是同性,可我还是羞得满脸通红,眼睛不知该放哪里合适。所幸浴池雾气腾腾,基本看不清人的表情。我在我妈的帮助下,站在一个龙头下冲洗身体,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姑娘,她大概抱着盆找了一大圈了,最后才找到了比我们的柜子还偏僻的一个,柜门上还有个洞。
她放下盆,先清理了一下柜子,然后开始脱衣服,她把外面的厚重的衣物去除后,身上就只剩一身黑色的健美服。那时候刚开始流行健美裤,我两个妹妹都有一条,而我嫌它太贴屁股没有要。穿健美裤的我见得多,可这样穿一身的很少,再加上她刚刚发育的身体,散发着青春美的味道。穿着健美服的她,并不急于继续脱衣服去冲洗,她开始在那梳她的长头发,就像慢动作一般梳得精细。我一边冲洗,一边欣赏她,看着看着我脑海里出现一个成语:搔首弄姿。因为她每梳一下头发,就用余光看看有没有人在看她,那眼神并不是害羞别人看她,而是渴望别人来欣赏她。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去过公共浴池,都是在家洗浴,几乎是每天一次,无论冬夏。而想再欣赏一次年轻的漂亮的女孩子的虚荣心再无可能,漂亮的姑娘们也都自己在家洗澡了。
后来,新华街在原有的商场基础上,开发出来一条步行街,估计是和南京路学习而来。步行街一度承载了银川以及全区乃至临省的购物天堂,步行街两侧商埠林立,佐丹奴、班尼路、真维斯、特步……后来的阿迪达斯、耐克……等等,凡是你知道的当时的一线品牌在新华街步行街一带都可以找到。
商埠构成也很合理,新华百货、购物中心、华联商厦等这几个大商场满足中产及以上消费人群需求,剩下的小专卖店则满足了年轻及前卫人士的需求。我在刚来的那几年,逢年过节都是带着老家人穿梭在新华街和步行街,那不仅是女人的天堂,也是孩子们的乐园。
小吃街,听名字就应该和吃挂钩,我印象里它和吃有关联的就是那里的夜市和仙鹤楼的饺子。和它相关联的路口叫羊肉街口,据说那里曾经是专门卖牛羊肉的市场,后来改造成了小吃街,虽然不卖肉了,但它的街名到今天还在使用。而小吃街也不是以吃著名,它是名副其实的家电一条街。在小吃街,你能买到所有你家里需要的家电,价格还很便宜,所谓物美价廉在这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前段时间,我开车拉着我妈去附属医院路过小吃街,它的样子还是古香古色的四合院模样,绛红的墙面在阳光下有些斑驳,我妈指着中间的一处店面对我说,这套营业房本来是咱家的,你爸那年让人骗了精光不说还欠了一堆债,十五万把它卖了去还账。我听了遗憾地啧啧啧着,说放到现在怎么不值个几百万啊,而且每年租金也不少呢。我妈也啧啧啧地说,那也没办法,谁也没长个前后眼。咱家没那个命,和这房子就那么点缘分,用尽了就没了。我妈这无意中的一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遇到过一些人生中重大的挫败,我都会想起我妈说的这句话,人生一世,和万物都是个缘分,用尽了就别强求。我也曾执拗地去努力争取过自己认定的东西,到后来用头破血流的教训证明了我妈这句话。
活着,随缘就好。
南门城楼子
到银川,下了汽车,随着人群出站,很多人会提着大包小包去车站对面的南门广场先留个影。南门广场仿佛高仿的天安门广场,北京于我们而言遥不可及,而这里唾手可得。
作为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大省名市学习先进经验无可厚非。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这个城市和人一样走过一些弯路,也有过迷茫,但不管怎样它都在一条伟大复兴的路上阔步前行着。
就像这南门广场,从外形看,它好像天安门的微缩版,连挂在城门楼子的毛主席照片都一模一样。我每次经过城楼,都好像能听到从城楼传来那声敲击人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湖南话,伟人的力量或许不止于他当时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他传承下来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千万个普通人勇往直前。每个站在南门城楼前留影的人,他们都把最挺拔的腰杆留在了那里,那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着他们,站在那里,沐浴着西北的骄阳与冷风的人们心中涌动着股股暖意。
在广场上支着相片架子,脖子上挂着相机的人成了最时髦的人。这些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数字技术还不成气候的时候积攒下了第一桶金。他们中一部分人,在这个城市开起了影楼,因为无论穷富,结婚时大都要照一套价格不菲的婚纱照。我周围的人要结婚就必要到名气很大的士良、小牛、樱花、贵妇人等影楼去拍一套照片。然而这些照片很多都随着他们日渐貌合神离的日子变成了鸡肋,我曾经在我家楼下发现了一堆婚纱照,新娘的照片脸被划得面目全非,而新郎还是咧着大嘴,一身挺括的西装意气风发地站在一棵椰子树下。他的脸上被人扔了垃圾,洒了菜汤。后来随着数字技术超速发展,一部手机干掉了照相机、电视和电影院。到今天它又毁了实体店、钱包,使小偷失了业。现在街上偷钱包的人几乎绝迹了,人人都不带钱包了,还偷什么呢?
城门楼子前面有一片很大的广场,水泥浇筑的台面,灰突突的,广场周围种了树,中间并不见花坛。这里是最初的劳务市场,来城里打零工的都在这聚集。白天他们在这揽活,晚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这摆夜市、卖烧烤、卖衣服、搞娱乐项目,什么套圈,卡拉OK、吼秦腔。
早年这边治安不太好,有点乱,城中央的人不喜欢来这边玩,后来随着城中村改造,把那些几十年的烂平房推倒盖起一排排楼房,好像老家里的小动物,一旦圈养起来就乖多了。其实这得益于城市治安的大整顿,我有个同学,据说在严打的时候偷了辆自行车坐了几年牢,人出来的时候,同龄人都奔向了更好的明天,只有他像个小老头儿一样躬了腰。
周边环境好了,出来摆夜市的就多了,天一黑,这里的小摊贩一家挨着一家,都是卖一些低廉的物什,我妈常给我们在那买袜子之类的小物件,几块钱就能买一堆。沿着广场摆成一溜的是烧烤摊子,每个摊子的模样和菜品都差不多,只在味道上争高下。我打小不喜羊肉,但唯独吃羊肉串兴致勃勃,夏天的時候,我爸带我们乘凉,偶尔给我们买羊肉串改善生活,我们三个人一次能干掉一百串。吃得我妈心疼得皱眉头,回家了免不了数落我爸,我爸总回她一句:还能吃穷了吗?
广场的一角,围着一堆人吼秦腔。我对秦腔并无太多兴趣,我父母亲、爷爷奶奶他们都是秦腔迷,这大概是老陕的执念。家里条件好点的时候,我家买了一个双卡录音机,就是中央电视台广告时段一个小伙子背着吉他唱着“燕舞燕舞,一起歌来一片情”的那个牌子的录音机,我爸还买了一抽屉的秦腔磁带,什么周仁回府、秦香莲、铡美案等等,可我印象里,他们在家并没有听几回磁带,大部分时间录音机里放的都是我的英语磁带,后来流行随声听,我好不容易拥有了一台灰色的迷你随声听,这个录音机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它在我的写字台上摆了一段时间后,我对我妈提出抗议,太占地方了,我的书都没处搁,那时我的嘴脸全是嫌弃,完全忘记了我第一次见它时兴奋到嘴角抽搐的样子。我妈也苦于家里太小,东西太多而烦恼,最终它和那一抽屉磁带被打包放到了楼下的小煤房。当年住楼房的人,每户都会分配一个小煤房,有点像现在的地下室,不过小煤房在地上。小煤房的用途不止用来放冬天的煤,它还可以放自行车,放杂物,它在某种意义上缓解了楼房的逼仄压力。
广场听秦腔的都是各处涌来打工的人,我爸偶尔也会凑热闹,不过他不愿意围过去,况且那声音吼得几条街都能听到,也不用凑得太近。第一次见识到的时候我也围过去,可很快就退了出来,那个包围圈里的味道实在是太呛人了。白天打工凭力气吃饭的人,身上没有点劳动的味道,那岂不和不劳而获一样可耻。我看着这些朴实的人们,他们的每一滴汗水都洒在我居住的这片土地上,没有他们,这个城市以及千万个城市不足以谈发展话繁荣。建设阶段和革命阶段一样,总有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人匍匐着前进,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一座城的昌盛,大海之所以宏阔,是因为有千万条河流奔向它,汇集而成,而我们的幸福也是因为这些善良的脊梁成全。
图书馆和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是全国各地的标配。走到哪都会见到似曾相识的一间铺面,不同的只是店面大小,店员的模样,书店里的书排面不排面。
我在老家就去过一次新华书店,是刚上小学,爷爷带我买《新华字典》。《新华字典》是上学的标配,和九年义务教育一样,是人生的必需品。转学过来后,我家离鼓楼很近,从县城来首府的人都很喜欢逛街,而我像个另类一样,讨厌店铺的嘈杂与熙攘,对衣物又天生的没有额外要求。可我还是喜欢跟着大人们流连忘返于鼓楼、新华街一带,是因为在鼓楼的一角就有一家新华书店。我第一次进去,是一个冬天干冷干冷的星期天,那会儿快过年了,我妈为了方便自己带着老家来的亲戚们扫街买年货,把我带进了书店,一进门,书店暖和得像夏日,我还没有柜台高的个头,够着脖子看里面的书,货架上的书多得让我鼻梁渗出了汗珠。我妈对售货员说,来一本《西游记》,这是在来的路上我妈就问好我的,当时电视里还在播到今天都视为经典的“83版西游记”,以当时的我有限的文学知识而言,我能想到的也就是这本书。然而营业员斜看了我一眼,说,没货。这个营业员俊不俊的我不记得了,我的眼睛和注意力都在书架上一排排整齐排列着的花花绿绿的书上。不过营业员并没有不再理会我们,而是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安徒生童话》,对我妈说,现在孩子们看这个书的多。我妈并不知道安徒生是谁,但她懂“童话”是什么意思,她以为是孩子说的话,她觉得应该适合我看,我就是个孩子嘛。我也不知道安徒生是谁,可我懂“童话”的意思,我更喜欢的是它精致的封面。这应该是我的第一本课外读物,可惜它早就在时间的流转中消失不见,在这漫长的时光中,消失不见的不只是实物的书本,还有本应该被我铭心记住的封存的记忆,它们都在岁月中被我就着一餐餐饭食幻化。唯一庆幸的是,从此后,我的课余时间大部分都是在这里消磨,我的零花钱也基本上投资给了新华书店,看着它后来店面升级装修扩建,作为它死心塌地的投资者,我的脸上洋溢着傲骄,总觉得它建筑中的某几块砖是我资助的。可随着网上购物的兴盛,我在当当网这些网上书店买书得到的实惠和折扣是新华书店不能比拟的,那种花一百块钱就能买一箱书的快感在新华书店永远无法体会到,就像坐在新华书店的楼梯口看书的惬意一样,在网上你也永远无法获得。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总是得到此会失去彼,那种所谓圆满的快乐,就像嫦娥奔月,我们抬头望着明月,以为它代表团圆与美满,却不知它也存储了嫦娥的孤寂与相思。
鼓楼的一角是新华书店,玉皇阁的一角竟是图书馆。我不想深究建设者的深层用意,但我从它们的位置体会到了执政者的良苦用心。自古以来我们就奉行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念,一座城市对文化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它的文明程度。我们大概用了太长的路和太深刻的教训才懂得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市中心的繁华街角,用一片寸土寸金的土地盖书店和图书馆,这无疑证明了管理者倡导读书的决心与力度。
我转学来后,经常去书店,却很少去图书馆,因为我太喜欢在书上勾勾画画了,我第一次借书就把借来的书画得乱七八糟,那是一种无意识操作,最后图书管理员要我买来一本一模一样的书赔偿,否则要罚款。没办法,我只能背地里把爷爷塞给我的零用錢买来一本新书换回了那本旧书。其实这之前书上也有其他人留下的痕迹,不过他们都没被管理员发现罢了。自此后,我对借书有了阴影,以后的日子我很少借书,这就逼得我咬牙攒钱买书,当然那时候课业比较重,我买的书也是有限的。加之我妈认为凡是和考大学无关的一律叫闲书,包括她给我买的那本《安徒生童话》也被她没收,假期才还给我。所以我的买书行为都是地下活动。我妈也和专家一样认为读书重要,可她心目中的书就是为了考试生产的书,其他的一概是废品。这是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母亲的共识。而今,斗转星移,时代变迁,母亲们的共识也不可同日而语,不管孩子想读还是不想读的书,她们都会慷慨解囊,现在你但凡走进银川市某个家庭,孩子的房间都会有琳琅满目的书籍,没有哪个家长会因为孩子喜欢课外书而气急败坏。
我到了高三的时候才发现了图书馆的另一个用途,就是自习室。那是一间有三个教室那么大的房间,一排排黄色的像画案那么宽大的桌子,一张桌子面对面可以坐八个人。我第一次去那里是一个周末,本来高三我们几个同学都报了数学补习班,等到了教室才被通知老师家里有事取消了补课,那是学校老师的义务补课,我们一分钱都不掏,所以大家都没任何怨言地准备回家。不过话说回来,在没有微信、QQ、电话的年代发生这种事也再正常不过,谁都不会觉得意外与愤怒。换作今天,不知会招来多少家长的抱怨,而且这样的义务补课也不敢想象,现在免费的除了父母给你的,其他的想想都是多余。
我垂头丧气地从教室出来,想到周末要在家面对母亲的管制,心情就灰暗得很。我其实是一个没有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但从小被父母留给爷爷奶奶抚养了十来年的我,和父母有种说不清的隔膜,我不会像妹妹们一样在他们跟前撒娇,也不会黏着父母,相反的,我时常想逃离他们。我妈是个营业员,她周末几乎没有休息,可那天我妈因为家里有事请假了,所以即便周末上课很累我也不怕,还有点开心。可老师突然的“罢课”让我脸色阴沉。
和我一起补课的同学问我不上课去哪,我沮丧地说除了回家还能去哪。她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图书馆自习。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们拉着我说去了就知道了。我们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没用一会儿就到了图书馆。我以前在图书馆二楼借书,她们领着我去了二楼借书处的另一侧,转过楼梯后我看见了一个大大的门扇,里面坐了一些人在看书,有学生也有大人。我抬眼看见门头上挂着一块匾,写着:自习室。
进门后,我们几个人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我们把书包里的书和作业掏出来,各自开始看书写作业。我的同学她们是常客,很快就投入到学习中去。而我好奇地四处观望,自习室里有和我们一般大的学生,也有小一点的,还有一部分成年人,都在埋头苦学。离我不远就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我看她放在背包旁边的书是什么注册会计考试用书。我为同学带我来这么有氛围的学习园地而开心,斯时我不知道这是收费的。等到管理员来划卡的时候,我才知道在这里学习包月十元钱。临时来的一天五毛钱,学习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七点,中午管理员休息,来学习的人请自便,有很多人都是有备而来,带着面包和杯子,图书馆免费提供开水。我同学她们都有自习室的包月卡,我要交钱,她们抢着帮我划了卡。我很感激,不过第二次去我就办了一张卡,我太喜欢这个氛围了。这之后的节假日我除了书店又有了新的去处。只要是去学习,我妈都不会反对。
我们写了一会儿作业,那个看会计书的女的被一个男的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那个女的回来收拾书本,她的脸色很不好看,好像还哭过,我回头看了眼门口,那个男的牵着一个小朋友怒气冲冲地等着。女的背着背包走了。我旁边的同学压低声音对我说,这个女的一来看书就被她老公喊回去,上个星期两个人在自习室门口还吵架了,男的只想让女的在家做饭带孩子。结了婚的女人真可怜,我以后可不要嫁人。这个对我说以后不要嫁人的女同学,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在家相夫教子,反而是我这个对此事并无太多感受的人到今天还在围城外徘徊。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我看过多遍,书里那句关于婚姻的名言:“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我刻在了骨子里。
在图书馆除了学习,还成全了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最朦胧最纯真的情感世界。喜欢一个人,最初的想法更多的不是占有,而是存在。就希望和这个人能多一些时间相处,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什么似乎都有无穷的力量。后来我想这可能和我们当时没有手机,没有iPad,没有网络有很大关系,能对我们产生诱惑和刺激的事实在不多。对于男女之间的情事,我们只是出于本能的好感,并不会产生过度的想法。当然,这是对于多数人而言,个例必定存在。
——徐州市鼓楼小学校
——以高增鼓楼为个案的分析
——走进福州市鼓楼第五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