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新作,过誉了
邹迪阳

电影《怪物》的主人公凑和依里
电影《怪物》的海报上,主人公凑和依里的目光径直投向每个路人,两张幼小而童稚的脸爬满了泥污,仿佛在暗指他们未被世俗熏染的内心。
2018年凭《小偷家族》问鼎金棕榈、再攀职业生涯高峰后,是枝裕和便向许多大导看齐,开始将重心迁向海外。期间推出的《真相》《掮客》虽都入围了欧洲三大主竞赛,但在媒体和观众间只落得“止步于中庸”的评价。不少人预言:是枝裕和已开始走下坡路,《小偷家族》是其最后的才华证明。
以此为标志来看,《怪物》的诞生,像是一种忙于自我修正的策略。毕竟,“去国远游”是门玄学,很多在这件事上摔跟头的导演,都得重返主场才能拾回创作的从容感。
在卡司阵容上,除了有坂元裕二执笔,《怪物》还请到了二搭的安藤樱,更有配乐坂本龙一的遗作光环……
但坐进影院里,我并未收获如期的情感轰鸣。取而代之的,是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操纵,或曰“背叛”。《怪物》就像个剥洋葱似的魔术,不断撩拨起人们解谜的冲动,只是在其精心编织的结构下,满是机巧的设计和切痕,鲜见是枝裕和最娴熟的对日常肌理的刻写。
谁孵化了那只“怪物”
《怪物》的开头,以某个小镇上发生的火灾为起笔,随后迅速搁置了这一线索,转向“是枝化”的日常白描:安藤樱饰演的单身母亲早织,靠开洗衣店拉扯着儿子麦野凑。最近,孩子身上多了些异样的征兆(被扯伤的耳朵、丢失的鞋子、剪掉的头发),憂心忡忡的她追问无果,只能杀到儿子所在的小学,找校方要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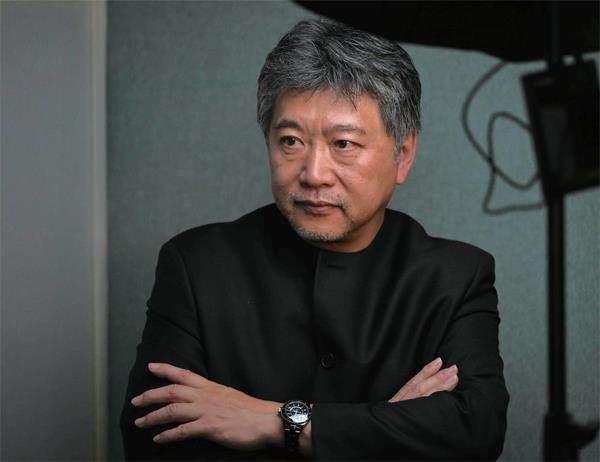
导演是枝裕和

电影《怪物》的编剧坂元裕二(左)与配乐坂本龙一
但凡栖身于压抑社会体制和俗规下的个体,都可能被不理智的情绪吞噬,走向异化。
这一整段的情感逻辑和布局,都紧扣着“母亲”视角,观众得以顺势代入其紧张、焦灼的监护人身份,察觉到一系列水平面下“不合理”的冰山:在车上聊到结婚成家时,儿子为何突然跳车;校方客气的假面和道歉“声明”下,究竟隐瞒了什么;被控诉体罚的体育老师保利,怎么看起来毫无知耻悔罪的态度?
至此,影片行进到半个多小时,便已弥散开许多烟幕。直到后两段分别以保利和主人公(凑和依里)为主体的情节释出,观众才得以还原整个故事的全貌。另一方面,这种严整的三段式演绎,也揭开了影片核心的文本技巧—“叙诡”(narrative trickery),即通过肢解真相、将拼图打碎后重组,诱导观众去体会世界的复杂和多义性。
影片最大的谜团,无关具体的火灾、校园暴力、同性情谊等明线,而是片名所裹挟的疑云:“怪物”是谁?又是谁将它带到了这个世上?答案则藏在错综曲折的迷宫内。
比起传统的各自为营,片中三个段落都埋了些伏笔,用来推翻或为前文找补:被指虐童的保利老师,其实是个阳光心善的人,在拉架时不慎碰伤了凑的鼻子;被目击和依里扭打的凑,对前者心存好感,却害怕被同龄人起哄而唤醒了“恶”的种子;表面和蔼的校长,在超市伸腿绊倒孩童,曾在倒车时意外轧死孙女,让老伴来蒙受牢狱之灾。
与其说这些赤裸裸的人性刻画,意在为角色赋予明确的性格和立场,毋宁说,当中丛生的暗礁湍流,折射出的恰是现代社会中流言和背刺的杀伤力,以及人如何自囚于主观经验的促狭。
换言之,所谓的“怪物”可以是任何人,但凡栖身于压抑社会体制和俗规下的个体,都可能被不理智的情绪吞噬,走向异化。
这个推论当然是“正确”的,创作者藉由多处细节渲染,奏出极强的警示意味。但诡异的是,影片并未以此为重点进行深挖,反而在第三段搬出抒情式的尾调,继而猛踩油门,驶向了空泛而经不起敲打的社会隐喻。
一服真空的安慰剂
“唯一真实的乐园,是我们已经失去的乐园;唯一有吸引力的世界,是我们尚未踏入的世界。”
影片末尾,坂本龙一《Aqua》舒缓的旋律中,当凑和依里从被压垮的小火车厢中奇迹般“复生”,在阳光下肆意奔跃、呼喊时,我的脑中闪过普鲁斯特这句话,怅然之余,又很快被提醒着银幕上这方小小的自由天地,是以何为“代价”建成的。
和层层递进的视点一样,在场景的设置上,影片选取了家庭、学校、小镇三个主要的切口,来描绘“怪物”所处的生态系统(培养皿)。与充斥着隐性规训的“表世界”相对照的,则是凑和依里的秘密基地—森林内一节废弃车厢。也是在这个几无外在威胁和凝视的地界内,我们才能直观看到两个主人公之间萌动的情愫。
《怪物》更像一篇落笔奇峭的议论文,连同每个登场的配角,都在道德漩涡中打转。
在着手进一步说明前,有必要提及另一部被不少人拿来对标的电影,即2022年获戛纳评审团大奖的《亲密》。二者共享着同种情感羁绊,并且在由此衍生而来、对有毒男子气概的抨击上,也做了一番自觉的尝试。
无心插柳的巧合,足可视为近年来性别气质之争的风向标。二者一大特点,都在于话题自身的辐射性:基于男性友谊之花的夭折,讲述社会成见对于异类的驱逐和戕害。
然而,调性上最大的分野,在于《亲密》具有导演德霍特本人的自传属性,遵循了心理剧的模式,采用大量特写和跟拍,来反映主人公的挣扎。如果将其喻为一篇特稿,《怪物》更像一篇落笔奇峭的议论文,连同每个登场的配角,都在道德漩涡中打转。
拿凑的母亲早织来说,在丈夫和出轨情人一道丧生后,她对儿子隐瞒了父亲的死因,还将遗照摆在家中显眼的位置,期许凑能以父亲为榜样长大,并告诉他男孩知道太多花的名字,不会讨女生喜欢。
和凑一样,依里也有个残缺的原生家庭。父亲终日活在妻子出走、职场不如意的苦闷中,遂将仇恨转移到文弱儿子身上,怒斥其为“猪脑”,并擅自决定让依里转学,试图以此矫正。
体育老师保利,则会在课上目睹凑摔倒时,调侃道:“这样还说自己是男人吗?”他化解学生冲突的方式,是鼓励对方“像两个男子汉那样握握手”。
谜底揭晓后,观众方能意识到,无论家长、老师、以校长为首的公职人员,还是结群排挤依里的同学,都曾在某个时刻,扮演了加害链条上沉默的一环。
这种集体性的轻率和漠视,正应了是枝裕和在戛纳接受采访时的发言:“某些形式的爱意的表达,对于另一方来说其实是一种暴力,这一点是很残忍的,且并不专属于东亚家庭。”
就此而论,影片并未拘泥于传统的日式BL情结,“酷儿”的语义在此延绵、扩展为所有被主流观念判为“异端”“病态”的群体(最有力的他证,便是被舆论处刑的保利老师)。
在善恶游移的屏障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灰度、苦衷和“免罪”金牌,但也很难在有限篇幅内碰撞出完整的主体性。他们的存在,更像是为了搅浑观众视线,或输出一些高亮的台词。

電影《亲密》剧照
艰难的转型之旅
在围绕《怪物》的讨论中,有一种声音颇值得玩味:编剧坂元裕二才是那个占主控权的人,是枝裕和身为导演的存在感则被大幅度削弱。
这种观点,既源于影片花哨的文本修饰,也让我们得以反观是枝裕和的优势所在。《无人知晓》里枯死的花盆,《奇迹》中飞驰的新干线,《小偷家族》那场只闻其声的烟花……这些日常符号,彰显出创作者对生活熟稔的捕捉和提炼。
这也是为何,是枝裕和的电影既能跻身艺术片殿堂,也能向普通人敞开探索的大门。每个攒够了经验和阅历的人,都不难从中悟出那个道理:生活的戏剧性或不在于“偶然”闯入,而在于闲笔的划拉中,点滴滋长出来,如同安然度日也是一种“抵抗”。
当这种散漫的美学诉求与更具规则的商业类型叙事相溶时,导演不得不像踩钢丝一样,在把控宏观情节的同时,不埋没自己以小见大的本领。如果说《第三度嫌疑人》在踉跄学步之余,尚能透出些许破茧的决心,前作《掮客》对于婴幼贩卖现象的指涉,则因着强拗的“全员善人”设置,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虚浮感。
到了《怪物》,我们或能记住一些残余的灵光,譬如两个男孩躲在车厢玩猜谜,几度吹响的铜管号,以及台风天里怎么也擦不净的车窗。但,它们更像是强设计的配方里,匆忙撒了些调味,随后任其被呛鼻的油烟盖过。
补刷了一圈编导的采访后,我才逐渐反应过来,这种看似任性、图省事的做法,正代表着两位年逾半百的创作者,对成人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拒斥和失望。就像片尾砸在每个大人身上的滂沱雨点,对其施以惩戒,以反衬孩子们的“纯爱”是何等勇敢。
可矛盾在于,既然主创深谙“人不是非黑即白的”,那理应往前一步斟酌,难道清除了名为误解的毒素,就能让“怪物”得救吗?或者说,这样的世界当真存在吗?对于幸福的捍卫,对于自我价值的确证,必然是在自我与世界的反复博弈中,才成为可能,而不是让他们喊一喊“时间倒流、宇宙坍缩”之类看似浪漫却不着边际的空话。
意欲将笔锋拐入社会的幽深处,却又跳不出自我设下的陷阱,除了导演控制力的衰落,这也和坂元裕二初涉电影工业受到的掣肘有关。成名于互联网萌芽期的他,最拿手的便是对各色都市人群的摹状。“坂元式金句”一度刷屏社交媒体,成为某种情感哲学的写照。
遗憾的是,纵观坂元裕二近年来编剧的作品,无论《花束般的恋爱》还是《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都在无形间向着流行(网红)文化渗透,曾经怡然的碎碎念变得越发速食化,多了些溢出的匠气。《怪物》亦复如是,本该用单元剧形式去承载的剧本,却强行被三段结构吞并,而在这种“日常”和“非日常”的相互抵牾中,影片余味尽失,徒留满是戏剧性激烈的切片。
至于豆瓣8.6的高分,究竟沾了多少教授(坂本龙一)和题材的光,很难一言以蔽之。
特约编辑姜雯 jw@nfc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