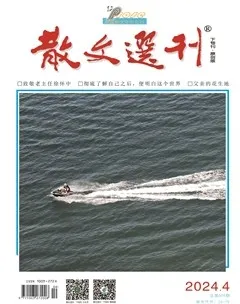回家
张玉

我出生在松花江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小时候,爸妈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爷爷和老叔把我接到了他们的家。日子过得好好的,出了正月的门,不知为什么爷爷和老叔分了家。分家的时候爷爷什么也没拿,领着我走进了一间多年无人居住的半小土屋。
那年春天,爷爷领着我到集市上,花光了他所有积蓄,买了十几只鸡雏和满脑门上长着黑花的猪崽。秋天的时候,小鸡崽长大了,下蛋了。爷爷做了我平生第一次吃到的蒸鸡蛋糕、焖米饭。爷爷蒸的鸡蛋糕,滑滑的、嫩嫩的,上面还撒着星星点点的葱花,拌米饭吃特别香,可他一口都舍不得吃,坐在桌边看着我狼吞虎咽地造,还边看边说:“吃饱饱的,快点长大个!”我好奇地问:“爷爷,你怎么不吃呀?”可爷爷总是说:“还是盐豆好吃,自己种的豆香啊!”盐豆就是把大豆放进锅里炒熟,放点盐水和葱花搅拌一下,焖一会儿,盐豆就做好了。有条件的放一点儿酱油和香油味道会更好一些。那时,我和爷爷的生活条件极差,根本买不起香油之类的调料品,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我十八岁了,学业无成,整天游手好闲,这一年,爷爷把我送到同村一位在城里做房屋装修的大伯那里当学徒。爷爷认为大伯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叫我一定要跟着他好好干。刚一见面,那位大伯看我长得又瘦又小,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说我只能干点零活,给口饭吃。学徒是没有工资的,爷爷爽快地答应了。
进城之后,我每天的工作是装卸废旧建筑材料,有时间就给负责装修的大伯打下手,类似倒沙子、搬水泥……一些重体力的活。一年到头我没有挣到一分钱,看到伯父家里的几个工人都在准备过年时的生活用品,我有些沮丧,突然间想回家,想家里的爷爷了,竟当着老板大伯的面哭起了鼻子。
第一次回家,我拿出临出门时爷爷给我的几十元过河钱,给爷爷买了一只他老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吃过的烧鸡。火车上又困又饿,望着包里的烧鸡,垂涎欲滴,我强忍着口水,火车开过几站地后,我还是没有忍住,小心地掰下烧鸡的一个翅膀,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食不甘味地吃了。下车了,我拿着剩下仅有的几元钱理了发,吹了风,装出很体面的样子。
爷爷已经摸不到我的头了,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高兴地说:“我的娃儿长高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当天,我又吃到了久违的鸡蛋糕、焖米饭,小肚子吃得特别鼓、特别圆,幸福地哼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年夜饭的餐饭上,爷爷摆上了断掉一只翅膀的烧鸡,一碗我永远都吃不够的小鸡炖蘑菇。爷爷点亮了一年都舍不得用的电灯,坐在我的身边,目光久久地注视着我,一刻都不想离开。我猜出了爷爷的心思说:“明天我不走,后天也不走。”爷爷寻思半天才放下手中的旱烟袋,和蔼地说:“该走就得走,男子汉在外面闯一闯才有出息!”
又一年快过完了,天越来越冷了。
对于一个学徒工来说,积累的不是金钱,只有增长的年龄和精湛的技术。还好,老板大伯看我平时工作努力、装修技术学得扎实、干活干净利落,破格給我发了两千元的奖励。这一次,我用自己赚的钱,给爷爷买了两只最爱吃的烧鸡,几斤上好的哈尔滨红肠。到农贸服装市场给爷爷买了一件纯羊皮的军用大衣,一身新棉衣棉裤,几双爷爷喜欢穿的军绿色的袜子,还有两双棉胶鞋。
火车上,我第一次吃了一盒快餐,两根红肠,感觉很饱、很充实。下车的时候,我又到附近的理发店吹了一个最帅的头型,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爷爷和往常一样,披着一件破棉袄,抽着旱烟,见我回来,磕磕手里的烟袋锅,第一时间又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蒸鸡蛋糕、焖米饭,鸡蛋糕还是那么好吃,滑滑的、嫩嫩的,我对爷爷说:“教我蒸鸡蛋糕的手艺吧。”爷爷说:“没耐心的人是不会掌握蒸鸡蛋糕技巧的,蒸久了会老、时间短了会生,要火候和时间恰到好处才行。”我似乎听出了爷爷的话外之音,好像在说:爷爷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老了,可我还没有成熟长大,没学到生存的本领。我在心里说:爷爷,我会长大的,我一定会学到生存的本领。
年三十,爷爷把我买的两只烧鸡全都端了上来,红肠切了满满的一大盘子。这一次,爷爷像个孩子,穿上我买的衣服鞋袜,拿着我交给他的钱,在附近的小卖店买了小烧,饭桌上爷爷给我也倒上一杯,我和爷爷的脸都喝红了。灯光下,看着爷爷日渐消瘦的脸上,越来越深的皱纹,那铺不平的深沟里不知刻着多少岁月的沧桑,为了抚养我长大,背后不知付出了多少辛酸。我又一次流泪了,发血誓,一定要好好学本领,多挣钱,在城里给爷爷买个大房子,让他老人家享几年清福。
几天以后,我又要走了,爷爷只是拉着我的手,和我走到村头就停下了。爷爷老了,走不动了,当我回过头看爷爷的时候,爷爷正蹲在白茫茫的雪野之中,蹲在生长着高粱和大豆的地边,蹲在送我去诗和远方的起点,向我摆着手,示意让我快走,不要回头。我的眼泪没有控制住,又一次迎着西风,在松花江边的羊肠小道上一路小跑着。
后来,我果然不负爷爷所望,在省城开起了美术装潢的分店,钱像我的年龄一样递增了。最近几天,总在梦里梦到爷爷,不是梦到爷爷送我出门的画面,就是梦到爷爷给我做了一大桌子好菜,看着我吃。我白天精神恍惚,心情也很压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不出我所料,上午十点,我接到了家乡小姑的电话:“大宝,快回来吧,你爷爷可能不行了!”我的头“嗡”的一声,心跳加速,眼前一片空白,还没有回过神来,电话那边的小姑带着哭腔大喊:“爸!爸!!爸!!!”我如五雷轰顶,瘫坐在地上。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回家,回家,我要回家!这一次我什么也没买,坐汽车、赶火车,饭吃不进去一口、水喝不进去一滴,像一个被掏空的机器人,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进村时,我没有理发、没有吹风、灰头土脸地一步一个头磕到爷爷的灵前。攥着他老人家的手不肯撒开,絮絮叨叨:“爷爷,孙子回来晚了,孙子长大了,挣钱了,今年准备在城里买个房子,接您享福呢,爷爷,我还没吃够您给我蒸的鸡蛋糕呢……”
爷爷走了,我心中的避风港也被爷爷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