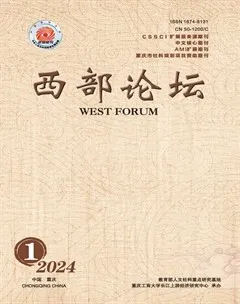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县域经济;金融排斥;长尾效应
中图分类号:F294.27;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4)0-0018-14
引用格式:梁桂保,张利杰,刘葵容.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J].西部论坛,2024,34(1):18-31.
LIANG Gui-bao,ZHANG Li-jie,LIU Kui-ro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abor mobility and county economic growth[J]. West Forum, 2024, 34(1): 18-31.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域内,以城镇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和利用各种经济社会资源而形成的功能较为完备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综合性区域经济系统。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而且是联结城鄉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目前我国县域的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经济能级总体较低。同时,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使得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资源要素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受到基础设施不完善、资金和金融服务不足、劳动力流失等多方面的约束(杜鑫,2022)[1]。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其中,数字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催生并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向社会各主体提供机会平等、成本可负担的金融服务为重要目标,能够突破地理限制,扩大金融服务范围,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郭峰 等,2020)[2],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的缺陷,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功效来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尽管传统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加速资金回流、推动产业发展、带动创新创业等路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刘冲 等,2019;康继军 等,2020;张珩 等,2021)[3-5],但传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局限。一方面,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传统金融机构的空间布局存在非均衡性,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密度普遍低于城市,导致县域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县域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尹振涛 等,2016)[6]。另一方面,基于风险控制的要求,传统金融服务的门槛较高,且审批严格,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排斥(康继军 等,2020)[4],削弱了金融服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姚梅洁 等,2017)[7]。总之,由于县域经济能级偏低,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与金融机构的客户需求和偏好存在一定差距,降低了传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及实际效果(周孟亮 等,2023)[8]。而数字普惠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其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开展各种金融服务(Gomber et al.,2017)[9],具有广覆盖、低门槛、高效率等诸多优势,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随着数字金融的持续发展,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不断深化。国内相关实证检验的结论大多支持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观点,然而已有文献的经验分析大多基于省级区域层面,较少从城市和县域层面进行验证。由于省级区域的地域范围较大,且省内的地区差异明显,仅从省域层面进行研究不利于全面细致地把握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机制。粟麟等(2022)分析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该作用对西部县域、贫困县域、金融排斥较强县域更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提高资本配置和产出效率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0]。汪雯羽和贝多广(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政府干预对该影响具有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11]。潘启娣(2023)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县域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三条路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12]。刘鑫和韩青(2023)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传统金融效率提高可以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3]。
总体来看,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但相比省域层面的研究,县域层面的经验分析较少,而金融排斥更多地体现在县域层面,县域经济发展获取金融支持的难度更大(粟芳 等,2016)[14]。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同时,从作用机制来看,已有文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拉动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缺陷、增进资本积累、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及地区创业等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增长)的路径(王儒奇 等,2023;尹少华 等,2023;鲁钊阳 等,2023;王文姬 等 2023;张蕊 等,2021;宇超逸 等,2020;钱海章 等,2020;齐美东 等,2023;张贺,2021)[15-23],但缺少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机制研究。尽管有研究论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要素配置的影响(王儒奇 等,2023;徐伟呈 等,2022)[15][24],但还未涉及要素流动层面,且更多的是讨论资本要素的配置和积累(粟麟 等,2022;宇超逸 等,2020;齐美东 等;2023)[10][20][22],鲜见针对劳动力要素的探讨,仅有徐伟呈等(2022)考察了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劳动力分工影响区域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机制[24]。一方面,地区间的要素流动是促进结构红利释放的重要方式(王振华 等,2019)[25],合理的劳动力流动能够有效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王婷 等,2020)[26],并对劳动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改变本地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进而影响劳动力的流入和流出。因此,有必要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县域为研究对象,从劳动力流动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以深化和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研究,并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系统融合发展的产物,能够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有效缓解传统金融因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造成的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低成本、广覆盖等特点,可以显著缓解传统金融存在的金融排斥,促使弱势群体有更多机会获取更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地区的投资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具体来讲,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拓展了长尾客户群体。作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是促进县域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但是,在传统金融体系下,资本量和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等县域经济主体通常会面临比大型企业和城市经济主体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而且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往往也较高,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手段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获取成本(谢获宝 等,2022)[27],还能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存贷服务流程、简化支付方式等途径降低交易成本(邢赵婷 等,2023)[28]。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的降低使金融主体更有动力和可能拓展以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为代表的长尾客户,有利于缓解县域经济主体的融资约束,进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增加县域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以线上模式为主的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的地域限制,能够实现金融服务广覆盖,有效弥补因金融机构物理网点密度小引致的县域金融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傅秋子 等,2018)[29],从而显著增加县域金融资源供给。同时,金融资源与劳动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可以有效促進县域生产力增长,释放县域结构红利(王振华 等,2019)[25],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因此,作为一种缓解县域经济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有效手段,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排斥程度各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宇超逸等(2020)、何宜庆和王茂川(2021)分析认为,数字金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20][30];方先明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金融排斥效应越强的地区越显著[31];陈啸等(2023)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32];粟麟等(2022)的研究也表明,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县域、贫困县域、金融排斥较强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较强[10]。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优势在于其“长尾效应”,即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和提高金融服务可达性,将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客户群体纳入服务范围,促进县域金融业务的增长。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关键在于将金融服务范围延伸至更多的县域中小客户,满足被传统金融长期排斥在外的长尾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有效发挥其普惠效应。相比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水平总体上相对较低(江红莉 等,2023)[33],金融排斥更加严重(粟芳 等,2016)[14],金融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情况更为普遍,此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产生更强的“长尾效应”,从而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2:相对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2.劳动力流动的中介作用
一般来讲,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劳动力流出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长期以来,人口外流带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过度流失问题严重阻碍了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发展的进程(张杰 等,2019)[34]。以青壮年为主的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乡村振兴缺乏中坚力量支撑(彭长生 等,2019;陆杰华 等,2021)[35-36]。劳动力回流则会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第一,劳动力回流会产生聚集效应,不仅能够增加县域劳动力总量,也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回流劳动力不仅可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资金和技术支持,还会成为重要的消费群体,进而引发产业聚集和消费拉动效应;第三,高技能劳动力回流,除其自身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外,还会产生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从而形成乘数效应;第四,返乡劳动力中以创业为目的的主动回流会直接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见,劳动力回流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智力流失和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本文用“劳动力流动”指代县域劳动力的净流入,劳动力流动增长是指县域劳动力流入的增加或劳动力流出的减少。因此,如果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劳动力流动增长的作用,则促进劳动力流动成为其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获取门槛和成本,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谢绚丽 等,2018;杨佳 等,2022;熊德平 等,2022)[37-39],这不但有助于吸纳本地劳动力以减少劳动力流出,还能吸引劳动力回流和外地劳动力流入。人口迁移是迁移者在成本与收益比较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推拉理论认为,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可以分为推力和拉力。从推力来看,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减小对劳动力流出的推力,从而降低劳动力流出规模。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低成本和便利的融资渠道,有助于提高本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减少劳动力外流的动机;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和智能风控模型的开发应用,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加精准地评估项目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及贷款项目质量,使劳动力获得更稳定可靠的就业和发展机会,降低失业风险。从拉力来看,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加大对劳动力流入的拉力,从而扩大劳动力流入规模。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拓宽当地创业者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对个人和家庭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包含理财、保险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提供了更丰富的投资渠道,有利于居民投资性收入的增加;与此同时,数字化支付等服务的应用增强了县域居民生活的便捷性。县域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增加、生活品质的提高均有利于增强对劳动力流入的拉力。此外,我国县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巨大,数字普惠金融为县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有利于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县域发展红利(方君娟,2022)[40],进一步增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三、实证检验设计
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为检验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提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pgdpit=α0+α1indexit+α2XCONit+μi+λt+εit
其中,i表示县域,t表示年度,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pgdp)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县域人均GDP来衡量,该指标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李彦龙 等,2022)[41]。核心解释变量(index)为“数字普惠金融”,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进行除以100处理),该指标涵盖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和33个具体指标,能够科学全面地反映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参考潘启娣(2023)等的研究[12],选取以下控制变量(XCON):一是“收入水平”,采用县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用以反映县域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财政依存度”,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用以反映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三是“产业结构”,采用县域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之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四是“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
为检验劳动力流动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中介作用,参照温忠麟等(2022)和程方方等(2013)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42-43],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migit=β0+β1indexit+β2XCONit+μi+λt+εit
pgdpit=η0+η1indexit+η2migit+η3XCONit+μi+λt+εit
其中,中介变量(mig)为“劳动力流动”,采用县域劳动力净流入率来衡量。参考段平忠(2013)和史桂芬(2020)等的研究[44-45],假定90%的迁移人口为能够参与劳动的适龄人口,则劳动力净流入率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乘以90%再除以户籍人口”,劳动力净流入率大于零的县域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小于零的县域为劳动力净流出地。
2.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我国县域为研究样本,由于县域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2014年才开始统计,以2014—2020年为样本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县域宏观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县域样本,使用插值法对个别缺失数据进行补充,最终获得1 754个县(市、区、旗)的面板数据。由于控制变量及工具变量的数据存在部分缺失,人工剔除不但会损失样本容量,还可能破坏样本的随机性,因而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王珂英 等,2016)[46],这也是实证检验中样本量发生变化的原因。
本文运用Stata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限于篇幅,具体结果略,备索),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与控制变量“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关系数最高(0.658),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0.8以内,表明变量间的独立性和可区分性在可接受范围内;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最大的VIF值仅为1.9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F检验与豪斯曼检验进行模型筛选,结果显示:F检验统计量为50.40(Prob>F=0.000 0),表明个体效应显著,拒绝使用混合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统计量为616.67(Prob>chi2=0.000 0),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将采用同时控制年份效应和县域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2)列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本文提出的假说H1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别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的(3)(4)(5)列。“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的发展均能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从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来看,“覆盖广度”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明显大于“覆盖广度”的系数,“数字化程度”的系数又大于“使用深度”的系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化程度提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使用深度加深的促进作用次之,覆盖广度拓展的促进作用最小,这与范晓莉(2023)的研究结论相一致[47]。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拓展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小的原因可能在于,该维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基于支付宝的账号、用户及使用情况,而支付宝的使用者主要是个人,未能全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状况。
2.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一方面,县域经济的发展会提高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理财、投资等金融活动,从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众多,回归模型难免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为缓解由于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等引发的模型估计偏误,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参考郭峰等(2017)、黄群慧等(2019)、田杰等(2021)的方法[48-50],选取两个工具变量: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滞后1期项(“L1.数字普惠金融”),前一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不会受到当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可以排除反向因果關系的影响。二是样本县域到杭州球面距离与上一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互项(“距杭州距离×L1.数字普惠金融”)。再借鉴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和刘松涛等(2023)的做法[51-52],将两个工具变量同时纳入模型,采用2SLS法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Panel A。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F检验值远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依然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进一步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夜间灯光亮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hen et al.,2011;Hendersno et al.,2012)[53-54],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GDP数据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及受地区间价格因素干扰等问题,参照李彦龙和沈艳(2022)的研究[41],使用VIIRS灯光亮度DN的总值除以栅格数得到县域平均灯光亮度(“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二是增加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加入“消费水平”变量。三是对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上述检验结果见表4的Panel B,“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3.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将样本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组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吉林、黑龙江、辽宁;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的(1)(2)列。“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都可以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从系数大小来看,“中西部地区”组明显大于“东部地区”组,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本文提出的假说H2得到验证。进一步比较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样本期间的县域平均发展水平(见表6),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县域虽然发展基础较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人均GDP均小于东部地区),但发展速度较快,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趋于缩小,表明欠发达地区较大的发展空间有助于数字普惠金融以较低成本激发“长尾效应”,从而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再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2014年发布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名单将样本划分为“非贫困县”和“贫困县”两组,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的(3)(4)列。“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贫困县”组的系数明显大于“非贫困县”组,再次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
4.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7,为避免内生性干扰,同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流动”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县域劳动力净流入率的提高;“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县域劳动力净流入率的提高有利于县域人均GDP的增长。可见,劳动力流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来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H3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在传统金融体系下,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从而可以通过长尾效应缓解传统金融中的金融排斥,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并有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不仅可以减少本地劳动力的流出,还能吸引劳动力回流和外地劳动力流入,而劳动力流出的减少和流入的增加均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数据分析表明:(1)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县域人均GDP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提高、使用深度加深、覆盖广度拓展均可以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但三者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2)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3)劳动力流动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加快传统金融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应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积极推进传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增加金融服务产品种类,拓宽金融融资渠道,不断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破解金融服务难以触达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二,打破地域限制,兼顾效率与公平,加快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继续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缓解区域间金融、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第三,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畅通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流动渠道。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不断提高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吸引人才回流,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杜鑫.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粮食生產的影响——基于2020年全国10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问题,2022(3):104-115.
[2]郭峰,王靖一,王芳,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4):1401-1418.
[3]刘冲,刘晨冉,孙腾.交通基础设施、金融约束与县域产业发展——基于“国道主干线系统”自然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35(7):78-88+203.
[4]康继军,杨琰军,傅蕴英,等.转型期中国金融排斥困境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574个县(市)数据的空间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6):44-57.
[5]张珩,罗博文,程名望,等. “赐福”抑或“诅咒”: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21(3):86-105.
[6]尹振濤,舒凯彤.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模式、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2016(1):103-107.
[7]姚梅洁,康继军,华莹.金融排斥对中国县域经济影响研究:实现路径与动态特征[J].财经研究,2017,43(8):96-108.
[8]周孟亮,王立聪.数字金融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脆弱性的影响研究[J].财经论丛,2023(7):46-57.
[9]GOMBER P,KOCH J A,SIERING M. Digital finance and fin tech: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7,87(2):537-580.
[10]粟麟,何泽军,杨伟明.数字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与异质性研究[J].财经论丛,2022(9):59-68.
[11]汪雯羽,贝多广.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42(2):41-53.
[12]潘启娣.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新金融,2023(2):46-55.
[13]刘鑫,韩青.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传统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J].中国流通经济,2023,37(4):107-115.
[14]粟芳,方蕾.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的比较分析[J].管理世界,2016(9):70-83.
[15]王儒奇,陶士贵.数字金融能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与中国经验[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7):71-82.
[16]尹少华,罗汉祥.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3(1):41-49.
[17]鲁钊阳,杜雨潼,邓琳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会月刊,2023,44(23):128-134.
[18]王文姬,夏杰长.数字金融、居民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J].求索,2023(4):96-105.
[19]张蕊,余进韬.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J].现代经济探讨,2021(7):1-9.
[20]宇超逸,王雪标,孙光林.数字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J].经济问题探索,2020(7):1-14.
[21]钱海章,陶云清,曹松威,等.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6):26-46
[22]齐美东,吴金科.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异质性与作用机制[J].财会通讯,2023(13):84-90.
[23]张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5):55-62.
[24]徐伟呈,刘海瑞,范爱军.数字金融如何驱动高质量经济增长?——基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的三重内驱机制[J].投资研究,2022,41(4):113-133.
[25]王振华,孙学涛,李萌萌等.中国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结构红利视角[J].软科学,2019,33(8):68-72.
[26]王婷,程豪,王科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人口红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兼论新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转型[J].人口研究,2020,44(2):18-32.
[27]谢获宝,敬卓尔,惠丽丽.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J].南方金融,2022(8):33-48.
[28]邢赵婷,钟若愚.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3(4):142-156.
[29]傅秋子,黄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68-84.
[30]何宜庆,王茂川.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与异质性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平滑转换模型与分位数模型的实证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1):54-64.
[31]方先明,刘韫尔,陈楚.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来自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3):40-50+146-147.
[32]陈啸,孙晓娇,王国峰.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J].经济问题,2023(6):34-40.
[33]江红莉,蒋鹏程,黄丹晓.金融集聚、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J].宏观质量研究,2023,11(1):27-37.
[34]张杰,张珂,赵峰.农业劳动力转移性流失、耕地抛荒与“柔性”政策选择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19(6):131-140+159.
[35]彭长生,王全忠,钟钰.农地流转率差异的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9(3):49-62.
[36]陸杰华,刘芹.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七普”数据的解读[J].人口与经济,2021(5):13-24.
[37]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4):1557-1580.
[38]杨佳,陆瑶,李纪珍,等.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J].管理科学学报,2022,25(11):43-68.
[39]熊德平,黄倩.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J].东岳论丛,2022,43(9):38-48+191.
[40]方君娟.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10):75-79.
[41]李彦龙,沈艳.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不平衡[J].经济学(季刊),2022,22(5):1805-1828.
[42]温忠麟,方杰,谢晋艳,等.国内中介效应的方法学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22,30(8):1692-1702.
[43]程方方,孙曰瑶.数字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差距: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J].经济体制改革,2023(4):61-69.
[44]段平忠.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3):115-121.
[45]史桂芬,李真.人口流动助推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面板数据[J].华东经济管理,2020,34(6):10-18.
[46]王珂英,张鸿武.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截面相关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6):122-129.
[47]范晓莉.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4(9):94-103.
[48]郭峰,孔涛,王靖一.互联网金融空间集聚效应分析——来自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的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17(8):75-85.
[49]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50]田杰,谭秋云,陈一明.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西部论坛,2021,31(4):82-96.
[51]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18,53(2):20-34.
[52]刘松涛,罗炜琳,梁颖欣.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FDI流入——基于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的视角[J/OL].(2023-11-16).产业经济评论, https://doi.org/10.19313/j.cnki.cn10-1223/f.20231116.001.
[53]CHEN X,NORDHAUS W D. Using luminosity data as a proxy for economic statistic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1,108(21):8589-8594.
[54]HENDERSON J V,STOREYGARD A,WEIL D N. 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outer spa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2):994-1028.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abor Mobility and County Economic Growth
LIANG Gui-bao1,ZHANG Li-jie1, LIU Kui-rong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Chongq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50, China)
Abstract: As a bridge and link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economies, advanc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new countryside. However, constrain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is weak, the overall economic capacity is low,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pace for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integration form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DIF)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promoting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ED). Nevertheless, curren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nd there is a lack of mechanism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obility, which is yet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to carry out a more in-depth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counties from 2014 to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CED in China, and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after considering the night lighting data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ounty economy and endogenous problems. Furthermore,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 on CED.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coverage and depth of use,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of DIF has a more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in poor counti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CED, reflecting the inclus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F.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labor mobility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DIF and CE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ands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one hand, unlike existing studies that mostly take the provincial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unty level,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IF and its sub-dimensions on CED,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geographical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obi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DIFs effect on CED and expands the previous path research from a brand-new perspective.
To a certain extent,our research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labor force as the most active and dynamic factor in all kinds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influence of DFI on CED, which is helpful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labor mobility guidance 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for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so a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abor mobility; county economy; financial exclusion; the long tail effect
CLC number:F294.27; F832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24)0-0018-14
(編辑:黄依洁;刘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