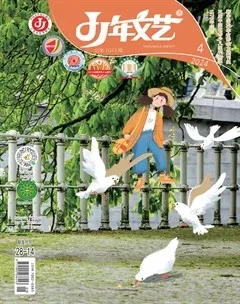弦上的梦(外一篇)
周韫

我跑几步这么一蹦,从六楼一层一层下去,这是一幢很老的黑暗的住家楼。忽然,我看见这些台阶的上空,为楼道光线所射穿的黑暗里,浮着一朵白色的柳絮,不动,静静地。向着光线这一边的绒毛,显得银亮。这个不速之客。我想捉住它的时候,它从窗户飞出去了。映着蓝天,我看见它毛茸茸的中央,有一粒种子。种子呈淡淡的黄色,顶端缀着一个小黑点。
春深了,也到了柳絮纷飞时。有一天,我在草场门大桥畔的公交站候车,那儿很开阔。不经意抬了下眼,咦,怎么漫天飘起了雪花?有点蒙,想到春雪,又否定了,这才回过神来:是柳絮。且打一下油:未若白雪因风起。
水龙头哗哗放水,老妈在洗青菜,一边洗,一边哼:“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跟谁战斗呀?”我笑问。
“跟你,”老妈把洗净的菜放到篮里,“谁让你欺负倍儿。”
这是一首老掉牙的歌,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插曲,那时我还小,还没有现在的倍儿大,没看过这部电影,听到过有人哼这首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现在没有人哼了,老妈还哼,翻来覆去就哼这两句:“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倍儿也哼,哼不全,就这两句,逢到有什么不顺心的,小组长冤枉她呀,小伙伴拌嘴呀,她就大声唱这两句,不是哼。
我和倍儿在必胜客就餐,倍儿嚷嚷:“妈妈妈妈你看!”餐桌面的底下,我们膝盖的上面,有一小朵白色的柳絮静谧飘浮,倍儿想去捉,它一闪身飘走了。这小精灵!倍儿要去追,我手臂一伸,拦住:“它在空中飞,你追不上。”
倍儿追了一阵子,不追了,问:“它要飞到哪儿去呀?”
“玩呗,玩累了回家,跟你一样。”
“它的家是不是在天上?”
没完没了,我跺了下脚:“不在天上,在地上。”
“那它为什么在天上飞哩?”
“在天上飞才能看得远,看到它地上的家。”
我愣了一小会儿神,柳絮的生命不是那白色轻盈的絮,而是絮里面裹着的小黑点,那是种子,我跺了下脚的地方是坚硬的水泥地,不是它要去的安身立命之地。
那公园里河堤上有的是泥土,怎么没见冒出一棵柳树?可见安身立命也不是那么简单。也许,漂泊就是柳絮的宿命。
受倍儿的鼓舞,把斜挎的吉他向背后推了一下,它在飞,我在追。一路追到河堤上,堤坡上繁花盛开,紫罗兰、粉色猩红小花、鸢尾、金盏。那儿有很多很多的柳絮在飞。堤岸下面,地上,有些柳絮飞不动了,就在地上粘成一个一个蓬蓬松松的大团子,风大了,它们就在地上滚,滚着滚着翻一个筋斗,挺萌的。我把吉他挪到怀里,划了一个琶音,词改换了:“启航启航启航,我们的远行像诗篇。”这是老妈洗菜时哼的。我一弹,老妈就乐。
我坐在长堤上弹吉他,十里柳堤,满眼绿,柳枝媚人,在风里摆来摆去。片片柳絮在枝条间穿过,像雪。我疯狂地弹,那些柳絮像小精灵,在我周围上上下下跳舞。有一朵柳絮快要落到我的弦上,被我一个扫弦给震飞了。
弹累了,躺在一棵柳树下,吉他搁在我的胸脯上。
手指挑起一根弦,铮的一声,又一声。
夜色深沉。一粒一粒星子,划着弧线急坠下来,到了近地的时候,化成漫天柳絮,轻轻地,柔柔地,落向堤岸下面的水波。
我一骨碌坐起来,弹那个老妈喜欢的:“启航启航启航,我们的远行像诗篇。”
光
倍兒跟我合养过三只蝈蝈。它们长什么样子,在我记忆里都比较模糊。倍儿记得,第一只是棕色的脸,第二只是蓝色的脸。她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蓝脸形象有点恐怖。
我们养过的这几只都不是哑巴,都叫。倍儿告诉我,她学习法布尔,观察蓝脸,它长得有点奇怪。脸是浅蓝色的,翅膀像两片透明的枯叶叠在一起。
刚买回来的几天,蓝脸一声不吭,我每天负责清洁蝈蝈笼,倍儿喂嫰黄瓜毛豆。它好像是被感动,“开口”了,完全放松情绪,想什么时候叫,就什么时候叫,而且越叫越欢。每天下午,它会睡上一小会儿,养足精神。大半夜叫得最响,也不怕影响旁人休息。倍儿在阳台上做作业,它也乱叫一气。嫌它烦,吓唬,让它闭嘴。可是它停了一会儿,又故伎重演。先是试探地“嚓”一声,像剪刀剪了一下,见倍儿没制止,又叫开了。它似乎也很喜欢听歌,并且伴奏似的配合。我弹吉他,不拨弦时,它也会停下来。如果弦上的声音再次响起,它就会“嚓”的一声,又清脆明亮地叫起来。倍儿悄悄对我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蓝脸的叫声并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而是靠背上的两片翅膀极速振动摩擦发出的,真的很奇妙。”我说不奇妙,昆虫都这样。
跟倍儿说,好日子不多了,蓝脸是百日虫,生命属于它也只有一次而己,不要让它的一生都在笼子里度过,我的意思是放生。倍儿爽快同意,这我没想到,虽则心里肯定是不舍得的。商议了几种方案,没有一种尽善尽美。可一个突发的事故,使我俩的计划全泡汤。我用牙签清除蝈蝈笼里的一粒屎的时候,它利用笼门打开的时机,突然冲了出去,看来是蓄谋已久。猝不及防,我用手去罩,弄折了它的一条大腿。这下不能放生了,只好另想他法,他法也没什么选项,只有为它养老送终。
天气由初秋向中秋去,我想了个法子,把台灯挪近笼子,用灯光温暖它。亮度是可以调节的,但太暗,温度上不来,不够;太亮了又怕伤它的眼睛。倍儿想了个主意,用一层薄薄的布,把笼子罩住,两全其美。我说:“这个法子好。”
日子过得真快,眼见快到重阳,园子里虫声越发稀,终至寂寥。只有蓝脸“嚓”地打开翅膀在叫,算算,早过了百日的生死大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