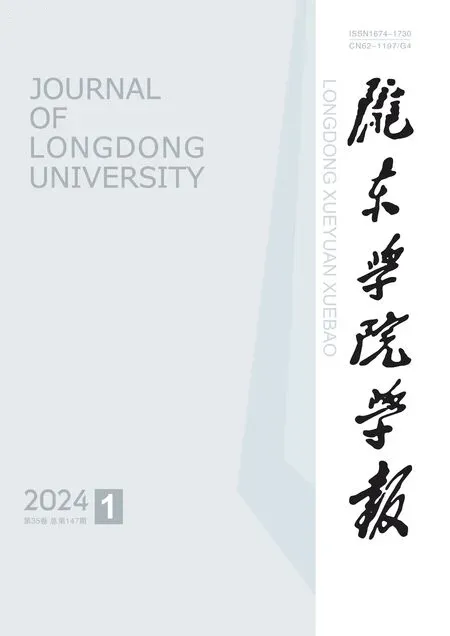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探赜
傅羿超,张自慧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先秦名家是中国哲学史上较为特殊的学派(1)其特殊性体现在关注逻辑思辨上。冯天瑜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以关注现实的人伦秩序为中心,较少关注抽象的概念思辨问题,而后者正是先秦名家的核心论域。该学派以惠施、公孙龙等人为代表。。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记载于《庄子·天下》篇,与其余二十个辩题统称为“辩者二十一事”。但是历代学者对该辩题的解释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它代表了道家“守静”的思想[1]146,有学者认为它是公孙龙“离坚白”派的思想[2]14,有学者认为它是诡辩[3]。但是这些说法似乎与该辩题的本质内涵有一定差距。基于此,文章将从辩题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及价值三部分对其作出澄清,以供学界参考。
一、名实相乱: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提出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贯穿三代的基本社会秩序遭到空前破坏。此时,以儒、墨、道、法等学派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界开始对这种混乱的社会现状进行反思,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提出化“彝伦攸斁”为“彝伦攸叙”(2)“彝伦攸斁”及“彝伦攸叙”均出自《尚书·洪范》。宋蔡沉在《书集传》中指出:“彝,常;伦,理也,所谓‘秉彝人伦’也。”彝伦就是常道、常理,主要指人伦关系。“彝伦攸斁”是人伦关系失序的状态,而“彝伦攸叙”是人伦关系有序的状态。的治世方案,名实之辩便产生于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具体来说,名实之辩包括“以名制实”与“以名举实”两个方面。“以名制实”指通过订立名分,使具体的“实”符合某一“名”,如孔子的“正名”思想,主要以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为旨归;“以名举实”则指使用概念来对事物、对象进行指称,如后期墨家和名家的思想,主要以解决抽象的理论问题为旨归。可以说,前者是“一阶”的名实之辩,后者是“二阶”的名实之辩。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就是“以名举实”的一个实例。
(一)“上以明贵贱”:“以名制实”的现实要求
名实之辩是先秦思想家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本目的是解决混乱的社会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新事物和新的社会关系逐渐形成,对长久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名实关系问题上升为学术界最主要、最受人们关注的大问题,“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重‘名’”[5]。儒家的“正名”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它要求人们遵循周礼的名分进行活动,属于“以名制实”,即通过确立名分对对象进行限制。无论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还是“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都表达了极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作为处于人伦关系之中的个体来说,不同位置承担着不同的道德责任,而人伦就是通过各种称呼体现出来的。如果称呼(名)与自己所处的人伦地位(实)不相符,便会造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的混乱局面,从而导致社会失序、礼崩乐坏。孟子关于“天爵”与“人爵”的区分同样表现了他对“以名制实”的关注。他从社会地位(人爵)与道德水平(天爵)两方面对“正名”思想进行阐释。他指出,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是天爵与人爵相统一,而所谓“天爵”就是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孟子·告子上》),即具有道德理性的君子;“人爵”则指如“公卿大夫”处于高位的官吏。从而他主张“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告子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鲜明体现了“上以明贵贱”的现实关怀。
法家的“正名”思想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与儒家不同,其主张“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韩非基于“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的思想指出,作为臣子,需要时刻保持对君王的忠诚,君臣虽然处于不同的位置,但他们的目的都是通过法使社会有序运行。
可见,无论是主张以“礼治”为理想的儒家还是主张以“法治”为目标的法家,均将“正名”作为解决社会失序问题的前提与手段。这种“明贵贱”的思想正体现了“以名制实”的现实要求。
(二)“下以辨同异”:“以名举实”的理论要求
与儒、墨、法等学派不同,名家与后期墨家更多地表现出“以名举实”的理论关怀。所谓“以名举实”,即通过使用概念以指称或反映对象,不同于儒、法等学派的“以名制实”。名实之辩之所以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向,一方面与学术思想的发展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与不同学派的立场差异有关。就前者而言,现实的社会问题造成了诸子对名实关系的讨论,但随着讨论的继续深入、概念的使用也愈加复杂。此时便需要对作为讨论核心的“名”“实”诸概念进行界定,逐渐从现实政治中抽离出来,上升为较为抽象的理论思考。就后者而言,儒家、法家等学派具有较为浓厚的贵族气质,但名家和后期墨家与之不同,一部分是从事商业的小市民(如邓析),另一部分是从事手工业的小生产者(如后期墨家),还有一部分是贵族的门客(如惠施、公孙龙)。因此关注点更为具体,如“名”“实”等基本概念的内涵与自然现象等。嵇文甫先生指出:“名家学说是市民思想的反映,是从商业都市中孕育出来的。”[6]商业活动需要灵活的思维和流利的口才,门客则要效忠主公,建言献策,没有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有较为充足的闲暇时间,具有所谓哲学思辨产生的基本条件。
名家的发展与齐国稷下学宫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稷下学宫的学术风气十分自由,而尹文、田巴与兒说三位稷下先生作为名家先驱都在其中做出突出的贡献。钱穆指出,学宫代表了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的最高水平:“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既则齐之稷下。”[7]是时,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学派均在稷下学宫进行学术论辩,风气十分自由开放。这一时期的名家在理论层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后期名家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稷下名辩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诡辩学说,几乎都被惠施、公孙龙接受下来,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变成他们用以构筑其诡辩理论体系的东西;反过来说,在惠施、公孙龙那里,几乎每一诡辩命题,都可以在稷下名辩思潮中找到其胚芽形式。”[3]实际上,将惠施、公孙龙的思想一概视为诡辩,是值得商榷的,但毫无疑问,稷下学宫这种思想自由的风气促进了名家的发展。
总而言之,“以名举实”的理论需要,一方面产生于“以名制实”的现实关注之后,另一方面又与名家和后期墨家小生产者、小市民与贵族门客的立场有关,且受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思想自由之风气所影响。作为名家的一个重要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体现的正是这种“以名举实”的理论关怀。
二、同一与生灭: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内涵
“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是战国时期名家辩者提出的一个辩题,出自《庄子·天下》篇的“辩者二十一事”。景,影也;未尝,不曾也,是说在空中飞翔的小鸟,影子不曾运动。该辩题有两种解释维度,分别是同一关系与生灭—动静关系。
(一)“鸟影非鸟”:鸟影与鸟的同一性关系
第一种解释维度说明的是飞鸟与鸟影的同一性关系。一般认为,飞鸟的影子是随着飞鸟时刻运动的,因此不能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但是名家“以名举实”的理论基础重视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此处的鸟影不动正体现了“以名举实”的理论要求。为了使逻辑更加清晰,故将此辩题放到两个参照系中:
第一个参照系:飞鸟从左向右匀速飞行。由于太阳光是平行光线,故地上的影子也在匀速“运动”(3)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影子的变迁属于生灭变化,并不能算作“运动”。,鸟(1)与影(1)、鸟(2)与影(2)、鸟(3)与影(3)…组成的光线可以视为一组平行光线,因此鸟影与飞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对静止关系,即飞鸟相对于鸟影静止。另外,从运动的主动与被动方来说,飞鸟是施动者,鸟影是受动者,鸟影是随着飞鸟的运动而“动”的,但是鸟影相对于飞鸟来说还是处于一种静止状态。顾实说:“鸟影尝随鸟而生;鸟动而影随鸟,固未尝动。”[1]70从这一点来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成立。
第二个参照系:站在地上的人并未跟随飞鸟做匀速运动,故在他的视野中影(1)、影(2)、影(3)…与他的距离时刻在发生变化,根据直观必然得出鸟影在运动的结论。从这一点来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不成立。
从上述对两个参照系的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第一个参照系体现的是飞鸟与鸟影这一对“实”与“未尝动”这一个“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光学与逻辑同一性的理论要求,体现了名家“以名举实”的思想。第二个参照系体现的是常识思维对鸟影的认识,并不是名家的理论立场。
(二)“说在改为”:鸟影是生灭变化而非动静关系
第二种解释维度说明的是“动静”与“生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将二者相混淆。这也是一种反常识的解释,源于后期墨家的著作《墨子·经下》:“景不徙,说在改为。”这是说,飞鸟的影子之所以不动,是因为它是时刻改换的,而改换并不是运动。《墨子·经说下》作为《墨子·经下》的注释,也对此问题作出说明:“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这是通过说明影子产生的原理指出影子的改换并不是运动。对于影子来说,如果光线照射到的地方它就不会产生;如果光线一直存在,照射的地方就始终不会产生影子。这就是说,飞鸟的影子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飞鸟遮挡了太阳光,在地上投射出来一片影子。
具体来说,这一种解释维度也涉及两个参照系:
第一个参照系:就影子来说,它是生灭变化而非动静关系。由于每一片影子都是光线被遮挡所致,所以影(1)与影(1)之后1秒的影(*)已不是同一个影子,而是飞鸟在运动的过程中遮挡了不同的光线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子。当影(*)产生的时候,影(1)早已消失,其余影(2)、影(3)…亦是如此。当到鸟(5)的时候,它的影子就只是影(5),其余无数个影子都随着被飞鸟遮挡光线的产生而消失了,由此便得出“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结论。郭湛波援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说:“如看活动写真,虽见人物生动,其实都是片片不动之影片也。影已改为,前影仍在原处,故曰尽古息。”[8]胡适还以照相机为例说:“若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便知前影与后影都不曾动。”[9]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即使前影的位置并未改变,但由于光线的照射,影子早已消失,并不能认为它“仍在原处”。
第二个参照系:就飞鸟来说,它是动静关系而非生灭变化。飞鸟作为运动的主体,它与作为由于主体遮挡光线而产生的影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运动的主体不会由于受到光线的遮挡而时刻生灭,相反,它是产生影子的必要条件。因此鸟(1)与鸟(2)、鸟(3)等都是同一只飞鸟,所不同的只是位置的变化,不同于随时生灭的影(1)、影(2)。
从上述对两个参照系的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第一个参照系体现的是鸟影生灭而“未尝动”的“实”质,是名家“以名举实”思想的具体反映,第二个参照系体现的则是飞鸟运动变化的“实”质。二者都是对客观现象的科学反映。
(三)“唯乎其彼此”:公孙龙思想的具体体现
名家虽然强调“以名举实”,但其内部也有分歧(4)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狭义的名家可以分为惠施的“合同异”派和公孙龙的“离坚白”派,而广义的名家则包括后期墨家。后期墨家虽无明确的代表人物,但有著作流传,即现存《墨子》的第四十至四十五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与《小取》。这六篇集中展现了这一学派的名辩思想。。“合同异”派重视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如其辩题“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庄子·天下》)就体现出对天地、山泽等处于两种不同位置的事物同一性的追求;“离坚白”派则强调同类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如坚白石之辨认为人要么只能通过触觉认识到坚石,要么只能通过视觉认识到白石,但无法既通过视觉又通过触觉认识到“坚白石”。因为“事物诸属性之间不存在必然性联系,人们只能通过不同的感觉功能分别感知它们。”[10]后期墨家则结合当时科学的发展对上述名家争论的问题做出初步回应,如指出“离坚白”夸大了同一事物不同属性的差异,与事实不符,应改为“盈坚白”:“无(抚)坚得白,必相盈也”(《墨子·经说下》);惠施的“合同异”思想则夸大了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因为“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墨子·小取》)而作为“辩者二十一事”之一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则应解为“说在改也”(《墨子·经下》)。
该辩题就思想内涵来说属于公孙龙“唯乎其彼此”的思想。《列子·仲尼》将其视为“公孙龙七说”[2]14之一,它对“有影不移”的解释是“影不移,说在改也”,与《墨子·经下》的说法一致。公孙龙的思想除“白马论”“坚白论”之外,还有明确提出“唯乎其彼此”的“名实论”。他指出:“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公孙龙子·名实论》)这是说,对于对象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说,一个对象应对应与之相应的概念,如果将不同的对象使用相同的概念指称,就会造成混乱。对于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来说,鸟动与影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影“改”与影动的内涵也不同,如果认为“飞鸟之景,动也”或“飞鸟未尝动也”就会陷入“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公孙龙子·名实论》)的谬误之中,既与“唯乎其彼此”的思想相违背,又与“以名举实”的理论要求相冲突。
总之,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体现的是名家“以名举实”的理论要旨,与公孙龙“唯乎其彼此”之说一致。
(四)名实相副:对诡辩论误解的澄清
诡辩是指一种运用错误或虚假的根据歪曲客观事实的论证方式。黑格尔指出:“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11]如芝诺的“飞矢不动”命题便属于诡辩。他通过划分时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得出“如果每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本身相等的空间时是静止的,而移动位置的东西在任何一个霎间总是占据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飞着的箭就是不动的了”[12]这一错误结论。事实上,在空中飞行的矢不可能处于静止状态。
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并不属于诡辩。通过分析得出,鸟影不动一方面体现的是飞鸟与鸟影的同一性关系,另一方面体现的是鸟影生灭变化的光学现象,二者都建立在名家“以名举实”和公孙龙“唯乎其彼此”思想的基础之上,符合科学与逻辑规律。
因此,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说明了鸟影与飞鸟的同一性关系与鸟影生灭变化的实质,是公孙龙“唯乎其彼此”思想的具体体现,符合名家“以名举实”的理论要求,并不属于诡辩。
三、思辨理性与求知精神:“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辩争的价值
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产生于名实相乱的春秋战国时期,既受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以名制实”大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开创了“以名举实”“唯乎其彼此”的思想小传统,并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关注激发出关注万物的求知精神,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包容性。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名实一致,继承了大传统的理论关切。中国哲学的大传统是对经验世界与人生的关注。先秦名家继承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儒、墨、道、法诸子与“六经”古学,在后者“以名制实”的现实关注之后提出了“以名举实”的理论构想。“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作为名家辩题之一,虽然体现的是对以名副实的理论问题的关注,但深层次的关怀则是试图通过对“名”(概念)与“实”(对象)含义的探讨进而推进名实之辩。
第二,关注概念分析,促进了思辨理性的发展。名家与其他诸子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概念与思辨的关注上,而处于大传统之中的儒、墨、道、法等诸子均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为鹄的,即使在名实之辩中也较少关注概念本身的内涵与意义。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通过讨论“飞鸟”“鸟影”“动”“改”等概念的异同,得出鸟影不动是因为“说在改也”之实,颠覆了常识的朦胧认识,促进了思辨理性的发展。
第三,聚焦自然现象,激发了关注万物的求知精神。名家的理论建构与其余诸子不同,他们主要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反思性解释展开,如惠施“历物十事”就有通过讨论天地与山泽的位置(5)指“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等论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合同异”思想;“辩者二十一事”中的“卵有毛”“郢有天下”“火不热”“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庄子·天下》)等辩题亦鲜明反映了辩者对自然现象的关注。
第四,展现多元一体,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包容性。中国哲学在诞生之初便以注重现实性、实践性和实用性为特征,无论是作为滥觞的“六经”还是作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的先秦诸子大传统,都体现了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在名实之辩方面提倡“以名制实”。与之相反,以惠施、公孙龙以及后期墨家为代表的广义的名家却将视角转到“名”与“实”本身,提出“以名举实”的研究方法。以“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为代表的名家诸辩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形成了关注概念分析的小传统。作为早期中国哲学的先秦诸子大小传统并存,体现了中国哲学多元一体的特征及其包容性。
先秦名家的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名实相乱的思想与时代背景之下,在名实之辩的学术氛围中继承并发展了六经古学与儒、墨、道、法诸子“以名制实”的思想,提出“以名举实”的理论构想,对名实之辩做出了理论推进。该辩题的思想内涵和解释维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鸟影与飞鸟的同一性关系证明“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二是从鸟影改换、生灭与“运动”的差异证明“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由于它符合公孙龙“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的“唯乎其彼此”思想,应属于公孙龙派。它追求名实相副,符合科学与逻辑的规律,故将其视为诡辩并不符合事实。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体现了对大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其基于追求名实一致的大传统,从关注概念分析入手对名实之辩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思辨理性的发展;其体现出名家对自然现象的关注,激发了关注万物的求知精神,亦丰富并扩展了先秦哲学的广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巨大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