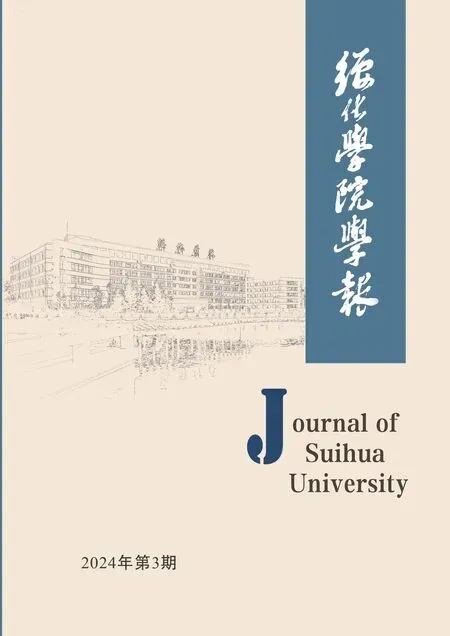作为“策略”的文学:伊格尔顿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新发展
张凤梅
(安徽工程外国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伊格尔顿在2012 年出版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一直未引起国内学界广泛关注。其实在这本书中,伊格尔顿提出了“文学策略论”的重要思想,将文学视为一种想象性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是他对文学本质思考的深化,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与深刻内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应该说,伊格尔顿的“文学策略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言语行为理论启发的结果。他在书中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对我们迄今为止竭力廓清的文学概念有很大启发,尤其是它关于虚构性的重要洞见。”[1](132)可见这是他提出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伊格尔顿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兴趣主要来自他对于文学性这一概念的思考。可以说,“什么是文学”这一涉及文学本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文学理论导论》时,他曾明确提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坚称文学是没有本质的,所谓“文学”并没有一个或一组共同的属性。此后,随着以语言为核心的“高理论”(high theory)的式微,以及以文化批评为表征的“低理论”的勃兴,文学研究似乎沦为其他人文学科的附庸和衍生物,这使得伊格尔顿颇为担忧。他要让文学研究回到那个把文学和虚构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视为头等大事的“高理论”时代。[2](128-129)因此,他写作《文学事件》这本书,就要解决“文学何以发生”“文学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不过,伊格尔顿并不把这种努力视为欧陆体系“高理论”的继续,而是把自己称为英美体系“文学哲学”传统的继承者。他戏谑地称二者的差异在于,前者任性随意,“穿衬衫必敞领口”,后者古板而严谨,“任何时候都系着领带”。[1](引言2-3)
伊格尔顿在英美体系的文学哲学传统中寻找“文学何以发生”这一问题的答案,其突破口就是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事件》一书的第四、五章他用较大篇幅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阐释,称之为文学哲学中“最具前沿性的一支”,对于理解文学概念有深刻的洞见。[1](P147)他认为言语行为其实是“魔咒”这一古老传统的世俗变体——只要念出词语,就会令天地变色——这显示出词语具有无穷的创造性力量。文学作品也具有这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便来自作品的虚构。虚构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伊格尔顿认为,作家之所以进行虚构,是因为对人类社会有深刻的洞见,想要与人分享,写作于是成为他们进行共享的建构性活动。如何进行虚构?就是作家采取一定的策略,把真实世界夸大、重组、变形,例如“将日常生活大胆地剪辑成一部前卫电影”,这种夸大、重组、变形的虚构方式,是作家“策略性计划的一部分”[1](P165-166),以达到文学作品制造意义、产生影响、引发行动之目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伊格尔顿可以说继承了奥斯汀开创的传统,对语言的施为性特征进行了深入阐发。作家为何进行创作?创作的激情来自哪里?目的何在?又如何进行创作?这些涉及文学本原的问题都可以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找到答案。文学具有“魔咒”一样的力量,能够“改天换地”,那么,作家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构建出自己的“魔咒”,从而来按照自己的期许来改造世界。
伊格尔顿以《简·爱》为例来解释他的“策略论”。在小说结尾,伊格尔顿注意到夏洛蒂·勃朗特为了使简·爱与罗切斯特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有意先把二者强行分开,继而再使得二人通过“心灵感应”这一神话般的方式走到一起。期间,一把大火烧毁了男主人公的全部财产,罗切斯特变得又瘸又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疯女人伯莎也在火中丧生,通过这种哥特式的手法,作家把罗切斯特强行降级,以让简爱获得自由平等的爱情。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文学式的“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是作家“策略性计划的一部分”,但却弘扬了一种跨越等级、平等自由的爱情。当现实中这种爱情无法实现时,作家通过虚构,使其在文学作品中想象性地得以实现。勃朗特的这一写作策略使得“19世纪的妇女读者在道德范围内实现欲望的僭越,同时又避开道德风尚的舆论非难和审查。”[2](P141)
伊格尔顿认为,《简·爱》为了克服某种道德或社会困境,在传统的文学叙事遇到问题,没有现成的现实主义方案可以解决时,便选择倒退,求助于具有寓言性或神话色彩的技巧来解围。这种技法在维多利亚小说中很常见。伊格尔顿虽然没有再详细举例,但指出,“诸如时机恰好的遗产、找回多年失联的亲戚、及时雨般的突然死亡、奇迹般的改变心意,在维多利亚小说中随处可见。”[1](208)这些写作技法都是作家策略性计划的一部分,它们都指向现实主义“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人类之所以需要这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人类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伊格尔顿指出,人类的劳动本身是一种意义建构模式,为满足自身需要把现实合乎逻辑地组织起来,但人类还需要“一种元意义建构模式,一种由人类的劳动和语言开启的具有猜想性质的反思力。这就涵盖了从神话、哲学到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的全部符号领域。”[1](P202)换言之,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乃是人类征服世界并赋予其意义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对征服过程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帮助指导与修正人类的发展轨迹,因而对建构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作为一种策略,文学勾勒出人类生活美好的前景。
伊格尔顿的这一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很早就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探讨,提出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文学从根本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经过20世纪80年代各种文化理论的洗礼之后,伊格尔顿更是认识到文学依附于其他文化、失去自我的做法是有很大问题的,他在《理论之后》中尤其对文化理论热衷于研究性欲、大众文化的做法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文化理论过于执迷于对“性”的分析,“文化理论现今的表现就像一位独身的中年教师,不经意之间与性邂逅,正在狂热地弥补已逝的青春韶华”[3](P6);而大众文化看似贴近现实生活,又往往缺乏深度,只是做表面文章。因此,文学应该摆脱文化研究的束缚,回到自己的本体论。而言语行为理论所倡导的语言所具有的施为性功能,赋予他新的视角。
伊格尔顿的“文学策略论”在几个方面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深化。一是凸显了“作者意图”,强调作者改变与创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对奥斯汀与塞尔开创的传统的继承,反驳了企图淡化或反对作者意图论的主张。“作者意图”一直以来是西方文论争论的焦点,不少理论家反对“作者意图”说,如新批评学派代表人物维姆萨特(W·Wimsatt)提出“意图谬误”说(Intentional Fallacy),否定作者意图对文本阐释的影响;英国学者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说(Significant Form),切断了作者与文本生产及建构的关系。伊格尔顿的“策略论”表明作者意图不仅在场,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伊格尔顿在言语行为中强调道德实践性。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强调“文学作品代表着一种实践的或者行动中的知识”[1](63),而这种知识和古代对于道德的理解是类似的。可见,文学作品的本质在于它与道德的密切联系,“文学作品是道德知识的形式”,具备一种道德性。他甚至提出:“不去谈论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文学还会存在吗?”[1](70)简言之,文学的本体论价值,就在于其道德性。这种对文学价值与意义的追问,与中国古代提出的“文以载道”是不谋而合的。
伊格尔顿的“文学策略类”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打开了新思路,带来新启示。不少文学作品,都带有作者策略论的明显痕迹。以非洲文学之父阿契贝的作品而言,他的小说中具有詹姆逊在分析第三世界文学时提出的“民族寓言说”明显倾向。究其原因,这是阿契贝等第三世界作家的策略性选择,是作者意图的体现。因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经受过殖民统治的苦难,没有什么比这种家园被毁、传统丢失更令他们伤怀的。如同阿契贝所说,回顾过去、重写非洲的历史,不再让非洲的过去呈现为“漫长的黑夜和野蛮”,而是像其他地方一样,也“充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非洲作家的使命。[4](P223)
实际上,即便是西方世界的作家,这种策略论的意图亦是非常明显。美国作家玛丽莲·罗宾逊是典型的具有美国特征的作家,在小说中极力渲染宗教之美,努力刻画积极正面的牧师形象,一反以往文学作品中对神职人员的负面描写。其实这正是作家意图的体现。罗宾逊致力于在一个愈来愈世俗化的世界里恢复真正的清教传统,以文学书写来教化民众,“策略”意图非常明显,有学者称她是一个“讲故事的加尔文”,不无道理。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最后一部小说《恐怖分子》写于“911”恐怖袭击之后,探讨了一个穆斯林小伙在高中毕业后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在极端思想影响下走上暴力恐怖道路的故事,体现了厄普代克对美国社会冲突的反思。作家通过对文本的操纵,以实现其“策略”意图,是文学作品的本质所在。
伊格尔顿“文学作为策略”的思想深化了言语行为理论,有助于读者深入挖掘作者掩藏在作品中的深刻思想,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作品乃是作家的“一种策略性的劳作——一种将作品置入现实的方式”。[1](P171)也就是说,文本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的投射,还体现出作者对于现实问题策略性的解决方案。它是“词语与现实之间的乌托邦式统一”“是一个行动的完成和替代,是一种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对不可能实现的愿景的补偿”。[1](P194)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不是作为记录世界的工具,而是作为创造与改变世界的策略与方法而产生,文学是作家现实关切、社会参与的重要体现。这是继米勒之后对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领域的新突破。可以说,伊格尔顿这一思想使文学研究更进一步,从反映论、表现论、结构论、符号论,发展到“策略论”。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