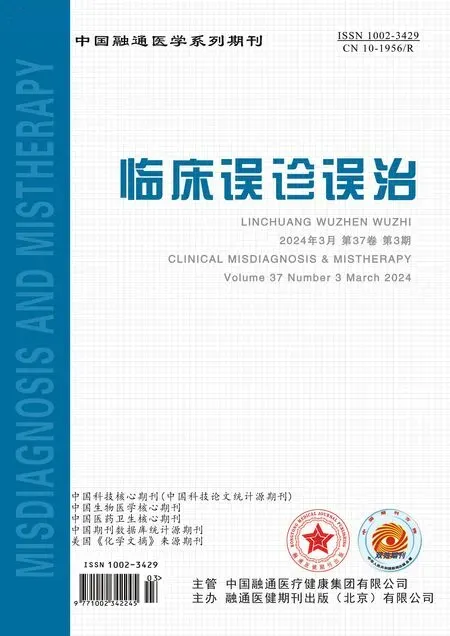误诊为膜性肾病的狼疮肾炎临床分析
王文丰,张 周,钱 悦,宋 洁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以自身免疫性炎症反应为突出表现的典型弥漫性结缔组织病[1]。临床上约50%的SLE患者会出现肾损伤临床表现,通过肾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会发现SLE患者的肾脏受累比例可高达90%[2]。膜性肾病(MN)的发病率占总肾小球疾病的24.9%,且呈逐年上升趋势[3],临床表现以蛋白尿为主,可伴血尿,与狼疮肾炎(LN)表现较为相似,易造成误诊。本文回顾性分析误诊10余年的LN 1例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提高临床对该病认识。
1 病例资料
女,33岁。因双下肢水肿伴泡沫尿13年收入院。13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水肿,呈指凹性,伴尿中泡沫增多,就诊于当地医院。入院诊断:肾病综合征。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查体:血压120/75 mmHg;双下肢水肿,呈对称性,指凹性,其余未见明显异常,不伴发热、脱发、皮疹和光过敏等不适。实验室检查:24 h尿蛋白4.06 g,血清白蛋白27.1 g/L;尿素5.4 mmol/L,血肌酐55.1 μmol/L,尿酸340.8 μmol/L;总胆固醇6.76 mmol/L,三酰甘油1.76 mmol/L。自身免疫抗体和肝炎病毒等筛查均为阴性。行肾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光镜可见6个肾小球,肾小球系膜细胞及基质无明显增生,毛细血管襻轻度弥漫性均质增厚、僵硬,伴节段性空泡变性,未见钉突形成,上皮下可见嗜复红蛋白呈细颗粒状沉积。肾小管间质灶状萎缩伴纤维化,受累比例约10%。免疫荧光检查可见3个肾小球,IgG(++),IgA(+/-),IgM (++),C3c(++),C1q(+/-),FRA (+/-),HBsAg和HBcAg阴性。未行电镜检查。诊断:Ⅰ期MN。给予泼尼松每日50 mg口服,环磷酰胺每日0.2 g静脉滴注,经治疗17 d后患者尿蛋白降至1.49 g/24 h。遂出院,门诊随访。10年间患者病情时有反复。2个月前患者因牙龈炎于当地诊所就诊,治疗4 d后出现双下肢水肿,尿中泡沫增多,尿量减少,遂转至我院就诊。有荨麻疹病史15年,每年发作,近6个月发作3次。4年前妊娠34周左右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查体:血压141/90 mmHg;体质量指数19.46 kg/m2。双下肢轻度水肿,毛发较稀疏,颈部皮肤可见淡红色皮损。24 h尿量0.59 L,尿蛋白>10 g/24 h;血清白蛋白25.7 g/L;白细胞2.75×109/L,血红蛋白91 g/L;肾功能正常。免疫学检查:总IgE测定 806 U/mL,Smith抗体(+),补体C3 0.36 g/L,补体C4 0.054 g/L,抗核抗体阳性(1∶320),其余未见明显异常。根据2019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美国风湿病学会(EULAR/ACR)制订的SLE分类标准[4],临床诊断为SLE。行肾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光镜可见7个肾小球,其中1个纤维性新月体伴硬化,其余肾小球毛细血管襻肥大,系膜细胞和基质轻度弥漫增生,节段毛细血管腔内细胞增多,偶见中性粒细胞浸润,基底膜轻度增厚,上皮下、基底膜内、内皮下和系膜区嗜复红蛋白沉积,节段性白金耳状结构形成,可见1个小细胞纤维性新月体形成,1个节段性硬化,1个球囊粘连。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及颗粒状变性,灶状萎缩,管腔内见少许蛋白管型。肾间质灶状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少量中性粒细胞浸润伴纤维化。免疫组织化学:C4d(+++),肾小球毛细血管壁、系膜区、部分管周毛细血管襻颗粒样沉积;免疫荧光:IgG(+++),IgA(+),IgM(+),C3c(++),C1q(+++),FRA(+/-),ALB(+),κ(+++),λ(+++),IgG1(+++),IgG2(+++),IgG3(+++),IgG4(+)。诊断:弥漫增生性LN合并膜性LN(Ⅳ+Ⅴ型),AI=8,CI=3,见图1。给予醋酸泼尼松、吗替麦考酚酯和羟氯喹联合治疗。经治疗19 d后,复查尿蛋白较前下降,血红蛋白和白蛋白较前明显上升,尿量正常,病情缓解出院。出院后15 d于外院门诊随访,24 h尿蛋白3.57 g,血清白蛋白25.8 g/L,皮损面积较前缩小,病情控制良好,无其他不良反应。

1a.肾小球纤维性新月体伴硬化,间质灶状炎性细胞浸润伴纤维化(PASM+Masson染色×100);1b.肾小球节段毛细血管腔内细胞增多伴小细胞纤维性新月体形成(PAS染色×200)。
2 讨论
2.1 临床特点
SLE是一种终身自身免疫性疾病,常累及多个器官和系统,包括皮肤、关节、肾脏、大脑、肺和心脏[5],部分患者可累及甲状腺[6]、淋巴结[7]、微血管内皮组织[8],危及患者生命。因此,不同SLE患者临床表现差异较大,且SLE自然病程多病情加重与缓解交替出现,故同一患者在不同阶段临床表现也有所不同[1]。SLE可起病于全年龄段,15%~20%患者在儿童期发病;在成年人中,女性发病率是男性9倍,育龄期发病率最高[9]。SLE这种性别的差异性,在青春期以前并不明显[10]。上述特点都是造成SLE易误诊的原因。
LN是SLE引起的肾脏损害,是我国终末期肾病的常见病因之一。LN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轻者可表现为无症状性蛋白尿和(或)血尿,重者可出现肾病综合征或急进性肾小球肾炎,临床常出现尿量异常(少尿或夜尿增多)、血尿、蛋白尿、水肿和高血压等表现,故需与多种肾脏疾病相鉴别。
2.2 诊断及鉴别诊断
目前,临床上LN的诊断标准尚存在一定争议。肾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对SLE分类的诊断价值也曾被多次否定,直到近年来又再次被提及[11]。199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最早定义了LN的诊断标准:SLE患者出现持续性蛋白尿[24 h尿蛋白>0.5 g,或尿蛋白>(+++)];或出现各类型细胞管型(红细胞、颗粒和混合管型等)[12]。但在此之前及后续的研究中,发现部分SLE首发于肾脏,而后在随访观察中才慢慢出现其他脏器及系统损害[13-15]。2012年SLE国际协作组(SLICC)对SLE的诊断标准进行了补充,纳入了对肾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的评估指标[16-17],且这一观点也在2019年EULAR/ACR的分类标准中被延续了下来[4]。
本例SLE首发于肾脏,且无血清学和临床证据,通常被称为“前LN或者亚临床型SLE”[14],病理上则被称为LN。这一特殊类型的LN,肾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可以见到一些特征性改变,如“满堂亮”(IgG、IgA、IgM等免疫球蛋白和C1q、C3等补体沉积),C1q≥(++),肾小管网状包涵体,肾小球外免疫复合物沉积,肾小球内多部位免疫复合物沉积[18]。但这些特征性表现也可见于病毒感染相关性肾小球肾炎、MN、IgA肾病、IgG4相关肾炎和非狼疮“满堂亮”肾病等人群中[19-20],所以临床需要注意鉴别。此外,大多数学者会最先关注到的是此类患者的“满堂亮”及“C1q强阳性表达”。“满堂亮”是LN特征性病理表现之一,但不一定会贯穿LN病程的始终,也不能以此作为直接诊断LN的依据。如果单以“满堂亮”作为诊断LN的依据,则会使特异性为100%的SLICC标准大幅度下降至91%[21]。临床需要重视“C1q的强阳性表达”的诊断价值,虽然其他类型的肾小球疾病也会出现类似于“满堂亮”的病理改变,但与LN相比,MN、IgA肾病、非狼疮“满堂亮”肾病等的C1q表达强度较弱[22-23],特别是在鉴别LN与非LN性MN,“C1q的强阳性表达”的意义更加重大[18]。而本例在第1次肾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中C1q仅为弱阳性表达,这是导致误诊的重要原因。此外,临床鉴别膜性狼疮肾炎(LMG)与膜性非狼疮肾炎(NLMG)时,肾小管网状包涵体同样具有较强的鉴别价值,其更常见于LMG[18,24]。
除了免疫学及形态学的鉴别要点之外,重视MN靶抗原的检测也显得尤为重要。LMG与NLMG的靶抗原有着明显的差异,原发性MN最常见的靶抗原为M型磷脂酸酯酶A2受体[25]。而LMG大约33%~46%的靶抗原为Exostosin1/Exostosin2[26-27];6%靶抗原为神经细胞黏分子1[28];6%靶抗原为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3[29]。所以,在鉴别LMG与NLMG时,应当重视靶抗原的检测。
2.3 误诊原因分析
分析本例误诊主要原因为首诊病理检查结果表现不典型,光镜下肾小球系膜细胞及基质无明显增生,而典型的LN病理改变,往往以增生性病变为主;免疫荧光虽表现为“满堂亮”,但C1q的表达较弱。其次,本例首诊在SLE起病早期,与SLE常累及多个器官和系统临床特点不符,早期误诊率较高,文献报道其误诊率为41.7%~68.5%[30]。另外,首诊接诊医师未对疾病进行详细鉴别诊断,也是导致本例误诊的原因之一。MN虽然和SLE一样可发病于全年龄段,但MN主要发病年龄集中在40~50岁,且男女发病比为2∶1[31],这与SLE好发于育龄期女性这一特点有较大差异。所以,临床在遇及患者病理免疫荧光提示“满堂亮”,且患者为育龄期女性的情况下应当重点与SLE鉴别。同时,本例未能及时观察到患者皮损和脱发等症状,而MN和LN在治疗方案中有一定重合的地方,最终导致误诊长达10余年。
2.4 防范误诊措施
临床医生应提高对SLE的认识,即便是非风湿免疫学科的专科医生,也应当掌握SLE的临床症状及鉴别诊断要点。对于育龄期女性及其他SLE高风险患病人群,需要将SLE作为重要的鉴别诊断疾病来看待,并做好随访观察。另外,接诊医生需要拓宽诊断思路,重视查体相关信息,对既往有其他疾病的患者,不要过分迷信既往诊断,要认真做好相应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王文丰:数据分析、论文撰写;张周、钱悦:采集数据、研究指导;宋洁:研究指导、论文修改、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