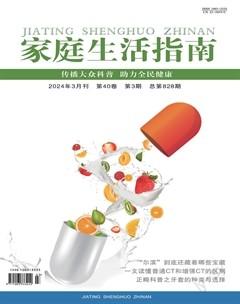“苹果”探名
钱伟

在西方世界,苹果似乎总是与各种传说和典故相联系,其文化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一般水果,比如人们常说上帝有三个苹果:一个诱惑了夏娃,一个砸醒了牛顿,一个成就了乔布斯。与之相反,中国古诗文中出现过桃、李、杏、梨、枣、橘乃至西域的葡萄、江南的梅子、岭南的荔枝,却唯独不见苹果的影子。这是为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苹果的身世说起。苹果虽然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水果,但作为“外来户”,它到中国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古书上记载了一种类似于苹果的本土水果叫作“柰”(读作“奈”),也叫“花红”或“林檎”。称其为“林檎”可能是因为其果熟味甘能招来飞禽栖落林中。在日语中,“苹果”至今依然写作“林檎”。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超过了两千年,早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撰写的《上林赋》中就有记载。只是其口感酸溜溜、软绵绵,类似于山楂和苹果的结合,无法勾起人们的食欲。于是,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只作为水果的配角,根本无法与桃、李、杏、梅平起平坐,因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果子是苹果家族的一员。
元代中后期,一种新奇的水果从西域引入大都,被精心种植在皇家苑囿里,嫁接在林檎树上后长出了色泽红润的果实。该叫它什么呢?时人想到了佛经里提到的色丹且润的“频婆果”,于是就这么叫起来。后又按汉语习惯改写成了“苹婆”。这种水果与柰本属同类,但经过改良,外观、口味已与柰有较大区别。元末,朝鲜王朝流行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描写主人公在大都的筵席:水果包括八種,分别是“柑子、石榴、香水梨、樱桃、杏子、苹婆果、玉黄子、虎刺宾”。其中就提到了苹婆果。此果在当时非常稀罕,与西凉之葡萄、吴越之杨梅并称为天下名果。
明代万历年间,农学家王象晋所撰的植物学著作《群芳谱》中,第一次将苹婆果简写成“苹果”,并称其“光洁可爱玩,香闻数步”,但“味甘松,未熟者食如棉絮,过熟又沙烂不堪食”。到了清代,苹果见于记载愈多。康熙帝对苹果有特别的喜爱,常用以赏赐臣下。到了乾隆年间,苹果放下了身段,价格大降,又因其还让人联想到了平安吉祥、太平盛世等吉祥词语,于是成了宴席上必备的四鲜果之首。
不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天市场上常见的苹果,看起来很本土,实际上也并非康乾盛世时的苹果子孙,而是来自大洋彼岸旧金山的西洋果。1 8 7 1年,有位爱好园艺的美国牧师倪维思来到山东烟台。他开辟农场,引进并培植了果大瓤脆、皮红肉硬的旧金山苹果。这种苹果虽不如中国本土苹果气味清香,却产量高、易储藏,很快被当地农民接受并推广种植。到清末,随着西洋苹果的广泛种植,“苹果”之名逐渐取代了“苹婆果”等名称。
由上述内容可知,在古诗文中没有苹果的影子,不是古人觉得苹果不值得吟咏,而是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苹果———既没有“苹果”这个词,也没有我们今天吃的这种脆甜可口、又大又圆的果子。
来源:《咬文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