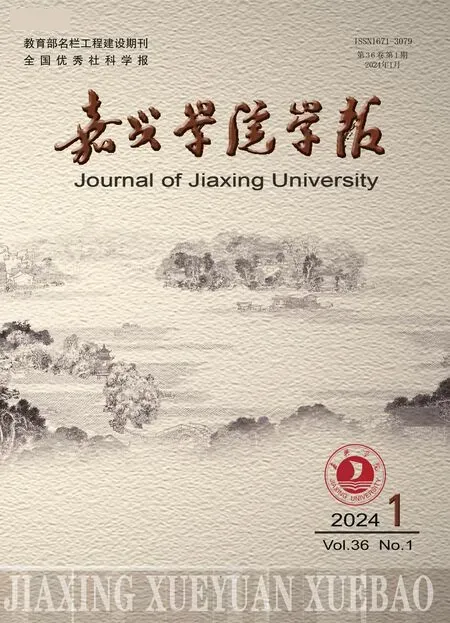《人间词话》“内美”与“修能”之辨析
李世娇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从“内美”与“修能”的关系出发,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本身难以分离,任何足以成为典范的艺术创作都需天赋与后天习得的才能,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虽然王国维深受康德、叔本华影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对其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看待以“天才说”作为基础的“内美”与“修能”的关系上,王氏总体上认为二者缺一不可,相互影响,但是在具体的作品点评当中又出现了“内美”重于“修能”的倾向,体现了其思想的矛盾,而矛盾的存在展现了王国维复杂的内心。
一、“内美”与“修能”之关系
王国维所谓的“内美”是建立在他的“天才说”基础上的,“内美”是一种与生俱有的美质,强调自然天赋;“修能”是后天的修养,在王国维词学批评当中更多是指对先贤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技巧等的深度把握与熟练运用。既然“内美”是建立在王国维“天才说”基础之上的,那么其“天才说”从何而来便不得不说清楚。王国维的“天才说”是一个“混合物”,是对中西文化的兼收并蓄。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司马相如的“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万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1],还是袁枚的“天性使然,非关学问”[2]326“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2]526,都强调天分。虽然“不同作家的先天性在创作中的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得自天然,有的是精思而致,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过程都与作家的先天禀赋有关”[3],但至少都肯定了“天才”在艺术创作当中的重要性。而“内美”的含义又不止于此,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天才”观点进行了升华。从王国维对“境界”的建构中,或许可以窥见关于“内美”的一些特质。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思想的吸收是显然的,康德说“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ingenium),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4]115-116“天才自己不能描述或科学地指明它是如何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来的,相反,它是作为自然提供这规则的”[4]116,可以看出康德对天才的界定与“自然性”密切相关,而这“自然性”表面是指情感自然流露、创作自然天成,但其实内核来源于柏拉图“灵感说”,强调灵感对艺术家、作家等的刺激从而激发他们的创作。中国古代文论里面所讲的“偶得”与“顿悟”就是指灵感的闪现,强调偶然性,这偶然性背后就是天赋。王国维将这种“顿悟”纳入其“内美”概念当中,比如,王国维谈到的“伫兴之作”“须臾之物”就是强调创作的灵感闪现。那么,这种须臾之思如何才能进入王国维所谓境界呢?在王国维看来,创作必须要合乎自然,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佛雏认为这种合乎自然对应“赋比兴”当中的“赋”,偏重于写实。佛雏在论及王国维“写境”与“造境”时说道,“‘写境’重写实,‘合乎自然’……又必有所‘虚构’,则又‘邻于理想’……‘造境’重理想,又‘必从自然之法则’……其理想超出于所寄托的‘一人一事’之外”[5],可见,无论是“写境”还是“造境”其实都离不开“自然”,也就是说作品要能回味无穷,其内质必然是合乎自然的;而“邻于理想”在佛雏看来就是“赋比兴”当中的“兴”,是艺术境界不可穷尽的前提。“合乎自然”与“邻于理想”便是指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理想必然出自诗人自身所感所悟,自得而成,那么如何才能使自然与理想或者说现实与理想巧妙地结合并让理想成为现实的升华呢?这就必然要谈到王国维对康德和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借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6]。这里所谓“观”指的就是审美静观,就是说诗人本身合乎自然,要忘掉个人的存在,自由进入审美静观当中。康德认为天才艺术家是作为自然赋予艺术以规则,叔本华讲“唯自然能知自然,唯自然能言自然”[7]287-288,“而天才的本质就在于进行这种观审的卓越能力”[7]259-260,只有当艺术家、诗人忘掉一切外在束缚、摆脱意志束缚,才能真正进入自然并领悟其中的美妙。这三者所强调的自然之诗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客观性。虽然王国维将文学创作看成是“客观的知识(认识)”与“主观的感情”“二者交代(交错)之结果”[8]112,但客观性仍然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叔本华为“天才”下了一个定义,即“天才只不过是最完全的客观性”[7]240,王国维则将这种客观之境界定义为“无我之境”。进入“无我之境”就是摆脱“有我”而深入自然人生,王氏认为“诗人对宇宙认识,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9]15。无论是“出”还是“入”,其实都强调对客观的把握,但这种把握又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否则诗歌没有生气,也无法达到高致,王国维始终凝视着现实,忧生忧世是他理想的底色。但需要注意的是,王国维眼中的“天才”并不仅仅是创作自然真实之作的诗人,而是在此基础上诗人还要有对宇宙人生有深刻的灵魂感悟,最终的落脚点是“终极关怀”这一层面。因为在王国维看来只有做到“入乎其内”后还能“出乎其外”的诗人才能达到“内美”境界,是真正的天才诗人。什么是“入乎其内”?即诗人能够对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人生体验总结提炼,使其生气勃勃,但这还不能形成精妙之作,还需要“出乎其外”,也就是将日常积累的素材放到更深层的思索中,追求“终极关怀”,使其有高致。王国维之所以欣赏叔本华,就是因为叔本华强调天才之苦,即思索宇宙人生的痛苦,因为真正的天才见人生百态、感人生的深刻苦痛,所以他们对宇宙人生的关怀是深刻的,这与王国维当时的心境相符,所以视叔本华为知音。具有“终极关怀”这一深层内涵的作品,能够“独能洞见”“独有千古”。也即“‘内美’丰盈之‘天才’‘诗章’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10]139,王氏认为要真正达到有境界,必然要将理想落在“忧生忧世”之上。“忧生忧世”通过理想的升华得到展现,并使得境界韵味无穷,这个理想其实就是叔本华所谓“永恒的理念”的再现,而这种再现必然是先天的“美之预想”,因此境界的达成必然和天赋有关,甚至可以说天赋决定了这境界达到何种程度。故“内美”是基于“天才说”而生发的,但其内涵是通过“境界说”而丰富的。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当中对美的特质进行了规定,认为应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美,其中第一、第二契机涉及质与量。从质的方面来看,美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只要其中混杂丝毫利害关系,那这种美就不是纯粹的了;从量的方面来看,“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4]35,审美判断具有普遍性,而这种判断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王国维不仅以质的标准来进行词学批评,认为真正有境界的作品应该是自然纯粹的,而且以质与量两个标准构建了“古雅说”。“古雅说”的内涵与康德的天才理论是紧密相关的,古雅与康德所谓优美、宏壮的审美经验是一致的,但是王国维为了区分古雅与境界,又将古雅定义为低等的优美与宏壮,认为优美宏壮的审美判断是先天的判断,所以是普遍的必然的,而古雅却是后天的、经验的,不具备普遍性,更不是天才之物。那么,王国维的“古雅说”又如何与康德的天才理论建立联系呢?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在于对立,“王国维的‘古雅说’就是一种颠倒过来的西方天才理论,或者说是对西方天才理论的一种否定形式的表达”[11]。王国维认为,“古雅说”并不依赖先天的禀赋,可以通过人力达到,“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优美及宏壮则非天才殆不能捕攫之而表出之”[10]620-621,既然古雅不依靠天赋,那么它所代表的作品必然也缺乏独创性而为一种模仿的艺术。如果说天才的创作源于无意识的冲动,那么古雅的作品就是有意识的雕饰。因此,古雅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模仿的、技术性的,在王国维看来,这种艺术哪怕精妙无比也不能称之为天才之作。“修能”指后天习得的各种才能与技术以及修养,以“修能”为基础创作的作品无先天禀赋支撑,有模仿雕琢之气,这与古雅作品是一致的。虽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当中并未提及“古雅说”,似乎是故意回避此说,但其实“修能”就是“古雅说”的一种外化,也就是说在《人间词话》当中,王国维依然以天才理论来进行词学批评与实践,而天才理论又指向以“境界说”为基础的“内美”和以“古雅说”为内质的“修能”。在王国维词学体系当中,“内美”的丰富内涵来源于“境界说”,而“修能”则与“古雅说”密切相关。
“内美”的内核是“天才说”,而其表象则为灵感、自然和客观,通过这三者才能真正体现“内美”的天才性质。从“天才说”的角度而言,“内美”指向天才天赋,而“修能”指向后天学习,“修能”作为后天修习而来的能力,是对“内美”的一种补充。在王氏词学批评当中,“修能”又指向对前人的学习,这与康德所谓相对于天才而言的那种模仿几乎一致。从诗人的角度来说,“内美”指天才/天赋诗人,“修能”指有才能的诗人,此时“内美”与“修能”可区别诗人之才气,天才诗人善创,其作品有创意而不可学;有才能的诗人善因,也就是善于模仿学习前人的技巧等。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来讲,“内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内质,有理想化色彩,而“修能”是后天的学习与积累,与现实更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可以将“内美”与“修能”之间的关系视为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天才天赋也离不开后天的修习,天才诗人亦是有才能之人,理想固然美好但终究离不开现实的支撑,因此,可以说“修能”补充“内美”,但有“修能”之人不一定就具有“内美”。在王国维看来,真正好的作品除了作家的天赋加持之外,还要有诗人高尚之品格的支撑,否则就难成真正的艺术。艺术的创作需要天赋,但是对于道德与品格却不存在天赋之说,而须得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培养,从这个层面来讲,“修能”的确是很重要的,“内美”与“修能”缺一不可。但因为境界之有无取决于诗人之理想(先天)和想象(先天与后天皆有)是否能够巧妙结合,“内美”之于境界的重要程度超越了对道德的强调,所以,王氏将“内美”置于“修能”之上。然而王国维虽强调客观自然,但他缺乏“亲在”,因此,对于一些诗人和作品的评价或许还是存在犹疑的,这种犹疑在理论上体现为:王国维在处理“内美”与“修能”的关系时想要兼顾二者但更偏向于前者即“内美”,在偏向“内美”的情况下又有二者之间的对立,“内美”以天才理论为立足点,是对天才理论的具体表现,“修能”以“古雅说”为基础,是对天才理论的反抗。
二、“内美”重于“修能”之表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更多以有无“内美”来辨别作品是否为“天才”之作,他很明确地说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9]27,“内美”的核心内容即灵感、自然和客观,在抒情文学当中这种“内美”是必要的,由灵感、自然和客观构成的“内美”指向一种对纯真的追求。及时捕捉闪现的灵感,客观地对待情感并将情感自然地表达出来且显出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这就是王国维在词学批评当中追求的“纯真”境界。如何才能达到“纯真”呢?王国维认为,当词人拥有真正的赤子之心时,创作就能达到“纯真”的境界。比如“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之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9]4,他认为李后主是具有“赤子之心”的,所以“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9]4。那么到底什么是“赤子之心”呢?在谈到李后主赤子之心时,原稿里面是有解释的,“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9]4,“天真之词”与“人工之词”区别何在?“天真之词”在王国维看来就是合乎自然、灵性充盈的天才之作,是具有“内美”的词人创作的能够达到“纯真”境界的作品;而“人工之词”是指在遣词造句上浮现雕刻之气的作品,是具有“修能”的词人创作的能够达到“古雅”境界的作品。王国维曾谈到过“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分别指向“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这里的“主观之诗人”身上便有这种天真美好,而溯其“赤子”的直接源流在叔本华所谓天才的“童心”,后主的“赤子之心”就是指他具有儿童般的天真与单纯。因此,他作为“主观之诗人”能够进入客观,自由的静观,这是他作为“孩童”的特长,所以王国维才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9]4。从这里便可以推断出,王国维所谓“天才”其实是指能够进入无我状态并自由地审美静观书自然之语、表自然之情,也就是“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9]2,同时也是相对于“人工”而言的,即创作不饰雕琢。仍然回到对李后主的两句评价当中来,既说后主处于深宫之中,又说他的词眼界开阔、感慨深切,可见阅历不多却能写出这样深刻的词,真正的是一位“童心未泯”的天才诗人,刘勰说神思就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12]248,而后主就是“形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海之上”,他的天赋才能体现出天才的本质。叔本华认为天才的本质是一种反思性,天才之所以具有这种反思性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意志的束缚、摆脱了个人的局限,所以能够深入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当中,而后主能够于深宫中写出如此超脱的词作就是他能以冷静超然的态度看世界、世人和人生。王国维称赞“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9]5,就是在说他对天才本质的深刻的呈现。“个性至深,人性始呈”是后主“天才”之所在,他的性情之真即天真与纯真造就了其词的超凡脱俗。“不懂世事而真曰‘天真’,透视人生而真曰‘纯真’”[13]10,后主的词真而意韵深远,是“真正之大诗人”,因为他以人类情感作为自己的感情,也就是叔本华所谓“人生的理念”,将整个人生真正的苦难、罪恶再现出来,所以王国维为何盛赞后主便可知了,因为李后主的创作展现了“内美”。王国维曾将境界分为“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所谓“诗人之境界”就是“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9]73;而“常人之境界”即“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惟诗人写之”[10]23,从表面上来看是在区分诗人与常人,其实是在区分天才诗人与非天才诗人,天才诗人能够摆脱个人意志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静观整个世界,而非天才诗人沉浸于意志当中,深陷尘世旋涡当中,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世界。因此王国维盛赞后主就是因为他达到了诗人之境界,他是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具有独创性而不可学。
“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9]20“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9]72。以上论说提到了“伫兴”“须臾”,都是说情感短促且难以捕捉,而王国维认为,真正的诗人能够把握这“须臾”之物,写出不朽文字,成为“伫兴之作”,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其中深刻的感情,而这感情是一般人无法捕捉且无法言语的。这与西方传统的“灵感说”是极相似的,前面也说到王国维受到西方“天才论”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古典文论“灵感”“顿悟”的深悟,王氏对“伫兴”“须臾”的强调恰恰体现了他对“内美”的重视。同时,“伫兴”“须臾”之作就是“诗人之境界”的体现,真正“内美”之诗人能感常人所不能感,能捕捉常人所无法知觉的细枝末节,这全然是因为天才诗人能够摒弃意志,冷静客观地注视世界、观察世界。因此,以“天才说”为基础的“内美”在王国维这里是指:“天真”与“纯真”并存,能捕捉常人所不能感之情物并“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9]2而不饰雕琢。
“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9]37,最好的作品不仅是要有创造力之表现,还要善于继承古人的创作精神与技艺。而创造力之表现更依赖于先天的才气,“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9]17,所以王国维在评价词人时实际上采用了两种标准,即天生禀赋所造就的自然之作与后天修养所成就的精妙之作,前者善创之诗人所作,后者善因之诗人所作,善创者天才也,善因者才子也。王国维心中的“天才”具有双重身份,即天才之诗人与天才之作品,天才诗人的作品当然是天才之作,但非天才者亦能创作天才作品,王国维也曾以古雅来说明这个问题,古雅作为后天习得的经验,可以对“内美”不足之人作补充,使得其作品能够达到低等的优美与宏壮,也就是说尽管这类作品被称之为天才绝妙之作,但与真正的天才诗人所创作的天才作品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只有‘天才’才具有审美力与艺术技能或卓绝大师的代名词”[13]9,天才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力,还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在创作过程中能自然运用而无雕琢之气;卓绝大师便是才子的代名词,或许他们缺乏独特的、天赋的审美力,但他们具有精妙的艺术技巧,虽有雕琢或模仿痕迹,却仍可以赋予作品非凡的意境。前者如冯延巳、李煜等,后者如周邦彦等。“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9]8“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9]8,“内美”的含义以“天才说”作为底色,王国维评价词人常关注创作技巧,其中也包含了他对“天才”的理解,天才作词不需雕琢便有境界,天分欠缺者或模仿、或技巧、或既模仿又技巧。他赞扬周邦彦是因为周邦彦的技巧用得自然,浑然一体,虽有雕琢痕迹,但胜在巧妙运用。即“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9]74-75,周邦彦的创作缺少天才气,然其作品也的确是精妙之作,算不上天才诗人,只能说是卓绝大师,其作品能称得上天才之作,有“善因”之才,而王国维也始终认为周邦彦是一个能够达到雅致却不能深刻到优美宏壮的非天才诗人。
因此,“内美”作为“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与“境界说”核心内容相契合,都强调真实自然,即客观状态下情感的真实自然、创作的真实自然。在此基础上再来评价词人,便有了依据和标准,即何谓真正的诗人?要以纯真之心、写真情实感、写“伫心之作”而不雕琢,此为天才的诗人,是“内美”之功;写真情实感而雕琢者,有“善因”之才,成就天才的作品,是“修能”之功。王国维在具体词学批评当中试图将“内美”与“修能”兼顾,却仍然滑向对“内美”的强调,他对“天才”的两种评价标准就体现了这一点。在《人间词话》当中王国维用“可学”与“不可学”来区分南宋词与北宋词,但其实“可学”与“不可学”也可以用来区分天才诗人与非天才诗人,其本质就是独创与模仿之间的对立。“内美”之人所创作的作品是天才之作,是不可学之作;“修能”之人创作的卓越作品也可以被定义为天才之作,但却是可学之作,也就是说尽管如周邦彦这类词人能够创作精妙作品但却永远不能与“内美”诗人的创作相比,这其中蕴含着王国维对“内美”的偏向。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才说”认为,先天禀赋与后天修养并重,但这更多是在儒教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观点,其实在更多时候大家还是更偏向于认为创作取决于先天禀赋。比如,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虽将先天禀赋与后天修养都尽可能考虑到,但实际上他并未始终陷于折中的状态,而是将先天禀赋看作是作家的先决条件,强调作家才略的重要性,这在他的《才略》篇中表达得很清楚;又比如,颜之推也看到了文艺创作与做学问之间的区别就是有无天才,他认为文艺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赋;再比如,明代的汤显祖非常推崇自然灵气,他认为创作文学作品必然要具备灵气,否则文不成奇文。这些都表明在中国古代文论当中还是比较倡导天才论的,或者说天才之于创作的重要性是非常确定的。西方文论则十分推崇天才诗人,王国维对中西文化的吸收铸成了其以“天才说”为核心的“内美”概念。但在具体使用时却又出现了分裂,比如对周邦彦的评价,在此他的“天才”立足于作品,认为周邦彦的工巧成就了作品,所以他可以成为第一流作家,而非天才作家。论及冯延巳、李后主等人时,又将“天才”立足于词人,认为是词人的先天才气铸就了佳作。虽然前者属于善因、后者属于善创,但实质上是王国维“天才说”的摇摆。也就是说,他认同后天修养对于先天基础具有维持与提升的作用,但是在其评价当中始终将“内美”也即“天才”置于“修能”之上,这体现了其思想的矛盾。
王国维为何会有这样的矛盾?第一,王国维写成《人间词话》时仅二三十岁,年轻气盛,对叔本华的“天才论”很是迷恋,一些表述还比较浅薄,对于后天修养的重要性避之不谈;第二,王国维的“天才”理论有两个来源即中国古代与西方传统,中国古代虽有对天才禀赋的强调,但更多还是将天赋与后天修能视为同等重要的,甚至将后天修能的重要性拔高到天赋之上,而西方传统自古希腊以来始终将天赋视为最重要的,居于这两种思想当中的王国维陷入了矛盾之中;第三,王国维所处时代变幻莫测,国家危难,革新在所难免,这里面有王国维自己的回应,他虽然更重视对“内美”的强调,但革新必然是求变的,而求变需要学习与模仿,“修能”便成为了革新的必要条件,所以在他的表述中就表现出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王氏其实都已觉察到应在诗人与诗匠、天才与人才间划一界限,事实上,在论及艺术品位级差时已将两者分开了……”[14]但“若以‘天才’即非功利的审美力为准,他无疑将失却对平庸艺术的批评权;若以‘天才’即高品位艺术创造力为准,那么,他的美学建筑赖以奠定的基石又将被动摇”[14],所以,在如何认识“内美”与“修能”的关系上,王氏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展现了其思想上矛盾复杂的一面。
三、“内美”何以重于“修能”
(一)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
中西方都有关于“天才说”的论述,西方自柏拉图以来都突出“天才”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更加强调后天学识的中国古代也存在强调先天气质比后天修养更重要的偏向。比如,叶燮在《原诗》中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15],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文章由学,能在天资”[12]341,刘禹锡也曾在论诗时说“工生于才,达生于明”[16],虽然文人学者仍然关注到后天修养对于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但是后天修养是建立在先天基础之上的,若是朽木,便不可雕。天赋与后天学习在文艺创作上最突出的区别就是“诗性直觉”,“诗性直觉既不能通过运用和训练学到手,也不能通过运用和训练来改善。因为它取决于灵魂的某种天生的自由和想象力,取决于智性天生的力量”[17]。前文也有提及,在中国古代文论当中有很多强调先天禀赋重要性的论述,只是囿于文化环境不得不将此认识推向一种中庸的折中状态。但这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古代有将先天禀赋看作是文艺创作的先决条件的情况,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才略》就是对儒家传统以道德来压制文才的观点的突破。儒家是比较轻视才能而重视道德的,在才与德的问题上,儒家一直是推崇后天的道德修养而蔑视先天的才华禀赋的,而天才论就是对儒家观点的一种反叛,因为具有先天禀赋的创作者往往能够冲破道德教条的束缚,这是儒家十分忌惮的。王国维在谈及天才论时也并未摒弃儒家的观点,相反他对儒家观点有所继承,比如,他认为,真正的天才之作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创作的,也就是说他虽然强调先天禀赋对创作的重要意义,但并未舍弃道德方面的约束,这是他的天才理论的创新之处,他将“内美”置于“修能”之上,但也将道德判断考虑进来,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天才诗人进行了一种约束,是一种更为严苛的判断是否为天才诗人的标准。但这种天才理论与道德标准结合的词学批评并未真正给王国维带来解决良方,而是让他常常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强调纯粹的审美判断,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的作用,虽然道德判断在他的词学批评当中较少出现,但也并不代表他将道德标准置于批评之外。因此,王国维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吸收是多面的,他认可古代文论当中对天才的肯定与重视,但也认可儒家所强调的道德规约,在此可以说,王国维的天才理论并不是与西方一致的纯粹天才理论,它是中国古代文论色彩浓厚的具有民族特质的天才论。
西方自柏拉图到叔本华等人,无一不强调天才的先天基础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也是将其提升到最重要的位置,认为天生的气质是诗人最为重要的品质,这决定了其作品的成就。甚至他们对于灵感的定义等,也是非常强调先天才能的,只有那些天才的诗人才能捕捉到那一瞬间的灵光,从而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艺术“就是天才的任务”[7]258。王国维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称其“思精而笔锐”,随后便读了叔本华其他论著,叔本华对于王国维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的深层哲学根基是叔本华哲学美学”[18]13。叔本华极力鼓吹人的纯粹意识的美,而这种美唯有天才可见,王国维“境界说”强调真实自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纯粹自然的美,也只有天才可感。可见无论是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十分重视先天禀赋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然而王国维在糅合中西理论时面对的是深奥难解的西方理论和复杂深厚的中国文论,于是王国维的理论便走向了一种不确定,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理论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时总会出现矛盾,这就决定了他在“内美”与“修能”关系上的犹疑。另外,王国维在对待中西文论的态度上更偏向于崇尚西方,他的理论移植西方理论并以此为体,因此,很难摆脱西方文论的强大影响且无法深入中国古代文论的内里。虽然中西都有强调天才的重要性,但是,西方天才理论的诞生与中国古代天才论的源起具有不一样的文化历史背景,西方的天才论之所以如此强势,就是因为它担负了抵抗古典文学的重要责任,而王国维将其完全移植过来企图与中国古代文论嫁接是十分困难的,所以,王国维在他的前后表述当中总是出现各种矛盾,而这矛盾的背后就是他对西方理论的崇拜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入不够,故他总是想要兼顾“内美”与“修能”的关系却又倾向于将“内美”置于“修能”之上。如果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底蕴是叔本华哲学美学,那么“它的理论内涵和表述方式又是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达到了兼容中西后的学理再创”[18]13。因此,以“天才说”为基础的“内美”概念是中西文学理论兼容的结果,但这种兼容又没有达到完美的融合,一方面是中国自古以来在对天才与后天修能孰轻孰重的几种观点中更倾向于推崇后天修能,另一方面是西方对先天禀赋的推崇,在具体的词学批评当中其实很难使得这两种倾向得到平衡。
(二)对现实的考虑
“夫考先生之严屏南宋者,实有其苦心在。词自明代中衰,以至清而复兴。清初朱(竹垞)、厉(樊榭)倡浙派,重清虚骚雅而崇姜、张。嘉庆时张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托尊词体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倡学梦窗,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风气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如铜墙铁壁,密不透风……先生目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之说以廓清之。《人间词话》乃对症发药之论也”[19]236-237。王镇坤先生这一段话便把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现实原因说得清清楚楚,词自明代中而衰,于清代复兴,然清代却极为崇尚南宋词,于是清代以来词的创作已经是学技巧形式而不得内容,宛如东施效颦,没有理解模仿对象之精髓要义,所以呈现出来的作品只能是“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如铜墙铁壁,密不透风”。王国维看到了当时文坛的问题之所在,所以重北宋而抑南宋,希望大家能够回到寻求真实自然的时代,而不是辞藻堆砌。重北宋而抑南宋也并非要复古北宋,而是“王国维的取法五代北宋,仅是为了弘扬其中的‘意境’”[20],“南宋人所失在‘专事摹拟’,如果在晚清再复古五代北宋,则其实不过是重蹈南宋之‘覆辙’”[20]。所以王国维对晚清词坛的批评更多是指向其对南宋的简单摹拟而失掉了词的意境。而意境的生发又必然要求创作的自然真实,虽人力亦可创造意境,然而在王国维看来真正深远的境界即自然、真切、深沉、韵味四者[21]非人力可及,只有真正的天才诗人才能做到。天才诗人的自然与真切才是创作者应该去学习的,故而将“内美”的地位抬高是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考虑,是一种有意为之,毕竟王国维内心还是认为“内美”与“修能”是并重的,因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8]113“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8]112。天才总是极少数,我们能做的就是向极少数天才学习,虽然这类作品有模仿雕琢之气,但也比堆垛故实、装点字面、东施效颦好得多。天才者不仅有深厚的学问还有高尚的品德,这也是后来者需要去学习的,只有学习到天才者的精髓才能成就好的作品。
王国维忧郁悲观的天性与求索人生的追求是交织在一起的,虽受叔本华影响,但全然没有冷眼看世界、看世人的冷漠,反而是悲天悯人的,对人世有所爱的。所以,《人间词话》必然还有除了肃清学问风气之外的目的,而这必然出自于先生对人世的悲悯。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先生既关心世变又不能涉身世务,于是退到学术研究,而在学术之中又无法忘情于世事,就在学问之中寄予理想。而那时的文学创作已然没有了传统文学的自然纯朴和深厚情感,正在消逝的《诗经》《离骚》的“风雅传统”,让热爱文学、研究文学的王国维无法置身事外,他深感悲哀,出于一种拯救中国文学的目的,他提出了“境界说”,提倡真实自然。清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分子陆续提出了“三界革命”,旨在以文学之改变拯救危难中的中国,提倡作家努力表现新的时代与新的思想,从厚古守古的旧文学中走出来,创造全新的境界,尤其是催生了文学进化的新观念。对此,王国维虽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实际上也是做出了一番回应的。针对当时“三界革命”影响文坛的现象,王国维是无奈的,他知道这是历史的必然,否则“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便无意义,但他仍然希望文坛不要忘却传统文学,不要只是求新而不知继承。“内美”是站立在“天才说”基础上的,代表了一种自然真实,“修能”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代表了一种求新求异,他将“内美”置于“修能”之上,代表了他对当时文坛的回应,即求新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放弃文学的传统,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求新。所以,他将“内美”的地位拔高,他不仅希望文坛众人能够清楚“天才禀赋”的重要性,更希望众人清楚由“内美”而生发的真实自然的表达和深远的思考才是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创造绝不是模仿,模仿是必要的,但绝不是出路。“修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模仿,学习新的东西、模仿前人的创作,在王国维看来这些绝不是从内心真正生发的情感表达,所以,尽管他也认为“内美”与“修能”同样重要,但还是在表达之中将“内美”置于更高地位,不仅是想要改变晚清文坛的浮靡与浅薄,也是想要回应当时文坛的“三界革命”,一味追求创新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所谓创新更容易变成模仿,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学了。谷永先生曾评价王国维说:“凡一种文学其发展之历程必有三期:(一)为原始的时期,(二)为黄金的时期,(三)为衰败的时期,此准诸世界而同者。原始的时期真而率,黄金的时期真而工,衰败的时期工而不真,故以工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二期及第三期者;以真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一期及第二期者。先生夺第三期之文学的价值而予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识也。”[19]237词创作至晚清已经是衰败的时期,工而不真,也恰好就是“三界革命”所带来的文学现象,新文学出现,但却失去了真,因此王国维将“内美”置于“修能”之上,的确有回应“三界革命”之意。
(三)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无论是中国古典文论还是西方文论的“天才说”,都关注到了天才对于宇宙人生的深刻关怀,这种关怀即叔本华所谓“天才的痛苦”。天才不同于别人之处就是能“摒弃欲念而对宇宙人生作持久的、非功利的审美静观”[13]11,正如王国维对后主的评价,说他“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9]5,只有看透人生本质之后才能达到这样的终极关怀。而这终极关怀是王国维诗学评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认为,只有那些天才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直击人心的字句,才是“独有洞见”之作。大诗人“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9]1,这里的“理想”包含了词境当中所凝结的意蕴,是对人生的遥深感悟。王国维“天才说”就是强调天才诗人的敏锐深刻以及他们对人生价值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形而上的,而是指向对人间的关注与思考。这里有必要谈一谈王国维的“人间性转向”,“人间”将《人间词》和《人间词话》连接起来,如果说王国维在《人间词》当中的抒发“更多的是在注重对个人、主体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词”[22],那么在《人间词话》当中他便将对“人间性”的追求运用到具体的词学批评当中。王国维的终极关怀不同于叔本华等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他的终极关怀从哲学的形而上思考转向对人间的注视。他的视角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从人间上升到宇宙人生,也就是说王氏的思考是从现实出发的。李煜书写的“血书”之所以能够得到王氏的极大认可就是因为后主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接受自己的情感,抒写自己的感悟,“血性真情”[23]是“人间性”的底色。“血书”情感的浓烈是基于对自己情感的正视与抒发,而其能够历经岁月走到当下并得到人们的共鸣绝不仅仅是其中流淌着的充沛的、真实的个人情感,更多还在于其中传达出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也就是说“血书”能够从个人走向社会并最终走向全人类。“个人‘血书’基础上的人类一般性之思”[23]便成为了“人间性”的境界。于是,“王国维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生之思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哲思,而是融入‘血书’真情体验的存在之思”[23]。
再说回到王国维将“内美”置于“修能”之上的原因,从个人的“血书”到“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不是简单的从个人到全人类的思考飞跃,而是从个人、人生、人世到人类的一次次突围,不仅是个人悲欢的抒发,也是历史人生的思考,更是对人类之思的哲学超越。因为这一历程从个人到形而上再到人间,若无天才的感知与敏锐是很难深刻的,更难实现种种思考视角的转换。当词人如李煜实现这种创作之后,还能跨越时间长河使得人们从中感受到深沉的悲叹与浓烈的情感,这意味着具有“人间性”的作品实现了作品与读者的交流对话。交流对话的基础是作品所具有的启迪性,启迪性不同于启蒙性,启蒙是对人类蒙昧的驱逐,而启迪意味着该作品对每个读者而言意义不同,每个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关于人生的不同理解。所以,在王国维看来,真正有境界的作品是从个人的“血书”到全人类的“血书”,从个人沉思到形而上的哲思再到人间烟火,而最重要的却是作品当中的启迪性,若无启迪便只能是创造者自己的感悟,意味着作品并未真正落实到“人间”。这是他诗学评价的最高境界,也是他对人世人生的注视,因此,王国维“天才说”的落脚点在于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上,而“内美”为何重于“修能”也更加明了,因为只有天才诗人才能“以血书人生”,达到终极关怀的境界,王国维“境界说”之理想境界是对于终极关怀的表达。
概而言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犹疑态度代表了其思想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内美”与“修能”哪个更重要的纠结,也可以说是关于“天才说”是否应该在文学创作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的思索。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纠结与矛盾都源于王氏对人世的关怀与悲悯,指向人生的终极关怀,他既关心世变又不能涉身世务,于是退到学术研究,而在学术之中又无法忘情于世事,于是就在学问之中寄予理想。理想源于现实,是对现实的深入,王氏的词学批评并未远离现实而是立足于现实。将“内美”置于“修能”之上是出自于对现实的关怀,对晚清文风的纠正、对文坛现象的回应,文学自身的发展不可阻也不可逆,王氏希望文学在“进化”过程中能够不失真、不浮躁、不浅薄,能够给国民以精神慰藉。因此,“内美”重于“修能”可以说是王氏的对于俗世的关怀在学问中的体现,其“天才说”也是不同于叔本华的,而是悲悯人世的、对世人有所爱的,正出于这样的悯与爱,他才会有“求其可爱”与“求其可信”的矛盾,才会有从形而上哲学思索到“人间性”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