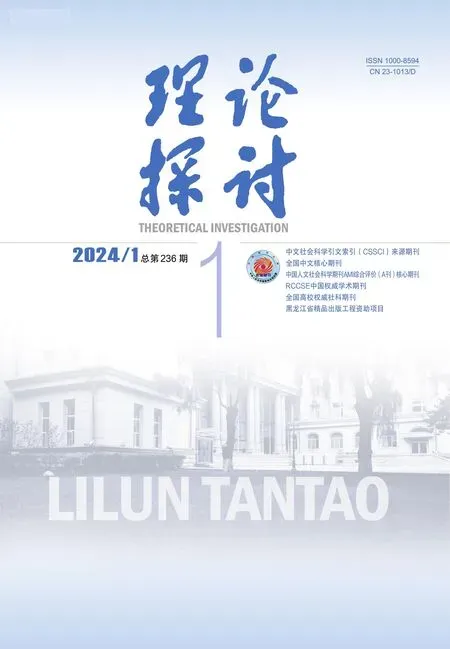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唐明燕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13的重要论断。此后,习近平总书记不断重申“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4]18。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便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从宏观层面解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探索其蕴含的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可以发现:“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支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的根本保障,“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构的基本方式。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探索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一、“人民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4]19,“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3]11,在上述理念与情感的指引下,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至上”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价值支撑,并贯穿整个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人民情怀既源自百年奋斗历程中与人民建立起的血肉联系,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群体本位”的价值导向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仁爱精神、德治追求和民本理想一脉相承。
(一)“人民至上”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群体本位”的价值导向
群体本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向导。这一价值导向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另一方面,得益于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
就农耕生产方式来看,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中国,农业耕作需要大量劳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产生最大的劳动效益。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中华先民追求人丁兴旺,由此催生出大家族的家庭结构。大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相对于核心家庭关系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群体利益摆在首位、以群体利益为价值导向,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维系大家族的稳定和睦,进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固。
就儒家思想的特点来看,儒学具有强烈的合群体性特征。儒学视野中的人是寓于群体之中的人,是有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在身的社会人,每个人都须按照社会关系定位自身,都要依赖群体才能生存。在儒学视野中,离群索居没有出路,即谓“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为了更好地“群”,儒学从创始时期便着手探索各种解决方案,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规定的是人们彼此间的责任、义务,所维护的是群体利益。从孔子开始,儒学就开启了在群体价值中实现个体价值的思维路向。例如,据《论语》记载,当子路追问孔子什么是君子时,师生之间展开了这样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绝不应止步于“修己以敬”,君子一定要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和抱负。这种不满足于独善其身,而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理念,伴随着儒学地位的提升,在古代社会被大力弘扬,进一步涵育、强化着中华民族“群体本位”的价值理念。
在“群体本位”的价值导向下,中华民族倾向于把群体利益作为评判个体价值的参照系,看重的是个体对群体的贡献而不是一己之得失,认可的是以大局为重的处世方式,弘扬的是甘于牺牲、奉献以及在必要时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勇气。这些价值取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导向,成为中华民族责任意识、担当意识、集体主义、爱国情怀的根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萌发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的文化渊源。
(二)“人民至上”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爱大众”的执政情感
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群体本位”落实到情感领域表现为“仁爱”,具体到执政情感,表现为仁爱大众。
从词源学的视角来看,“仁”作为会意字,表征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依靠的关系。当学生问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儒家重视血缘亲情,孔子所讲的仁爱首先指向的是血亲之爱,即“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但儒学并未将仁爱局限于血亲之爱,而是从血亲之爱出发,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同理心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同情心的推动下,突破血亲之爱的狭隘,将爱的对象拓展至更大的范围,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
孟子把推动“仁爱”拓展的这种同情心、同理心称为“恻隐之心”,又称为“不忍人之心”,即不忍别人受苦的心。这种不忍别人受苦的恻隐之心在执政情感上体现为仁爱大众。儒家认为,执政者若能将恻隐之心施于百姓,便有望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即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关于恻隐之心的发生机制,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证实: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主体通过目睹等方式体察到对象的痛苦而发生共情,真正的同情和怜悯会驱使人为了他人的切身利益而帮助他人[6]。儒家在提出相关理论时,尽管没有现代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实验数据作支撑,但是他们却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中直觉到了这一点,因而以追求王道政治为目标的儒家政治伦理一贯倡导君主体察民情、体恤百姓疾苦,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7]。
如果说在古代社会,这些对执政者的要求只能作为“理想”而存在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则将这些理想转化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作为自己的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8]。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9]66。他特别鼓励领导干部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和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去桂林考察,当村民因为他百忙中的到来而致谢时,他回答:“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10]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作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执政者仁爱大众的要求一脉相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自觉性,了解民情、体察民意以及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实践,是对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的仁爱精神的升华。
(三)“人民至上”立足并超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德治”的执政理念
“群体本位”的价值导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仁爱大众”的执政情感落实到具体执政理念上,主要表现为以民为重的民本思想和以德治为核心的治国理念。
“民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11]。“民本”意味着将民众视为政权的根基。“德治”主要表现为采用道德感召和道德教化等民众易于接受的柔性方式来治理民众。中国古代民本、德治的思想可以追溯至西周。西周统治者在政权确立的过程中看到了民心向背的力量,他们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开始重视道德在政权运行中的作用,提出了“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理念,例如,《尚书·蔡仲之命》便提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直接将天意与民心联系到一起。此后,民本、德治的思想被儒学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最为光辉的部分。在君民关系上,儒家认识到君权需要民众基础,政权稳固与否取决于民心向背。例如,儒家以舟和水的关系来比喻君民关系,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甚至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理念。为了获得民心,儒学规划了一系列具体的施政方略,例如,置民之产,使民以时、索取有度,德主刑辅、教化为主,收孤寡、补贫穷,取信于民,与民同乐,等等。
在重视民众力量和民心向背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上述思想精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3]9,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的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为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尤其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目前,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略与儒家政治伦理的思想精华有类似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又不同于儒家的政治伦理,因为“民本”并不是儒家政治伦理的单一向度,它还有另一向度,那就是“君本”,即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其在吸纳儒家思想而实行一些惠民措施时,主要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这些措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中国共产党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3]11-12。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在致力于进一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力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正由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4]6。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担负起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任。中国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这不但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5]。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契合“大一统”的中国传统国家理念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国家理念的集中表达,“大一统”国家的维系和巩固历来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大一统”的基本内涵是政权一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想一统,并以思想一统进一步巩固政权一统。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真正的“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庸》)的“大一统”理念却早已有之,在《尚书》这部记述上古时期历史的著作中便有体现。例如,《尚书·尧典》中就出现了“协和万邦”的说法,并把原本属于不同部族的驩兜、共工、四岳、皋陶、益、夔等,安排为尧、舜朝廷里的大臣,这反映的就是“大一统”的思想理念[12]。《诗经·小雅》中也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诗句。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孔子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视作天下“有道”的标志,孟子认为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认为“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墨子认为“上同而不下比”“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至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大一统”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并分析了缺乏统一领导的危害,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的“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随着时代命题的变化,“大一统”又被赋予疆域方面的大规模或大范围统一等含义[13]。在实践层面,历代王朝都围绕“大一统”的理想进行经济、军事、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建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大一统”的理念一直作为正统思想而存在并成为政治传统而深入人心,其对加强中央集权、增进国家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防止国家分裂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国家一盘散沙之际,重新给中国人民带来秩序、安宁和幸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责任。为此,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汲取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智慧并予以创新,在维护领土完整、民族团结、政权稳固、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证明:在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障的时期,各项事业就能迎来胜利;反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涣散的时候就会遇到挫败。因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强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3]11。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需要坚强统一的领导集体,而这个领导集体需要有坚强有力、受到党和人民衷心拥护的领导核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着9,8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具备战斗力和凝聚力。领导核心是全党的定盘星,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掌舵者。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14]。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9]26。
(二)“全面从严治党”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答案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19,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就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自我革命主要包含两个向度:一是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二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方面,党中央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促使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方面,以严为基调,从引起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的作风问题抓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特色党建活动,尤其在反腐败方面更是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取得了卓越战绩。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从2012年的75%上升到2017年的93.9%;人民群众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的信心,从2012年的79.3%提高到2018年的94.1%[15]。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发掘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文化底蕴:
1.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政治伦理对执政者的个人素质十分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道德表率和道德感召力;二是重视执政能力。
首先,就做好道德表率、增强道德感召力而言,儒家认可的是“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即执政者在管理政事时首先要管理好自己。在儒家看来,执政者是“治之原”,是“民之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执政者的所作所为对整个社会发挥着强大的示范作用,足以引领社会风气。对此,荀子作了一系列生动比喻,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君主的道德表率不但是一种示范,而且还会产生凝聚力,赢得百姓的信任,甚至可以达到“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的理想治理效果。
其次,就提升执政能力而言,儒家认识到了规章制度的局限性。例如,荀子提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的观点,在荀子看来,既不存在注定治理不好的国家,也不存在不依靠人便能自行治理的法规制度,这就如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荀子·君道》)。后羿射箭以及大禹治理国家的方法尽管并没有失传,但是因为后世缺乏有能力运用这些方法的人,所以导致方法本身也失效了。由此,荀子认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因素在于治理国家的人,即“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
总之,注重执政者的道德品性和执政能力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全面从严治党”列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这就体现了对上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居安思危的辩证思维方式。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以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是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思维发达,在道家思想中体现得尤其明显。道家试图通过探索“道”的运行规律来为治国理政、为人处世提供指引。关于“道”的运行规律,《老子》的经典概括是“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反”所蕴含的一个重要含义是“相反”,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第二章)。而且,对立面依据一定的条件还会互相转化,例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基于这样的思想理路,道家深谙物极必反的道理,深具忧患意识。老子提醒人们应保持对事物性质向对立面发展变化的警觉,要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即“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略体现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思维的熏陶。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向好、蓬勃发展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危机,他反复提醒全党不能盲目乐观、安于现状,而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16],这是一种远见卓识。
三、“守正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4]20“守正”的核心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4]20。“创新”主要体现为紧跟时代步伐,在实践中不断拓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可以确保“创新”的正确政治方向;“创新”是守正的内在要求,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应对新事物、解决新问题,避免“守正”沦为教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17]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中华民族的“守正创新”主要表现在“革故鼎新”优良传统、“时”的思维方式以及“因时权变”的实践智慧,它们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的历史渊源。
(一)“守正创新”植根于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5],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中都有突出表现。以精神文明中作为民族精神重要来源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例,其发展历程便是一个守正创新的过程。
在西周之前,占据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是天命鬼神观念,西周统治者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感悟到了统治者的道德素质以及民心相背对政权兴衰的影响,这种认识是对人的主体能动价值的初步肯定。到了春秋时期,人道从神道中崛起的势头进一步加强,天命鬼神的地位则进一步削弱,关于道德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对孝、忠、信、义、勇等道德范畴有了初步探讨。春秋末期及至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深刻变革之中,思想家们针砭时弊、寻求出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后来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主要通过两重路向对儒学进行了理论建构:一方面承袭了西周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并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中所蕴含的道德因素突显出来,通过“仁”和“礼”的理论架构将其渗透进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孔子虽为儒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但其论述大多停留在“应该如此”的层面,而对“何以如此”未深入探究,留下了较大的理论探索空间。孔子之后,墨家、法家兴起,他们的理论锋芒皆直指儒学。这样,理论拓展以及应对外界挑战的任务便落到孔子后学身上,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更看重内在心性的力量,荀子则更看重外在规范的作用,他们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宗旨的前提下,批判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分别从“仁”和“礼”的维度对儒学作了较大创新。在两汉时期,在思想界占据上风的首先是黄老道家。黄老道家是在先秦老庄道家的基础上,通过兼容百家而发展起来的道家新学派。黄老道家“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因更适合汉朝初年百废待兴的局面、能够发挥医治战争创伤作用而受到青睐。随着汉朝内外形势的变化,代之而起的是儒学,大儒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的思想来改造儒学,使之更适合于封建统治,助推儒学走上了“独尊”地位。董仲舒之所以能称得上是儒学大师,不仅在于他为封建统治秩序作论证,而且在于他也以同样的方式为儒家所信奉的伦理道德作论证,从根本上来说,他并没有背离儒家的宗旨。此后,儒学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又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分,二者之间相互辩难,客观上推动了儒学的自我完善。此外,随着中国和“西域”的交往,佛教也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并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国佛教。此时,道家也在创新中谋求发展,一方面在坚守道家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对儒学相关理念进行批判、吸收,在魏晋时期形成了新的学术形态,即魏晋玄学;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佛教的一些观念和传播方式,创立了道教。东汉之后,中华文化形成了儒、释、道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的文化格局。在这一文化格局发展的过程中,儒学因经学的日益僵化以及佛、道的挑战,在学术上显现出衰颓之势。至唐朝中期,儒学的自救与革新被提上日程,儒家学者们既排佛、排道,又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为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人伦秩序进一步建构形而上的依据,使之系统化、精致化、哲学化,使儒学在宋明时期达到巅峰,即宋明理学。宋朝之后,学术自由的空气虽日益消退,但思想界的创新并未中止,中华文化仍在发展,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实学思潮、乾嘉朴学可以看作宋元明清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发现,有两股力量对推动思想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时代问题的关切与回应。例如,“百家争鸣”是对整顿社会混乱局面的回应,黄老道家的兴起是对汉初民生凋敝问题的回应,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是对加强中央集权政治需求的回应等,对时代问题的关切与回应是创新的重要动力。二是学派之间以及学派内部的张力与交融。例如,先秦时期的孟子与荀子之间、两汉时期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均体现出学派内部的张力与交融对创新的推动;而学派之间的张力与交融主要表现为儒、释、道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儒释道在自我批判和彼此批判中完成了对各自理论体系的改造与更新,而且在改造与更新中,各个学派又都守住了自身的思想之“正”,而没有被对方取代。
对时代问题的关切与回应,显现出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有使命担当的文化;学派之间以及学派内部的张力与交融,显现出中华文化是开放包容、富有反思批判精神的文化。中华文化这些自古以来形成的特质以及由此具备的突出的创新性,是支撑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深层动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5],“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5]。
(二)“守正创新”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的思维方式以及“因时权变”的实践智慧
“守正创新”不仅体现在大方向层面对思想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也体现在对具体思想理念的实际应用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能简单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套今天的中国实际,也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是怎么说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亦步亦趋,那还怎么前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8]打破教条主义、懂得通权达变,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是“守正创新”的应有之义。这一点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的思维方式以及因时权变的实践智慧中找到渊源。
以“时”的视野来思考问题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言之“时”并非单纯指“时间”,而是包括时、空、人、物等各种相关因素在内的综合体,呈现的是特定时空下存在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之间互动消长的总体状况。“时”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具体的“时”之下进行的。因而,要想取得成功,首先便要对当下所处的“时”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进而应“时”、乘“时”,这个过程是“因时而权变”的过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野中,能够因时权变是智慧的标志;反之,则是愚蠢的表现,即:“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论语·阳货》)“时”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因时权变的实践智慧在中国古代主要思想流派中几乎都有体现,儒学尤为明显。儒学是一个以道德为旨归的学派,考察儒家践履道德规范的过程,可以发现他们在具体运用道德规范时,往往会根据具体情景而呈现出比较高的灵活性,“动静不失其时”(《周易·艮卦》)。例如,儒家虽然崇尚“孝”,倡导孝子应对父母尊敬与服从,但是当出现父母违背道义的情况时,荀子明确提出了“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的观点;再如,儒家虽然崇尚“信”,并把“信”列为“五常”之一,但是当践行诺言就要违背道义时,孟子认为完全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下》)。关于儒家践履道德的这种灵活性,孔子曾有一段现身说法,他把自己同伯夷、叔齐等人作对比,得出一个自我评价:“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孔子认为自己与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自己并非固执于一定做什么、一定不做什么。当然,对道德原则灵活运用的“动静不失其时”“无可无不可”并非毫无原则的随意变通,而是有前提的,应“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义”即能够统摄诸种道德规范的更高的原则。在儒家看来,“义”绝不能违背,应在“义”的指引下全面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确定如何运用道德规范。对“义”的坚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守正”,“守正”是变通的前提。这种“守正”基础上的变通,既避免了教条主义,也避免了不讲原则的实用主义。
中国共产党秉承上述优良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事策略,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尽管是普遍性真理,但是普遍性真理也只有与中国当下具体实际相结合、领会其精髓并用于解决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才能发挥出切实作用。习近平强调:“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1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牢牢立足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变和不变,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在坚守正道、不偏离马克思主义即“守正”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深刻影响,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维方式、人文精神、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文化基因和深厚历史渊源,“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5],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色”的来源。
作为21世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熔铸了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积累的理论成果,又合理继承、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思想智慧。深入理解“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透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抓手。
On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ANG Mingyan
(School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 shining example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realities and with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and it contains the genes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onsistent manner: "people first" is the value support of the whole thought,"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all-around leadership"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le thought,and "observing the right and innovating" is the basic way of constructing the whole thought."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le ideology,and "observing justice and innovation" is the basic way of constructing the whole ideology.These consistent spirits are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adherenc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but also the reasonabl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combinations",especially the "second combination",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mprehensively recognizing and deeply grasp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Keywords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Two Combinations","The Second Combination",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