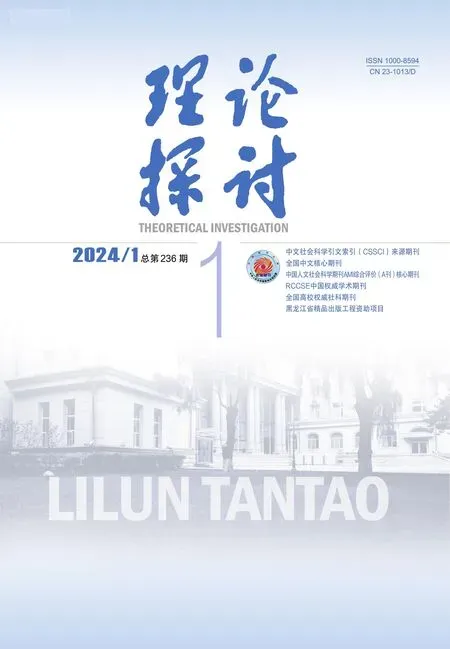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居民消费行为重塑
◎乔 榛
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如何扩大消费或推动消费需求增长?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消费首先是人类的生存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1]621人类的经济活动始于生产,但其目的是消费,对早期的人类来说也就是生存。虽然消费对人类非常重要,但很晚才进入经济学的视野。最早的经济思想关注的是财富生产,也关注到财富的交换,但并没有将消费引入研究领域内。古典经济学诞生后,其关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财富的性质和原因问题。恩格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从最广的意义上概括为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2]。消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被动地位,首先被马克思意识到,进一步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取得重要地位,成为“有效需求”的一部分并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研究。消费甚至从需求中分离出来,成为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更加凸显。随着消费问题凸显,研究消费本身和消费的影响因素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形成对消费越来越广泛的研究。
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可以大致分为生产因素、收入因素以及人们的消费行为因素。消费受生产决定,是消费理论较早的认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并不是研究的重点,亚当·斯密对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主导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线索。古典经济学的另外一位学者——萨伊,尽管关注了需求,但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供给自行创造需求[3],以此来否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实质上并不是要对需求或消费进行研究,而是把需求或消费看作供给或生产的“附庸”。因此,消费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虽有提及,但还谈不到对消费有真正的研究。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不仅关注到生产,还在广义的生产关系意义上纳入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环节。这四个环节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不断循环的生产过程,其中,以生产为起点,以消费为终点,以分配和交换为中间环节[4]91-92。如此,马克思给了消费应有的地位,并集中讨论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4]93-94马克思不仅提升了消费的地位,而且将它与生产建立起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成为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指出了决定消费的核心因素——生产,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不被重视的消费,在宏观经济学创立后有了重要地位,成为关注的重要对象。消费被经济学重点关注,是以消费作用凸显为前提的。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者的主导地位凸显,消费者的消费对生产有着强大的引致作用。市场上能够销售产品的种类和规模,决定了生产的取向和规模,即消费者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销售什么,消费者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销售多少。消费者的需要成为生产和销售的出发点。在这种消费者主权下,消费的决定因素主要是收入,并以此形成不同的消费理论。一是绝对收入假说,也即凯恩斯消费理论,阐述了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的思想[5]。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只以收入来解释消费,因此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收入是如何决定消费的?凯恩斯引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指出收入增长可以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加并不与收入同步,而是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会出现递减的趋势。这成为收入决定消费的重要机制,也是解决收入促进消费的关键。二是相对收入假说,由杜森贝里提出,核心观点是:消费者会根据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水平。因此,人们的当期消费是相对决定的[5]。三是恒久收入假定,为弗里德曼所提倡,认为恒久收入,即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着消费水平,或者说,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水平决定,而是由其恒久收入水平决定[5]。四是生命周期假说,由莫迪利安尼提出,其基本观点是:人们在特定时期的消费不仅与他们在该时期的可支配收入相联系,而且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生活的消费开支,以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5]。这四个消费理论是收入影响消费的主要理论,实现了对消费的收入因素的多角度分析,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除以上两类消费的分析视角以外,还有一个视角,对认识消费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具体来说,影响消费有生产的因素,反映了消费的根本性依据,还有收入的因素,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得以实现的主要依据。此外,人们的消费行为也会影响到消费需求的水平和结构,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消费行为的经济意义体现在不同方面。在较早的研究中,消费行为被界定为人们对可支配收入的使用方式,如节欲和挥霍。当然,这种对消费行为的描述也只限于有富余收入的人群。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消费只是一种自然行为。马克思曾就节欲和挥霍行为进行过分析。马克思通过对节欲论的批判来阐释自己的节欲观。是什么决定了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对此,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资本家的节欲程度。马克思认为,节欲并不是反映资本性质的资本家消费行为。除在资本主义初期由于生产水平决定的资本家节俭行为以外,由资本性质决定的资本家消费行为是挥霍甚至是奢侈,而不是节欲。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1]651由此可见,消费行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影响了消费,而且还是致富的手段。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制度学派那里有了泛化的理解,即将消费赋予社会意义并产生了一种新消费行为。如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占有财富,与其说是满足生理需求,倒不如说是为了面子。谁拥有的财富多,谁就是社会的优胜者,不仅社会地位上升,还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誉,从而使虚荣心得到满足。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性大为加强,人们社交范围也随之扩大,富人要想给陌生人留下富有的印象,最好的办法是大量消费,所以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一掷千金,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远在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还任情消费,挑选最好的商品,过着佳肴美酒、肥马轻裘、歌舞升平的奢侈生活[6]。凡勃伦所揭示的既是一种现象,也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批判,但指出了消费的一种社会意义,即消费不只是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炫耀其社会地位的行为。在这样的消费行为下,消费主义得以盛行,为消费需求扩大提供了新的动力。
消费所受到的不同因素影响,为理解消费和寻求扩张消费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其中,消费行为对消费的影响是一个人们虽有提及,但很少加以深入分析的问题。在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和进入高收入阶段,消费的扩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分析消费行为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二、消费行为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性特征
消费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命得以维系必须从外界获得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然而,人类的这一活动具有特殊性,因为他超越了自然属性,具有了社会意义。把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这一活动称为消费,也反映了人类生存的特殊性。人类消费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具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表现在消费行为方面的历史性更为明显。
(一)人类早期的消费行为简单且生存的特征明显
人类早期也即人类文化初期,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分为不同阶段。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引用过摩尔根的话指出:“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7]17人类获得生活资料的特殊性被赋予消费的意义,因此决定了人类消费行为的阶段性特征。在人类生产技能还十分低下的时期,消费作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手段,既有自然的性质,也有社会的性质。所谓自然的性质,是指消费用来满足人的生存,其行为与其他生物无异;所谓社会的性质,是指消费还需要保证群的存在,体现出来的消费行为具有利他倾向,当一群人合作打到猎物后会在整个氏族中平均分配,而不是谁打到猎物谁就占有并独自消费,这种消费行为非常重要,它成为人类得以脱离动物状态的前提。恩格斯就此指出:“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7]29为了维系这个群,人们的消费行为自然以能否维系群的存在为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初期的消费实现了一种个人和集体的有效结合,并且达到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条件下的个人生存和集体生存的统一,而且人类的集体生存和其他动物的群体生存不同,不但在规模上有区别,而且分工合作的程度也有差异。因此,对人类文化初期消费行为的考察可知,消费达到了一种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并成为人类进步的重要保障。
(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消费行为开始从社会性消费向个体性消费转变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消费在人类文化初期达成的个体和社会统一转向纯属个人或家庭的行为,形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力的进步。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实现了生产力的重大进步,曾经以渔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产方式发展到最早的农业生产方式,以此为标志,人类开始进入文明阶段。与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同步的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早期生产力进步的重要阶段,一个重要经济特征便是农业不断发展。种植业和养畜业从诞生到发展,逐步培育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在带来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创造出比过去更多的财富。这对于人类来说,不仅可以借此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人类的消费方式也从过去的集体消费变成个体或家庭消费。由此也引发人类消费行为的变化,消费不再是维系群体延续的行为,而是满足个体需求的手段。这种转变的背后包含另一个重要变化,即激活了人们追求生活富裕的动力,使消费或满足个体消费需求成为生产的动力,也使生产力发展有了新的动力。与其同时,人类社会也进入了阶级社会,阶级差距和不平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状态,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行为,使消费行为除满足自身生存以外,还有了引导和比附的特征。当然,进入文明社会或农业社会后,生产力的进步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落入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即生产力提高创造的更多财富导致人口增加,从而使增加的财富被增加的人口消费,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并未提高。在农业时代,这样的生产力进步逻辑显示的是一个近乎停滞的状态,虽有人口增长的趋势,但无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因此,基于农业文明改变了的人们消费行为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消费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被极大地抑制。
(三)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消费行为出现重大改变
随着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人们的消费行为得到释放,进入了一个消费时代,甚至掀起了一个消费主义潮流。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迎来一系列重大变革,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资本主义萌芽、工业革命等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特别是生产力巨大进步,开启了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增长时代。对于近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进步,马克思有过一个经典描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很大程度地释放了人们的消费行为,以追求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之外的生活需求主导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当然,由资本主义社会释放出来的人们消费行为,势必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明特征。社会的贫富分化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形成不同取向,并影响了消费行为的进一步演进。一方面,人们消费水平整体性提升;另一方面,人们消费行为受主流导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大发展,创造了多样而丰富的消费品,也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不仅生产出丰富的消费品,而且不断地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使人们既能够消费到更多之前没有的消费品,也能够购买到更多数量的消费品。消费品越来越丰富形成消费升级的新趋势,进而产生了消费行为的主流引导和跟随效应。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突出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消费升级呈现明显的梯度演进。资本家和富裕阶层人群是消费的引领者,他们最先消费高档消费品,并形成社会的主导消费倾向。这样的消费倾向会引导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驱使中低收入者也向高收入者看齐,成为驱动消费升级的一个特殊动力。当这样的消费倾向扩张成为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便产生了所谓的消费主义文化,消费至上成为社会的潮流。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的生存需求彻底转向生活需求,谋求生活舒适甚至奢侈生活成为一个重要取向。当然,这背后有生产力发展、商品价值实现对扩大消费的需求逻辑,但消费行为的独立性也越来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影响生产的作用。
(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反向消费倾向
反向消费是消费主义文化式微后的一种消费新倾向。反向消费是一种反映人们追求高品质和性价比消费观念的消费行为,因此,反向消费具有更多理性的成分,是对过去炫耀性消费的一种调整。反向消费是在具有引领消费潮流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的注重实际需求、关注产品真实价值、并且更加精打细算的消费行为。在反向消费这一新潮流下,人们对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的选择有着更加明显的服务化倾向。反向消费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遍,人们较少为名牌所困扰,朴素和舒适是人们的主流需求,更多的人趋向于提升消费的服务性和舒适度。我国在将要跨入高收入社会趋势下也表现出明显的反向消费特征。年轻人不再追求奢侈高端、价格昂贵的商品,更加注重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化的消费,消费的非理性向理性化转变,对消费品品质和消费体验的追求渐成潮流。
消费行为的转变,既是对消费主义的逆向反应,也是人们的消费需求转变使然。消费主义有其发生的时代根据,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一种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主义有其必然性,但是消费主义盛行越来越偏离了消费为满足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的目标,使消费变成目的,并成为人们证明自己的标准,如此在较长的时间里人们一定会感到迷茫,势必对这种消费主义进行反思。随之,人们开始理性地看待消费,不仅要使消费回归其本质,而且还要使消费升级有新取向。人类消费始终围绕衣食住行展开,不断提升消费水平也多是在这个范围内拓展和升级,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具备了满足人们这些需求的生产能力,开始从消费的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拓展[9],更高层次的服务消费成为满足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向。这不仅使消费功能内在化,而且开辟一个更加广阔的消费空间,并将锻造人们全新的消费行为。
梳理人类消费行为的历史变化,可以发现一个演进的规律,即人们的消费行为变化的基础在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为人类提供消费品的规模,而且影响着消费行为的形成。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时代,消费体现为较强的社会性,实现了消费的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的统一。当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的个体性凸显,消费行为倾向于追求自身满足的最大化,并逐步演化出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消费超越了生存满足功能而具有独立的意义,还具有了显示消费者身份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消费的攀比和竞争性倾向。这种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出现了“疲态”,以追求消费的性价比和品质的理性消费行为成为一种新倾向,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反向消费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消费行为的这种历史演进还伴有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成为关注消费需求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这种消费行为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影响,进而形成消费行为影响消费需求的不同机制,也即各有特色的机制。
三、消费行为影响消费需求的特殊机制
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有很多,最为直接的是生产力和收入水平。生产力决定了生产消费品的规模进而影响到人们能够享用消费品的数量。在自给自足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直接决定了消费需求的规模,因为是自给自足,并不存在收入水平与消费的关系,然而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并不能直接决定消费规模,因为人们获得消费品必须通过交换的途径。生产力虽然决定了消费品的数量,但人们要获得消费品,需要先有收入,再用收入去购买。因此,收入成为获得消费品的必要前提,收入多的人可能获得更多的消费品,收入少的人则难以买到自己需要的消费品。
(一)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是人们获得消费品的基础和条件
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阶段,人们面对稀缺的消费品,加之收入也比较低,消费属于一种被动的行为,严格地受到能够生产的消费品数量以及收入水平决定。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并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时,消费的被动地位开始改变。消费从过去被动地被生产决定转变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生产。这样的时刻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并发生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创造出超过之前历代所创造财富的总和。如此生产能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引起了严重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实质是生产过剩或者说是价值实现出现了问题,也就是需求不足,其中主要是消费不足。在这样的趋势下,消费的地位发生改变,不再是过去被动地接受生产的限制而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并不断增强。消费的主动性一方面表现为对生产具有一定的作用,成为商品价值实现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表现在消费本身也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具有显示人们地位的功能。消费具有的主动性凸显了消费的重要性,也使得消费行为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开始影响经济运行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消费行为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就有了现实价值。
(二)消费行为非理性影响消费需求的机制
人们把得到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用于消费?或者人们是否会把未来的收入用于当下的消费?这些都与人们的消费行为有关。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的消费行为被放大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消费行为放大有个过程,从最初的少部分人追求奢侈消费到更多的人跟随,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流行着一种节约的风气。如马克思所讲的:“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1]65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和之后的资本家消费的描述指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使是资本家的消费也有一个演变过程,从早期还有的节俭风格逐步转变到奢侈状态。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才使得消费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并显示了消费的行为性特征。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收入差距比较大的社会,消费行为只有在形成竞争或比附的局面时才能显示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力。资本家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有钱的人,也是引领消费潮流的人。在资本家的消费引领下,其他相对低收入者开始比附资本家等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行为,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消费潜力,促进了消费需求。在收入差距比较大并以此显示地位的情况下,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会引起相对低收入人群的比附,并随着程度加深而得以扩展。这也成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循环的一大景观,成就了一个高消费、高产出互动的经济发展新逻辑。从事实上来看,现代资本主义消费行为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繁荣期就具有典型意义。当然,必须认识到,这种消费行为有其消极的一面。过度的消费往往会透支未来,如此消费是不可持续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有消费狂飙的时期,但紧接着便是经济危机,出现消费严重不足、经济停滞的状况。20世纪20年代、50年代、60年代都出现消费扩张和经济繁荣的情景,但之后的经济大萧条和经济滞胀终止了消费狂热的趋势,使消费进入了新的低潮。因此,消费行为影响消费需求有着不同的取向,并形成不同的消费需求变化轨迹。从长期经济增长和扩张消费需求的角度看,形成更具理性的消费行为,是构建高生产力水平和高收入背景下消费行为影响消费需求有效机制的必要前提。
(三)消费行为的理性化影响消费需求的机制
这是关注消费行为与消费需求关系新的立足点,需要加以深入分析。在消费主义盛行时,消费的非理性、攀比、浪费等行为确实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不仅最大限度地花费了自己当前收入,还以债务的形式透支未来的收入。这种消费行为虽然极大地满足了当下的需求,但也积累了未来的负担,两相比较:在短期内,满足当下消费比未来负担有着更大效应,如此会促使人们更加放大自己的当下消费;在长期中,未来负担趋于现实并使自己感到极度压力,如此会引起人们对其消费行为的反思,从而向消费的理性化转变。各个国家根据其发展阶段的不同,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发达国家既经历了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也经历了消费的非理性扩张,但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逐步向理性化消费转变。如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放弃奢侈性消费甚至高消费、生活回归到平常的状态,或寻求简约且高品质生活。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形成了消费主义文化,攀比性甚至奢侈性消费盛行,一个还处于发展中的大国已达到奢侈品消费第二大国的水平。虽然有人口规模的因素,但消费的炫耀性和攀比性特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消费行为带来的影响越来越趋于消极的一面,因为人们始终受困于消费欲望难以满足的境地,不管自己的生活水平相较于过去有多大变化,但还是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仍然需要为达到更高的消费水平而奋斗。长期如此,势必会引起人们对这种消费行为的反思,去追问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目的这样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也开始转变自己的消费行为,使消费变得更加理性,出现如前所述的反向消费。
放弃了消费至上的消费主义文化,使人们无节制、无顾忌地消费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消费看作人生最高目标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得以转变,对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是有利的。当然,这种消费行为变化也会带来消费需求的相对减少,因为不愿维持高消费、放弃奢侈性消费、不愿透支未来消费,一定会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这也是人们对消费行为转变感到的一种担忧。不过,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转变消费行为,出现类似反向消费的情形,可能会重塑消费结构,形成一种新的消费增长趋势。仅以反向消费来看,短期内出现消费降级,不消费或少消费成为一种潮流,这虽然会影响到消费需求增长,但这种消费行为转向也是孕育新的消费倾向、形成新的消费观念的起点。可以相信,在人们的收入持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下,消费还将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行为,势必会创造出新的消费形式、形成新的消费结构。对于目前出现的反向消费现象,一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们消费躺平,而应该是对过去消费行为的一种反向修正,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修正后,一定会塑造出新的消费行为并以更高品质的消费塑造新的消费结构。其中孕育的新消费空间可以成为未来扩大消费的主要立足点。关键是如何引导消费者尽快完成消费行为转变,进入一个新的消费空间,以新的扩大消费方式来重塑消费增长机制,畅通经济新循环。
四、基于居民消费行为转向的扩大消费策略
扩大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如何扩大消费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需要多方探索、积极施策。扩大消费虽然要有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也需要增加人们收入的前提,但在收入水平继续提升的趋势下,关注消费行为成为必要的选择。我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收入还将进一步提高。按照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前列水平。我国未来居民收入增长还将有较大空间,进一步扩大消费还有较多机会,需要我们积极施策来助推消费增长形成新的趋势。为此,要寻求积极有效地重塑人们消费行为的对策。
(一)重塑居民消费信心,引导理性消费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信心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基点。在我国经济恢复过程中,消费发挥了拉动恢复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消费信心不足的问题,制约了消费需求潜力的发挥。因此,恢复消费信心是激发居民消费行为、推动消费需求扩大的出发点和主要抓手。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首先,要解决居民愿消费、敢消费问题。2023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加6.8万亿元,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94.2万亿元的历史新高。居民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而不拿出来消费,明显是不愿消费和不敢消费,表现出消费信心的不足。要想恢复居民消费信心,就必须使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有良好的预期,这需要快速恢复经济,使人们对未来中国经济有更大期待。其次,要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人们不愿多消费而把钱存入银行,其背后也有不敢消费的原因,主要是对未来的生活压力缺乏解压的保障,为此,要逐步解决老百姓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压力,让他们可以放心地去消费[10]。最后,要为人们提供更多且可持续的就业机会,以为人们消费提供根本性保障。在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基础上,要引导好居民消费行为,树立理性消费的新理念。在对消费主义文化盛行背景下形成的非理性消费反思和转变的趋势下,进一步的消费空间拓展应该建立在理性消费的基础上。理性消费既是寻求高性价比的消费,也是提升消费品质的消费。在未来的消费需求拓展中,以理性消费引导消费需求拓展将成为主流,这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做工作。从供给方面看,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消费品和创造更好的消费场景;从需求方面看,要升级消费结构,以更高品质消费品来引导具有理性消费理念的消费者升级其消费结构。
(二)迎接居民消费行为转变,塑造更大消费空间
在理性消费塑造过程中,人们将逐步形成新的消费行为,并将拓展出新的消费空间。消费行为的阶段性特征表明:一个新的时代都将伴有新的消费行为,因为人们契合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方式便是通过消费行为来显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迎来经济发展的新前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新征程,人们自然也将以新的面貌融入这个时代。在此背景下,要尽快扭转目前消费行为的一些困境,使消费行为变得更加理性,进一步拓展出更大的消费空间。目前,我国正处在消费行为转型时期,一方面,人们开始厌倦了过去消费至上而通过减少消费来释放压力;另一方面,人们需要养成的理性消费尚没有明确的方向而处于探索期。消费行为转型不仅是改变消费满足递减的要求,也是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对新消费的需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形势下,一定会产生许多新消费品,激发出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的消费取向,也会创造出许多新的消费需求。其中包含的消费空间是无限的,迎接这种新消费潮流,一定会带来巨大消费空间。需要我们做的是:努力转变目前如反向消费这样的消费行为,培育出人们更加积极的消费行为,通过重塑消费环境,减轻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压力,从更长远的角度去培养人们的可持续的消费行为。未来消费与生产循环关系越来越重要,而维持这种关系的出路是形成一种可持续互动模式,以达到消费空间创新和消费可持续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三)加强消费政策引导,推进居民消费行为转型
人们的消费行为转变需要一定的外力推动,其中,具有突出作用的便是国家的消费政策。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家转变对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认识,出台倾向消费的政策。在过去的较长时间里,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的消费的边际贡献并不大。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下,需要突出消费这个重要基点。因此,制定倾向于消费的政策紧迫而必需。其次,要有解除消费后顾之忧的配套政策,最为关键的是完善社会保障的政策。我国虽已建立了普遍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保障的水平总体比较低,难以发挥社会保障解除人们消费后顾之忧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释放我国巨大消费潜力的重要基础。再次,要净化消费环境以使人们放心消费,出台净化消费环境的支持政策。打击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恶意引导消费者的广告,提升服务领域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构建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等等,以此营造一个可以放心消费的环境,促进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最后,要努力升级消费以创造更大消费空间,在促进绿色消费上制定支持政策[11]。随着经济的绿色转型,生产的绿色化势必伴生消费的绿色化,如此形成的互动,既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是新消费的未来走向。在实现消费绿色转型过程中,一定会受到一些滞后因素的影响,如绿色消费的成本和便利问题抑制了人们消费绿色化转型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国家出台支持绿色消费转型的政策,以培养人们的绿色消费行为。如果绿色消费最终成为人们的消费时尚,由此形成的消费空间巨大,对缓解甚至解决目前消费受阻问题将具有重要意义。
Reshaping Consumer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Build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QIAO Z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150080,China)
Abstract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must be based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especially consumption.How to expand consumption? This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challenge,but also a theoretical problem.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ption.Production is the basis of consumption,and distribution is the prerequisite.It is a basic way to expand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However,when there is surplu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people's savings are rapidly rising,we must consider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namely consumption behavior.How much and what people consume with a certain incom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onsumption behavior.Consumption behavior is a basic form of human behavior.It shows a regular evo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reflected in the unity of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group continuation of consumption,to the prominent individuality of consumption and the prevalence of consumerism culture,and then to the evolution of rational consumption tendency.In this process,consumption demand also changes,forming a special mechanism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affecting consumption demand.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is mechanism,find a new path to expand consumption and effective supporting consumption policies,so as to release consumption potential to a greater extent,expand consumption space,and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wordsNew development pattern,Consumption behavior,Remodeling,Consumption demand,Consumptio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