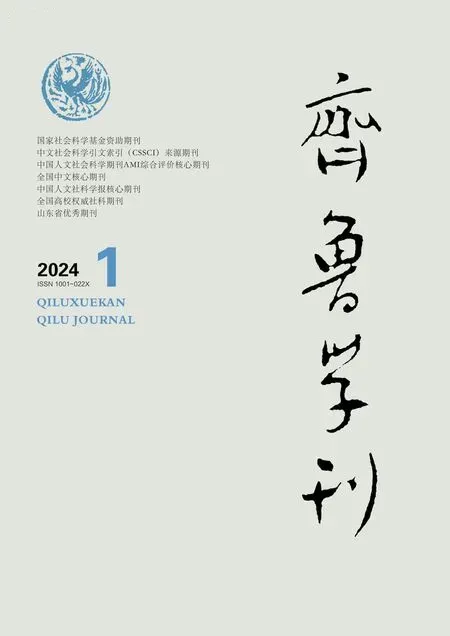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历史考证
宋剑华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丁玲在其一生中很少谈及《在医院中》这篇小说(她写于1942年的《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一文,是2007年才被发掘整理出来的),因此也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丁玲本人少谈《在医院中》情有可原,因为这篇小说的确曾使她在政治上吃尽了苦头,所以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能够理解。然而,人们为什么先是将其视为“大毒草”进行批判,现在却又反过来充分肯定它的艺术价值,难道仅仅是一个评价标准的变异问题吗?这一现象理应引起我们研究者的深刻反思。我个人认为,若要正确解答这一历史疑问,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历史原场,用客观事实而非主观情绪来说话。
小说《在医院中》究竟讲的是怎样一个故事?这是我们评价该作品的基本前提。丁玲本人曾在《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一文中概括道:“陆萍从一个无所谓的产科学生走到抗日的工作(在伤兵医院负务)又奔向延安,从抗大的生活追求马列主义(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到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需要,又重复回到最不愿意的接产生活(虽然带了很大的勉强和不彻底,却总算部分克服了自我意识),在‘不顺利’的环境里有矛盾,拿理智战胜了感情,努力坚持,结果接受了断足同志的解释,带着迎接春天的心情重上征途。”(1)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第105 -106页。果真如此的话,这部作品恐怕在历史上也不会存在争议,但“争议”却的的确确发生了。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根据我个人的阅读理解,小说《在医院中》的最大败笔,并非是一个表现手法成不成熟的技巧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去反映现实“环境”的态度问题。“虚构”是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创作规律。但“虚构”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即人物和故事情节可以去虚构,但是历史本身却绝不能任意虚构。尤其是那些表现平行历史的文学作品,每一个读者都是客观历史的见证人,如果作家随意地去改写客观历史,那么他(她)作品的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在医院中》究竟有没有违背这一评价标准呢?我想还是历史本身更能说明问题。
一、《在医院中》的“XX医院”考
小说《在医院中》描写的是发生在延安一所医院里的故事,故我们首先有必要去搞清楚那所“医院”究竟是指延安地区的哪所医院。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小说只是描写了一所医院而已,即使考证出来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认为这样做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还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部作品会惹上“麻烦”。丁玲在作品中交代说,主人公陆萍“在抗大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2)丁玲:《在医院中》,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由于丁玲只给了一个空间“距离”,既没有具体地址,也没有具体名称,所以读者很难去判断是延安的哪所医院。因为当时延安共有医院和卫生所十多个,医疗条件也千差万别不尽相同。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却令我感到诧异。
据房成祥、黄兆安在《陕甘宁边区革命史》一书中提供的统计数据:1940年的陕甘宁边区,全区总共有中医千余人,兽医50余人,工作在部队、机关的西医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而巫神则多达2029个(3)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仅从这一数字来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医疗情况确实非常落后。需要指出的是,这200余名西医主要集中在延安的几所大医院里。那么大医院的情况到底又是如何呢?延安地区最早建立的医院,是陕甘宁边区的边区医院,位于延安市安塞县真武洞镇黄瓜塌村。该院成立于1937年9月,由傅连暲为院长,距离延安城30公里。《新中华报》曾报道说:到1939年“该院规模已较前扩充,全院工作人员百人以上,将收病人百余名。该院治疗共分内、外、产妇和小儿等四科,并设有化验室,除原有X光线外,更添置显微镜及其它化验仪器多种”(4)江平:《病人的福音,边院的扩大》,《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第2版。。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第35医疗队有十几名医护人员,也在此工作到了1939年底。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医院1939年门诊1738人次,住院687人次;1940年门诊1040人次,住院568人次(5)陕西省卫生志编撰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页。。由于它离延安城有30公里的距离,肯定不是丁玲笔下的那所医院,故我们可以将其排除掉。延安第二兵站医院1937年底在延安甘谷驿镇正式成立,距离延安城有40公里。这所医院除了有自己的医护人员外,从1938年1月到1940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其中有白求恩)就在第二兵站医院工作,他们带来许多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以及专业医务人员,救治了大量的伤病员。比如,1940年4月26日《新中华报》的《边区新闻》中就曾报道说:第23医疗队“医术优良,设备齐全”,“他们在甘谷驿教堂建立了手术室和重症病房,医治病人40295人,检查1590人,实施手术635人,救治了不少伤病员,博得信誉和荣耀”(6)转引自金星:《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由于它距离延安城40公里,故我们也可以将其排除掉。延安中央医院筹建于1939年初,位于延安西北方向约5公里的李家坬村,由毛泽东亲笔题词“中央医院”四个大字,当时共设有内科、外科和妇产科三个科室。创院两周年时,该医院共治愈病人1934人,做手术600余次,病死率仅2%;1940年至1941年间,共收治孕妇565人,死亡仅2人,死亡率仅0.36%,而当时中国产妇的死亡率高达15‰(7)陕西省卫生志编撰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32 -36页。。由于该医院距离延安城太近,我们仍然将其排除掉。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了一个八路军军医院了。八路军军医院(1939年12月改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前身是军委直属疗养所,1938年11月在延安延川镇拐峁村筹办,1939年5月正式成立,离延安城恰好是40里路。当时“分内、外、产妇三科,并设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等。印度医疗队担任外科工作,全院可收容病人120余名,工作人员112名,医生9名,护士长1名,护士45名,其余为行政事务人员”(8)陕西省卫生志编撰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41页。。八路军军医院不仅平时要为部队和地方提供医疗服务,同时还承担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的体检工作,像刘伯承、张鼎丞、徐向前、王稼祥、陈毅、贺龙、陈赓、傅钟等都在此做过体检。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断了胳膊,也是在八路军军医院拍的X光片,并经专家会诊后提出治疗意见(9)参见边齐:《忆延安八路军军医院成长历程》,《中国医院》2003年第4期,第68页。。丁玲自己说:“一九三九年一月的时候天气很冷,我因为一点外科的割治曾住在离延安四十里路的××医院。这个医院是在1938年十一月延安城轰炸后才开办的,设备很不好,工作人员少,行政上医疗上的负责人都感到颇为棘手。我住了一个多月,同他们生活得颇为融洽,并且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神经质的产科助手。”(10)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98页。虽然丁玲本人并没有明确地说是八路军军医院,可是《丁玲年谱长编》却对此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说明:1939年1月,丁玲“住拐峁医院做痔疮手术。住院约2个月”,“根据上年初在拐茆医院住院的一段生活素材,以该院助产士余武一为原型,作小说《在医院中时》,初刊1941年11月15日《谷雨》创刊号”(11)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 -158页。。由此可见,“四十里路”和“拐峁”地名,再加上小说告诉读者,“XX医院”有“五间产科病室”,都把目标指向了八路军军医院。
八路军军医院刚刚成立之初,条件的确比较简陋,医院建在黄土高坡上,病房和手术室全都在窑洞里,无论医疗器械还是药品都严重缺乏。但在国内和国际友人的大力援助下,延安的医疗保障系统发展得非常快,医院的软硬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然而,小说《在医院中》却告诉读者,延安八路军军医院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医院外边“冰冻了的牛马粪堆上,蒸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病房里面“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到处都是“看得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12)丁玲:《在医院中》,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34、242页。。当时就曾有人批评丁玲把八路军军医院描写得不堪入目,“肮脏、无秩序、设备不完善,病人营养差,用具破了无人管理,病房不温暖,大家忙而又闲,流言纷起”,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13)燎荧:《“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5 -281页。。特别是全院只有一支“注射针已经弯了”,但“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真不知道丁玲本人在做手术时,是否也是用这支已经弯了的“注射器”打的麻药。其实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红十字会从1938年1月到1940年4月,总共派遣了第7、23、25、29、33、35医疗队到达延安,带来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而且印度医疗队也在八路军军医院,故偌大个医院绝不会连个“注射器”都没有,否则又怎能去给伤病员和中央领导治病呢?举一个例子:1938年何穆博士到延安,不仅带来了设备齐全的手术器械,而且还带来“一架手提X光机和治疗肺结核的气胸空气压缩机”,这些复杂的医疗器械大医院里都有,难道还会缺少一支小小的“注射器”吗?特别是一些外国记者在参观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中央医院以后,他们竟十分惊讶地发现“就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也没有像这样的医院”(14)转引自金星:《亲历延安的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第62页。。所以,《在医院中》对于八路军军医院描述的失真性,无论有意或无意都违背了历史事实。
二、《在医院中》的“人物事件”考
《在医院中》对八路军军医院描写的失真性,又引起了我对故事叙事中“人物事件”是非“真实”的强烈质疑。丁玲在作品中写道:“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15)丁玲:《在医院中》,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40页。,“她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16)丁玲:《在医院中》,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41页。。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不是“张医生的老婆”,便是“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17)丁玲:《在医院中》,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42 -243页。,无非就是靠裙带关系在医院里混饭吃。问题是,就这样一些“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的护理人员,究竟是如何做到了使产妇的死亡率仅为0.36%,接生婴儿3843个成活率达95%以上的成绩呢?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我只能去对此做一次求证。
我们先来看看丁玲住院期间八路军军医院的院长和指导员。院长靳来川是河南人,开国少将,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从红军时期开始,历任红5军团15军卫生部司药长、红3军兵站医院司药主任,以及红军卫生队队长、红军第3后方医院院长,1938年11月接任八路军军医院院长,时年27岁。指导员白崇友是四川人(丁玲明显把院长和指导员的籍贯搞颠倒了),开国少将,1933年参加红军,也参加过长征,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四后方医院党支部书记,八路军第一后方医院一所副指导员、第一兵站医院指导员,1938年11月任八路军军医院指导员,时年24岁。从这份简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二人都曾做过医院的医务或管理工作,对医务工作绝不会一无所知。而《在医院中》还告诉读者说,八路军军医院的外科只有两个人,一位叫郑鹏的医生主刀,一位叫黎涯的护士配合,这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因为当时八路军军医院外科有主任1人,医生2人,护士长1人,护士10余人,再加上印度援华医疗队,其建设目标被定位要“成为八路军的模范医院”(18)见《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八路军军医院成立”报道。。如果就这么两个人在那里撑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妇产科主任魏一斋是一位医学博士,他抛弃了北平协和医院的舒适环境,跋山涉水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1938年9月专门接见了他,并诙谐地说“魏大夫,人家是逼上梁山,你却是自投梁山,我们这里正缺一个安道全,欢迎,欢迎”(19)转引自曧之编著:《协和医脉:1861—1951》,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8页。,并为他亲笔题词“为革命服务”以示勉励(20)金星:《亲历延安的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第78页。。而魏一斋也不负众望,积极利用齐鲁大学校友的关系,从中国红十字会那里争取到了许多医学人才和医药器械,为八路军军医院妇产科的正规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可丁玲却把他描写成一副资产阶级的虚伪嘴脸,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诧异。此外,丁玲还说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又懒又脏”,“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21)丁玲:《在医院中》,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42页。,且产房里没有取暖,不利于产妇和婴儿。这也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由于当时医院里的物资十分紧张,故“使用的注射器都是玻璃制品,护士们小心翼翼洗涤干净,用蒸馏水冲洗后煮沸消毒,反复使用,直到漏气、漏液、磨损到不能再用为止”,“几乎所有外科的绷带、纱布,婴儿换下来的脐带布、尿布都要清洗、消毒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22)金星:《亲历延安的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第265 -266页。。而妇产科的护士不仅要负责接生,而且还要负责母婴的日常生活起居,“冬天还要给病房窑洞里的火盆生火,把婴儿室、产房的地炕烧好”(23)金星:《亲历延安的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第267页。。这些真实的历史记载,足以颠覆丁玲《在医院中》的失真性描写了。
现在我再来谈谈女主人公陆萍。丁玲反复强调说:“这个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却把她作为一个理想的人物给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这样做了,却又不愿意。”(24)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99页。这段话很是耐人寻味,既然“熟悉”和“同情”,为什么“却又不愿意”了呢?读罢《在医院中》我发现,丁玲其实并不了解“医生”陆萍,她所理解的是知识女性陆萍,我说这话自然是有事实依据的。比如,丁玲是这样描写陆萍被派去当产科医生时的沮丧心情的:
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钉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助产婆,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25)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第239 -240页。
丁玲告诉读者,陆萍虽然学了四年妇科,但她骨子里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普通的助产婆”;到延安“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26)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第239页。。说实话,研究者几乎都被丁玲这番交代给蒙骗了,以致有的学者说:“起初陆萍试图以各种理由拒绝医务工作,终告无效,于是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27)李晨:《〈在医院中〉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第99页。其实丁玲心里比我们都清楚,“陆萍是从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变来”的,但她又绝不是“那个真的产科助手”,“我是把两个欲念纠缠在一起,而随便使用了那个产科助手”,“然后加上许多东西”组合而成的一个人物(28)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102页。。我所关注的问题所在,恰恰是丁玲究竟在陆萍身上“加上”了些什么样的“东西”。从《在医院中》的故事叙事来看,人在延安的丁玲,当然知道在延安的医院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两件事情。
一件是中组部在“抗大”中发掘医护人员。“七七事变”以后,“一批一批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中有学过医务的同志,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大部分人还背着行李,步行千里来到延安,是为了学习抗日救国的真理,参加革命,和过去的‘自我’决裂”(29)金星:《亲历延安的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第9页。。当时延安急缺医护工作者,各大医院都向中组部申请,希望能够从“抗大”中发掘一批专业人才。像郁彬、黎平、龙静先、王广胜、邓良渭、马忠明等人,都是被中组部从“抗大”中发掘出来送到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尤其是郁彬和黎平二人,她们都是从上海来的“助产士”,而年龄也刚好同陆萍一样是20岁,这足以使人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了。值得注意的是,郁彬与黎平隐瞒自己的学医经历,并非是主观上厌恶从医,而是希望改变身份弃医从军,立志要上前线去杀敌报国。只不过由于她们两人身上都带有体温计,经常为学员们测量体温,故被组织上发现,调往中央医院去工作的,带着体温计说明她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医学特长。1938年底,中组部在“抗大”中发掘了大量的医护人员,仅女护士、助产士就20多人。这些人通过党组织的思想教育,深知延安各医院的艰难处境,不但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工作安排,而且还成为了中央医院、八路军军医院、边区医院、二兵站医院的骨干力量。据护士长郁彬回忆,当时延安医院的条件很差,吃饭用土陶粗碗,没有桌子就蹲在地上,用水要从山下挑,医疗设施也不完备,窑洞外有野狼内有老鼠,甚至于一两年的时间“都没有洗过澡,好的时候打盆水到洗澡房擦一擦”。可她们这些大上海来的医护人员,却都毫无怨言地说“当时苦是苦了一些,可是,我们年轻啊,每天都乐呵呵的,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过来了”(30)金星:《亲历延安的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第14页。。从这些青年医护人员的身上,我们看不到陆萍那种思想消沉情绪,因为她们都有着崇高的革命信念,所以并没有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到。从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丁玲在陆萍身上“加上”去的“东西”,无疑就是中组部在“抗大”发掘人才的这段经历,但是丁玲本人却没有对其进行如实的描写。
另一件是何穆博士的负气出走。何穆是上海金山人,1935年毕业于法国都鲁士医学院,学的是心肺专业,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医学博士。全民抗战爆发以后,1938年8月他与夫人陈学昭一道来到延安,在肺病治疗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一年以后,由于他还难以适应延安艰苦的生活条件,再加上他与医院管理干部在工作上产生了一些矛盾,于是他决定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办私人诊所。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专门叮嘱他如果有困难可以去找八路军办事处。何穆回到重庆以后诸事不顺:困难重重、物价飞涨、日机轰炸、特务盯梢、地痞捣乱、儿子夭折、经济拮据等等,使他几乎难以生存下去。关键时刻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等人及时地向他伸出了援手,使何穆感动之余终于意识到只有共产党人才是他的真正朋友。故1940年11月,他又带着一批医护人员和医药器械返回延安,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何穆曾深情地回忆说:
第二天,陈云、王首道二位领导人来看望我,说傅连璋同志年高、体弱、事多,中央决定委任我为中央医院院长……次日一早,我和其他六位同行者一起搬进了中央医院,石昌杰等同志在大门口等待欢迎我们,下午又参观了医院的各个科室和部门。在这一年里,中央医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已经步入正轨,我的心情十分激动。(31)转引自金星:《亲历延安的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第73页。
毛泽东也抽空接见了何穆,说:“延安需要你!欢迎你回来工作,把中央医院办好。”(32)转引自金星:《亲历延安的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第73页。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充分体现了延安的共产党人,对于知识分子的宽容政策,其政治意义影响极为深远。毛泽东一句“延安需要你”,道出了延安求贤若渴的真实心态。何穆事件当时在延安众人皆知,丁玲本人当然也不会例外,因为她曾与何穆的夫人陈学昭,于1940年同在文抗延安分会工作。如果说陆萍事件与何穆事件之间有何关联性的话,应是她把知识分子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意识,巧妙地转化成了陆萍与院方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构成了小说《在医院中》的故事情节。
现在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小说《在医院中》中的“医院”,只是一种作者对于延安政治生态“环境”的象征隐喻;陆萍也不是以那个“助产士余武一为原型”(这一历史人物究竟存不存在我们已经无法去考证了),而是“随便使用了那个产科助手……然后加上许多东西”的综合性产物——如果说郁彬和黎平赋予了“陆萍”以医务工作者的具体身份,那么何穆事件则赋予了“陆萍”与“院方”发生冲突的一个理由;作者经过“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33)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104页。的艺术构思,最后才合成了她所希望看到的“客观”的东西——延安地区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三、《在医院中》的“创作动因”考
《在医院中》创作于1940年,小说尾部就是这样注明的;但丁玲却又说她已经记不起具体的创作时间了,对此我个人感到非常纳闷,究竟是她真的“记不起”还是她本人根本就“不想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丁玲的思想和创作非常重要。1942年下半年,丁玲曾在《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一文(实际上是一份检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住院期间所认识的那位“神经质的产科助手”,“她的身体和心情的健康,常常萦绕在我的怀念中,久了之后不觉得这人物便更被夸大和凝固起来,偶然便有了把她放进我的小说的冲动。可是这人物并未成熟,我也没有热情的给她以生命,像一个剪影或一尊塑像似的,她在我脑子中生活了两年”(34)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98 -99页。。这段叙述显然不准确,因为她是在柳枝正在“抽芽”之际动笔的,只不过“小说写了一半,我停止了”,证明时间只有一年而不是两年。至于为什么要“停止了”,她说得也十分含糊,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仅用“我要修改这小说”(35)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99页。便一笔带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丁玲感到如此纠结,竟迟迟不能完成这篇作品的最终修改呢?我个人认为,1940年丁玲本人的艰难处境,是我们考证《在医院中》创作时间的最好参照。
1940年是丁玲情绪最为低沉的一年。她回忆道:“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一九三八年说的,我一九四O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36)丁玲:《忆弼时同志》,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6卷,第329页。丁玲所提到的“历史问题”,直接关系到她在延安的政治生涯。因为丁玲到了延安以后,她一直都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活跃在延安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如果失去了这一政治身份,不仅是对她革命信仰的一种否定,还会使她失去在延安的“大好前程”。但“历史问题”的甄别,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一年时间里,丁玲寝食难安、如坐针毡。据《萧军日记》中记载:当时丁玲“很痛苦,为了她党籍的问题,组织部又来麻烦她。她感情很冲动,要脱离组织关系”(37)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17 -318页。由于迟迟得不到中组部的审查结论,到了1940年9月,丁玲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比如,她曾多次对萧军哭诉说:“是啊!恋爱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也就算了。这个东西(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老实讲我算要吃不消了……虽然我应该忍受,但是我不能忍受了啊!……我明知就是脱离了……苦痛并不是说就完了……我离开延安……回家去……现在自己的人们却这样磨难我……要证人也没有;要证据也没有……就这样磨难我”,“我……共产党已经不信任我了!……我不做党的工作了。国民党就不会捉了我去,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了”,“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到冰窟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慢慢自己也就变得冷酷了!”(38)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第318 -325页。由于1940年丁玲与萧军的关系非同一般,故《萧军日记》里的这些文字记载史料价值很高,那段时间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不仅同病相怜而且还暗生情愫。比如,萧军同丁玲接触的时间多了,便对妻子王德芬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绪,尤其是当他发现王德芬偷看自己的日记时,更是内心不满地发泄道:“芬是只适于嫁一个年轻相等的世俗的青年已经够了,她不必非嫁我,我们底结合完全是偶然的,环境的力占多数”(39)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第312页。,他曾与丁玲约定三年之后一同去欧洲旅行。不过,萧军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丁玲和他绝不是一路人,眼下那种看似小鸟依人的形影相随,无非是一种逃避内心孤独的无奈之举。但无论怎样,在那段时间里萧军和丁玲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他们一方面联手去同“鲁艺”抗衡,另一方面又相互倾述对于延安的种种不满,甚至还准备共同写信给毛泽东去告状,等等。然而,当1940年10月4日中组部对于丁玲的历史问题审查完毕,正式结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40)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上卷),第156页。时,丁玲和萧军之间的暂时结盟便立刻土崩瓦解了。萧军发现他和丁玲之间的关系“已经一天一天恶化起来,她大概现在不需要我们了,他们党内要自己团结了”(41)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第358页。。所以,从1941年3月开始,丁玲这个名字已经逐渐淡出了《萧军日记》。
我在这里例举丁玲与萧军之间的关系,并非有意去闲扯什么文坛八卦,而是想透过丁玲这一时段的思想状态,去探索《在医院中》的创作动因和成文时间。现在我们大致可以断定,1940年春丁玲已经写了一个初稿,而且她为初稿确立的创作宗旨,也是借题发挥去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情绪。若要使这一结论能够令人信服,我们应该先去厘清丁玲与陆萍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丁玲说:“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她还残留着我的初期小说里女主人公的纤细而热烈的感情,对生活的憧憬与执着……陆萍与我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给她以生命。”(42)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104 -105页。这段说明至关重要,因为它明确地告诉我们,陆萍就是丁玲思想的代言人,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首先,无论“莎菲”还是“陆萍”的张扬个性,其实就是丁玲那种张扬个性的艺术呈现。比如,“莎菲”一个人跑到北平去自我放纵、率性而为,在“陆萍”身上也得以重现:表面观之,陆萍“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43)丁玲:《在医院中》,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43页。。但实际上,陆萍根本不顾延安地区的客观条件,一味地想按自己的意图去改变医院的落后现状,没有人会怀疑她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这种夸夸其谈恰恰又暴露出了她的个性意识。陆萍在医院里到处颐指气使地发表意见,“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44)丁玲:《在医院中》,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43页。。萧军对此感受颇深,他说丁玲的性格泼辣、容易冲动,故使她在延安树敌甚多。仅就这一点而言,陆萍与丁玲的确是“分不开的”。其次,陆萍的“消沉”与“救赎”,就是丁玲的“消沉”与“救赎”。阅读小说《在医院中》,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还不是陆萍与丁玲对于她们所处环境的攻击和否定,而是丁玲如何借助陆萍这一艺术形象去实现自我救赎。从小说的艺术结构来看,《在医院中》用了大半部篇幅,去描写陆萍同“医院”之间的矛盾冲突,故事情节通顺流畅大有一气呵成之势;可为什么到了作品的结尾部分,她却非要突兀地加进去一个“没有双脚”的“怪人”,让他用革命的道理去促使陆萍发生思想转变,并且愉快地去迎接未来的“新生活”呢?显然前面那大半部分情节是丁玲在1940年春天就已经写好了的,当时她正极度苦闷并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收尾。如果将陆萍写成负气出走(像何穆博士一样),虽然能真实地反映出她的真实心态,却又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如果给予她一个光明的结局,却又并非丁玲本人所愿且无从下笔,故只能将“那些原稿纸都请到我的箱子里睡觉”(45)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100页。。丁玲说这是一种“沉重和负咎”,因此小说《在医院中》,一直拖到了1941年10月《谷雨》约稿时,她经过内心世界的痛苦挣扎还是选择了后者——“于是在一个下午便努力继续下去,而把我怀念的梦秋同志(失去双脚的人)塞上去,做为了小说的结尾”,至于她在精神上的“沉重和负咎”与无法“自圆其说”,也只能“秘密着希望在下一次的创作中而得到解脱”(46)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100页。。有学者曾这样指出:那位“怪人”与陆萍之间的灵魂谈话,是一种政治上的“驱邪”仪式,它表明“小说没写医院有什么变化和改进,而陆萍是‘成长’了,或者说‘治愈’了”(47)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这种说法还是没有真正读懂丁玲本人的收尾意图。倘若一番政治说教立刻便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岂不是把思想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吗?丁玲安插那位“怪人”进入故事,虽然使整个情节呈现出一种断裂感,但是“怪人”对于陆萍的耐心开导与灵魂“救赎”,则象征着丁玲在感恩党组织对她的政治“救赎”(结束审查)。
那么,丁玲为什么不能“自圆其说”?又为什么内心感到“沉重和负咎”?实际上,这篇作品就是丁玲在借陆萍的所谓“遭遇”,来言说自己在政治上被误解的强烈不满。丁玲一生中之所以不谈(除了做检讨时)《在医院中》,原因就在于“为了要突出这人物,我不惜歪曲一些现实,在当时我曾感觉得有些地方写过了火,有些抱歉的感觉”,“我曾抱歉过的,我觉得对老干部有些冤,我是较偏于知识份子了,但我却给我自己解释,写小说不是写论文,不必一定要来一套八股,说他们是有功的,但也有缺点”(48)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108、112页。。丁玲的这份检讨貌似很深刻,但我还是有两个问题没有搞明白:第一,如果作品真是按照她本人所辩解的那样,意在描写陆萍思想的“成长”过程,那么1940年以后的延安医疗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她为什么不去同步描写延安医院的“成长”过程呢?第二,1940年底丁玲就已经写完了《在医院中》,1941年4月她又主编了《解放日报》的文艺栏,可为什么不把这篇作品发表在影响最大的《解放日报》上 ,却偏偏要发表在出了几期便停刊了的《谷雨》杂志上呢?答案或许并不那么复杂,丁玲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去发表这篇作品,后来由于《谷雨》杂志的不停约稿,丁玲认为这个刊物刚刚创刊且影响不大,所以才会毫无顾忌地把小说交给了他们。无论现在的研究者如何去提升这篇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但它对历史的“虚构”和“失真”一直都是悬在丁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四、“文艺整风”与丁玲有何关联性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最早是以“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目标,统一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集中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49)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 -15页。。毛泽东之所以要把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定位为党内的高级干部,因为在他看来“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才是下级干部”(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3页。。所以,他强调必须在党内高层彻底“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51)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换句话说,“整风”一开始与文艺界无关。然而在这期间,延安地区的一些知识分子文化人,却突然“出来刮了一阵子小资产阶级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纳入正路”(5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78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通过分析和研判,意识到王明的路线错误与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歪风”,其思想根源都是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去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故对高级干部进行路线教育以及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便合二而一成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宗旨。
“延安文艺座谈会”无疑是文艺界的“整风”开始。胡乔木曾指出:文艺界内部的“整风”运动,“不能拿王实味作文艺界的代表……当时,主要是围绕着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其他一些人多少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53)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55页。。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这番话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王实味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丁玲(包括萧军)的问题则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两者应该严格区分对待。那么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为什么要拿萧军和丁玲来开刀呢?因为他们二人分别代表着党内外的自由主义思想。萧军作为党外人士,他虽然佩服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却心高气傲从骨子里对共产党人颇有微词,并极力辩解文艺与政治的平行关系。萧军解释他到延安的目的很明确:“我知道我的任务,应该用文艺的力量影响和教育这些高级负政治责任的人。”(54)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第508页。毛泽东后来在《讲话》中曾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绝不能“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5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卷六,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第993页。,此言明显是针对萧军等人的错误观念有备而发的。而丁玲的错误就在于,1940年10月组织上解除了对她的政治审查,她也同萧军断绝了一切来往,但灵魂深处仍保留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比如,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上把党的宣传工具交由她去负责,可她却充分利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这一平台,去大肆宣扬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比如,她不仅发表了严文井等人与延安政治相背离的文学作品,为此博古还专门提醒她注意,她本人却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屑一顾(56)丁玲:《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经历》,张军锋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下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37 -38页。;而她自己也公开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强调:“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57)丁玲:《我们需要杂文》,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第59页。尤其是1942年春,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一批青年,在“矢与的”墙报上发难,丁玲作为《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负责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对这股“歪风”给予了积极配合,并连续发表了《野百合花》(王实味)《“三八节”有感》(丁玲)《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艾青)《还是杂文时代》(罗烽)等文章,进而导致了“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58)《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的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转引自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文献卷》(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49 -450页。。毛泽东对于这种现象非常愤慨,他在和艾青谈话时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59)转引自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实——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3期,第205页。毛泽东的愤慨是有道理的,他深知文化人的一支笔,抵得上3000支毛瑟枪,如果这股“歪风”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会对延安的政治文化生态造成非常恶劣的负面影响。因此,他决定亲自去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关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胡乔木一再提醒我们注意:“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之间的关系要弄清楚,究竟是会前文艺界已经在整风,还是在会后才开始整风?”(6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56页。一定要厘清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他是在告诉我们文艺界的“整风”与党内的“整风”还是有区别的,文艺界“整风”主要是一场针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毛泽东在《讲话》开篇便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一是“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共产党员还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是否还有认识得不正确或者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是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立场。”(6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70页。“立场问题”旨在提醒知识分子文化人,投奔“革命”不仅要认同“革命”,而且还要无条件地去服从“革命”。朱德说得更为直白,“投奔”就是“投降”(62)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张军锋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下册),第61页。。丁玲通过学习《讲话》也认识到,革命文艺工作者“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63)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第69页。,就必须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真正站在工农兵大众的立场上去说话。二是“态度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6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85页。所以无论文艺工作者怎样标榜自己,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故“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6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91页。。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延安共产党人所持的消极态度,说穿了就是他们对于工农兵大众的拒斥态度,证明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三是“对象问题”。“对象问题”是对“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的深度阐释,毛泽东指出工农兵大众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理应是工农兵大众,以及作为他们的当然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故“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划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决定渺小……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6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91页。这不是一个艺术标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丁玲心里明白,《讲话》是针对她和萧军等人的,所以她在大会小会上,做过无数次的自我检讨。然而,她是否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文艺座谈会以后,丁玲检讨的主要问题,是《“三八节”有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对《在医院中》这篇作品,她不但内心十分纠结,而且还一直在为其进行辩护。她说《在医院中》绝不是一篇“党八股”似的文学作品,至少她把女主人公陆萍塑造成了一个“有血肉,有感情,能被读者了解,与读者相亲切,气息相通”(67)丁玲著,王增如整理:《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第101页。的艺术形象。但延安的读者却并不买账,他们批评说:“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他是在描写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人为地把这所革命医院描写成了“一个比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与此同时,作者也忘记了“她是在写一群互称为‘同志’的人群,忘记了她是在写革命政党的党员”(68)燎荧:《“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77、278页。。恐怕这种“忘记”,正是丁玲对小说《在医院中》讳莫如深的原因所在。